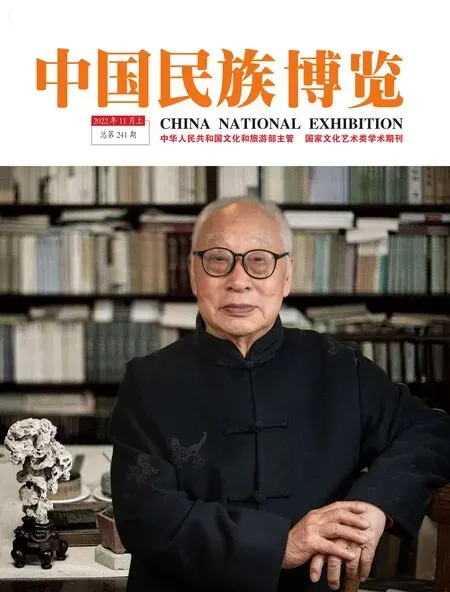墻頭馬上,知君斷腸
——淺析元代愛情喜劇《墻頭馬上》
周藝霖
(武漢大學藝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000)
一、人物表意敘事
結構主義分析的要點在于,在劇中那些看似是“主體”自身的主動行為,但內里往往是人物關系的內在結構和個體身處其中而不自覺產生的行動欲望決定了其相應的主體位置。即故事的主體是組成故事內在框架的一個個位置,而不是劇中的具體人物。而人物在劇中做出的一系列動作也是因為故事深層的結構在對他進行召喚,每一個人物都可以被與之類似的人物替換掉。因此本文試通過探究人物性格特點,從而深入研究其內在沖突。
(一)通過探究人物形象及人物關系探尋劇作發展動力
在《墻頭馬上》中,角色本身即具有符號意義。每個角色都有自己鮮明的行為特征,共同構成了劇本的敘事結構。下面將通過對主要人物的形象進行具體分析,對其矛盾沖突加以客觀透視,便可以把握敘事文本的深層結構,進而發現《墻頭馬上》文本的深層意義。
在戲曲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李千金代表的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反抗與裴行儉代表的封建權威壓迫之間的對立沖突,是推動故事發展的主要對立項。隨著裴父在花園中發現李千金和兩個孩子,故事逐漸進入高潮。李千金一出場便立住了她“敢愛敢恨、渴望自由自主”的人物形象,她聲稱:“我若還招得個風流女婿,怎肯教費工夫學畫遠山眉。寧可教銀缸高照,錦帳低垂。菡萏花深鴛并突,梧桐枝隱鳳雙棲。”[1]在她身上,看不出絲毫大家閨秀的羞怯之感,在她遇到裴少俊并對他一見傾心之后,她大膽且主動地與裴少俊在后花園中私定終身。即使后面被嬤嬤撞破也沒有絲毫的畏懼,不僅又是下跪求情又是撒潑打鬧地爭取自己的愛情主動權,更是甘愿為愛私奔、放棄自己錦衣玉食的生活。當裴行儉撞破這一對小夫妻之事時,李千金絲毫不加遮掩,大膽直接地坦白了她與裴少俊的夫妻關系。面對裴行儉震怒后的侮辱時,她仍堅持強調婚姻自由和愛情至上。同時,李千金面對一段需要質疑的愛情時,她的拒絕是果斷干脆的,沒有絲毫的留戀。當曾經放棄她的裴少俊帶著父親重新上門求和時,她沒有絲毫對舊日情分的纏綿不舍,而是果斷的拒絕了自己鐘情的少年郎。在愛情和人格尊嚴之間,她清醒且迅速地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她并非是已經不再愛裴少俊,而是在她心中,沒有什么比自己的人格尊嚴更加重要,哪怕是愛情也不能夠。李千金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物,她身上閃耀著婦女勇敢追逐自己的人生、把握自己的命運的光輝,與封建傳統禮教作徹底的反抗與斗爭,捍衛自己人格的尊嚴。
裴行儉和很多話本中嚴父的形象一樣,是封建傳統禮教的權威象征者。他對兒子裴少俊的仕途十分上心,在發現李千金后斷定她不像大戶人家的女兒,定是個會毀了兒子的大好前程的狐貍精,“你無顏敗壞風俗,做的是男游九郡,女嫁三夫。可不道“女慕貞潔,男效才良”;“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你還不歸家去。”[2]執意拆散這一對苦命鴛鴦。裴行儉象征的封建禮法是來約束李千金所象征的新生解放的思想,這兩種大相徑庭的思想碰撞在一起,激發矛盾產生戲劇沖突,表現封建制度對人以及人性的壓制。更諷刺的是,在裴少俊考中狀元,裴行儉得知李千金的真實身份后,原本高傲的裴尚書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去求兒媳婦回裴府,就算被兒媳婦回懟回去也只能是忍氣吞聲。這里也暗含著作者的美好愿望:新舊思想的交鋒下,隨著時代的發展,舊思想必定會為新思想讓步。
裴少俊和奶母則是在封建權威下的擁護者和屈服者。裴少俊是翩翩貴族公子,也正是這樣的身份讓他畏懼自己家中一言九鼎的父親。也正是如此,面對父親的高壓,他第近乎習慣性地選擇了服從。“卻少俊是卿相之子,怎好為一婦人,受官司凌辱?情愿寫與休書便了,告父親寬恕。”[3]在面對李千金對他拋妻棄子的無情嘲諷時,他也是無力地將一切責任推到了別人身上。“這是我父親之命,不干我事。”[3]一個裴少俊身后,是千千萬萬那個時代唯父母之命是從的官宦子弟的縮影。他的確愛李千金,在寫休書時他也怨過父親:“父親,你好下的也。一時間將俺夫妻子父分離,怎生是好?”又瞞著父親將李千金送回洛陽,但這些蒼白的舉動無法遮蔽他在面對父權壓迫時的怯懦。墻頭馬上的愛是真的,拋棄妻兒的懦弱也是真的。他或許曾想要突破反抗,但最終仍是無力地接受自己被枷鎖禁錮的人生。而嬤嬤則是封建傳統禮教的衛道士,她作為李千金成長路上的導師,自然希望李千金成為那個時代下標準的“大家閨秀”。在撞破兩人的私情后,她代表的是封建大家長的角色,要仔細盤問清楚,甚至要送到官府。可李千金絲毫不懼恐嚇,面對嬤嬤的咄咄逼人慷慨陳詞,甚至以死相逼。白樸在兩人私奔前設置嬤嬤撞破兩人并斥責問責這一情節,更加凸顯了李千金面對封建勢力的壓迫毫不懼怕,并誓要沖破封建傳統的束縛、勇敢追逐自己所愛、捍衛自己人格獨立的權利的可貴品質。
張千和梅香是裴李二人的小廝和丫鬟,在劇中起到推動故事發展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盡管他們沒有接受過什么教育,但兩人在劇中幫李千金和裴少俊通風報信、出謀劃策、積極鼓勵兩人追求自己的愛情。因此,《墻頭馬上》作為一出愛情喜劇,白樸很巧妙地處理了各方人物關系,使他們完整地構成了格雷馬斯矩陣。可以說,墻頭馬上的愛情是當時無數才子佳人幻想的“私奔”“大團圓”的圓滿愛情的縮影。而主要的六個人物則是當時四種群體的符號,其本質還是處于封建傳統倫理道德之下官宦家庭中彼此對立且矛盾關系。
(二)戲曲文本敘事結構對李千金人物形象的塑造
同時,作為一出愛情喜劇,在短小的篇章中白樸依舊利用矩陣關系創造出雙重戲劇沖突,讓劇情波瀾起伏。第一次是裴行儉撞破花園中的李千金和兩個孩子,發現裴少俊私定姻緣后的雷霆震怒,用銀瓶和玉簪刁難李千金,逼她驗證她所認定的“天賜姻緣”都是假的。這顯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隨著銀瓶沉底、玉簪折斷,兩人之間的幸福生活也戛然而止,李千金被賜一紙休書與孩子丈夫天涯相隔——在此處情節中,李千金處于孤軍奮戰的一方,面對不通情理的裴相公、恐嚇威脅的嬤嬤、軟弱無能的丈夫,李千金雖據理力爭但奈何勢單力薄,在當時的環境下她想要的獨立與愛情是不可能獲得的,這更加深了讀者對追求愛情與人格尊嚴的李千金的認同感和同情感。而第二個高潮則是在裴少俊功成名就考取狀元后,裴行儉得知李千金原是名門望族之后,遠非他所認為的風塵女子,父子倆一同來求李千金回家。李千金與其他戲本中的千金小姐形象大相徑庭,她沒有哭哭啼啼與丈夫互訴離別之情。此時李千金心中的計劃只有她一人知曉——讀者也被蒙在鼓里,而李千金后來對父子倆譏諷冷漠的反應更是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因為在那個時代甚至在現在,都鮮有女子可以做到這般地決絕與清醒,從而戲劇進入第二個高潮。李千金并不對自己因裴家父子而遭受的不公的待遇自怨自艾,對丈夫重修舊好的請求一口答應,而是對兩人進行了極致的挖苦諷刺。她的思考中更有對裴少俊“讀五車書,會寫休書”的辛辣嘲諷,對裴尚書“枉叫他遙授著尚書,則好教管著那普天下姻緣簿”的無情奚落,有“怎將我墻頭馬上,偏輸卻沽酒當壚”的憤恨不平。李千金既追求自己理想的愛情,同時也追求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4]不僅“負心漢”丈夫在她這里討不到一句好話,就連公公裴行儉也碰了一鼻子灰還只能忍氣吞聲。李千金的人物形象由此豐滿而立體,這是古代戲曲文本中極為少見的擁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女性形象。不同于白樸的另一出雜劇《梧桐雨》中依附唐明皇愛情而活的楊貴妃,她在后院深宮中以為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依靠,短暫的享受了愛情的歡愉后,面對心愛的丈夫唐明皇的“賜死”的詔書卻無力改變自己死亡的結局。李千金是可以主動捍衛自己尊嚴,而不是被環境裹挾著被動接受或被動反抗的女性形象。正是這樣的人物及敘事建構,使劇本情節節奏把控得當,層層推進。
二、接受美學視域下看《墻頭馬上》
“接受美學”注重將讀者放在作品創作的最重要的位置,而《墻頭馬上》塑造出李千金這一大膽潑辣的女性形象,在之前戲曲中絕大部分“無意志”的女性客體形象之上有了極大突破。這一大膽的改變滿足了觀眾的“期待視野”,在文體期待、意象期待、意蘊期待中均有所突破,因此由于其出色表現大大超超出了觀眾對其的預判從而獲得了巨大成功。
(一)文本的空白性
“召喚結構”是接受美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強調文本的空白點,給觀眾留下空白的懸念點從而吸引觀眾如同進入劇中探險一般,陪伴角色經歷劇中的故事,有如身臨其境之感。
《墻頭馬上》盡管被現在稱為“愛情喜劇”,但劇中在李千金為了一雙兒女妥協,答應裴行儉的求和后戛然而止,并沒有繼續寫李千金跟著裴行儉回到裴家后的故事。那李千金的未來會如何、以后在婆家是否還會為了孩子忍氣吞聲等等問題都不得而知。《墻頭馬上》的結局是不圓滿之中的圓滿,這種破鏡重圓、幸福美滿的歡喜之后,他們二人的愛情是否又能否一帆風順,倘若李千金失去她的名門望族身份之后裴家又會如何對待她?她是否還會被趕出家門?這一切都不得而知,需要讀者在其期待視野中對這些懸念進行帶有自我色彩的填充與想象,引發讀者對其后面故事的想象與沉思,甚至是根據讀者自己的理解會衍生出多種不同的后續。同時,根據上文所闡述的李千金的形象背后是新思想的覺醒與封建權威的斗爭,那如此這般花好月圓人長久的結局是否也在暗示著新思想最終斗爭失敗的悲慘結局呢?那《墻頭馬上》從這一維度上的闡釋是否又不再是愛情喜劇而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呢?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正是這樣多重的空白點與不確定性給了讀者再創《墻頭馬上》的豐富的可能性,這也是《墻頭馬上》得以被保存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的原因之一。
黃梅戲、昆曲、京劇及粵劇都有對《墻頭馬上》進行不同維度的改動并將其搬上舞臺,其在內容主題、人物塑造方面更貼合現代大眾視野的審美取向,以更貼近現代人審美心理的敘事方式,充分迎合了當代觀眾的審美意識,且風格迥異。[5]時代在不斷變化,人們的價值取向也在不斷變化中。在當下女性地位不斷提高的現實,人們相比之前更愿意看到夫妻互訴衷腸,似乎更愿看到李千金狠狠出上一口惡氣,為自己的顛沛流離報仇。因此在戲曲舞臺的呈現上,導演都對文本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賦予了文本更多樣化的意義。
(二)戲曲舞臺改編
黃梅戲版《墻頭馬上》由黃梅戲劇院劇作家陳望久先生改編,在保持原有故事的基礎之上融入了黃梅戲的特色,不乏大量幽默風趣的情節和富有生活氣息的臺詞,讓戲曲表演打破常規,可以滿足多種觀眾群體的“期待視域”。
在人物形象上,裴行儉、裴少俊和李千金等角色都根據時代的發展特征以及觀眾喜好的變化進行了進一步的豐滿和雕琢。在保持原劇本中對裴行儉不近人情、迂腐的諷刺和批判的基調之上,也給他這個封建的衛道士增添了些許人情味。他面對自己的一對親孫兒會疼愛有加,有時又會因年齡大了樂得當一個糊涂的酒鬼。而在男主角裴少俊的身上,更是少了一份軟弱,多了一份擔當與責任。他是風流浪蕩的少爺,但也會在面對父親的怒火時將妻子攔在身后護住他。在這個愛情變為快餐的時代,如此堅貞不渝的愛情,更是讓讓觀眾多了一份對他們“覓得良人卻無緣相再續”的唏噓與感慨。
在情節設置上,變得更加首尾呼應,前后的對比也給這一出愛情喜劇更加增添了趣味。當受盡磨難與歧視的李千金面對前來求和的丈夫和老公公時,除了言語上的諷刺與奚落,更是將裴行儉之前故意刁難她的伎倆——“石上磨玉簪”“井底引銀瓶”原封不動地歸還到了他身上。裴行儉無可奈何照做的滑稽動作也在給劇本增添趣味的同時,消磨了那一絲淡淡的悲哀,留下的更多的是家庭的溫馨與破鏡重圓的美好。同時,更加突出了李千金敢于打破世俗常規、獨立自主的“大女主”形象,符合當下時代大背景下眾多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的“期待視域”。
三、戲曲中物象符號的東方美學塑造
“一切景語皆情語”,電影的空間敘事亦實亦虛,它既是地理特征的表述,也有意象空間的韻味營造和情感流露。兩者交融相依,營造出電影的“詩情畫意”。在白樸的《墻頭馬上》中,這一出才子佳人一見鐘情而私奔出現的場景是在中國傳統的墻院中,而裴少俊“金屋藏嬌”也是在后花園這樣一個曖昧之地,這兩處地方也常出現在中國傳統戲曲中。這兩處物理建筑不僅為劇情發展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起到了空間敘事的表意作用,更營造了獨具特色的中式古典美學意蘊,塑造了濃厚的東方美學。本文將對“墻”及“后花園”二者進行探討。
(一)“墻”頭相望一見鐘情
在中國古代畫本中,“墻”一直是承載著青澀愛情萌芽的地方,無數的佳人才子隔著那樣一堵青灰水泥的固體屏障暗許芳心。四四方方的水泥墻圍砌起來的,不僅是物理形態上的“家”,更是在青年男女的成長期于他們的心靈上套上的厚重枷鎖,是封建教禮教對他們個性自由發展的束縛。而戲曲文本中常出現的“翻墻”“私奔”等情節,更是超越其束縛、追求自我價值存在的表現。
《墻頭馬上》便是一個從“墻”開始的故事,裴少俊奉父命在洛陽搜集奇花異草,翩翩公子騎馬游園時被墻頭賞花的李千金看到。李千金賞花卻瞧到賞心少年郎,裴少俊也在尋花時遇到美嬌娘,兩人一見鐘情。李千金直白的表達出少女的春心萌動并大膽地與初次邂逅的少年互留訊息,在明白裴少俊與之有著一樣的情投意合的濃烈情愫后,李千金大膽地回答“莫負后園今夜約,月移初上柳梢頭”,將那些閨閣里嬤嬤耳提面命教導的的規矩拋之腦后,主動邀約心愛的裴郎跳過墻頭私定終身。最終兩人為了彼此之間純粹而又炙熱的愛情決定縱身一躍,越過那深深高高的庭院,與心愛之人打破那阻攔彼此的厚障壁。此處的“翻墻”也是裴李二人打破封建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抑制,對自由婚姻的追求,大膽地向封建傳統禮教宣戰。
(二)后花園內私定終身
后花園作為重要意象之一,其功能既有制造情節沖突、營造波瀾起伏之效,其深層也象征著封建傳統束縛下女性放置心靈的私密空間以及違背父母媒妁之言的愛情的“禁忌”。
在《墻頭馬上》中,李家的后花園給男女主人公提供了私定終身的場所。在此處,后花園意指少女春閨夢的孕育和承載之地。在古代大家閨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生活里,后花園是連接閨房和外面世界的過渡地,也是她們距離外面世界最近的地方,因此后花園對于李千金代表的大家閨秀具有“神秘”“禁忌”之感。而她們前往后花園也都是悄悄前往不敢讓人知道,李千金如此潑辣直率的少女也只敢在父母不在家時才可前往,并且都有丫鬟陪同,可見后花園在閨閣少女心中如同伊甸園般地存在。也正因如此,裴少俊和李千金在李家的后花園私定終身,圓了少女的春閨夢,走向美好婚姻。兩人婚后也是躲藏于后花園中,此處的后花園也象征著“曲徑通幽處”的私密之情和禁忌之愛。花園中轟轟烈烈的花是兩人火熱而真摯的愛情,隱秘的位置則象征著兩人無法見天日的“夫妻關系”。
而后花園在《墻頭馬上》中還有另一處重要存在,那便是兩人私定終身后,裴少俊私藏李千金的住所。在古代的大戶人家中,花園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也是權力和榮華富貴的象征。這樣的設計不僅暗示著裴家是顯赫名門,而這樣的顯赫名貴之家竟然發生了在當時被視為“極大恥辱“的私定婚姻,這更凸顯出李千金突破世俗常規、封建教條的大膽與難能可貴,同時也為之后裴行儉這樣一位“老學究”、一心盼望兒子成才的“嚴父”發現被兒子私藏起來的李千金后怒斥其是風塵女子這一情節埋下伏筆,認為其與裴少俊門不當戶不對這樣的門第觀念埋下伏筆。
《墻頭馬上》雖改編自唐代白居易《井底引銀瓶》,但其劇情卻又與《井底引銀瓶》大相徑庭:在白樸兼具歷史的嚴謹性又裹挾著熱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的筆下,劇中的女主角不再是怯懦、唯命是從的小女子,而變成了大氣豪爽、潑辣獨立的新女性形象,將“愛情”這一人性主題放在了首位,更具自由奔放的超脫色彩。這也與白樸生活的時代及其顛沛流離的生活有關。白樸生于金末,自小便見過朝代更迭民不聊生的社會,在他的作品中都帶有一絲隱世飄逸之氣。他寫作不是為了抨擊時局,而更多是為了抒發自己內心熱烈奔放的理想與追求,展現自己超脫奔放的內心世界。盡管《墻頭馬上》的結局并沒有打破門當戶對的局限性,但其塑造出李千金這一敢愛敢恨、直率潑辣的經典女性形象,使其成為中國古典戲曲文本中極少數的有獨立意志的女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李千金這一潑辣、果決、具有豪俠氣的理想女性形象讀來讓人更覺耳目一新、酣暢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