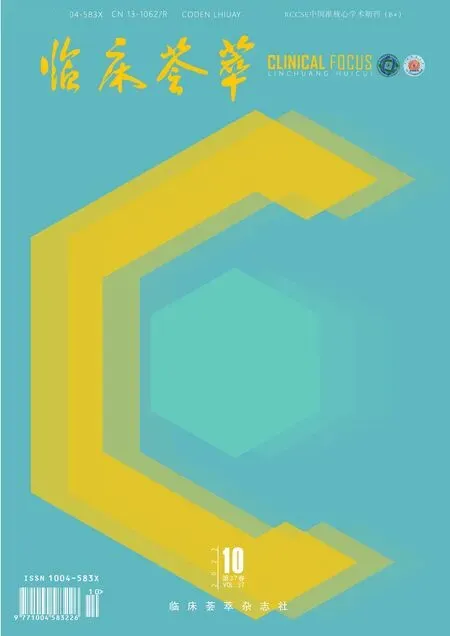改善循環治療加重帕金森病患者體位性低血壓1例
李文君,張 策,劉俊艷
(河北醫科大學第三醫院 神經內科,河北 石家莊 050051)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是常見的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臨床主要關注其運動癥狀如靜止性震顫、肌張力增高、運動遲緩、姿勢步態異常等。而未引起臨床醫師足夠重視的非運動癥狀如自主神經功能障礙、感覺異常、異動睡眠、精神癥狀等,則可能給患者及家屬帶來更嚴重的負擔[1]。雖腦血流障礙在PD發病機制中的作用尚不明確,但臨床治療中發現改善循環藥物可減輕PD患者的運動癥狀。本文報道1例PD合并高血壓患者,在給予降壓及調整藥物治療后出現了體位性頭暈,停用降壓藥物并予以改善循環治療后,體位性低血壓癥狀加重并出現暈厥。臨床醫生應加強對于PD患者非運動癥狀的關注,尤其是在其應用改善循環類藥物時。
1 臨床資料
患者男性,59歲,主因“肢體震顫,動作笨拙5年”于2016年3月21日就診于我院門診。患者于2011年出現左下肢不自主抖動,靜止時出現,運動時減弱,入睡后消失,次年出現運動笨拙,表現為體育鍛煉時左下肢活動不利,2013年初出現左上肢靜止性震顫伴活動不利,2015年出現右下肢震顫,伴雙下肢疲乏感、起步費力、便秘、情緒低落。無汗液分泌異常、嗅覺減退等癥狀。于外院診斷為帕金森病,予以“吡唄地爾1片, 2次/d,卡左雙多巴1片, 3次/d”口服,用藥后患者動作笨拙及肢體震顫癥狀好轉。但隨著病程延長,上述藥物療效減退,為求進一步改善癥狀就診于我院門診。既往有高血壓病史,血壓控制不佳,門診測量血壓160/100 mmHg(1 mmHg=0.133 kPa)。專科體格檢查示:運動遲緩,左側肢體及右下肢不自主震顫,左側肢體肌張力高,余無陽性體征。予以調整抗PD用藥為:吡唄地爾 1片, 3次/d;普拉克索半片, 3次/d(1周后改為1片, 3次/d);多巴絲肼半片, 3次/d;司來吉蘭早午各1片;金剛烷胺早午各1片。半月后患者復診,運動遲緩及震顫癥狀好轉,測量血壓160/100 mmHg,專科體檢示左下肢可見不自主震顫,左上肢肌張力稍高。調整多巴絲肼為1/4片, 3次/d服用,加用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控制血壓。1個月后患者復診,自覺近半月左手震顫加重伴頭暈,頭暈于站立時明顯,伴多汗、排尿費力、便秘,嗅覺減退、睡眠中驚醒、記憶力減退等癥狀。復測血壓100/70 mmHg,專科查體:左側上下肢不自主震顫伴肌張力增高。囑其停用馬來酸左旋氨氯地平,監測血壓4次/d,增加普拉克索為1.5片, 3次/d。并予以氯化鈉注射液250 ml+馬來酸桂哌齊特320 mg靜脈點滴, 1次/d,連用1周。用藥期間患者出現頭痛,頭暈加重,并出現體位性暈厥2次。考慮患者存在嚴重的體位性低血壓,停用桂哌齊特,囑其多飲水、少食多餐、應用醫用彈力襪、體位改變前活動下肢以減輕體位性低血壓癥狀,經上述處理后患者癥狀好轉,未再出現暈厥。
2 討 論
分析該病例特點如下:①中老年男性;②隱匿起病,漸進性加重;③主要表現為肢體震顫、動作笨拙,病變從一側肢體波及另一側,伴便秘、情緒低落;④查體提示靜止性震顫及肌張力升高,雙側不對稱;⑤應用多巴胺能藥物治療顯效;⑥既往有高血壓病史,無毒物、藥物、外傷、腦炎、卒中史。依據《中國帕金森病的診斷標準(2016版)》考慮患者帕金森病診斷明確[2]。
PD的發病機制主要為黑質致密部多巴胺能神經元丟失,導致腦內遞質失衡,而腦血流動力學因素在PD發病機制中所發揮的作用尚不明確。臨床治療中發現:桂哌齊特等鈣離子拮抗劑類改善循環藥物可減輕PD患者的運動癥狀,增強口服藥物的治療效果。研究發現腦血流廣泛性低灌注是PD腦退變的內在特征之一[3]。PD患者的額、頂、枕葉均存在腦血流量降低[3-6]。與對照組相比,PD患者的特征性灌注模式為頂枕部皮層、楔葉、楔前葉、額中回灌注減低,而蒼白球、殼核、前扣帶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的灌注相對保留[4]。但不同表型的PD患者腦灌注缺損表現不同[5, 7]。腦血流降低于PD早期階段即可發生[8]。伴或不伴癡呆的PD患者均存在皮層區域腦血流量降低[8-9]。Taguchi等[10]發現抗PD藥物可明顯增加基底節及丘腦處感興趣區的腦血流,而降低額葉感興趣區的腦血流;且深部結構腦血流改變較皮層明顯。二者腦血流反應的不同可能源于微血管的多巴胺能神經密度及神經變性程度不同。因此,研究者建議結合新的分析方法將異常的灌注及代謝模式用于PD患者的鑒別診斷、疾病進展、修飾及治療反應評估的生物標記[4, 11-12]。
為探討PD患者腦灌注改變的原因,Biju等[11]應用ASL對過度表達人類野生型α突觸核蛋白的轉基因PD小鼠進行研究,發現轉基因小鼠存在皮層腦血流量降低,從而認為α突觸核蛋白與PD患者的腦血流量降低存在因果關系。研究者推測轉基因鼠及PD患者皮層腦血流量降低與過度表達的α突觸核蛋白影響腦血流自動調節及神經血管偶聯相關。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對腦血流量有重要的調節作用,而RAS與多巴胺存在反向調節。過度表達的α突觸核蛋白可導致多巴胺減少,通過反向調節引起RAS激活,進而導致腦血流量下降。此外,RAS活化可激活NADPH氧化酶使活性氧產生增加,引起氧化應激及神經炎癥,導致PD病理改變。另一個可能的腦血流量下降原因是α突觸核蛋白過表達導致神經代謝異常,進而導致腦血流減低。盡管腦慢性低灌注是神經退行性病變的病因還是病程尚無定論,但是有研究指出慢性腦低灌注可通過氧化應激、神經炎癥、tau蛋白磷酸化、內皮素1功能上調、突觸功能異常、神經元丟失等多個途徑促進神經退變[3]。故推測桂哌齊特等改善循環類藥物可通過擴張血管、增加腦血流、改善慢性腦低灌注狀態而發揮對PD患者的治療作用。
此外,桂哌齊特還是腺苷增效劑,可增強腺苷和環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的功效;并可抑制cAMP磷酸二酯酶活性,使cAMP數量增加[13]。cAMP參與多巴胺在腦內的信號轉導過程,進而參與基底節對皮層的運動調節[14]。在中樞神經系統,cAMP還參與認知、感覺、記憶、情緒及神經發生、突觸可塑性等多個生理過程,而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發生則主要與這些過程的不同程度障礙或損傷相關[15]。磷酸二酯酶(phosphodiesterases,PDE)是體內cAMP的唯一水解酶,具有多種亞型,廣泛分布于紋狀體。PDE的表達和活性可直接影響細胞內cAMP的水平[14-15]。故而,調控體內cAMP水平及其下游信號,可能為桂哌齊特改善PD患者癥狀的另一原因。
桂哌齊特雖為鈣離子拮抗劑,但其不良反應主要為急性粒細胞缺乏、頭痛等,很少導致低血壓發生。藍蘭等[16]總結了桂哌齊特的不良反應,發現該藥可致過敏反應甚至過敏性休克,但未有血壓降低的報道。胡鵬洲等[17]對541例桂哌齊特不良反應報告分析發現,4例患者出現嚴重低血壓,但未對其展開描述,不除外為藥物過敏導致的休克狀態。本例患者有高血壓病史,在給予降壓及調整抗PD藥物治療后出現了體位性頭暈,停用降壓藥物并予以桂哌齊特后出現嚴重的體位相關性血壓降低、暈厥,停用桂哌齊特并予以對癥處理后,患者癥狀好轉,未再發生暈厥。考慮該現象的發生與其自主神經功能不全相關,而桂哌齊特的應用加重了其臨床表現。
血壓調節障礙是PD患者自主神經功能障礙的主要表現之一,其具體表現為體位性低血壓(orthostatic hypotension,OH)、臥位高血壓(supine hypertension,SH)及餐后低血壓(postprandial hypotension,PPH)。其中,以OH更為多見,發生率為5%~51%[18]。其診斷標準為直立傾斜試驗(傾斜角度≥60°)或主動站立試驗中,從臥位轉為立位3 min內,收縮壓下降≥20 mmHg或舒張壓下降≥10 mmHg,伴或不伴相關癥狀。若合并臥位高血壓,則以收縮壓降幅≥30 mmHg或舒張壓降幅≥15 mmHg為診斷標準更為合適[19]。OH的典型臨床表現為體位相關性頭暈甚至暈厥,其發生主要與心血管系統交感神經支配降低及壓力感受器反射弧功能不全相關[18-20]。在PD患者中,OH發生的危險因素為高齡、病情重、病程長、應用抗PD藥等。其他的誘發因素包括脫水、貧血、環境高溫、攝食或飲酒、某些藥物(利尿劑、三環類抗抑郁藥及擴血管類藥物)等[18-19]。研究發現OH與PD患者生存率降低,癡呆、跌倒和姿勢不穩風險升高相關[21-22]。
目前臨床上可應用非藥物治療及藥物治療改善PD患者的OH癥狀。非藥物治療包括:避免可能導致OH的情況如高溫環境、緊張過度、進食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飲酒、長時間站立、突然的體位改變等。適當增加水鹽攝入以維持足夠的血容量;使用醫用彈力襪或腹帶等加壓設備;出現癥狀時采用下蹲、抬高下肢等對抗性動作等[19]。當非藥物治療無效時,則采用藥物治療,可應用的藥物包括米多君、屈昔多巴、氟氫可的松、吡斯的明等[18-19]。對于并發OH及SH的PD患者,建議先對OH進行處理,允許餐后血壓輕中度升高。而SH治療方案的確定依賴于患者血壓升高的程度及是否合并靶器官損害:當血壓的水平在160~180 mmHg/90~110 mmHg時,可根據患者情況選擇是否用藥;當血壓≥180 mmHg/110 mmHg時必須用藥。此種情況的降壓治療建議選用短效藥如可樂定、硝酸甘油透皮貼劑、短效硝苯地平等。同時應注意到SH的治療會增加OH發生風險,進而引發跌倒、骨折等相關并發癥,如本例患者。平均血壓不低于75 mmHg可作為權衡OH及SH藥物治療的標準[18]。新近研究表明,腦橋深部電刺激可調節PD患者心血管系統功能,其可使體位變化引起的血壓降低減小并改善在Valsalva動作中的心血管反應[23],提示手術治療有望成為改善PD患者非運動癥狀的新療法。
而新近一篇持續了7年的研究[24]發現PD患者的OH發生率高于對照組,其相對風險度從基線的3.0(95%CI1.6~5.8;P<0.01)增加到7年后的4.9(95%CI2.4~10.1)。在初診的PD患者中,19.5%合并OH,1.7%合并有臨床意義的OH(平均動脈壓≤75 mmHg)。隨訪結束后,合并OH的PD患者達到65.4%,合并有臨床意義OH的PD患者升至29.2%,但僅有0.5%的患者應用抗低血壓藥物治療。故OH是PD患者早期常見,但診治不足的并發癥。而該病例顯示桂哌齊特等具有輕度血管擴張作用的藥物即可加重其臨床表現,增加患者跌倒、外傷及癡呆風險,降低治療效果。提示臨床醫生應加強對于PD患者的血壓監測,關注尿便障礙、泌汗異常、性功能障礙等自主神經功能損害癥狀,并注意完善臥立位血壓及腦血管反應性檢查,以及早發現患者并發的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及其程度,尤其是對于合并高血壓而應用降壓藥或血管擴張類藥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