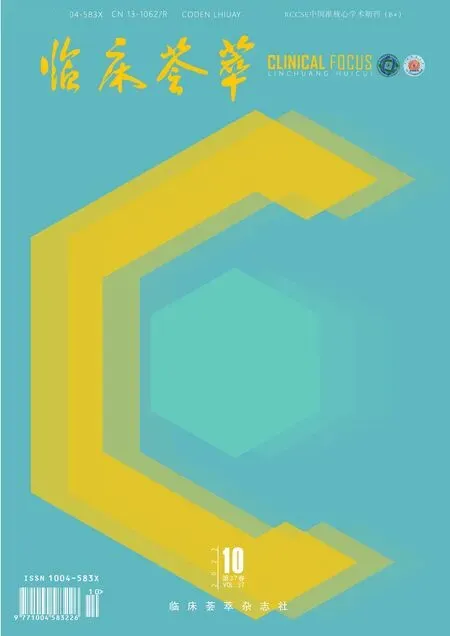心血管系統常用藥物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風險及不良預后的影響
周子涵,崔 煒
(河北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河北省心腦血管病研究所 心內一科,河北 石家莊 050000)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給世界各地的醫療保健系統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迄今已有6.2億例病例和650萬人死亡[1]。關于心血管系統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各研究之間尚無一致定論。本文將歸納總結現有薈萃分析結果,以確定心血管系統常用藥物與新冠肺炎的發生率和不良預后是否存在關聯,為臨床用藥提供指導。
1 降壓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在新冠肺炎患者中,已證實高血壓與疾病的嚴重程度和死亡率相關。最常見的藥物暴露是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CEI)/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ARB),因此成為關注焦點。先前的證據表明, ACEI和ARB可提高心臟ACE2基因表達或誘導心臟ACE2活性[2-3]。這就提出了問題,這些藥物是否會影響SARS-CoV2感染的風險以及新冠肺炎患者的預后。
1.1對SARS-CoV-2易感性的影響 共有13篇[4-16]薈萃分析提及ACEI/ARB對SARS-CoV-2感染風險的影響,其中12篇[4, 6-16]發現ACEI/ARB與SARS-CoV-2感染無關,1篇[5]發現ACEI可降低SARS-CoV-2感染的風險。在研究高血壓人群的6篇[9-12, 14-15]薈萃分析中,結果均發現ACEI/AR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SARS-CoV-2的感染風險。共有2篇[12, 17]提及β受體阻滯劑對SARS-CoV-2感染風險的影響,其中1篇[12]發現β受體阻滯劑與SARS-CoV-2的感染風險無關,1篇[17]發現風險增加。共有1篇[12]關于鈣離子通道阻滯劑(CCB)及利尿劑與SARS-CoV-2易感性的薈萃分析,結果發現上述兩類藥物均不會增加新冠肺炎發病風險,見表1。
1.2對SARS-CoV-2感染后嚴重程度的影響 多數薈萃分析對嚴重程度的定義是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需要機械通氣或入住ICU。其中重型/危重型肺炎的定義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委員會確定疾病嚴重程度標準。重型肺炎定義為符合如下任何一條:①呼吸窘迫,呼吸頻率(RR)≥30次/min;②靜息狀態、無吸氧時指脈氧飽和度≤93%;③動脈血氧分壓(PaO2)/吸氧濃度(FiO2)≤300 mmHg(1 mmHg=0.133 kPa);④影像學顯示24~48小時內肺部浸潤>50%。危重型肺炎定義為符合如下任何一條:①出現呼吸衰竭,且需要機械通氣;②出現休克;③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收入ICU治療。
1.2.1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 在以ACEI/AR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27篇[4, 7-12, 14-15, 18-35]選擇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作為終點,其中19篇[4, 7-8, 11-12, 14-15, 19-25, 27, 30-32, 35]發現ACEI/ARB不會增加嚴重疾病的風險,7篇[9-10, 18, 26, 29, 33-34]發現風險降低,1篇[28]發現風險增加。共有13篇[8-12, 14, 29-35]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其中9篇[8-11, 14, 30-32, 35]發現使用ACEI/AR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嚴重疾病進展的風險,4篇[12, 29, 33-34]發現風險更低。在以CC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4篇[12, 36-38]選擇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作為終點,其中3篇[12, 36, 38]發現使用CCB不會增加嚴重疾病的風險,1篇[37]發現風險更低。共有2篇[36-37]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其中1篇[36]發現使用CC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嚴重疾病進展的風險,1篇[37]發現風險降低。共有2篇[12, 17]關于β受體阻滯劑與重型/危重型肺炎風險的薈萃分析,1篇[12]發現β受體阻滯劑與嚴重疾病進展無關,1篇[17]發現風險增加。共有1篇[12]關于利尿劑與重型/危重型肺炎風險的薈萃分析,結果發現利尿劑與嚴重疾病進展無關,見表1。
1.2.2入住ICU 在以ACEI/AR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17篇[5, 7, 12, 14, 16, 22, 24-25, 27, 30, 33-34, 39-43]選擇入住ICU作為終點,其中12篇[7, 12, 16, 22, 24-25, 27, 30, 39-41, 43]發現使用ACEI/ARB不會增加入住ICU的風險,4篇[5, 33-34, 42]發現風險降低,1篇[14]發現風險增加。共有7篇[14, 16, 30, 33-34, 42-43]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其中4篇[14, 16, 30, 43]顯示使用ACEI/AR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入住ICU的風險,3篇[33-34, 42]發現風險降低。在以CC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3篇[36-38]選擇入住ICU作為終點,其中2篇[36, 38]發現CCB不會增加入住ICU的風險,1篇[37]發現風險降低。共有2篇[36-37]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其中1篇[36]發現CC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入住ICU的風險,1篇[37]發現風險降低。共有1篇[17]關于β受體阻滯劑與入住ICU風險的薈萃分析,結果發現風險增加。尚無關于利尿劑與入住ICU風險的薈萃分析,見表1。

表1 降壓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1.2.3無創/機械通氣 在以ACEI/AR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有17篇[5, 7, 14-16, 22, 24-25, 30, 33-34, 39-44]選擇無創/機械通氣作為終點,其中11篇[7, 15-16, 22, 24-25, 30, 39-41, 43]發現使用ACEI/ARB不會增加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5篇[5, 33-34, 42, 44]發現風險降低,1篇[14]發現風險增加。共有8篇[14, 16, 30, 33-34, 42-44]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其中4篇[14, 16, 30, 43]發現使用ACEI/ARB不會增加高血壓人群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4篇[33-34, 42, 44]發現風險降低。在以CCBs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3篇[36-38]選擇無創/機械通氣作為終點,其中2篇[36, 38]發現CCB不會增加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1篇[37]發現風險降低。1篇[37]包含了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發現CCB可以降低高血壓人群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在以β受體阻滯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1篇選擇無創/機械通氣作為終點,結果發現β受體阻滯劑增加了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17]。尚無關于利尿劑與無創/機械通氣風險的薈萃分析,見表1。
1.3對SARS-CoV-2感染后死亡率的影響 在以ACEI/AR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43篇[4-5, 7-16, 18-35, 39-51]選擇全因死亡率作為終點,其中25篇[4, 7-8, 11-13, 15-16, 20-22, 24-25, 27-28, 30, 32, 35, 40-41, 45, 47-49, 51]發現ACEI/ARB與死亡率無關,17篇[5, 9-10, 18-19, 23, 26, 29, 31, 33-34, 39, 42-44, 46, 50]發現死亡率降低, 1篇[14]發現死亡率增加。共有20篇[8-14, 16, 29-35, 42-44, 50-51]單獨研究了ACEI/ARB對高血壓人群死亡率的影響,其中6篇[14, 16, 30, 32, 35, 51]發現ACEI/ARB與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的死亡率無關,14篇[8-13, 29, 31, 33-34, 42-44, 50]發現死亡率降低,見表1。
然而,關于單獨使用ACEI或ARB治療對于死亡率的影響仍存在差異。Wang等[34]觀察到ACEI和ARB治療亞組之間的死亡率無差異,而Yin等[39]發現相對于ACEI,ARB的使用與較低的死亡率相關,其指出這可能是由于ARB直接阻斷AT1R,但不阻斷AngII,生理性AngII的積聚可能導致ACE2產生保護性多肽Ang1-7,見表1。
在以CCB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3篇[36-38]選擇全因死亡率作為終點,其中2篇[36, 38]發現CCB與死亡率無關,1篇[37]發現死亡率降低。在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中,共有2篇[36-37]研究了CCB死亡率的關系,結果均發現CCB可降低新冠肺炎合并高血壓患者的死亡率。在以β受體阻滯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1篇選擇全因死亡率作為終點,結果發現β受體阻滯劑增加了死亡風險[17]。尚無關于利尿劑與死亡率關系的薈萃分析,見表1。
根據目前所有薈萃風險結果,抗高血壓藥物的使用不會增加新冠肺炎的易感性、嚴重不良事件的風險和死亡率,不建議新冠肺炎患者在服用降壓藥的情況下停止服用。考慮到ACEI和ARB在保護心血管系統方面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在高血壓患者中,無論是否在伴有冠心病、心力衰竭和糖尿病腎病,此類患者在用藥后預后均有所改善。特別是ACEI/ARB,有研究表明合并心力衰竭的患者住院期間停用ACEI/ARB會增加患者心功能失代償的可能性,與較高的出院后死亡率有關[52],因此建議合并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患者繼續用藥。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中國指南中對老年高血壓患者的一線推薦是CCB而不是ACEI/ARB[53]。目前大部分薈萃分析的高血壓患者服用ACEI/ARB,新冠肺炎與CCB、β受體阻滯劑及利尿劑的薈萃分析數量較少,無法為臨床上降壓藥的選擇提供建議。
2 降脂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他汀類藥物是一類廣泛用于治療代謝綜合征和心血管疾病的藥物。他汀類藥物主要通過抑制HMG-CoA還原酶來降低血脂,同時具有抗炎、抗血栓、抗氧化和免疫調節等功效[54-55],有效地防止血栓栓塞癥的發生。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血栓栓塞癥是導致嚴重新冠肺炎患者高死亡率的兩個并發癥,明確他汀類藥物在新冠肺炎中是否仍存在臨床獲益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療具有重大意義。
2.1對SARS-CoV-2易感性的影響 僅1篇[56]薈萃分析提及他汀類藥物對SARS-CoV-2感染風險的影響,結果發現他汀類藥物與SARS-CoV2感染無關。尚無關于非他汀類降脂藥物與SARS-CoV-2感染風險的薈萃分析。
2.2對SARS-CoV-2感染后嚴重程度的影響 關于嚴重程度的定義,大多數薈萃分析同樣定義為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需要機械通氣或入住ICU。
2.2.1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 在以他汀類藥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3篇[56-58]選擇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作為終點,2篇[56-57]發現服用他汀類藥物與重型/危重型肺炎的風險無關,1篇[58]發現風險降低,見表2。
2.2.2入住ICU 在以他汀類藥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6篇[59-64]選擇入住ICU作為終點,其中4篇[59, 61-62, 64]發現他汀類藥物不會增加入住ICU的風險,2篇[60, 63]發現風險降低,見表2。
2.2.3無創/機械通氣 在以他汀類藥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有6篇[59-64]選擇無創/機械通氣作為終點,其中2篇[59, 62]發現他汀類藥物不會增加無創/機械通氣的風險,4篇[60-61, 63-64]發現風險降低,見表2。
2.3對SARS-CoV-2感染后死亡率的影響 在以他汀類藥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薈萃分析中,共有14篇[56-69]選擇全因死亡率作為終點,其中4篇[56-57, 59, 64]發現他汀類藥物不會影響死亡率,10篇[58, 60-63, 65-69]發現死亡率降低。共有5篇[63, 65, 67-69]薈萃分析對混雜因素如年齡、性別和心血管疾病進行了單獨亞組分析,發現在老年(>60歲)、男性和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的人群中,服用他汀類藥物的患者死亡率更低,見表2。

表2 降脂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與非他汀類藥物使用者相比,他汀類藥物使用者的預后有所改善,尤其是在降低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方面較為顯著。考慮到當前關于他汀類藥物與SARS-CoV-2感染相關的薈萃分析數量有限,尚不能確定他汀類藥物對于SARS-CoV-2感染具有保護作用。
對于他汀類藥物的受益人群,不同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發現。Chow等[62]比較他汀類藥物對ICU患者與非ICU患者死亡率的影響,發現在非ICU患者中,使用他汀類藥物的患者死亡風險更低。 Vahedian-Azimi等[64]僅納入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人群,發現僅前者的總死亡率降低。Diaz-Arocutipa等[69]發現只有長期使用他汀類藥物的患者才有獨立較低的死亡率。他汀類藥物使用者死亡率更低的4個群體包括:①住院期間服用他汀類藥物的患者;②非重癥患者;③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④長期服用他汀類藥物的患者。
然而,有多項研究[62, 64, 66]發現入院前接受他汀類藥物治療的患者并不能從中獲益,這可能低估了入院前他汀類藥物的保護性作用。考慮到他汀類藥物用于心血管疾病一級或二級預防,院外他汀類用藥患者數量龐大,仍需更多的研究來明確入院前他汀類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鑒于他汀類藥物在減少心血管不良事件方面的多效性作用以及對新冠肺炎預后的有益影響,建議患有血脂異常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仍繼續服用他汀類藥物。
3 抗血小板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嚴重SARS-CoV-2感染患者容易發生多器官損傷,導致血小板活化不受抑制,活化的血小板與中性粒細胞相互作用促使細胞外基質蛋白降解和凝血酶生成,造成機體高凝狀態。阿司匹林是心血管疾病中使用最廣泛的藥物,通過不可逆地抑制環氧合酶(COX)對血栓素A2的激活,抑制血小板黏附、聚集、活化[70]和炎癥級聯反應過度激活,進而降低主要器官功能障礙發生的風險[71]。有研究表明在非SARS-CoV-2感染的危重患者中,阿司匹林可以降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的發生率和患者的病死率[70, 72]。然而阿司匹林屬于非甾體抗炎藥,其可以改變中性粒細胞功能,延緩細菌清除和炎癥消退,從而加重肺部疾病進展[73-74]。關于抗血小板治療,是否會增加新冠肺炎感染的風險,以及是否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的嚴重程度及死亡率仍存在爭議。
3.1對SARS-CoV-2易感性的影響 尚無薈萃分析發現抗血小板藥物會增加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不過研究發現在所有抗血小板藥物中,只有阿司匹林可以通過阻斷巨噬細胞中的前列腺素E2和上調I型干擾素的生成來限制病毒復制[75],這一發現有待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3.2對SARS-CoV-2感染后嚴重程度的影響 1篇[76]薈萃分析研究了抗血小板藥物與嚴重疾病進展之間的關系,發現接受抗血小板治療患者與未接受抗血小板治療患者進展為重型/危重型肺炎的風險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篇[77]薈萃分析選擇血栓形成作為終點,結果發現接受抗血小板治療患者血栓形成風險更低。2篇[77-78]薈萃分析選擇大出血作為終點,其中1篇[78]發現抗血小板藥物與出血事件無關,1篇[77]發現抗血小板藥物會增加出血事件,見表3。
3.3對SARS-CoV-2感染后死亡率的影響 共有9篇[76-84]薈萃分析選擇全因死亡率作為終點,其中3篇[77, 79-80]發現抗血小板藥物對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無影響,6篇[76, 78, 81-84]發現死亡率降低。共有7篇[78-84]單獨研究了阿司匹林與死亡率的聯系,其中1篇[79]發現服用阿司匹林和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之間沒有聯系,6篇[78, 80-84]發現死亡率降低。共有3篇[76, 78, 81]調整了諸如年齡、吸煙、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壓、糖尿病、冠狀動脈疾病、心力衰竭、肥胖、中風和慢性腎臟疾病等疾病的干擾后,發現該保護作用依然存在,見表3。

表3 抗血小板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依據現有薈萃分析結果,支持阿司匹林對新冠肺炎患者存在潛在治療意義。關于阿司匹林的保護劑量各研究之間尚無一致定論,Ma等[78]研究發現在住院前或住院期間服用小劑量阿司匹林(每日80~100 mg) 即可降低死亡率,而在中劑量阿司匹林(每日150 mg)治療組,該保護作用將不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服用中劑量阿司匹林的患者有更多進展為嚴重疾病的危險因素,例如:高齡、冠狀動脈疾病、糖尿病等,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排除這些因素的干擾,來確認阿司匹林的保護劑量。
4 抗凝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新冠病毒感染可造成廣泛的血栓形成和微血管病變[85],其中靜脈血栓栓塞(VTE)、肺栓塞(PE)和肺原位血栓形成和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的發生率較高[86]。在嚴重的新冠肺炎中,大量產生的促炎細胞因子會導致高凝狀態、血管高滲、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87-88]。低分子量肝素(LMWH)已被確定為新冠肺炎患者的有益治療策略,然而針對不同嚴重程度的新冠肺炎患者,抗凝方案的選擇仍存在爭議。
4.1對SARS-CoV-2易感性的影響 尚無關于抗凝藥物對SARS-CoV-2易感性影響的薈萃分析。不過有研究發現肝素除了發揮抗凝作用外,可結合SARS-CoV-2棘突蛋白,競爭性抑制病毒進入,從而降低病毒的傳染性[89],這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驗證這一結論。
4.2對SARS-CoV-2感染后嚴重程度的影響 大多數薈萃分析將嚴重程度研究終點定義為為血栓事件、出血事件、需要機械通氣或入住ICU。關于預防或治療劑量的定義,每項研究都有自己的標準,沒有一致的參考劑量。在所匯總的薈萃分析中,大多數研究將預防劑量定義為:①普通肝素(UFH)<5 000 IU;②LMWH 20~40 mg/d;③LMWH 1 mg/(kg·d)。治療劑量定義為:① 5 000 IU
4.2.1血栓事件 共有2篇[91-92]薈萃分析選擇血栓事件作為終點,其中1篇[91]發現接受抗凝治療(包括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與未接受抗凝治療的患者發生血栓事件的風險相似,1篇[92]發現風險降低。
共有18篇[91-108]薈萃分析比較了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血栓事件的發生率,其中12篇[91-93, 95, 97-98, 100-101, 104-107]發現相比于治療劑量,接受預防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VTE風險較高,6篇[94, 96, 99, 102-103, 108]發現風險無差異。其中15篇[91-93, 95, 97-107]發現接受預防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PE風險較高,3篇[94, 96, 108]發現風險無差異。患者類型選定為危重新冠肺炎患者(D-二聚體>3 μg/L,血小板計數>100×109/L,PT<14 s)或ICU患者時,共有11篇[92-95, 99-100, 102-104, 107-108]比較了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血栓事件的發生率,其中7篇[92-95, 100, 104, 107]發現相比于治療劑量,接受預防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發生所有血栓事件的風險較高,4篇[99, 102-103, 108]發現風險差異,見表4。
4.2.2出血事件 共有6篇[90-92, 109-111]薈萃分析比較了接受抗凝治療(包括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與未接受抗凝治療的患者出血事件的發生率,其中4篇[91-92, 110-111]發現風險相似,2篇[90, 109]發現風險增加。
共有21篇[90-109, 111]薈萃分析比較了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出血事件的發生率,其中19篇[90-99, 101-104, 106-109, 111]發現接受預防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出血事件風險較低,2篇[100, 105]發現風險無差異。共有11篇[92-95, 99-100, 102-104, 107, 109]對危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亞組分析,其中4篇[92, 94, 107, 109]發現接受預防劑量抗凝治療的患者發生出血事件的風險較低,7篇[93, 95, 99-100, 102-104]發現風險無差異,見表4。

表4 抗凝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4.2.3機械通氣/入住ICU 共有2篇[16, 106]薈萃分析選擇機械通氣/入住ICU作為終點,結果均發現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在發生機械通氣/入住ICU方面無差異,見表4。
4.3對SARS-CoV-2感染后死亡率的影響 共有12篇[90-92, 109-117]薈萃分析研究了抗凝治療對死亡率的影響,其中5篇[109, 112-114, 117]發現抗凝治療對死亡率無影響,7篇[90-92, 110-111, 115-116]發現接受抗凝治療的患者死亡率更低。
共有26篇[16, 90-109, 111, 113, 115-117]薈萃分析比較了預防劑量抗凝治療和治療劑量抗凝治療對于死亡率的影響,其中21篇[16, 91-108, 111, 113]發現兩種抗凝方案的死亡率相似,4篇[90, 109, 115-116]發現治療劑量抗凝方案降低死亡率更為顯著,1篇[117]發現預防劑量更有優勢。共有15篇[90, 92-96, 98-100, 102-104, 107-109]對危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亞組分析,其中13篇[92-95, 98-100, 102-104, 107-109]發現2種抗凝方案對危重患者死亡率的影響無差異,1篇[90]發現治療劑量死亡率更低,1篇[96]發現預防劑量死亡率更低,見表4。
基于以上薈萃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新冠肺炎患者中開展抗凝治療有明顯的益處。同時預防劑量抗凝與治療劑量抗凝相比,可以得出以下結論:①出血事件的發生率降低;②血栓事件的發生率升高;③死亡率無差異;④在普通和危重患者中顯示出一致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考慮到在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中開展治療劑量抗凝治療會顯著增加出血風險,從而減少抗凝治療獲益機會,支持在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中開展預防劑量抗凝治療。而危重患者中可能存在肝素抵抗現象,即需要大劑量肝素(超過35, 000 IU/d)才能達到治療活性[95],更高強度的抗凝治療在危重患者中使用則更有益。
臨床上常見抗凝藥物,包括低分子肝素、普通肝素、磺達肝葵鈉和直接口服抗凝劑等,用于新冠肺炎患者的預防和治療。對于抗凝藥物的選擇,目前尚無標準,臨床上仍可能是基于醫院抗凝藥物的調配、醫生的經驗、治療目標和患者自身的因素來進行選擇。僅Alsagaff等[118]發現在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中,與普通肝素相比,低分子肝素治療與更低的死亡率和血栓風險相關,并且不會增加出血風險,支持住院期間將低分子肝素作為抗凝治療的首選藥物。另有研究表明接受口服利伐沙班治療并不能降低患者死亡率[119]。由于相關研究較少,目前尚不清楚新冠肺炎患者使用各類抗凝藥物抗凝治療療效上的臨床差異,還需隨機對照試驗來進一步指導新冠肺炎患者抗凝藥物的選擇。
針對抗凝的最佳開始與持續時間的問題,Tacquard等[120]指出預防性抗凝治療轉變為治療性的抗凝治療,則應在血栓形成風險較高的入院后前10天開始。對于沒有治療性抗凝指征的患者,抗凝劑量可能應逐漸降低至預防劑量,以限制出血風險。
盡管新冠肺炎的進展常伴有凝血功能紊亂,建議在普通的住院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預防性抗凝,而不是更高劑量的治療性抗凝。國際血栓與止血學會最新指南同樣也支持此結論[121],在因新冠肺炎入院的非危重患者中,建議使用預防性劑量的低分子肝素或普通肝素;對于D-二聚體升高或需氧量增加的患者,應考慮治療劑量的低分子肝素/普通肝素;反對添加抗血小板藥物。對于病情較重的患者,臨床醫生應謹慎權衡治療性抗凝治療減少血栓形成事件的益處,因為較高劑量的抗凝劑使用會顯著增加出血風險。此外,無論開展何種劑量的抗凝治療,用藥前必須權衡抗凝劑的各種不良后果,尤其對新冠感染引起的血小板減少的患者,謹防出血事件發生[122]。
5 降糖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心血管疾病患者常合并有糖尿病,而糖尿病本身導致了低級別的慢性炎癥,其特征是先天性和適應性炎癥系統受損。這種炎癥紊亂會導致免疫反應失調,促炎因子水平升高,抗炎細胞因子水平降低。因此,被認為是新冠肺炎最嚴重的并發癥之一,會惡化疾病的發展和預后。現已被批準用于治療糖尿病的降糖藥物包括胰島素、二甲雙胍、二肽基肽酶4抑制劑(DPP-4i)、磺脲類、格列奈類、鈉-葡萄糖共轉運體2抑制劑(SGLT-2i)、胰升糖素樣肽-1受體激動劑(GLP-1RA)、α-糖苷酶抑制劑和噻唑烷二酮類(TZDs)藥物。由于各類降糖藥作用機制不同,明確各類降糖藥物對于新冠肺炎患者的影響,對于臨床上降糖藥的選擇具有指導意義。
5.1胰島素 共有6篇[123-128]薈萃分析研究了胰島素對死亡率的影響,均發現胰島素會增加死亡率,1篇[123]薈萃分析發現胰島素還與嚴重/危重新冠肺炎的進展相關,見表5。
5.2二甲雙胍 共有8篇[126-133]薈萃分析研究了二甲雙胍對死亡率的影響,均發現二甲雙胍與更低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風險相關。共有3篇[127, 131, 133]研究了二甲雙胍對嚴重程度的影響,2篇[131, 133]發現二甲雙胍可以降低入住ICU和機械通氣的風險,1篇[133]發現二甲雙胍降低了重型/危重型肺炎進展風險,1篇[127]發現二甲雙胍對嚴重疾病進展無影響,見表5。
5.3DPP-4i 共有11篇[126-128, 133-140]薈萃分析研究了DPP4i對死亡率的影響,其中5篇[126, 133-135, 138]發現DPP4i對死亡率無影響,5篇[127, 136-137, 139-140]發現死亡率降低,1篇[128]發現死亡率增加。共有3篇[127, 133-134]研究了DPP4i對嚴重程度的影響,結果均顯示DPP4i不會增加疾病進展、入住ICU、機械通氣或高級生命支持的風險,見表5。
5.4磺脲類 共有4篇[126-128, 133]薈萃分析研究了磺脲類藥物對死亡率的影響,其中2篇[127-128]發現磺脲類藥物對死亡率無影響,2篇[126, 133]發現死亡率降低。共有2篇[127, 133]研究了磺脲類藥物對嚴重程度的影響,結果均顯示磺脲類藥不會增加疾病進展、入住ICU、機械通氣或高級生命支持的風險,見表5。
5.5格列奈類 僅1篇[133]薈萃分析研究了格列奈類藥物對新冠肺炎患者的影響,結果發現服用格列奈類藥物的患者死亡率更低,同時不會增加不良預后風險,見表5。
5.6SGLT2i 共有4篇[127-128, 133, 140]薈萃分析研究了SGLT2i對死亡率的影響,其中1篇[133]發現SGLT2i對死亡率無影響,3篇[127-128, 140]發現死亡率降低。共有2篇[127, 133]研究了SGLT2i對嚴重程度的影響,結果均發現SGLT2i不會增加疾病進展、入住ICU、機械通氣或高級生命支持的風險,見表5。
5.7GLP-1RA 共有5篇[127-128, 133, 140-141]薈萃分析研究了GLP-1RA對死亡率的影響,其中1篇[133]發現GLP1-RA與死亡率無關,4篇[127-128, 140-141]發現死亡率降低。1篇[133]研究了GLP-1RA對嚴重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GLP-1RA不會增加疾病進展、入住ICU、機械通氣或高級生命支持的風險,見表5。

表5 降糖藥物對新冠肺炎的影響
5.8α-糖苷酶抑制劑 僅1篇[128]薈萃分析研究了α-糖苷酶抑制劑對死亡率的影響,結果發現α-糖苷酶抑制劑與死亡率無關,見表5。
5.9TZDs 共2篇[127-128]薈萃分析研究了TZDs對死亡率的影響,結果均發現TZDs與死亡率無關,見表5。
現有研究結果發現胰島素對新冠肺炎患者存在不良影響,盡管潛在機制仍不明確,但考慮到胰島素在控制血糖和糖尿病并發癥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在找到更好或更安全的降糖藥用于合并糖尿病的新冠肺炎患者之前,不建議放棄胰島素治療。
此外,在合并糖尿病的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二甲雙胍、DPP4i、磺脲類、SGLT2i、GLP-1RA是有益,建議在合并糖尿病的新冠肺炎患者中繼續使用。目前關于α-糖苷酶抑制劑、格列奈類、TZDs的研究數量較少,不足以得出關于此3類藥物對新冠肺炎患者臨床預后影響的可靠結論,還需更多的研究來探索上述藥物對新冠肺炎患者的影響。
6 抗心律失常藥物
尚無關于抗心律失常藥物對新冠肺炎影響的薈萃分析,無法得出此類藥物對新冠肺炎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使用胺碘酮更有可能產生肺部毒性并發癥,最常見的表現是間質性肺炎,一般在用胺碘酮治療2個月后出現。胺碘酮的肺部毒性癥狀包括呼吸困難、干咳和發燒。胸部影像通常顯示雙側斑片狀間質或肺泡浸潤[142],需和新冠肺炎相鑒別。
除此之外,已有研究證實在新冠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患者中靜脈注射美托洛爾的安全性,可有效減少肺部炎癥、改善氧合狀態以及減少機械通氣和入住ICU風險[143]。Caracciolo 等[144]發現在新冠肺炎患者中使用吸入性腺苷治療同樣可以改善患者預后。
關于其他抗心律失常藥物的研究較少,合并心律失常的新冠肺炎患者是否可以接受常見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還需更多的研究證實此類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7 小結
本文分類總結了常見心血管藥物對新冠肺炎感染風險及不良預后的影響。然而,有相當一部分新冠肺炎患者可能同時患有多種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同時服用了多種藥物,如ACEI/ARB和二甲雙胍。雖然現有結論發現ACEI/ARB與新冠肺炎死亡率降低相關,二甲雙胍也與新冠肺炎有密切關系。然而聯合用藥對新冠肺炎的影響尚不清楚,可能會影響對藥物的療效評價,還需更多的薈萃分析來為臨床用藥提供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