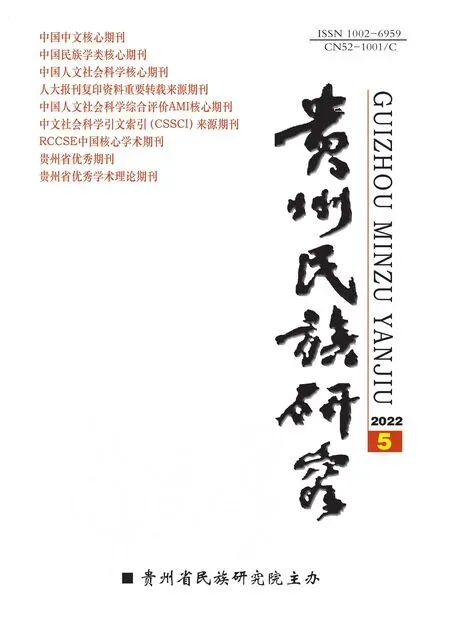茶村小農的兼業模式、人情網絡和空間策略:“去內卷化”的歷史視野和當代實踐
黃華青
(上海交通大學 設計學院,上海 200240)
一、問題的提出
2021 年4月中旬,清明時節將過,溧陽天目湖的白茶季方興未艾。天目湖東岸Z村的空氣中彌漫著炒制茶青的香氣,村后起伏的山野上仍有星星點點的采茶工在辛勤勞作。山上傳來的割茶機聲音卻讓筆者疑惑——作為國內高端綠茶的代表,天目湖白茶竟會使用大批量低端茶常用的割茶機?事實并非如此:茶工手中的割茶機并未將茶芽和嫩葉收割到布袋中,而是棄置一旁作為養料。初看起來,這是一種令人費解的浪費行為。要知道,茶樹每年可抽芽兩到三次,明前茶葉嬌嫩,適合制作高端茶,晚摘茶葉則用于味道濃郁的平價綠茶或紅茶。在天目湖,茶農主動“割茶”的行為意味著只保留價格最高、產量最低的“明前茶”,而放棄廉價但量大的“明后茶”。
這樣“自斷一臂”的行為背后,存在著一套與農業產業化趨勢相悖的實踐邏輯。在中國,強調生產、加工及流通整合的“縱向一體化”[1]路徑長期作為政府支持的主流方案,一般基于如下立場:規范行業生態,以標準化茶企替代非正規的小農生產,以維系茶葉品牌的“正宗性”,亦有利于行業管理和稅收[2];提升行業競爭力,以規模化生產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大農帶動小農,讓先富起來的龍頭企業為小農提供工作或其他收入[3]。而天目湖茶農的割茶行為,構成了對農業產業化的隱性對抗,讓人聯想至關于“內卷化”和“去內卷化”的討論。如黃宗智所言,內卷化的根源在于勞動力過剩、勞動用地少、勞動附加值低等農業生產問題[4],然而茶葉無法簡單歸入“高度內卷化的‘糊口’農業”之列。放在歷史語境下,茶葉作為中國南方廣泛種植的經濟作物,雖然亦存在與棉花等產業類似的過密化特點[5],但往往能以一種看似“內卷”的生產方式實現“去內卷化”邏輯下的較高勞動報酬,乃至呈現一定程度的資本化動力。因此,對于茶農的產業化或“去內卷化”進程的分析,亟需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視野。
無論是農業企業帶動的農業產業化路徑,還是以密集勞動為代價的“內卷化”方向,都不能完整體現當代茶農的選擇——兩者皆未充分展現茶農在產銷鏈條中的能動性。茶農的“去內卷化”行為對于政府頂層邏輯以及學界對“內卷化”的認知提出了有力質問:非正規小農經濟必定會破壞“正宗性”嗎?分散化的小規模生產一定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嗎?小農的積累和致富道路只能寄希望于大農或合作社嗎?
這三個問題指向了本文的核心敘事。通過兩個代表性茶區的調查,從三個層面進行回應:茶村小農如何基于兼業模式適應競爭壓力極大的茶葉生產,如何受人情網絡的約束而確保茶葉品質,這種產銷模式又如何物化于小農的分散化生產空間。這種圍繞個體能動性的產銷模式不僅契合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茶業以家庭化生產應對日增出口量的歷史語境,且更有利于在當代維系茶葉的正宗性、產銷平衡與健康行業生態,充分發揮自下而上的產業動力,對于鄉村振興事業中如何真正以農民為中心帶來啟示。
二、進入田野
文章選取的兩個田野地具有相似的茶葉生產背景,又反映出不同的時代語境和“去內卷化”路徑。G村位于福建南平武夷山,Z村位于江蘇溧陽天目湖東岸,兩者分別位于知名茶葉——正山小種(及其代表金駿眉) 和天目湖白茶——的核心產區。
G 村所產紅茶金駿眉,是在正山小種基礎上結合高端綠茶工藝創制,2006年初推出時便賣出2000元/斤以上的高價。為了在高端市場打開銷路,當地茶企通過編寫模仿古制的茶詩《駿眉令》、將木結構萎凋樓用作制茶展示地等方式,營造新茶的“正宗性”。“稀缺性”話語也一直存在茶葉營銷中,無論正山小種還是金駿眉,都必須采摘“正山范圍” (與G村村域范圍基本重合)內的高海拔茶青制作[6];金駿眉更是要求谷雨前后10天內的“頭芽”。比起傳統茶葉的采摘方式,金駿眉采摘的“浪費”十分明顯。
在Z村,浪費不只為了名義上的“正宗性”,也以政府和茶農自覺聯盟的方式控制市場供給。1997年起,溧陽引入業已成名的“安吉白茶1號”并逐步大范圍種植,2010年獲得國家農產品地理標志認證保護。天目湖白茶售價更勝安吉白茶,一般在500-1000元/斤(某些稀缺品種可賣至2000元/斤)。為了限量供給以維持市場價格,政府積極宣傳水源地生態保護的話語,控制天目湖周邊的種植面積,近年來又陸續以2萬元/畝的價格買斷天目湖周邊的大批茶山,讓其逐步荒廢并野化;茶農亦以“割茶”行為予以回應,有人向筆者道出了深層原因,“第二春的茶賣不上價錢,有的人拿來做紅茶,但大多數人不采,可能賣的價錢還不夠付采茶的工錢哩!”(訪談資料,2021年4月) 當然,減產依然與多數茶農的生產直覺相悖。筆者在調查中也曾偶遇農村婦女偷跑到被收購棄種、已長到一人多高的茶樹叢中摘取茶芽。
正宗性沒有可參照的“傳統”,稀缺性又自然引發關于生產權分配的爭奪,這樣的產銷策略也將兩個茶村的茶農置于激烈的階層競爭之中。大茶企往往是正宗性的發明者和定義者,而小農在作為被動惠及者的同時,亦借助其向上的流動性對市場施加不可忽略的塑造力。在G村,龍頭企業曾與十幾家大中型茶企為了金駿眉的商標使用權對簿公堂,最終金駿眉被法庭裁定為所有茶農皆可使用的通用品種,大茶企卻對此哀鴻遍野[7]。同樣,四家天目湖白茶規模企業在2004年牽頭成立“常州市天目湖白茶專業合作社”,在政府支持下全面實施“統一品牌,統一質量標準,統一生產技術規程”,對中小企業形成壓制;溧陽政府每年舉辦面向茶企的茶博會,當地茶農卻表示,“那些活動都是給大茶企搞的,跟我們小老百姓沒什么關系。”(訪談資料,2021年4月)
盡管小農的顯示度和影響力依然受其市場占有度和政治影響力的限制,但接下來本文將其放在歷史話語下,展現這種模式所指涉的中國鄉村社會經濟特征具有遠超其市場份額的意義。
三、文獻:從歷史語境到當代實踐
18~19 世紀的中國茶葉生產體系基于廣大農村人口,形成足以與英國、荷蘭的工業化殖民地相競爭的高強度生產,長期保持最大茶葉出口國的地位。這種競爭力是由分散化的小作坊式生產和層級化的金融收購系統所維系的。如波爾、福瓊等西方茶葉考察者曾描繪的,在19世紀中葉的武夷山,“紅茶一般種植在山的較矮處,或者村民家的院子”[8];山中分布“不下999座寺觀”,“僧侶在廟宇周圍種植茶樹,每年自己采茶”[9]。家庭和寺廟生產的初制毛茶經由茶販、茶莊、茶客、茶棧等中間商之手,由各國洋行從廣州、上海、福州等地遠航出海;而洋行為了控制產量和質量,將從銀行獲取的貸款通過“銀行-洋行-茶棧-茶莊-茶農”的縱向責任制體系滲透至農村。在這一產銷制度下,茶區的圖景大多相似,多數“茶農將茶葉種植作為第二職業,管理方式也很粗放。”男性在茶葉之外還要負責谷物種植,或到鄉村工廠打零工;大部分女性亦“需同時承擔薪資工作和家庭女性勞動的雙重職責。”[10]如加戴拉所指出的,中國農業的分散化模式始終能在不發生結構性轉變的前提下應對不斷增長的貿易[11]。
這種模式的小農生產對于農村社會的安定、茶葉品質的穩定也有顯著好處。首先,兼業家庭的生計錨固于土地,有助于社會穩定——作為對比,19 世紀末福建等地建立的現代化茶廠大規模招募的茶工多系“客氓”,每到“谷貴茶虧,則相聚剽敚”,給地方治安帶來極大困擾,在地方居民的抵制下紛紛以關停告終[12]。其次,茶葉品質由銷售端控制。19世紀的茶葉商人不再“僅僅是專門從生產區和貿易港口之間往返穿梭的商人”,而“同時監督生產的全過程”,深度參與到茶葉的加工和精制中[13]。彼時的收購體系亦不同于當代語境下“中間商”構筑的剝奪性體系,產量和需求的不對等讓茶農擁有更大選擇權,常有“五六十個買家相互競價。”[10]作為中間商的“茶客”借助外國洋行提供的預付款深入至山區收購,也將世界對茶葉不斷增長的需求和變化的口味傳遞到廣袤的中國腹地,刺激著土地、茶樹和勞動的調配,中國的小農家庭也因這種收購體系的作用,深刻而敏感地卷入全球市場。
這是否構成一種以網絡化的分散小農為基礎、沒有“資本化”的工業化?劉仁威一語中的,中國農民家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能夠在現代世界的“資本積累模式中發揮核心作用”,由此應重新考量“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以自由市場和自由勞動為特征的標準”[10]。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效率優先邏輯是否適用于中國特色的茶葉生產,是值得打上問號的。
當然,茶葉史中的分散化種植和集中化收購并非不存在對小農的隱性剝削,小農深陷于土地,使其在堅強的整體之下顯現出個體的局限性。而在城鄉一體化的當代背景下,小農的能動性無疑對資本集中化和小農生產的辯論提出了新的可能性。20 世紀90年代以來,一系列農業農村扶持政策和市場復興讓農民獲得新的機遇,但政府對農業企業的扶持大多忽視了小農在體制中的弱勢地位。如仝志輝、溫鐵軍批判大部分合作社為“假合作社”,大戶成為“中間商”以低價買進農戶產品、高價賣給部門和資本,形成“大農吃小農”的現象;由此認為只有多層次的綜合合作才能為兼業小農提供更多利益[14]。黃宗智基于對“家庭化過密化生產”的論述,揭示了“小農戶+大商業資本”模式的邏輯,認為龍頭企業和中間商利用農村的廉價輔助勞動力,獲得了高于雇工經營的資本主義規模生產的利潤[15];盡管他贊賞“地票交易所”“農超對接”等方式對農戶利益的提升,但仍承認加工銷售規模化的必要性,并以“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16]為小農的韌性辯護。然而,銷售端的規模化仍可造成農民的“半無產化”——如武廣漢指出的,小農在生產領域的“自主”實際掩蓋了其在流通領域從屬于中間商的“影子雇工”身份,而農民唯有自己掌握產品的流通才能恢復個體業主的身份[17]。
可見,大多數學者對于小規模銷售的可能路徑仍持懷疑或不看好態度。當代小農參與到流通環節所遭遇的困難在于缺乏穩定的銷售網、靈活的談判權;供需對等均衡也是重要前提。盡管小農在10余年來的電子商務發展、鄉村旅游等“消費革命”帶動下獲得日益多元化的渠道[18],但小農在銷售端的能動性依然受到來自政府、農業企業的制度性限制。如筆者在武夷山觀察到的,龍頭企業利用其對“定價權”的壟斷,榨取消費革命帶來的商業利益,將試圖實現階層躍升的中農擠出市場,重回原料供給者境地[19]。顏燕華對安溪鐵觀音產業的研究亦指出,政府將傳統生產方式改造為標準化、規模化的現代生產的邏輯與茶農基于生產技藝、農時安排和社會關系的靈活產銷之間存在根本張力;以“正宗性”名義對壓茶機等“非正宗”生產方式的整治,實則是對小農靈活生產實踐的“剝奪式重塑”[2]。
縱觀歷史至當代的產銷策略,當今主流農業政策的偏頗在于對小農能動性的忽視,以及對于銷售端對小農影響力的忽視。以下將借助田野實證來展現,小農能動性源于產量控制導致的議價權、兼業模式提供的靈活性、人情網絡錨定的穩定銷量和品質。筆者的田野報道人皆具兼業特征——不同于農民在城鎮中從事非農“副業”所構成的“半工半耕”[15],而在更多情況下,城鎮中的“副業”已成為支撐農民家庭收入的“主業”;同時,由農村輔助勞動力生產的農產品也不再是為了補貼家用,而成為兼業者在城市維系人情網絡的“禮物”。這種具有人類學意義的“禮物”不僅有助于開拓客戶群體,更幫助兼業者耕耘城鎮中的“主業”,進而在城市生人社會中立足。為此,茶村小農利用有限的宅基地,建造了兼具居住、生產、銷售等功能的功能混合性住宅,用這種分散化空間支撐其兼業的開展。
四、田野:小農的兼業、人情與廠宅
本文所定義的具有能動性的小農,指的是年產量1000斤左右(不超過2000斤) 的茶葉生產者,有時亦可進入中農之列[19]。在Z村和G村,這類小農是相對廣泛存在的群體。他們既有一定的上升動力和市場競爭力,同時,適中的產量讓他們無需承擔過大的產銷壓力,有充沛精力從事兼業。小農的兼業模式一般有幾種:1) 在鄰近的貿易城鎮開茶店,可兼營土特產;2) 從事與茶葉不相關的行業,如做生意、公務員等;3) 在農村老家經營農家樂、民宿等旅游產業。兼業的類型和程度在男女之間亦存在差異。多數情況下,女性是相對錨固于茶產業中的一方,其兼業更體現于橫跨家庭和農業生產的狀態;男性的兼業則較為靈活,地理活動范圍更廣,產銷茶葉往往成為副業。兼業行為的印證可見于筆者在G村發現的“家店錯位”現象——男性因長期不在農村,將城鎮中經營副業的商店視為主要居所,而農村的老宅則成了經營人情網絡的店,很多妻子抱怨自己在農村老家“就是個幫傭”[7]。
本文的論述主要來自兩位報道人。Z村的周總(約45 歲) 是當地小有名氣的制茶師,幾年前利用宅基地的富余空間開設茶廠,繁忙時要雇傭幾十名采茶工。讓筆者驚訝的是,他的主業并非做茶,而是建筑工程承包商,“我就是喜歡琢磨做茶而已……每年在家待兩個月,做個2000斤茶……”“這么多茶怎么賣?在外開茶店嗎?”“不,大多數都不賣。我在外包工程嘛,每年有大幾百斤茶都是送客戶朋友的……我弟在北京開茶店,也幫我賣一些……剩下的不多,朋友買買就差不多了,很多喝過我的茶的朋友都是回頭客。”(訪談資料,2021年4月) 周總的生產規模讓他幾乎躋身中農行列,而建筑工程生意顯然也沒有好到讓他放棄茶葉生產的地步。兩份營生形成了你中有我、互相依存促進的關系。
G 村的劉總(約38歲) 是村里的青年才俊,曾當選村干部。因其家族為外來移民,分到的茶山少、位置邊緣,對其參與市場競爭造成了限制。但劉家的幾兄弟家庭都具有很強的奮斗動力,如叔叔劉潤發所言,“我是我們村除了Z公司(村龍頭企業) 外最早做茶的幾個人之一……(因為高價) 很多茶農都愿意把茶青賣給我……我便自己背著麻袋,挨家挨戶地去武夷山和福州賣掉……”(訪談資料,2016年4月) 這種躍升動力還體現在,2012 年金駿眉剛走紅時,劉總便號召幾戶親戚新建住宅,新宅不僅具有整齊劃一的“徽派”風格,還擁有民宿、用餐功能,成為村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劉總在2017年考取縣鎮公務員,這隨之成為他的主業,家中的茶葉生產則由年邁的父母經營,每年產量1000~2000 斤。
兩個茶村,一個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平原,一個在交通不便的閩北山區,但兩個村的茶農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依托兼業與人情網絡的產銷模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兼業為茶農帶來了茶葉銷售的穩定客源。如果說農業產業化體系將大多數小農想象為錨固于土地的生產者,不得不依存于大戶或中間商的收購,那么兼業小農則擁有在城鄉之間流動的靈活性以及建立自主茶葉銷售渠道的主動性。不論是在城鎮開土特產店、從事其他行業,還是在農村經營休閑民宿,茶農利用自己的社交逐步積累起可靠的客戶群。如G村王女士,朋友圈賣茶是她的主要經營手段,“我們沒有那些大茶企的金字招牌,只能通過多結交點你們這些城市里的朋友,慢慢把自己的品牌做起來吧!”(訪談資料,2015 年10月) 一位在G村旅行的茶葉愛好者告訴筆者,“現在網上賣茶的品質大多不能相信,三姑鎮的茶葉店也大都是外地人開的,只有直接向茶農買才可靠!”(訪談資料,2015年8月) 相對可靠的朋友客源讓這批兼業小農成為少數跳脫龍頭企業對定價權的控制的幸存者[19]。雖然這些朋友圈客戶是為了比其他渠道更低的價格而選擇小農,但價格仍高于大戶或中間商的收購價,這一利潤空間讓他們在茶青收購、采茶工雇傭市場上獲得更強的自主權。
其次,茶葉作為“禮物”,穩定了兼業所需的人情網絡,同時減小了茶葉銷售的壓力。有人可能認為,朋友圈銷售不足以支持年產1000~2000斤的茶農生計,確實如此。但如周總所言,他每年所產近半數的茶葉是作為禮物送給生意上的客戶和朋友。他自豪地告訴筆者,“我還接過南京某大學的工程項目呢,當時經過朋友介紹在飯局上認識,送了她幾斤茶,后來她一直買我的白茶,又因為機緣巧合給我介紹了那個工程。”(訪談資料,2021 年4月) 茶葉作為禮物,不僅助他開拓了施工生意,還幫他結識了更多喝茶的客人。而劉總作為公務員,需要維系人情網絡的場合更是多不勝數。筆者最初經某地方官員介紹與他見面時,他便對官員半開玩笑地說,“這輛車開山路不好,我現在難得回村,你有需要的話拿去開好了。”(訪談資料,2015年10月) 不難推測,禮物換來的人情償付間接提升了家庭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境遇,實際需要銷售的茶葉數量因此變得更少。
另外,人情網絡對于穩定茶葉品質形成很強的牽制作用,消費端的個體口味往往可直接塑造生產端的個人實踐——這讓人聯想起近代茶葉買辦對生產端的控制,比市場監管或行業標準的控制具有更強的滲透力和持續性。在筆者調研中,常聽到類似“給客戶訂制茶”“看客戶的口味來做”的說法。以小農每年1000斤左右的可銷售量而言,幾十個穩定客戶便足以消化。其客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收到禮物的人或需要送禮的中間人,大多與茶農形成某種互惠關系,是茶農精心維系的社會資源;另一類則是因社交網絡發展出的購茶者,一般購來自飲。這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喝茶習慣牢固、對茶葉的品性較為了解,對品質有很高要求。為了博取客戶的信任,茶農甚至坦率地告知哪種茶是“正山”茶青做的、哪些是“外山”茶,不再對這一茶界“機密”諱莫如深。因此,茶葉的好壞與官方標準中的正宗性并無關聯,而取決于每個客人的口味偏好。正宗性的定義由此不再僅把握在少數茶界精英的手中,而成為一個眾包的、流變的、卻始終維持高水平的品性。
受到近年鄉村振興事業的提振,很多茶村開始迎接形形色色的旅行者。G村位于武夷山國家公園核心區,一直是自然愛好者的熱門目的地;而Z 村所在的溧陽,也擁有“一號公路”等標志性旅游產品。二者都是理想的招待客人之所。筆者在溧陽調研期間居住的民宿,老板原是廚師,旅游興起后辭職將自家房子改造為農家樂,主營住宿、餐飲、旅游包車等服務——當然也不免向住客推銷自家茶葉。這座農家樂成了他維系和拓展人情網絡的基點。更多情況下,茶農的人情網絡為原本偏遠的農村帶來人氣,結交朋友是大多數茶農樂此不疲的活動;他們慷慨地給到訪的客人提供好茶,也讓茶葉生產與人情網絡之間形成了良性循環。
依托于兼業模式和人情網絡的產銷策略,催生了茶農在宅基地改造中的特定空間策略。筆者曾將這類建筑定義為“廠宅”——在茶產業發展驅使之下、扎根于鄉村農宅建設語境之中,將家庭、生產、經營空間融于一體的當代鄉土建筑[20]。廠宅的出現,除了解決茶農在“一戶一宅”限定下茶葉生產設施的短缺,更能適應兼業茶農將客戶帶到家中體驗農家生活、觀看茶葉生產的新需求。如劉總的新宅,除了一層用作茶葉生產外,還容納了10多間客房。他說,“我家的民宿基本沒有對外經營,都是用來招待熟客和朋友的。”(訪談資料,2016年4月) 相比之下,周總的廠宅改造投資較小,一層容納茶葉加工不同工序的設備機械,另配有餐廳、廚房和簡樸的品茶間,二樓由主人自住,三層閣樓則用于解決高峰時期采茶工的臨時住宿。無論如何,他們都在宅基地允許的范圍內,最大化地開發了農村住宅的空間潛能。
對于茶農而言,原本普通的農村住宅營建活動,成了一種兼具功能性和象征性的空間實踐。在Z 村,這種策略限于小規模、功利性的改造,建筑外立面沒有整修,維持了普通農房的特征,只是高效利用了宅基地的空地來實現功能拓展;也沒有提供民宿,因為市區的旅游設施十分便利。而在對名義正宗性更重視的G村,廠宅則被作為茶農參與市場競爭的象征資本。在農村攀比性的“家宅換代”傳統[21]影響下,他們斥巨資建造豪華的廠宅,讓不少中小農深陷債務之中——這類廠宅的建造對于試圖實現階級躍升的茶農具有遠超實用性的意義。但是,兩者都兼具“居”“產”“銷”的功能,為小農的兼業生計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因此,是否擁有小規模、分散化的產銷空間設施,成了小農能否有效利用兼業模式和人情網絡參與茶葉市場競爭的關鍵所在——在G村,政府因保護區規定而限制農民新建住宅,不時有農民在更新廠宅時與巡查隊發生沖突;相比之下,龍頭企業很多年前便擁有了保護區內唯一受允許建造的大型茶廠。這樣的張力,恰體現了空間策略在農村資本積累和階層流動中的重要地位。
五、結論與討論
茶村小農的產銷模式可總結為一個穩定的三角關系:茶農的兼業啟發了人情網絡的建設,拓展可靠的客源,并有效控制了茶葉產量和價格;人情網絡反過來讓兼業模式更有利可圖,并對茶葉品質形成了隱性約束,維系了市場規則;功能混合的廠宅策略最終確保了兼業和人情網絡的可持續。三者構成了茶農能動性地參與市場競爭的穩定閉環,也為當代中國茶葉市場構想了一條縱向一體化之外的、由小農自主開辟的替代路徑。此處應補充的是,本文面向的茶農群體有一定限制。一方面,正山小種和天目湖白茶都是代表性的新型名優茶,既有較高的市場認可度,市場需求和供給相對均衡,又沒有過大的傳統包袱,生產的正當性也未完全把控在少數“代言人”手中。另一方面,本文的報道人無法代表所有小農,而是小農階層中積極向上流動的群體。這部分小農既可能借助相對可靠的生產技術條件和城鄉社會資源實現階層躍遷,也隨時可能因市場萎縮、政策變化和大戶壓制等原因而重回小農身份。
無論如何,具有上升動力的中小農很可能成為未來中國名優茶的生產主力。就像中國茶葉史所證明的,分散化的農村家庭完全可以滿足以不斷增長的城市中產家庭為基礎的消費需求。反觀龍頭企業和大戶:其產業鏈的經營成本造成茶葉過高溢價;茶青收購的不可控因素大,不得不大量采用外地茶青,反而成了茶葉“正宗性”的潛在威脅。對大戶和小農關系的考察或可借鑒西方的名酒市場——盡管法國、英國的酒業皆存在資本深度介入,但大批中小型酒莊依然構成了市場主體,貢獻了很多受消費者追捧的頂級名酒。對茶農而言,兼業提供的多元化收入進一步疏解了產銷壓力,更能與當代鄉村振興事業有機結合,讓鄉村振興的實效真正落實到農民——當然,也要警惕人情網絡的銷售模式對于農村社會及家庭關系的反噬,如夫妻長期分居帶來的關系淡漠、政治“尋租”的制度危險等潛在危機。
與其一味將政策紅利傾斜于見效快、易聯結的大茶企,不如遵循共享、共擔、共榮的概念,給小農以更多機會:一是由政府控制與小農聯盟上下并舉,約束茶產區的產量和質量,進而推進小農共擔的市場管理和商戶誠信體系建設。二是政府搭建的宣傳平臺應更多向小農傾斜,與其舉辦只為宣傳渠道業已充裕的大茶企搭臺的茶葉博覽會,不如支持以中小茶農為主的技能競賽。三是警惕圈層化、金字塔型的正宗性建構和品牌的權屬化。制定規則的頂層少數專家和傳承人“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容易造成更嚴峻的社會分層,而本文展現的眾包式品質控制或更能促進茶葉品牌的健康發展。四是保護小農能動性的首要關切應是保護分散化的生產設施。盡量鼓勵小農更新家宅以獲得生產、銷售的空間設施,鼓勵靈活、集約、環保的空間策略,讓小農的兼業模式得以維持,整個茶葉市場也會具備更可持續的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