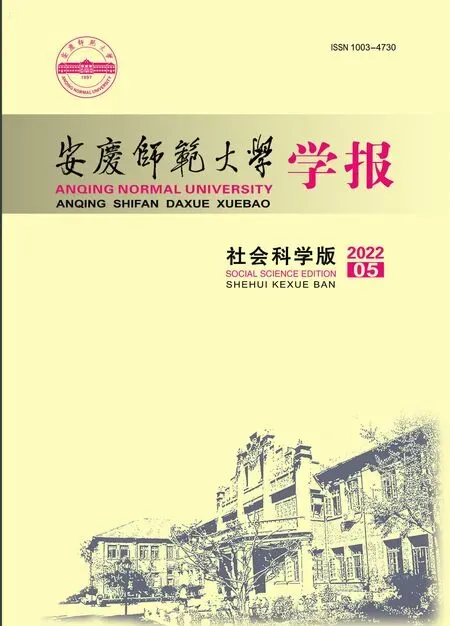論方潛的 “心性之辨” 及其詩歌表達
蔣明恩
(安徽大學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辦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方潛①方潛,原名士超,字魯生,后改名與字。他在《心述舊序》中說明了自己改名、字的原因: “我無用于世,世亦誰用我?更名潛,號碩存,而著《心述》,存《易學體一》,曰《述易》為前編,括此虛靈之心之全體大用也。” 由此可知,方潛改名及字,非一時興起,而是其思想轉變的重要表現。(1805—1868)②方潛生卒年,存在爭議,有生于嘉慶十四年(1809)年說法,卒年有同治八年(1869)及同治十二年(1873)兩種說法。參照方潛之子方敦吉所撰《桐城方文通先生年譜》及其時交流者相關日記資料,可斷定方潛具體生卒時間為:生于嘉慶十年(1805),卒于同治七年(1868),其他說法皆誤。,初名士超,字魯生,一字碩存,當時學人私謚文通先生,安徽桐城人。諸生。晚清理學家。先后主講于山東膠西書院及桐城培文書院,著述甚多,涉獵頗廣。在思想上始宗奉程朱之學,后由陸王而浸淫于佛老。然在與吳廷棟、倭仁、方宗誠等理學名儒的交流過程中,開始自我反思,嚴辨儒釋、心性之關系,轉而又以程朱之學為歸,但仍夾有兼顧程朱陸王的私心。目前對方潛及其學術思想的研究,僅見有方婉麗《晚清吳廷棟與方潛之辨學》[1],該文從宇宙本體之辨、儒釋之辨、心性之辨等三個方面詳細分析了吳、方二人思想的異同,但并未就方潛哲學思想的變化過程及前后差異進行深入探討。本文嘗試圍繞方潛 “心性之辨” 來關照其哲學思想的動態演進過程,并結合其詩歌創作,詳細分析其哲學理路與文學表達之間的內在關系。
一、方潛 “心性之辨” 的歷史語境與內在邏輯
蒙文通先生說: “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術淵源。”[2]以此看待方潛的 “心性之辨” 便甚為合宜。照理說,在程朱一派看來,心與性的關系,朱子已辨得極詳,后儒似乎無需再多作討論,那么何以方潛又將這涉及本體論與工夫論的核心議題再次提及呢?回答這個問題,正需要回歸到方潛 “心性之辨” 的歷史語境中去。方潛早年并不以程朱之學為宗,而是博觀雜取, “于周秦以來子家儒者之言,皆究極其旨”[3],尤其浸淫于陸王佛老之學。后來與倭仁、吳廷棟、方宗誠等理學大儒相交,開始用功于性理之學,并力辟佛老、糾正陸王,否定自己之前所撰的《心述》,又著《性述》以闡明 “心性之辨” 。表面看來,這只是方潛個人的思想轉型,其實方潛思想的這一前后變化,恰恰與時代學術風尚緊密相關,也能由此透視出時代精神的具象。現結合具體的時代學術環境,嘗試從兩個方面對此加以闡釋。
一方面,晚清心學悄然復蘇。明亡以后,士人都將亡國的原因歸咎于陽明之學,以為心學空談誤國。到了清初,統治者以程朱之學為官方正統,于是宗奉程朱者又以正本清源的姿態,對心學進行批判打壓。隨后,漢學大盛,學者們多著意于字句訓詁,對不尚實而流于空談的心學更不以為意。正因如此,心學在清代長期處于沉寂的狀態。然而到了晚清,由于時代局勢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是國內動亂不斷以及西學的涌入,原本相對穩定的學術局面被打破,學術思想開始活躍起來,其中佛老諸子之學開始萌動,心學也于此間逐漸探出頭來。可以說 “在晚清學術的發展變化中,陸王之學的復蘇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學術動向”[4]。心學于晚清的復蘇,也并非偶然,而是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承擔著新的歷史使命。相對于漢學只究心于故紙堆,無法濟世,而宗奉程朱者又多將心思放在身心性命上,無法再邁開一步,心學則顯得更加靈活多變,因而更容易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其中,有部分程朱的宗奉者看到了心學實用的一面,欲借之以完成理學從內圣到外王的轉換,從而達到以行動濟世的訴求。因此他們開始逐漸消除長期以來的門戶之見,并認為陸王心學也是圣學的一支,只不過為走捷徑而體性不全,然終究能殊途同歸。如方潛說: “蓋心學之于理學,正如霸術之于王道,不得不謂功之首、罪之魁耳。”[5]正因如此,晚清理學與心學有頓漸歸一的趨勢。方潛也是在這一學術背景下 “由程朱而陸王,因而出入佛老”[6],以體察心體之全。在方潛看來,陸王雖流于禪,但也因此體心最真,而重點是如何在體認心性的過程中,不浸淫于佛老。所以,方潛對心性的談論雖表面看來是在程朱與陸王之間展開,但落腳點卻在儒釋之辨。方氏以自己出入程朱陸王以及佛老的自身經驗來分析,何以陸王之學流于禪,以及如何在體心的過程中規避佛老之惑,從而正確處理心性關系。當然方潛欲兼顧程朱陸王的意圖,也引得部分理學家的不滿,如吳廷棟便批評道: “此處若合,雖他處不合,不難講求以歸于合;此處不合,即他處盡合,終難彌縫以強其合也”[7]。他認為方潛強行兼顧程朱陸王而破綻百出,正說明二者本根上就有異,不可調和,必須徹底擯棄陸王而歸于程朱,方為正道。
另一方面,儒學道統受到嚴重挑戰。方潛身處之世,社會局勢紛繁復雜,各種思想充斥其間,特別是太平天國戰爭爆發,拜上帝教大肆盛行,對以儒學為主導的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打壓。太平軍所到之處焚孔廟、毀孔子之像,并且還下令 “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8]。因此,曾國藩撰《討粵匪檄》控訴道: “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9]曾國藩為維護道統而搖旗吶喊,立即引起了諸多理學同道們的重視,他們紛紛以昌明學術、接續圣賢之脈為職志,以遏此蕩滅倫常之橫流。方潛的 “心性之辨” 即為此間之一應和,其力辨心性,正是為了正道統。如他說道:
外國之教,更有令人滅天棄祖而奉其所謂天主耶蘇者,傳染各省,污及學校,將來大患不知伊于胡底。我輩欲昌明正學,茍非確守孔孟程朱正脈,而或稍有夾雜,出入自己。正學且講說不明、不備,更何以遏橫流、挽狂瀾、救人心、回世運于方興未艾之邪教哉?于乎[10]!
方潛認為佛老對理學的沖擊,尚不至于動搖理學的根基,而天主教的傳入,則威脅極大。因此亟需捍衛名教以挽救人心,而道統的捍衛,首在正學的純明,故而重新體察理學內部的本體論問題便至關重要。在方氏看來,心性關系是理學的內核,若心性二字不能辨論清楚,則容易混淆其他,從而使學術不明、正學不純,如此怎能遏橫流、挽狂瀾、救人心、回世運呢?只有辨之最精,才能防之最嚴,況且方氏還認為 “心性不明則文章、經濟無一是處”[6]。
由上可知,方潛的 “心性之辨” ,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下展開的,并折射出時代學術發展的趨勢。那么方氏如此不遺余力地論辯心性關系,其思路和方法是怎樣的呢?又呈現出何種效果?現嘗試對此加以分析。
方潛對心性關系的討論,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積極與主流學術人物互動,如倭仁、吳廷棟等。其中吳廷棟更是就此問題與方潛論辯了三年之久,中間通信二十余封, “旬面談者四次”[5]。方潛首撰《心述》,以心為本體, “貫古今、包天地、通有無、該人物”[11],包含理與氣,并認為 “殆三千年孟氏沒,圣教衰,虛靈之命脈托孤于老佛者千五百年。周、程起,圣教復興,宋有朱、明有王,左提右挈以闡此虛靈之全體大用,光明者復七百年”[11]。對此,吳廷棟加以批評,他不認同方潛將陸王之學同歸于圣道,且指出方潛《心述》 “專以虛靈為極,則是明覺之妙也,雖亦以有條不紊為理,而意之所指,則認虛靈為理,是所謂性即理者,仍心之覺體之謂”[7]。在與吳廷棟的辯論中,方潛開始自我反省,并自稱已悟得佛老陸王 “彌近理而大亂真之實”[5],于是否定先前所撰《心述》,而復著《性述》,以闡發 “性即理也” 之旨。他在給吳廷棟的信中說道:
夫心學豈不直截了當,然本體上究隔一膜,只緣以虛靈不昧為極至,而不知此體原有所具之理,必物格知至乃足以應萬事而無窮也,故一流便入佛老。我輩確宗朱子,自是圣學正宗。然必外足以見諸實用而內以通達大原,庶為有體有用,本末一貫之學,否則徒循理學門面,轉恐為心學所藉口耳[12]。
方潛承認程朱之學才是孔孟的正學,而陸王之學則因為一味講求心體,導致認 “性” 不全,忽視了氣質之性的存在,從而不肯在格物窮理上下功夫,最終難免摻入佛老之學。
然而,盡管方潛已明白佛老陸王認心為性,未能窺見圣道之全體大用,但他依然肯定佛老陸王對心的體認。他認為 “禪誠不知性,未嘗不知心”[6],并又在評汪紱《讀〈困知記〉》時說道:
心者,氣之靈,而究不得謂之氣。氣有聚散,而心無生滅,其生滅者,心之念頭也。佛氏認心體最真,故敢自大。陸王亦實有見于此,故曰 “心即理也” ,而掃除程朱 “性即理也” 之說。今 “心” 字認不真,則無以服陸王而折其認心為性之非也[7]。
方氏在這里一方面遵從程朱,以心為氣之靈秀者;另一方面又對佛家 “心無生滅論” 持肯定態度,顯然在邏輯上存在巨大漏洞。因此,吳廷棟對其加以反駁, “‘心無生死’則幾于釋氏輪回之說”[7],并認為方氏依然認心為性,沒有完全脫離佛窟,于理氣心性之關系未能真正辨析清楚。不僅如此,方潛所著《性述》亦受到倭仁的批評,如倭仁批 “《性述》未能闡發經義,而援釋氏,多支離” ;又批 “‘人心惟危’條云:此章人心即耳目口鼻之欲,與釋氏所見人心覺體,雖皆屬氣而精粗不同,釋氏一層似嫌牽涉”[5]。對于倭仁的批評,盡管方潛亦有回應,但也充分反應了二人所見不甚相合。
綜合來說,方潛雖然在吳廷棟、倭仁的勸誡下,選擇放棄佛老陸王之學,轉而歸依程朱,但是他依然不愿將 “心” 置于次等的地位,而是一再強調心之大用,甚至認心為仁體。因而又引得吳廷棟對其加以批評,以釋老牽涉儒學,見道不純,未能真正認得 “心” 。之所以方潛對舊學依然無法做到徹底舍棄,是因為他有著兼顧程朱陸王的意圖。在方潛看來: “考亭門人及后來宗程朱者,大抵知性即理,而未嘗真知自家心體,其病痛亦不小也。”[6]他批評后之宗奉程朱者,不僅不識自家心體,還未必能真正見性, “彼且不知心之為心,安知性之為性哉”[6],而陸王之學雖認心為性,但其體心最真,后世程朱者見地未必有陸王深刻,卻將之全盤否定,未免批之太過。因此,他在給吳廷棟的信中說道: “近儒之宗程朱者,往往墮于一偏,空言性而不知心耳。若程朱以上大賢,雖剖明性善、性之即理,何嘗歧心與性而二之乎?”[6]可以說,方潛的 “心性之辨” ,不只旨在批評陸王認 “心” 為 “性” ,墜入佛窟,還針對那些固守門戶的程朱者,他們只言性不言心,而且一談及 “心” 字便斥之為佛禪邪說,未免因噎廢食了。正因如此,方潛的哲學理路是始終圍繞 “心性之辨” “儒釋之辨” 展開的,而這從其詩歌創作亦能有所窺見。
二、方潛哲學路徑的詩歌表達
方潛《毋不敬齋全書》中含詩歌三卷,名為《永矢集》,此三卷詩雖藝術成就并不算高, “大抵抒忠憤、寄感慨也,間涉逃禪語”[13]。然從方潛所創作的這些詩歌中,能清晰洞見他由出入佛老,到嚴辨儒釋、心性,以及最后又以程朱之學為歸宿的心路歷程。現結合方潛詩歌創作,對其哲學路徑的內在轉變進行探析。
首先,多涉佛老語。方潛早先常慕于心之高妙,以心能主宰一切,因而曾長期沉浸于佛老玄虛之學,并深度研讀佛教《楞嚴經》《楞伽經》《華嚴經》《金剛經》以及道家《老子》《莊子》等典籍,并撰有相關解讀著述。因此縱觀方潛的詩歌,最大的特色之一,便是對佛老典故及意象的運用。如化用《莊子》中典故及句子,有 “大鯤化鳥怒而飛” “蝸國分疆勞苦戰,蛙朋坐井說真歸” “浸羨鴻蒙游是已” “百年曰期不是期,彭祖特聞久亦歸” “自信摶風有健翮,不隨蜩鸴榆枋飛” “風來竅號風去止” “愿君大奮圖南翼,沖破青天勿遽止” “南郭老翁踰七十,顏成子游獨侍立。偶然大塊吹天籟,惹得蝴蝶栩栩集”[13]等。方潛這些詩句所化用的典故及句子,多來自于《逍遙游》《齊物論》中,涵蓋的正是道家思想的精髓處。不僅如此,方氏還將道家甚至道教中的一些代表性意象運用到詩句中,如 “金丹 ” “ 青 牛 ” “ 真 君 ” “ 太 乙 精 ” “ 嶗 山 ” “ 神 仙 ” “ 蓬 萊 ” “清虛” ,等等。除常化用道家語典之外,方潛詩歌對佛禪語涉及更多。如《觀戲有感》二首:
生鐵何難作繡針,磨來全賴用功深。成真證果無他術,伏虎降龍只自心。竅妙已曾窺在昔,蹉跎不覺到于今。慈悲多是藏游戲,直使愚頑淚滿襟。
直使愚頑淚滿襟,但求無間不求深。止能定靜儒傳道,歇即菩提佛語心。證入圓通根種夙,攜來因果悟從今。功夫鍛到塵都凈,生鐵何難作繡針[14]。
由以上兩首詩可見,方潛對佛家之心體觀充分肯定,并認為體悟世間的因果,除功夫之外,更在一菩提之心,一菩提心能貫徹萬事萬物。所謂的功夫磨煉,旨在對心體的體認。又如《次魯存翁送春二律招飲一律韻輪疊成十五首》中,有 “秀而不實苗空碩,果必成因根始歸” “諸凡有相皆非相,畢竟無歸乃大歸” “閑中來往春都盎,顛里菩提佛不歸” “《楞嚴》《楞伽》參已透,禪關永晝閉寒暉” “任天證果猶乾(千)慧,我法同空是了期” “禪關永晝閉寒暉,佛法僧三寶不歸”[13]等句,皆含禪理之精義。另外,還有對佛家典型意象及詞語的化用,如 “羅剎” “諦觀” “火宅” “赤鬼” 等。從以上方潛對佛老典故及用語信手拈來般的化用可知,他對佛老之學有著很深的體悟,由此也便形成了將佛老之學格義儒學的思路,因而在主觀上難免將三者相互混淆。
其次,匯孔孟老佛程朱陸王而為一。在出入佛老的過程中,方潛自以為體悟到心體之真,他認為儒釋道在 “心體” 問題上是統一的,并將佛家《華嚴經》與《中庸》《易經》相比較,認為三者是相通的,皆旨在發揮心量。因而在《心述舊序》中說道:
率性全理,以立此虛靈之心者,則謂之圣;化形守氣,以復此虛靈之心者,則謂之老;超形與氣,以住此虛靈之心者,則謂之佛。是圣也,是老也,是佛也,三者一致,殊途而莫可強同,而其立教也,同導人反此虛靈之一心[11]。
方潛認為儒以性立心、老以氣復心、佛以空住心,三者雖異轍且不能強行相參,但在導人認識心之全體大用上是相通。不僅如此,他的部分詩歌也表達了這一貫通三教的意圖。如《和陶三首》(其三)云: “惟此一心耳,其他無足語。三教大圣人,至今在一處。最勝最珍貴,無來無去住。……此心焉有盡,請君無多慮。”[14]這里方氏認為儒釋道三教之精義皆在一 “心” 字,只要具體此一 “心” ,體認得真,那便能體悟到三教之精髓,具備源源不斷的智慧,以及掃卻一切障礙的能力。又如《寄江龍門》其中一首有句云: “此心即天心,萬變不能屈。憂憫東山圣,慈悲西方佛。即此心忠君,即此心愛物。我心與君心,混同非仿佛。”[14]這首詩更能體現出方潛兼顧儒釋的意圖。他一方面沒有割舍儒家綱常倫理以及忠君愛民的情懷,另一方面又對佛家普度眾生, “即心無行作” 的慈悲給予肯定。可見,他只從 “心” 出發,卻忽視了二者 “心” 的不同。正因如此,方潛以 “心” 勾連三教時的思想又是矛盾的,這種矛盾體現在他將三教進行了內部比較,并認為盡管三教皆以傳心為妙訣,但是卻在境界上有高下之分。他指出佛老只在山腰徘徊,而孔子之道則位于山之巔,站立于斯,可以小天下。因而得出 “莊不如老,老不如佛,佛不如圣。讀《南華》不如讀《中庸》,放之彌六合,卷之藏一心。”[14]的結論。可見,方潛盡管浸淫于佛老,但是始終沒有真正舍棄圣道,他仍心心念念于儒家人倫道德。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晚年在與吳廷棟、倭仁等理學家的交流中,才能夠順利從佛老之中抽身出來,并以 “入虎穴得虎子” 的立場展開了儒釋、心性之辨。
最后,復歸程朱,嚴辨儒釋、心性。方潛早年長期徘徊于儒釋道之間,常因為無法真正找到歸處而陷入迷茫,到了晚年因為吳廷棟等人的勸誡,又花了近五年的時間,才真正決心由佛老而返程朱。而方氏這一思想轉變的全面過程,在其《連夜夢馬命之》一詩有詳細闡述,現將該詩中重要段落呈現如下:
三十乃究程朱語,收斂浮氣學冬烘。中間忽遇沖虛子,為說老聃真猶龍。認活子時調嬰姹,一氣貫注轉長虹。忽然三更紅日出,十萬方晶瑩吾何從?西方圣人名曰佛,三千大界一芥容。呵斥十仙盲修煉,有為法中逞機鋒。乃知常道道非道,真空空不空寂滅。……四十復讀四子書,恍然吾道為大宗。活潑潑地鳶魚妙,誰謂西來單傳嶺過蔥?注解翻教語晦塞,帖括更使義冥濛。陸立大體王良知,程朱大學補格窮。兼包并取二氏長,一張一弛猶天弓。但使我朱其孔揚,何惡間色奪紫紅。五十幸遇真紫陽,愧我知非始發蒙。乃信性即理也四字的圣傳,取之不窮用之不竭[15]。
該詩詳細說明了方潛由程朱而出入佛老,又由佛老而返歸程朱的全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方潛四十歲時并沒有對陸王之學進行否定,也沒有徹底放棄佛老之學,還是抱著以佛老彰程朱的想法,并且認為程朱格物窮理能補陸王的空談。直至其五十歲后,他開始放棄 “心” 的全體大用地位,轉而以程朱 “性即理也” 四字為標的,并且不再主張以儒為主兼包二氏,而是認為道不同不能強謀,陸王尚且不能體認性之真,只認心為理,佛老更不足談,若兼參之則必流弊甚多。因此,他在《始悟性即理也四字寄存之》一詩中云: “龍眠著述枉多年,今日方如夢覺然。好下懸巖踏實地,漫從涸澮待源泉。器形有極藏無極,理具先天孕后天。豈必诐淫是二氏,陸王證道已非全。”[14]并發出感慨: “痛掃從前出老入佛、援儒歸釋之狂談,廿年風魔一朝止。”[14]
回歸程朱后,方潛開始力辨心性并認為 “性窮理窟方通命,學創心宗已逆天”[14]。他指出窮理盡性才能達天至命,如此才是圣道正途,而佛老以心為宗,是與正學悖逆,陸王則魚目混珠于圣道之中,如同兒戲一般。因此,方氏反復強調心與性之區別,如其《得存之書賦以自策》一詩云: “性者天之理,心者天之神。性理心神合,天人無或分。……上言窮物理,下戒慕高深。高深敢徒慕,物理久搜尋”[15]。他認為在天為理,在物為性,人為天地之心,而人之心又是氣之靈秀者,即神。因此,他一方面遵從程朱之格物窮理以盡性,另一方面又以為在體認 “心” 之時,須小心謹慎,不能惑于靈虛之高妙。但是似乎方潛對 “心” 的體認并不完善,他雖放棄了之前慕虛靈高妙之弊,卻又走入另一誤區,因此吳廷棟稱其為 “井中救人”[7]。雖然方潛已堅守 “性即理也” 四字,但對 “心” 的體認與主流程朱者仍有區別,因此他在闡釋 “敬” 字的過程中,便認 “敬” 字不真,導致在功夫論上,出現 “病痛” 。如其在《毋不敬齋銘》一詩中云: “靜未必敬,敬無不靜,是以不曰主靜,而曰持敬。敬之篤即是誠,敬之純即是仁,敬之化即是圣,敬之極功即是神。” 中間 “敬之純即是仁” 一句明顯與其 “心性之辨” 的邏輯相悖。 “敬之純” 當是指盡心的一種狀態,是功夫論的層面,不能與性相對等,因此將敬之純等同于仁,并不準確。朱熹說 “敬,只是此心自作主宰處”[16]“敬則心之貞也”[17],即是此理。此外,方潛嚴辨心性關系,還有一個目的值得重視,即破除部分確守程朱者的門戶之見。方氏批評一些程朱者抱門戶之見,并不能公正地看待陸王之學,殊不知 “心學家洗滌其心,使之極虛極靜未為不是,高景逸六合皆心之說亦非無所見”[5]。他認為陸王之過只在不知性即是理,其闡明心之體量亦頗有可取之處。因此他有詩云: “不屑主奴出入易,敢將規矩方圓違。虛靈《大學》先窮格,活潑《中庸》指躍飛。八字腳跟立千古,余姚仍是借余暉。”[14]他認為陸王雖流于禪,但終歸是圣道之一途,不可矯枉過正,反倒是一些程朱者指責佛老陸王認心為性,自己卻不識心, “反認意為心”①這主要針對的是晚明清初,以劉宗周為主的理學家們,以 “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 ,此與朱子 “意者,心之所發也” 的觀念明顯矛盾。。因此方氏的最終目的是不昧于佛老陸王,不昧于儒,只以圣人為師,從而認全心與性,使得圣道昌明。
綜上可見,方潛的詩歌通過化用佛老中的語典或事典入詩句中,來敘述自己由浸淫佛老到返歸程朱圣道的整個心路歷程,從而闡釋心與性的關系,表達自己以正道統、昌明學術的理想訴求。方潛借助詩歌來闡發自己義理哲思的過程,也由此形成了獨屬于其自身的詩歌特色。只不過方潛作為理學家,因此將 “義理” 看得更為重要,而對文詞則稍有忽視,未能加以修飾,從而導致詩歌遣詞造句稍顯粗糙,未能精細。但從整體上來說,方潛詩文能由真性情而出,亦能突破一些常規②比如《題蕭敬甫秋水讀南華圖》一詩,不拘格套,韻腳跳躍,長短句夾雜其間,而又能一氣貫通,形成了氣直而體曲的獨特面貌。,中間也不乏一些亮眼的詩句,可謂桐城詩歌中一道獨特風景。
三、余 論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儒學道統面臨巨大威脅,方潛、方宗誠、戴鈞衡、朱道文、馬命之等一批桐城理學家,他們隱逸于深山之中,相互切磋道學,除著書立說外,還通過身體力行,企圖挖掘出理學內部新的內涵,以應對社會復雜多樣的局勢。其中他們對佛老陸王之學的重新思考值得關注,而將佛老陸王心性學說滲入到理學之中更值得重視,這也不失為應對晚清理學陷入僵化而無法進一步突破所尋求的一種相對合理的辦法。當然除了對道統補充及維護之外,他們對文統的重建也是不遺余力。如他們重申方苞 “義法” 說,試圖修復已漸離析的文統與道統,并且由此也建立起了相互統一的文道觀,即他們都認為詩文之作 “自然而然,莫知其然”[18],乃人文也,其作用在于闡發道蘊、推明事理、記載忠孝節義、感發人心。因此他們在詩文創作中尤為注重 “神” “理” “氣” 的統一。如方潛對陶淵明及杜甫特別推崇,認為此二人之詩純為 “神” “理” “氣” 之合,而結合方氏的詩歌創作可發現,雖然其詩間有理學家常用的語錄體甚至佛家偈語,但是大部分詩歌從章法布局到語言內容,遵從桐城派 “言有物,言有序” 之旨,明顯氣充神現,內涵義理之精微。可以說,方宗誠、方潛諸人對文道觀念的探索,為之后馬其昶、方守彝、姚永樸、姚永概諸人提供了諸多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也為后期桐城派的發展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方向。也正是這些老輩學者精神的指引,清末民初二姚一馬諸人面對道統的逐漸崩塌,努力從傳統學術中汲取新知以來挽救日益淪亡的民族文化,從而表現出強烈的衛道意識,也給近代歷史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