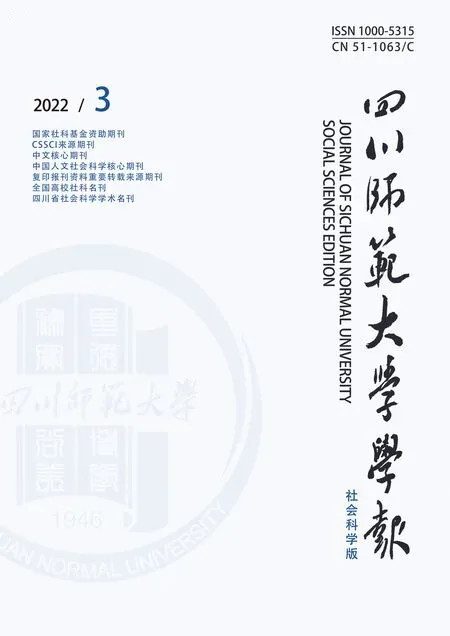從《新史學》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啟超的器與道
劉開軍
1902年是戊戌變法失敗后的第四個年頭。是年初,已進而立之年卻仍被迫“蟄居東國”(1)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文集之11,第19頁。的梁啟超,秉持“對于政府而為其監(jiān)督”、“對于國民而為其向?qū)А钡霓k報理念(2)梁啟超《敬告我同業(yè)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36頁。,在日本橫濱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并以“中國之新民”為筆名于1902年2月8日至11月14日間在《新民叢報》第1、3、11、14、16、20號上連載他的史學作品《新史學》(3)梁啟超最初設(shè)想把《新史學》寫成一部專書:“《新史學》本自為一書,首尾完具。著者胸中頗有結(jié)構(gòu),但限于時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觸即書,先為散篇,其最錄之俟諸異日。”(《〈新史學·論正統(tǒng)〉著者識》,《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35頁。)不過,史學界早已習慣將之視為一篇專文。核諸篇目次序和正文,《飲冰室合集》收錄本較之《新民叢報》初刊本已有一些改動,故本文所引之《新史學》皆以《新民叢報》本為準。。梁啟超素以學術(shù)高產(chǎn)著稱,但這篇約兩萬字的《新史學》卻用時十個月。雖然此一時期梁啟超還撰寫了其他論著,但也可見他在該文的問題選取、思想提煉和理想投射上花費了許多心血。以當時產(chǎn)生的學術(shù)效應(yīng)及其在后世掀起的學術(shù)沖擊為標準,評選清末最有分量的史學專論,《新史學》當居首位。1902年歲末,梁啟超效仿戊戌死友譚嗣同《三十自述》的作法寫下同名自傳,以飽滿的情感書寫了自己的一段心靈史。這一文一傳,頗能傳遞出梁啟超在1902年關(guān)于學術(shù)、政治與天職的思考。120年過去了,雖說時移世易,然梁啟超《新史學》與《三十自述》中所蘊含的器與道,仍值得回顧與珍視。
一 對舊史學的指控
據(jù)梁啟超自述,他4歲習經(jīng)史,12歲之前日治帖括之學,在史學方面熟讀了《史記》、《漢書》、《綱鑒易知錄》等書,一部《史記》竟“能成誦八九”。15歲時,梁啟超舍棄帖括,轉(zhuǎn)向訓詁詞章之學。1890年,18歲的梁啟超得見《瀛寰志略》和上海制造局的譯書,眼界頓開,又從訓詁詞章轉(zhuǎn)入西學,不久即投入康有為門下,康有為“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shù)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使梁啟超受“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又“教以陸王心學,而并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至此,梁啟超的政治與學術(shù)理念為之一新,“決然舍去舊學”。1891年,梁啟超求學于萬木草堂,縱覽“二十四史”、《明儒學案》、《文獻通考》諸書,康有為則為他“講中國數(shù)千年來學術(shù)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這是梁啟超一生治學的轉(zhuǎn)折點,也是由舊入新的分水嶺,“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4)以上引文,見: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6-17頁。。這雖是梁啟超30歲時對十余年前舊事的追憶,但參之史事,所言大體可信。1898年流亡日本后,梁啟超得以直接接觸域外學說,思想再次更新。此后,梁啟超到夏威夷,再輾轉(zhuǎn)上海、香港、印度、澳洲等地,復(fù)還至日本。經(jīng)歷此番輪回,無論是知識、眼界、體認,還是閱歷,30歲的梁啟超都已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同輩人。從這一段學術(shù)成長史來看,作為一位從舊史學陣營中走出來的新史家(5)1902年,梁啟超在學術(shù)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求“新”。是年,除了《新史學》,他還發(fā)表了《新民說》、《新中國未來記》、《新民議》等,創(chuàng)辦了《新民叢報》、《新小說》,自稱“新史氏”,處處凸顯“新”意。,梁啟超無疑具備了從內(nèi)部攻擊舊史學的動機與能力。《新史學》之作,一點也不突然。
《新史學》囊括了史評所應(yīng)具有的幾大核心要素:批評對象是明確的,批評態(tài)度是鮮明的,批評理論是先進的,批評標準是嚴苛的,批評內(nèi)容是言之有物的,批評結(jié)論是鏗鏘有力的。《新史學》隨處可見對舊史家、舊史書與舊史學的指責,表現(xiàn)出誓與舊史決裂之心意。這些表述雖有差異,但音調(diào)是一致的。除了已成為今日史學常識的“四蔽”、“二病”、“三惡果”外,有必要再看幾條梁啟超對舊史學“罪行”的判定:從司馬遷到趙翼,“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shù)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6)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1、42、44-45頁。;舊史家“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guān)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shù)千卷,猶不能于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7)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3號,第61頁。;舊史學不過是“賭博耳,兒戲耳,鬼蜮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而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8)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tǒng)》,《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43頁。;舊史家醉心于褒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9)梁啟超《新史學·論書法》,《新民叢報》1902年第16號,第32頁。。無需羅列更多的證據(jù),梁啟超對舊史書和舊史家的態(tài)度,簡直可以用嗤之以鼻、深惡痛絕來形容。上面這些話殺傷力極強,一則它的確擊中了舊史學的一些要害,對舊史家把歷史書寫視為榮辱和利祿之事進行了犀利且有效的攻擊;二則毫不諱言皇權(quán)對史權(quán)的操控,“后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于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10)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3頁。,這些言論頗能引起時人思想與情感的雙重共鳴。《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篇末,梁啟超特意選錄了屈原《離騷》中的幾句話作為補白:“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愿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11)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8頁。這里的“哀眾芳之蕪穢”,也暗示了梁啟超對舊史學的觀感。就這樣,存在了兩千多年、居于四部之學第二位的舊史學,被鞭打得遍體鱗傷,令人徒生不堪入目之悲。
梁啟超之所以能夠作出上述這些攻勢凌厲的批評,與他掌握了新的理論武器密不可分。首先,他對何謂“史學”有了全新的理解:“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2)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3號,第61頁。“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jié)果也。”(13)梁啟超《新史學·論書法》,《新民叢報》1902年第16號,第32頁。這是清末國人有關(guān)“史學”最權(quán)威的界說,較之梁啟超1897年所述的“史者,鑒往以知來,察彼以知己”(14)梁啟超《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0頁。之說法已有云泥之別。這一概念包含了人群、民族、進化、公理公例、原因、結(jié)果等關(guān)鍵詞,形成了一套新的話語系統(tǒng)。其次,梁啟超辨析了多個與歷史哲學密切相關(guān)的概念,初步構(gòu)建了與舊史學迥異的新史學理論框架。概念既是思想的結(jié)晶,也是論述的邏輯起點。在一套新理論提出之時,概念的辨析至關(guān)重要。這里僅舉梁啟超有關(guān)“循環(huán)”、“進化”與“主觀”、“客觀”這兩對概念的界說,以見其大端。“何謂循環(huán)?其變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fù)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fā)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xiàn)象是也。循環(huán)者,去而復(fù)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至于“主觀”與“客觀”,梁啟超如是說:“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而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觀而略于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15)梁啟超《新史學·史學之界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3號,第57、61頁。這些認識,凝結(jié)著梁啟超個人的治史經(jīng)驗,也吸取了域外史學的理論,是他執(zhí)行史學批評的利器。此外,《新史學》樹立“他者”,援引新術(shù)語,“國民”、“愛國心”、“民族主義”、“民智”、“文明”、“群治”、“國家思想”等新術(shù)語密集出現(xiàn),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術(shù)語效應(yīng)。持此以觀察舊史學,自然會得出與舊史家完全不同的認識。
坦白地說,《新史學》對舊史學的批評并非無懈可擊(16)關(guān)于《新史學》局限性的相關(guān)討論,可參閱:瞿林東《中國史學走向變革的宣言》,《學術(shù)研究》2002年第12期,第20-22頁;路新生《梁啟超“史界革命”再審視——對〈新史學〉線性進化論與“四弊二病”說的批判》,《河北學刊》2013年第5期,第53-61頁;楊艷秋《20世紀初的“新史學”思潮及其意義——兼論梁啟超〈新史學〉的局限性》,《齊魯學刊》2015年第3期,第32-39頁。,甚至可以找到許多例證反駁梁啟超。比如梁啟超將中國史學的派別劃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政書、雜史、傳記、地志、學史、史論、附庸(外史、考據(jù)、注釋)等10種22類,但他批評舊史學時卻主要拿正史作為靶子,采取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策略。他說歐陽修《新五代史》“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這樣評價《新五代史》顯然不夠客觀;他一方面說包括《史記》在內(nèi)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譜,另一方面又說司馬遷是“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17)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5、46頁。,多少有些自相抵牾的意味。他痛陳舊史學陳陳相因,只能一味因襲,但又揀選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為具有創(chuàng)作之才的“六君子”,認為中國史學二千多年間有此“六君子”何嘗不可以傲視世界!《新史學》將“新”與“舊”完全對立起來,割斷了事物之間的本來聯(lián)系,甚至比同年發(fā)表的《新民說》“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18)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4,第5頁。的思想也遜色不少。然而,《新史學》作為一種全新的史學樣態(tài),一時間令讀者有“亂花漸欲迷人眼”之感。1902年7月8日,夜讀《新史學》的孫寶瑄,就產(chǎn)生過這樣的感覺:“觀《新民叢報》,梁卓如有《新史學》篇。其論我國舊史之弊……皆非無所見。而余平心思之,終覺其有未安之處,一時亦無以難之也。”(19)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3頁。一言以蔽之,《新史學》的一些瑕疵,被其澎湃激烈的文辭和新穎熾熱的思想所掩蓋遮蔽了。
二 激昂的“謗書”
1899年,梁啟超已被泰西士人動輒譏諷國人“無愛國之性質(zhì),故其勢渙散,其心耎懦”(20)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65頁。的話刺痛了自尊。更有甚者,日本人也用蔑視的口吻稱中國為“老大帝國”,而流亡海外的梁啟超不能接受這樣的恥辱:“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21)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5,第8頁。彼時,梁啟超只承認國人的愛國之心尚處在“隱而未發(fā)”之階段,故撰《少年中國說》對所謂“老大帝國”之說予以回擊(22)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67頁。。基于他前半生的人生軌跡、政治實踐,加之梁啟超寫作《新史學》時生出“風云入世多,日月擲人急”的歲月感慨,并為“所志所事,百未一就”(23)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5頁。而懊惱悲慚,再結(jié)合他在《新史學》中明確表白的致用觀念,我們有理由認為,《新史學》的撰寫意圖不是單一的,或者說梁啟超憑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學上有一番大作為。《新史學》還是一篇戰(zhàn)斗性的政論文章(24)20世紀90年代,黃敏蘭提出《新史學》“主要是或者首先是一部政治理論著作”,“《新史學》的實質(zhì)是政治性的”(參見:黃敏蘭《梁啟超〈新史學〉的真實意義及歷史學的誤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9、234頁)。這一論斷對于全面認識《新史學》有重要意義,但也有可商榷之處。梁啟超在《新史學》前一年發(fā)表《中國史敘論》,計劃撰寫一部《中國通史》,已經(jīng)開始思考史學理論和通史編撰問題,從政治實踐轉(zhuǎn)向?qū)W術(shù)建設(shè)。《新史學》是史評,也是政論。忽視《新史學》的政治屬性固然不妥,把它主要當作政治理論著作,過度強調(diào)其政治意涵,也有矯枉過正之嫌。,若借用古代史學概念,可稱之為一篇“謗書”。梁啟超口誅筆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內(nèi)的歷代專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舊的政治文化觀念。
其實,早在戊戌變法前,梁啟超的史學與政治觀念中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新史學”的某些思想先機。以“君史”指稱中國舊史,以“民史”指代西方史學的思想,在1897年他發(fā)表的《變法通議·論譯書》中已十分顯豁:“中國之史,長于言事;西國之史,長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謂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鄉(xiāng)教養(yǎng)之所起,謂之民史。”(25)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譯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70頁。《新史學》著力撻伐的正是舊史矚目于“一朝一姓興亡之所由”。類似的表述還見于同年發(fā)表的《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民史之著,盛于西國,而中土幾絕。中土二千年來,若正史,若編年,若載記,若傳記,若紀事本末,若詔令奏議,強半皆君史也。”(26)梁啟超《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續(xù)》,《飲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59-60頁。這些話里都隱藏著對舊政治的極大不滿。親歷戊戌變法的高潮,旋即目睹希望的破滅,梁啟超對于政治革新與民智開化有了更加切膚的感受。《新民叢報》之命名就寄予了梁啟超20世紀初年的政治理想,該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27)《本報告白》,《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廣告,第1頁。。《新史學》之作,恰恰反映了這樣的政治訴求。
需要留心的是,《新史學》評騭舊史學所采用的是政治標準,而不是舊史學本身的學術(shù)價值,如傳統(tǒng)的良史、求真、直書、實錄、曲筆等。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在梁啟超之前,也不乏以政治衡量史學的先例,但主要還是堅持學術(shù)標準。劉知幾對唐以前史書編纂的批判,杜佑對歷代典籍闕載典章經(jīng)制的反思,章學誠對古代史學利病的辨析,莫不如此。即使有一些從政治著眼開展的史學批評,也基本籠罩在帝王意志、本朝立場和朋黨政治的陰影之中,不具有多少積極的意義。唯有《新史學》,在時代劇變之際,明確拒絕史學淪為帝王和朝廷之工具,在觀念上超越了一姓之帝王、一朝之隆替、一人之私利,把史學是否有助于開啟民智和民族主義作為評判的尺度:“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fā)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28)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39頁。既然中國的舊史學不能擔負起這樣的使命,就理應(yīng)遭到拋棄。
1902年的梁啟超,思想務(wù)實。他無暇也無意于從事純粹的學術(shù)理論構(gòu)建,在他看來,“理論而無益于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29)梁啟超《新民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104頁。。《新史學》猛烈批判舊史學,大聲疾呼史界革命,目的之一在于“新民”,因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30)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之4,第1頁。,顯然有開啟民智、激揚民族主義之意。梁啟超的思想邏輯是,中國之進步,仰仗于“新民”,而“新民”則有賴于新史學。由此而論,建設(shè)新史學,是梁啟超“新民”的一個重要手段。他撰寫《新史學》時的心境,也印證了這一點: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yōu)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guī)熘袛?shù)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yǎng)吾所欲,給我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31)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8頁。
這在他1902年發(fā)表的《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中也有回應(yīng)。在撰作該文時,梁啟超期盼恢復(fù)中國舊有的“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zhí)牛耳于全世界之學術(shù)思想界”,為此,梁啟超熱血沸騰,“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焰之何以湓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32)梁啟超《論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2頁。。此中心志,與《新史學》并無二樣。
梁啟超發(fā)展了他1897年所作出的“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擬仿佛,百中掇一二,又不過為一代之主作譜牒”(33)梁啟超《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0頁。的論斷,在《新史學》中指出:“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34)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2頁。,又稱:“不掃君統(tǒng)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35)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tǒng)》,《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36頁。這些話無一不是指向?qū)V凭跖c君權(quán)。為了開啟民智,梁啟超還把矛頭直指清廷,講了不少“大逆不道”的話。他否定清朝稽古右文的成績:“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借。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36)梁啟超《新史學·中國之舊史學》,《新民叢報》1902年第1號,第43-44頁。他質(zhì)疑順治時期清廷的正統(tǒng)地位,說:“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歷,尚存正朔,而視同閏位,何也?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偽也?”梁啟超還譏諷清廷增祀遼、金諸帝王,是“兔死狐悲,惡傷其類”(37)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tǒng)》,《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38、41頁。。在對清初重要歷史人物洪承疇、史可法的評價上,梁啟超也拆穿了清代帝王的伎倆:“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為國史《貳臣傳》之首,史則為《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顧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38)梁啟超《新史學·論書法》,《新民叢報》1902年第16號,第35頁。他甚至為李自成、洪秀全等“敗寇”惋惜,“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贍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jīng)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yè)太祖高皇帝’之徽號”(39)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tǒng)》,《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43頁。。120年前說這些話,是需要膽識的。梁啟超的膽識源于他的愛國之心和骨子里的那份責任,正如其所言:“人茍非有愛國心,則胡不飽食而嬉焉,而何必日以國事與我腦相縈。”(40)梁啟超《自由書》,《飲冰室合集》專集之2,第90頁。為了“新史”與“新民”,梁啟超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以筆為槍的斗士。
同理,梁啟超對舊史家爭論不休的正統(tǒng)、書法和紀年等問題,表現(xiàn)出不解與排斥的情緒。在他看來,正統(tǒng)、書法等愚妄之論,“咬文嚼字,矜愚飾智”(41)梁啟超《新史學·論書法》,《新民叢報》1902年第16號,第36頁。,都有礙于民智的開啟,也不利于民族主義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千余年來,陋儒龂龂于此事,攘臂張目,筆斗舌戰(zhàn),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fù)以煽后人之奴隸根性而已。”(42)梁啟超《新史學·論正統(tǒng)》,《新民叢報》1902年第11號,第35頁。《新史學》中反復(fù)出現(xiàn)“奴隸”這個扎眼的詞語,從一個側(cè)面表達了梁啟超強烈的政治訴求。梁啟超之所以處處挑戰(zhàn)舊史學,譏諷舊政治,為《新史學》涂上一層厚厚的“謗書”色彩,在于他認為舊史學為朝廷服務(wù),早已淪為君王的奴隸,以致泱泱中華停滯于現(xiàn)代文明的門檻之外。
三 “盡國民責任于萬一”
1902年,梁啟超談及國人之天職時說:“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43)梁啟超《敬告留學生諸君》,《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21頁。此語雖是對留學生而言,但實有夫子自道之意。如果說《新史學》反映了梁啟超在史學和政治上的除舊布新,屬于“器”的層面的話,那么《三十自述》言說的則是梁啟超30年來懵懂、掙扎、苦悶、彷徨、奮斗的心靈史,從中可見他一生堅守之“道”。
《三十自述》是一篇匠心獨運的文字。且看梁啟超對于自己的出生是怎樣述說的:“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后一年,普法戰(zhàn)爭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這樣的寫法顯然是特意為之。梁啟超把自己的出生與太平天國的失敗、晚清重臣曾國藩之卒以及普法戰(zhàn)爭等中外大事聯(lián)系在一起,暗含著他不能無視自己生活在一個多事之秋,其個體命運又與國事興衰緊密關(guān)聯(lián)。梁啟超介紹自己的故鄉(xiāng),也不是平鋪直敘或者一般性的地理敘述,而是在歷史的交替中尋找故鄉(xiāng)的位置:“于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群雄之表數(shù)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于歷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zhàn)不勝,君臣殉國,自沉崖山,留悲憤之記念于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xiāng)也。”(44)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5頁。原來,梁啟超出生在這樣一個地方:這里早在秦漢之際便留下英雄的名譽,也在宋元之交寫下悲憤的記憶。梁啟超的《三十自述》開篇就將自身置于這樣一個特殊、特定的時空中,不能說沒有一點“屬辭比事”的意味。這些令人浮想聯(lián)翩的文字,也包含著梁啟超的心理獨白:既然出生于這塊不平凡的土地上,自然要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跡。
《三十自述》把重點放在1890年梁啟超開始追隨康有為至1898年戊戌變法的九年,這正是“中國以一瘠牛,偃然臥群虎之間”(45)梁啟超《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2,第61頁。的時代。此間,梁啟超建學會、開報館、辦學堂,以一套新學與一顆愛國心攪動起清末的知識界與政界。即便是在變法失敗,梁啟超不得不登上日本大島兵艦逃亡后,他也一刻不曾停歇。在“一日百變”的時代里,梁啟超仍在為國奔走呼號。這篇自述最終以這樣的文辭和語氣結(jié)尾:
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shù)可以盡國民責任于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今春為《新民叢報》,冬間復(fù)創(chuàng)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zhì)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廣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后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46)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9頁。
“空言喋喋”非其所愿,“無補時艱”是其心結(jié),“只有慚悚”乃其慨嘆,“力小任重”言其使命,“驚心動魄”見其肝膽,“舍此更無術(shù)”中的“此”指的是其“筆舌生涯”,這也是梁啟超彼時唯一可用之“術(shù)”。而他念茲在茲的,乃是“盡國民責任于萬一”。
1902年,梁啟超激烈批判舊史學,非議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動,但相較而言,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驅(qū)使他發(fā)出這些言論并不斷付諸實踐的,是他心中無法抹去的國民責任,或曰天職。這才是他平生所懷抱的“道”。道在器中,器不離道。1902年之后,梁啟超的大部分時光都在“筆舌生涯”中踽踽獨行。盡管梁啟超手中之器屢變,心中之道卻始終不改,這是梁啟超留給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