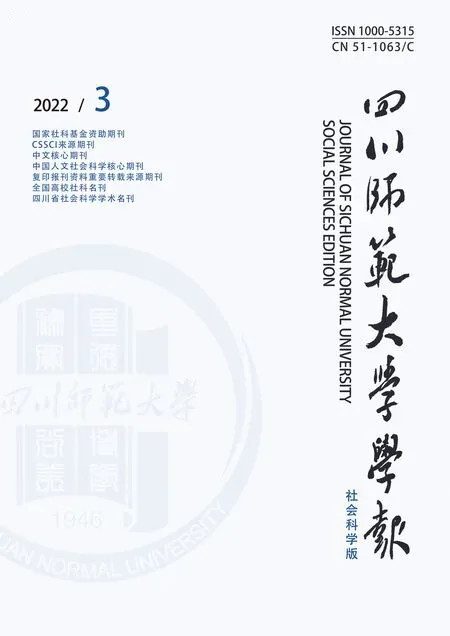《法學引注手冊》示例的若干問題和修改建議
羅銀科
一 我國的引注規范及《法學引注手冊》的意義
我國的學術期刊引注規范,較早地可以追溯到1987年版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7714-87,以下簡稱《著錄規則》)。1997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后簡稱“中國知網”)成立,基于大型數據庫檢索與評價的需求,制定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以下簡稱《數據規范》),并于1999年經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在全國近3500種期刊中試行。這個數據規范的主體部分,實質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參考文獻著錄規范或者引注規范。此后,絕大多數學術期刊(特別是高校學報)采用了這個規范。如果說1987年國家標準《著錄規則》對參考文獻的著錄格式(體例)有“順序編碼制”和“‘著者-出版年’制”兩種,那么在《數據規范》中僅僅以示例的方式采用“順序編碼制”了。由于中國知網在大型網絡化數據庫建設方面的全面性和權威性,《數據規范》又反過來影響到了國家標準的制定,2005年版國家標準《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 7714-2005)的起草人中就有《數據規范》的起草人,所以《著錄規則》與《數據規范》逐漸趨于一致(國標仍然將參考文獻標注方法分為順序編碼和著者-出版年制),還特別規定了“著錄用符號”,實際上這個“著錄用符號”基本上都來自《數據規范》。
《著錄規則》和《數據規范》在21世紀初期基本上一統學術期刊的編排規范和引注規范,這對于我國的期刊引注規范的統一和意識的強化起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不過,它們的弊端也日益顯現。一是過分強調了順序編碼制的著錄體例,造成入編《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的學術期刊參考文獻著錄格式千篇一律。事實上,按照國際標準ISO 690:2010,參考文獻的著錄體例有“姓名和日期體例”(Name and Date System, or Harvard System)、“順序編碼制”(Numeric System)、“注釋”(Running notes)三種。國際上不同學科專業的期刊,采用的格式也不盡相同。比如采用哈佛體例的主要有美國心理學會(APA)、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LA)、英國藥品和保健品監督局(MHRA)、美國科學編輯委員會(CSE)等機構,采用順序編碼制的主要有英國標準(British Standard)、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等,采用注釋體例有《牛津大學法律引用標準》(OSCOLA)、英國標準等,其中有些標準是可以多種體例并存的。特別是《芝加哥手冊》,其著錄體例雖然僅區分為注釋和參考文獻(Notes and Bibliography)、作者-時間引用(Author-Date References)兩種,實際上前一種體例整合了Numeric System和Running notes兩種體例。這些機構或標準的引注體例也有一些細微的區別。二是參考文獻“著錄用符號”與漢語標點符號用法有較大差異,順序編碼制中參考文獻表中出現的符號不符合漢語語法,讓人看不懂,僅僅是方便計算機自動切分;此外,參考文獻類型標志(識)和文獻載體類型標志(識)采用英文字母縮寫形式,讓人看不明白,實際上國際標準都是采用的全稱或明白易知的縮寫(1)如國家標準“聯機網絡”的文獻載體類型標識代碼為“OL”,國際標準用的“online”。詳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GB/T 7714-2015),附錄B《文獻類型和文獻載體標識代碼》,中國標準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頁;ISO 690:2010, Information anddocumentatipn-Guidelines for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and citations to informaiton resources, 12-13, 18-19。。這種參考文獻著錄體例的缺陷逐漸顯現。
正是基于這個原因,2007年,15家高校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聯合發布了《關于修改編排規范的聯合啟事》(2)《關于修改編排規范的聯合啟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第147頁。,出臺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排規范》,提出綜合性期刊“一刊兩制”的引證體例,隨后各家刊物先后制定了各自的“著錄規則”,約定2008年開始實施。這些規范,大多摒棄了著者-出版年制所采用的文后參考文獻表的方式,而較多地使用腳注來著錄參考文獻。雖然這是對當時的《著錄規則》和《數據規范》的一種反撥,但最終結果是百花齊放、異彩紛呈,卻又使得作者無所適從。2015年修訂的國家標準《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起草人增加了人文社科期刊界的同行,在順序編碼制中增加了腳注方式,算得上是一種折衷。2015年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布了新聞出版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范 注釋》(CY/T 121-2015),將注釋的中的出處注(也即引注)分為順序編碼制、注釋-編號制和著者-出版年制三種形式,以新聞出版行業標準的形式規范了參考文獻著錄格式。但事實上,嚴格按照這個行業標準進行引注規范的期刊并不多。整體而言,我國學術期刊界特別是人文社科期刊界缺乏一種相對穩定、統一的引注規范,特別是某一專業行業的規范闕如。而國外,行業學術引注規范卻相對比較成熟,比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國心理學會、美國現代語言學會、《牛津大學法律引用標準》等。
有鑒于此,我國的學界和學術期刊界也在為行業引注規范做出努力。《法學引注手冊》于是應運而生。“統一、細致、合用的引注體例是一個學科成熟的標志,也有助于該學科進一步發展”(3)何海波《〈法學引注手冊〉編寫說明》,法學引注手冊編寫組編《法學引注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頁。為節省版面,后文凡涉及引用此書內容,只在文中括號標明頁碼,一些本應該呈現的《手冊》示例也做了省略處理,只指出了其在《手冊》中的具體位置。該手冊由多家法學期刊、出版社和法律數據庫聯合制定并由中國法學會法學期刊研究會推薦使用,在法學行業學術引注規范中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為我國體例統一、完善的行業引注規范的制定“導夫先路”。
二 《法學引注手冊》示例存在的問題
在研讀《法學引注手冊》(以下簡稱《手冊》)過程中,感到其中示例部分還有一些不盡善盡美的地方。本文為此指出示例中存在的問題或不足之處,期待這部中國最早的行業引注規范能夠在今后的修改中不斷完善,真正成為“中國的引用藍皮書”。需要說明的是,被歸入其中一類問題的示例,并非不能被歸入另一類。但我盡量做到,歸入其中一類后就不再歸入另一類。比如,所有的“不統一”實際上都可以認為是一種“錯誤”,但是我只將其歸入了“不統一”;有一些“錯誤”,實際上就是“不統一”造成的,但我放到了“錯誤”里。
(一)示例與《手冊》引注體例不統一
所謂示例與《手冊》引注體例不統一,是指《手冊》中所使用的示例與其提倡的做法不一致。
1.文獻作者
《手冊》指出:“姓名標示應當完整……特別冗長的姓名,在不引起誤解的情況下,也可以縮寫。”(第24-25頁)但在處理并不冗長的姓名時,《手冊》卻有部分缺失的情況:“Thomas Kellogg”應改為“Thomas E. Kellogg”(第13頁);“Paul Quirk”應改為“Paul J. Quirk”(第16頁)。
《手冊》指出:“作者人數為兩人或者三人的,一一列明。”(第25頁)但下例中出現兩個作者時卻省略后一個的情況,“高鴻鈞等”應改為“高鴻鈞、程漢大”:
高鴻鈞等主編:《英美法原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章“英美判例法”。(第1、35頁)
2.文獻名稱
《手冊》提倡圖書的名稱“以版權頁為準”(第6頁)。下例中,按版權頁信息,書名“美國行政法”應改為“王名揚全集:美國行政法”。同時,因為書名是包含作者姓名的個人文集,可以省略文集作者(第26頁)“王名揚”。
〔1〕 王名揚:《美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頁。(第1頁)
《手冊》規定:“引用文獻信息應當完整,包含被引文獻的基本要素。”(第6頁)副標題屬于基本要素之一,所以不應省略。只規定同一文獻二次出現時可以省略副標題(第14頁);特殊情況,“報紙文章標題包含引題或者副題,內容特別冗長的,可以省略引題或者副題”(第28頁)。可《手冊》的示例卻在不屬于這兩類情況的時候,多次漏掉副標題。漏掉副標題的文獻題名有:《司法改革與行政訴訟制度的完善》(第13頁)、《行政訴訟法修改研究》(第13頁)、《建設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給力》(第13頁)、《理想的〈行政訴訟法〉》(第13頁)、《執行難,難于上青天?》(第27頁)、《國際條約與國內法的關系》(第32頁)、Rechtsgüterschutz und Normgeltung(第72頁)、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第73頁)。
《手冊》有這樣的表述:
美國《統一買賣法》(第49、50頁)
中文版本譯作“美國統一買賣法”(4)《美國統一買賣法》,蕭榕主編:《世界著名法典選編·民法卷》,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頁。,著錄時我們也要把“美國”置于書名號之前嗎?如果依據是該法原名即沒有“美國”,那么照此類推《德國民法典》(第21、50頁)原名也沒有“德國”二字,為何又不置于書名號前了呢?所以,我認為不必使問題復雜化,譯本是什么樣就怎么著錄。著錄文獻的目的是便于讀者查找,而最便于查找的方式就是如實著錄。同樣的情況還有“英國《1996年仲裁法》”(第49頁)(5)《英國1996年仲裁法》,宋連斌、林一飛譯編《國際商事仲裁資料精選》,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390頁。。
《手冊》指出:“為方便中國讀者認知,(英文)刊物名用全稱,不縮寫。”(第60頁)法文沒有相關說明,雜志名直接用了縮寫(第68頁)。《手冊》還指出:“(德文)期刊名原則上使用德國學界慣用的縮寫。”(第72頁)難道只有英文需要方便中國讀者認知,法文和德文就不用了嗎?
“Histoire & mesure”(第71頁)為雜志名,按《手冊》規則(第68頁),應改為斜體。
何海波說:“文獻標題包含副標題的,副標題之前有的用冒號,有的用破折號。個人認為,冒號占地少,版面更干凈,提倡用冒號。”(第101頁)但與《手冊》所提倡的方式,即“所引文獻有副標題的,主標題和副標題之間的符號(冒號、破折號等),一般從原文”(第27頁)相抵牾。
3.非紙質文獻
《手冊》指出:“如果文章已在紙質出版物上發表,原則上應引用紙質出版物上發表的文章。”(第35頁)以下腳注有權威紙質版:
〔3〕 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1989年3月28日。(第8頁腳注)
所以引注方式宜改為:
王漢斌:《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草案)〉的說明——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9年第7號,第309頁。
4.版權頁
《手冊》指出:“圖書的作者、名稱和出版信息,以版權頁為準。”(第6頁)實際上,示例中很多例子并非都是以版權頁為準。如:作者信息“高鴻鈞等主編”(第1、35頁)依據的是圖書封面信息;“本書編寫組”(第24頁)是出現在版權頁版本信息項,卻沒有選擇我認為更合理的、同樣出現在版權頁CIP項的“《‘三個代表’重要論述釋義》編寫組編”;“夏新華、胡旭晟等整理”(第25頁)不是來自版權頁;“第8版”(第29頁)在《奧本海國際法》一書1989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的封面、書名頁和版權頁中均沒有交代,只是出現在“譯者前言”里(6)勞特派特修訂《奧本海國際法》上卷第一分冊,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1971年版,“譯者前言”第1頁。;“哈特穆特·毛雷爾”(第34頁)是根據書名頁或者封面來的,并非來自版權頁“毛雷爾”。實際上,構成圖書引注信息的各要素,很多時候需要綜合封面、書名頁、版權頁、前言、后記等處的信息來判斷,并不是簡單的“以版權頁為準”幾個字可以概括的。
5.文獻真實性
《手冊》“法文引注體例”部分,所有作者名為“Marc Poisson”的示例,可能都是從《人權評論》(LaRevuedesdroitsdel’homme)雜志的《腳注寫作指南》(Consignesderédactionpourlesnotesdebasdepage)照搬過來的(7)參見: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vdh/2747,2021年12月9日訪問。,既未如實說明,也沒有做必要的核實工作。導致的結果就是,《腳注寫作指南》的示例是半假設的,也就是說作者和文章名或者書名,都是假設的,而期刊名或者出版社是真實存在的。這樣的假設如果一以貫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手冊》在這之前或之后的示例都是基于真實存在而例舉,也在開篇引注的基本要求中號召“確保引用文獻的真實性”(第5頁),唯獨此處沒有,那就有悖于統一原則。
6.文獻簡寫
《手冊》講到“統一引注體例是首要目標”(第83頁),但我們看《手冊》自己的引用(8)《手冊》最后一部分“《法學引注手冊》編寫說明”,我把它當成是《手冊》規則的實際操作,實際上也完全應該如此衡量。:
〔3〕 See 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 (20thed.), 2015.電子版可以瀏覽Bluebook的官方網站,https://www.legalbluebook.com/Public/TOC.aspx。(第85頁腳注)
此引用多處違背《手冊》對于英文圖書的規定。此處是《手冊》首次引用此圖書,所以應該呈現完整的引用,而不應該簡寫。書名應改為斜體。“20th”中的“th”是否上標?除了在Word中輸入完“20th”后敲擊空格,“th”會自動上標外,據我所知,很少有學術規范會這么做。網址也僅需像Bluebook書名頁所呈現的網址那樣,只需提供www.legalbluebook.com。所以,按照《手冊》的格式規范,此條文獻正確的引注表述是:
Columbia Law Review Association et al. eds.,TheBluebook:AUniformSystemofCitation(20th ed.),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2015,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legalbluebook.com/.
(二)不恰當的示例
所謂不恰當,是指不應當有某示例或不應當將某示例用于說明某問題,應刪除或替換。
1.文獻作者
下例的“本書編寫組”屬于非“全名”,從檢索的角度,也屬于無效詞匯,同時缺了責任方式,應改為“《‘三個代表’重要論述釋義》編寫組編”:
本書編寫組:《“三個代表”重要論述釋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頁)
下例因為是“由一個龐大的法學編輯委員會負責編寫并由眾多人員參與編輯出版工作的集體作品”(第26頁),作者信息怎么寫都無法涵蓋,所以省略。如果這樣的理由成立,那么《手冊》也可以省略作者信息了,因為它也是“由眾多人員參與編輯出版工作的集體作品”: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頁)
另外,此辭書已有修訂版,應該用新不用舊,所以我推薦的著錄方式是: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輯:《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修訂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
2.文獻名稱
《手冊》將下例作為報紙文章的標題示例,但追溯此標題,可能是“南方新聞網”2010年8月5日的報道時所用題名(9)“南方新聞網”查不到此文,只是很多網站注明轉自“南方新聞網”。。也就是說,此標題可能不是來自報紙。同天《南方周末》有篇內容幾乎一樣的報道,標題是:《最高院很生氣,國土廳很“淡定”——陜西國土廳抗法事件調查》(10)陳鳴《最高院很生氣,國土廳很“淡定”——陜西國土廳抗法事件調查》,《南方周末》2010年8月5日,第A04版。:
《陜西國土廳否決法院判決 施壓最高院要求改判》(第27頁)
下例中,“LaLicorne”并非雜志名稱,而只是系列叢書名(11)官方網站上明確寫著“Collection La Licorne”(獨角獸系列),參見:https://licorne.edel.univ-poitiers.fr/index.php?id=102,2021年12月9日訪問。。而該文所在的那本書也是該系列之一,實際上另有其名,叫做Passion, émotions,pathos(12)參見:https://licorne.edel.univ-poitiers.fr/index.php?id=2047,2021年12月9日訪問。,書中所有文章的內容都圍繞此書名展開。實際上Google Sites在介紹該作者這一作品時是將其歸入“書籍的章節”(13)參見:https://sites.google.com/site/clairebadioumonferran/publications,2021年12月9日訪問。的。所以,此示例并不適用于此。
Claire Badiou-Mouferran, 《 La promotion esthétique du pathétiqu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LaLicorne, n° 43, 1997, p. 75-94.(第68頁)
3.圖書的版本
《手冊》指出:“圖書再版時變更出版社,沒有標明再版的,從版權頁出版信息。”(第29頁)隨后舉例:
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王名揚:《美國行政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此處第1個示例宜改為:
王名揚:《美國行政法》(第2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這樣才更符合“再版時”的預設。
4.網址
《手冊》指出:“微信公眾號早期文章的鏈接過長的,可以不標注鏈接。”(第38頁)并在腳注中舉了一個例子。《法學引注手冊(2019年版)》發布到網上(14)法學期刊研究會《法學引注手冊(2019年版)》,“法律出版社”新浪微博,2019年11月7日發布,2021年12月9日訪問,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36112734027798。后文提及時簡稱“2019年版”,不再標注。后,有人曾對這個問題發表過不同意見,認為還是要標注鏈接,并指出使用手機獲取就不會產生鏈接過長的問題(15)在下二十三《關于〈法學引注手冊(2019)〉的若干商榷意見》,“廣元路讀書紀”微信公眾號,2019年11月11日發布,2021年12月9日訪問,https://mp.weixin.qq.com/s/2RnzRewjTJgUJRSSMQc9Cw。。但《手冊》并未采納,理由是不需要提供鏈接“憑文章名稱完全可以在網絡上檢索到”,并且“學術文章幾乎都是在電腦上寫作”而不是用手機(16)何海波《關于〈法學引注手冊〉商榷意見的答復》,“中國法律評論”微信公眾號,2019年11月16日發布,2021年12月9日訪問,https://mp.weixin.qq.com/s/CnFuJSKuOOSTyv7nhWbUWQ。。我認為“憑文章名稱完全可以在網絡上檢索到”這樣的理由如果成立,著錄規范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懷疑了。我們提供獲取和訪問路徑的目的之一,是便于讀者查閱,此目的也是《手冊》反復提及的。《手冊》可能也并未對此好心提議者的解決方法作必要的復核。如果這樣做了,就會發現,并不是因為是“早期文章”才會鏈接過長,也不是因為查閱的方式是手機才變得很短的。
下例文章所在頁面明確提供帶DOI號的獲取網址時,選擇它是最穩定的方式,所以網址宜改為“https://doi.org/10.4000/histoiremesure.3543”:
Béatrice Joyeux-Prunel, 《L’histoire de l’art et le quantitatif》, Histoire & mesure, vol. XXIII, n° 2, 2008, [Enligne: http://histoiremesure.revues.org/index3543.html]. Consulté le 17 mars 2010.(第71頁)
5.已經發表的或紙質版本
《手冊》指出:“如果會議論文已經發表,原則上應當引用發表后的版本。是否已經發表,引用者有義務進行檢索。”(第41頁)就在這句話之前的會議論文示例:
姜明安:《新時代中國行政法學的轉型與使命》,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2018年年會論文。
就是已經發表的會議論文,《手冊》在使用時“有義務進行檢索”,但顯然沒有。正確的著錄方式是:
姜明安:《新時代中國行政法學的轉型與使命》,《財經法學》2019年第1期。
同樣,示例: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第49頁)
宜改為: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10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人民日報》2014年10月29日,第1、3版。
還有,示例:
信春鷹(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2013年12月23日。(第49頁)
我認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應該像此示例這樣在參考文獻中標明報告人身份。此說明有紙質版,那么著錄方式是否宜改為:
信春鷹:《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2013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14年第6號。
6.權威文獻
《手冊》提倡:“同一內容有多種文獻來源的,應當選擇權威文獻。”(第6頁)示例:
〔5〕 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第1頁)
該文注釋明確寫著“本文原稿約7萬字,全文載《比較法研究》(季刊)1993年第1期,1993年2月出刊”(17)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第83頁。,題名為《程序比較論》。用當下的學術規范考量,此文已屬于一稿多發。即便是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種情況是被允許的,我也提倡選取全文作為示例。同樣,示例:
民國大學訴工商總長劉揆一案,判決文書見熊元翰等編:《京師地方審判廳法曹會判牘匯編》(第一集民事·下編),京師地方審判廳1914年版,第232-236頁,轉引自北京記憶網站,http://www.bjmem.com.cn/literatureView?id=15120380。(第15頁)
從出版信息無法判斷“京師地方審判廳”就是出版者,我們只能推定封面上的“京師地方審判廳法曹會”為出版者。因為是推定,所以按照慣例,需要加上方括號。“北京記憶網站”作為此文獻的獲取和訪問路徑并不合適。因為該文獻獲取難度不大,國家圖書館和讀秀都有掃描電子版,如果真要給讀者指明來源,我也提倡用此類較大且穩定的數據庫(18)截至2021年12月9日,訪問北京記憶網站相關內容的網址是:https://www.bjmem.com.cn/#/literatureView/pdf?articleType=bjwh&recordNo=008483&tt=t1&column3=,已經不同于示例中的網址。。《手冊》也提倡“引用比較權威網站上的文獻”(第36頁)。即便是同意此獲取方式,獲取和訪問路徑也是有問題的(且不說是否有效),網址換行不應該自動生成連字符(literature與View之間的“-”),因為這樣網址就會失效。頁碼有誤,即便是使用頁面下方的后期添加的頁碼,也應該是“235-239”,而不是“232-236”,何況我不主張如此標注。我認為正確的著錄方式是:
民國大學訴工商總長劉揆一案,判決文書見熊元翰等編:《京師地方審判廳法曹會判牘匯編》(第一集民事·下編),[京師地方審判廳法曹會]1914年版,“物權”第1-5頁。
7.同一文獻多次出現
《手冊》在談到同一文獻略寫文獻時用了這個示例:
〔16〕 應松年、馬懷德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揚教授九十華誕賀壽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37〕 同前注〔16〕,應松年、馬懷德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的源流》,第330頁。(第14頁)
該文集中每篇文章都有獨立作者,所以具體引用時應該采用析出文獻的著錄方式:
劉莘、李大鵬:《論行業協會調解——制度潛能與現狀分析》,載應松年、馬懷德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揚教授九十華誕賀壽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頁。
即便是省略寫法,也該是:
劉莘、李大鵬:《論行業協會調解》,第330頁。
同一文獻多次出現,如果是外文,《手冊》舉了這個示例:
〔56〕 R.v.Panel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exparteDatafin plc [1987] QB 815.
〔57〕 Ibid.(第14頁)
有些學術規范,如最新版的《芝加哥格式手冊》(TheChicagoManualofStyle)已不鼓勵使用這種著錄方式(19)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7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14.34.。因為這樣做并不比縮短引文節省空間,也容易引起混淆。
8.轉引
下例腳注中的數據為轉引,但并未說明:
〔10〕 參見劉飛:《德國公法權利救濟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頁。如果只看普通行政法院審理的一審案件數量,則只有20萬件左右。(第55頁腳注)
同樣為轉引的示例還有:
Ralf Dreier/Stanley Paulson(Hrsg.), Rechtsphilosophie Studienausgabe, 2. Aufl. 2003, S. 181.(第73頁)
該書第181頁實際是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932年版《法哲學》(Rechtsphilosophie)的內容,所以引注方式要么標明轉引,否則就應該是: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1932, S. 181.
(三)《手冊》中出現的若干明顯錯誤
《手冊》指出:“未經查核的文獻不得引用。”(第5頁)而以下錯誤的產生,多半就因為未經查核。
1.文獻作者
張尚鷟:《試論我國的行政訴訟制度和行政訴訟法》,載《中國法學》1989年第1期;(第7-8頁腳注)
同樣,因為“對于那些總是使用名字首字母的作者,就不應該提供全名”(2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4.74.,所以下例作者“Adam C. Pritchard”依原文應改為“A.C. Pritchard”:
Stephen J. Choi & Adam C. Pritchard,BehavioralEconomicsandtheSEC,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6: 1, p. 1-73(2003).(第60頁)
還有,下例作者名“Marc Chevallier”應改為“Jacques Chevallier”:
Marc Chevallier,L’étatdedroit, Montchrestien, 4eéd., Paris, 2003, p. 16-29.(第68頁)
2.文獻名稱
下例名稱中間依原文應將“,”改為空格:
《執行難,難于上青天?》(第27頁)
同樣,下例“Strafrecht”和“Allgemeiner”之間宜加標點: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4. Aufl. 2006, § 15 Rn. 19.(第73頁)
下例書名部分缺失,應改為“『民法總則·物權法(民法Ⅰ)(法律學體系 コンメンタール篇2)』”:
我妻栄=有泉亨『民法総則物権法(法律學體系·コンメンタール篇)』(日本評論社,1950年)31頁。(第78頁)
下例“‘其他題名信息’有誤。因為原書封面寫著‘第一分冊’,內文才以‘卷’排序,為免混淆,所以‘第1卷’應改為‘第1分冊’”(21)羅銀科《國標〈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示例的編校失誤及其歸因》,《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28頁。:
① 陳登原.國史舊聞: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0:29.(第95頁腳注)
3.引文內容
《手冊》規范第6條的示例中有一大段引文(第9頁),這段引文的第6行“在省院會議上”之前,“李道民院長”之后都有省略,但未使用省略號;第8行的“是”應改為“要”;該引文也未標明具體引用頁碼。
《手冊》指出:“凡是涉及……統計數據等,需要交代出處而又不便在正文中敘明的,應當予以注明。”(第5頁)因此,第85頁第2段中“最初的26頁”、“最初的15頁”似乎也應該加注釋,便于讀者查證,如“《芝加哥大學法學引注手冊》……迅速擴展到今天的86頁”(第85頁)經查證就與OSCOLA“到2012年第4版時也達到了61頁”(第85-86頁)的統計標準不一致。前者的頁數是從目錄頁開始統計(22)無論是2018年版,還是2019年版均是如此,參見:https://lawreview.uchicago.edu/sites/lawreview.uchicago.edu/files/v86%20Maroonbook.pdf;https://lawreview.uchicago.edu/sites/lawreview.uchicago.edu/files/v87%20Maroonbook.pdf。2021年12月9日訪問。,而后者指的是整個PDF的總頁數,包括封面和空白頁(23)參見:https://www.law.ox.ac.uk/sites/files/oxlaw/oscola_4th_edn_hart_2012.pdf,2021年12月9日訪問。。
4.出版地
下例出版地有誤,版權頁并沒有交代出版地。即便是推測,也背離了史實。民國時商務印書館更多時候在上海。事實證明了,出版社所在城市并不是像《手冊》所說的“廣為知悉”(第100頁):
③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140.(第95頁腳注)
5.出版者
下例出版者有誤,“Yale University Press”應改為“Bobbs-Merrill Company”;該書中提到“反多數難題”的頁碼范圍是16-23頁,而不是此處的“16-28”,所以頁碼可能也有誤:
〔5〕 Alexander M. Bickel,TheLeastDangerousBranch:TheSupremeCourtattheBarof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6-28.(第10頁腳注)
6.報紙版次
下例版次有誤,“5”應改為“A45”:
① 宋華琳.行政基本法要在審慎中前行[N].法制晚報,2012-4-16(5).(第95頁腳注)
7.全稱
下例依該網站,“法國行政法院”應改為“法國最高行政法院”:
參見法國行政法院網站,http://english.conseil-etat.fr/Judging,2016年12月18日訪問。(第2頁,第55頁腳注)
同樣,下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應改為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
陸紅霞訴南通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政府信息公開答復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5年第11期。(第3、54頁)
還有下例,舉辦單位縮寫和缺失,“清華大學社科學院”應改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應加上“清華大學數據科學研究院”;“‘邁向數據法學研討會’會議”應改為“‘邁向數據法學’研討會會議”:
習超:《證券監管有偏私嗎?》,清華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社科學院“邁向數據法學研討會”會議論文,2017年12月23日于北京。(第41頁)
8.其他
有些示例的錯誤,如按照前文錯誤的分類方式,可以歸入很多項。為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和割裂,我就將這些示例歸為“其他”。
下例主副標題之間的冒號依原文應改為破折號;年份有誤,“2015”應改為“2013”:
李松鋒:《游走在上帝與凱撒之間: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關系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0頁。(第42頁)
下例China:TheBalanceSheet一書并無此文章(24)參見:https://www.piie.com/bookstore/china-balance-sheet-what-world-needs-know-now-about-emerging-superpower,2021年12月9日訪問。,中文譯本《賬簿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中亦無此文章(25)該書只在“致謝”中提到了“Jamie Horsley”,參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賬簿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中國發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頁。;或者說該文章并不在此書中(26)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羅列的出版物中分享了該文。從提供的信息看,此文屬于名為“The Balance Sheet in 2007 and Beyond”會議的會議論文,可能并未以紙質形式出版。參見:https://law.yale.edu/china-center/publications/recent-staff-publications,2021年12月9日訪問。。如果要保留該書作為示例,那么按照《手冊》的規定:“相關外文文獻有中文譯本的,原則上引用中文譯本,或者在引用外文文獻時提示中文譯本。”(第57頁)我們可以使用中文譯本;如果要保留文章,那么此示例只能以會議論文的方式呈現。
下例還存在如下錯誤:圖書缺失副標題,應加上“: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Jamie Horsley”應改為“Jamie P. Horsley”,“C. F. Bergsten, B. Gill, N. R. Lardy & D. Mitchell”應改為“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R. Lardy & Derek Mitchell”;出版者“Public Affairs Press”應改為“PublicAffairs”:
Jamie Horsley,RuleofLawinChina:IncrementalProgress, in C. F. Bergsten, B. Gill, N. R. Lardy & D. Mitchell eds.,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6.(第62頁)
下例版次信息缺失,應在書名后加上“(2nd ed.)”;出版者名稱拼寫有誤且不全,應改為“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William Sharp McKechnie,MagnaCarta:ACommentaryontheGreatCharterofKingJohn, Maclehose, 1914, also see Online Library of Liberty, http://oll.libertyfund.org/titles/mckechnie-magna-carta-a-commentary.(第67-68頁)
如果出于某種必須,要引用第1版,那么示例應改為:
William Sharp McKechnie,MagnaCarta:ACommentaryontheGreatCharterofKingJohn,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5, also see Project Gutenberg,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65363/65363-h/65363-h.htm#Page_1.
下例作者名有誤,“Mouferran”應改為“Monferran”;題名有誤,“XVIIe”應改為“XVIIe”:
Claire Badiou-Mouferran, 《La promotion esthétique du pathétiqu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LaLicorne, n° 43, 1997, p. 75-94.(第68頁)
下例作者名部分缺失,“Stanley Paulson”應改為“Stanley L. Paulson”;題名有誤,正確的題名應為“Gustav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 Studienausgabe”。
Ralf Dreier/Stanley Paulson(Hrsg.), Rechtsphilosophie Studienausgabe, 2. Aufl. 2003, S. 181.(第73頁)
下例出版社和出版年可能有誤,“有斐閣,1971年”應改為“巖波書店,1968年”:
我妻栄『新訂擔保物権法(民法講義Ⅲ)』(有斐閣,1971年)50頁。(第77頁)
(四)沒有清楚交代示例來源
沒有清楚交代示例的來源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示例本身基本要素不全;另一種是示例來自別的規范文本,卻未作必要的說明。
1.基本要素不全
《手冊》提倡引用出處相當簡短的常見古籍經典中的語句可以在正文中使用夾注,并舉例:
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這也就是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皋陶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第10頁)
我試著去查了兩個版本。“畏”原文本作“威”(27)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39頁。。阮元校勘記云:“古本作畏。”(28)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第140頁。又查唐代學者陸德明《經典釋文》,字作“畏”,云:“徐音威,馬本作威。”(29)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頁。而“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被斷為偽《古文尚書》。作為工具書示例的《手冊》,應回避使用這樣的示例。
《手冊》還提倡:“引用常用基本典籍,不涉及內容爭議的,可以省略出版信息。”(第33頁)并舉一例:
《論語·述而篇》(第33頁)
《〈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一文中就談及關于《論語》的許多爭議內容,包括《述而》(30)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9-17頁。。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否為常見古籍經典,確切地標明引用來源是必須的。
2.未交代示例來源
下例出版信息有誤。據報道,“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江杏溪來到蘇州,決定自立門戶,創立‘文學山房’書店”(31)王道《蘇州:96歲“網紅”書叟守望122歲“文學山房”》,“新華每日電訊”網,2021年5月14日發布,2021年12月9日訪問,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1-05/14/c_139944994.htm。。所以此處的“光緒三年(1877年)蘇州文學山房”應該是有誤的。查江杏溪輯《江氏聚珍板叢書》收錄有《古今偽書考》,所用版本即姚際恒光緒三年木刻單行本(32)江杏溪輯《江氏聚珍板叢書:古今偽書考》,文學山房1924年版,第48頁。,但并不能連起來敘述為“光緒三年(1877年)蘇州文學山房活字本”。實際上文學山房木活字本印刷時間為1924年(33)《江氏文學山房聚珍叢書序》,江杏溪輯《江氏聚珍板叢書》,文學山房1924年版,第2頁。。另,江杏溪輯《江氏聚珍板叢書》總目記錄“《古今偽書考》一卷”,所以此處的“卷三”作何解,不得而知。這一示例大概轉錄自《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之類學術刊物的引文注釋規范(34)《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關于引文注釋的規定(試行)》,《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第201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關于引文注釋的規定(試行)》,《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86頁。,因為連具體引用頁碼(第34頁)和表述方式都一樣,但并未做必要的核實:
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卷三,光緒三年(1877年)蘇州文學山房活字本。(第32頁)
同樣,下例則照搬《歷史研究》都已經摒棄的示例(35)《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歷史研究〉關于文獻引證標注方式的規定》中有此示例(第183頁),2004年第6期《關于〈歷史研究〉文獻引證標注方式的規定》中不再有此示例。:
《元典章》卷一九《戶部五·田宅·家財》,“過房子與庶子分家財”條。(第35頁)
下例來自《學術出版規范 注釋》(36)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提出《學術出版規范 注釋:CY/T 121-2015》,中國書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雷經天:《關于邊區司法工作檢查情形》(1943年9月3日),陜西省檔案館藏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檔案,檔案號15/149。(第42頁)
以下3個示例Bluebook也有(37)Columbia Law Review Association et al., eds., 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 20th ed.(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 2015), 159, 163, Quick Reference.,且先于《手冊》:
Charles A. Reich,TheNewProperty, 73 Yale Law Journal 733, 737-738(1964).(第3、58頁)
Barbara Ward,ProgressforaSmallPla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 1979, p. 89, 90.(第58頁)
Andrew Rosenthal,WhiteHouseTutorsKremlininHowaPresidencyWorks, New York Times, 15 June 1990, at A1.(第61頁)
“法文引注體例”部分,所有作者名為“Marc Poisson”的示例,可能都是從《人權評論》雜志的《腳注寫作指南》照搬過來的,但并未如實說明。
下例與蒙彼利埃大學圖書館《參考書目和注釋:法國文學和人文科學規范》(Rédactiondesbibliographiesetdesnotes:Normesfran?aisespourleslettresetscienceshumaines)中的示例一樣(38)參見:https://www.biu-montpellier.fr/sites/default/files/2019-06/Normes_francaises_LSHS.pdf,2021年12月9日訪問。,且蒙彼利埃大學圖書館在時間上先于《手冊》(即便是2019年版)。所以大膽推測,此示例可能是從蒙彼利埃圖書館照搬來的:
Claire Badiou-Mouferran, 《La promotion esthétique du pathétiqu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LaLicorne, n° 43, 1997, p. 75-94.(第68頁)
使用別的學術規范已經用過的示例本身并沒有問題,但最好予以說明。這是對別人勞動成果的尊重,也能體現編者的學術修養。使用并不等于照搬,必要的核實工作一定要去做,“不得引用未經查核的文獻”(第93頁)不只是說說而已。
(五)《手冊》缺失對一些示例情況的必要解釋
下例主副標題之間(問號之后)省略了原文的冒號。這種做法雖然遵循了英文文獻的通行慣例,如與《芝加哥格式手冊》的做法一致(39)“主標題以問號或感嘆號結尾時,任何副標題前都不要用冒號”。見: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4.96.,但卻與《手冊》中文引注體例所提倡的“從原文”的做法不一致。可是《手冊》并未在相應部分(如“英文引注體例”部分)做必要的解釋說明:
Thomas Kellogg, “CourageousExplorers”?EducationLitigationandJudicialInnovationinChina, 20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141(2007).(第13頁)
《手冊》規定非第1版圖書的版本信息括注于圖書名稱后。“外文圖書的中譯本一般無須標明原書版次;確有必要時,可以在書名后用括號標明原書‘第×版’”(第29頁)。如果是確有必要標明原書版次的外文圖書的非第1版中譯本,又該如何著錄呢?另外,關于英文圖書非第1版的示例,《手冊》也是缺失的。
三 對《手冊》的一些修改建議
真心希望中國能有一本拿得出手的學術規范手冊,所以除了指出硬傷,還希望《手冊》在以下這些方面予以注意。
(一)合理引入交叉引用
《手冊》將“示例”居首的做法多少有些借鑒Bluebook,既然都學到這一步了,為什么不把交叉引用的做法也學過來?這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工具書的“合用”。實際上,前置的絕大多數示例在后文中都有出現,交叉引用這樣的編排方式才更“方便查閱和使用”(40)何海波《打造中國的引注藍皮書——〈法學引注手冊〉編后記》,《法制日報》2020年6月23日,第9版。。
我認為應該做交叉引用的地方還有:斜體v(第15頁)應與規范第83條第1項(第64頁)交叉引用;《政法論壇》(第8、95頁)應與規范第39條第3項(第31頁)交叉引用;規范第47條談到“紙質出版物曾經刊載但查閱不到的,可以轉引互聯網上的文獻”(第35頁)時,可與第15條(第15頁)交叉引用;規范第48條第1項的示例(第36頁)可與第48條第2項“已經標明了上傳日期,可以不重復標明”(第37頁)交叉引用。
(二)必要的版本更新
與2019年版相比,一些示例因為有了更新的版本,《手冊》做了必要的更新,如《美國行政法》從2007年版改為2016年版(第1頁)。但還有一些示例,使用的不是最新版本,本著用新不用舊的基本原則(41)用新不用舊,除非有特殊用途,如《手冊》規范第44條中的示例之一(第33頁)。雖然陳敏《行政法總論》一書已經出到第10版(2019年),但此處是想用初版時沒有出版機構這一事實。,應該予以替換。如:TheLeastDangerousBranch:TheSupremeCourtattheBarofPolitics(第10頁腳注)1986年出了第2版;《英國2006年公司法》(第21頁)2017年出了第3版;《法律的道德性》(第22頁)商務印書館于2009、2011和2017分別出過“珍藏本”、“分科本”和“紀念版”,雖然基本上看不出變化(頁碼都一樣),但最好還是用較新版本;《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第26頁)2006年出了修訂版;《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第34頁)已出2017年版。
還有一些示例的新版本,與《手冊》同年或比《手冊》晚出版,可以在下一次更新中予以替換。如:《侵權責任法》(第1頁)可更新到第5版;《德國民法典》(第21頁)可更新到第5版;《民法》(第30頁)可更新到第8版;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第73頁)可更新到第5版。
當然,此處我是將引用原則套用到示例原則,多少有些牽強。
(三)建議性示例的呈現標準要統一
如《手冊》示例:
〔37〕 同前注〔16〕,應松年、馬懷德主編:《當代中國行政法的源流》,第330頁。(第14頁)
2019年版的這個示例省略了“主編”這一責任方式,此處又加上了。這樣做雖不違背“可以省略”的“建議性措詞”,但難免給人隨意之感。我認為建議性措詞可以有,但是所提供的示例,應本著“簡潔”的基本要求做減法。而不是一會兒省略,一會兒又保留。
再如下例:
〔13〕 參見何海波:《法學論文寫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尤其是第239頁。(第97頁腳注)
2019年版此處沒有“參見”,2020年版又加上“參見”。《手冊》對于“參見”用法的解釋是:“概括引用的,使用‘參見’引領;在引用意圖清楚的情況下,也可以省略‘參見’。”(第11頁)此處加上“參見”應該怎么解讀,除非有個交叉引用,否則確實難以把握。
(四)不重復使用同一示例或同一個人的示例
《手冊》的編排,尤其是示例的使用,我認為應該本著“寸土寸金”的態度來考量。既要選擇具有典型性的示例,又要力圖展現法學這個學科的全貌和最新進展。大量示例的重復使用,或者使用同一個人的多個示例,無疑有礙于這一目標的實現。
《手冊》開篇的“示例”部分,除開第5個示例,其余都在后文中出現過至少一次。或者可以這樣理解,此部分的示例本來就決定取材于后文,只是有一個疏忽了。除此之外,《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使用了3次(第26、28、35頁);《古今偽書考》使用了2次(第32、34頁);美國《統一買賣法》使用了2次(第49、50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使用了2次(第50頁);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使用了2次(第50頁);《德國民法典》使用了2次(第21、50頁)。
“王名揚”出現過6次(42)見《法學引注手冊》第1、8、14、29、40頁。,除開第29頁的兩次是為了說明同一問題,屬于必要重復,其余都可以替換。“何海波”出現了6次(43)見《法學引注手冊》第2、13、22、32、59頁。,并且還有一處只用了文章標題的示例(第60頁),作者也是何海波。
我認為《手冊》可以在下一次更新中定下這樣一個原則:每個示例只用一次,每個人的示例只用一個。
四 結語
《手冊》立志“打造中國的引用藍皮書”的抱負是值得稱贊的,從該書封面選用了與Bluebook一模一樣的藍色就足以看出。《中國法學》雜志社總編輯、中國法學會法學期刊研究會會長張新寶說,“與現有的引注體例相比,這份手冊具有明顯優點”:“第一,內容翔實”,“第二,考慮周全”,“第三,查閱方便”,“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中文法學領域一個比較完善的引注體例”(44)張新寶《法學引注手冊·前言》,《法學引注手冊》,第1-2頁。。《法學引注手冊》的出現,不但解決了法學領域作者面對眾多引注格式無所適從的問題,而且必將推動其他學科、專業的出版行業制定各自統一、規范的引注體例。我在這里近乎吹毛求疵地指出《手冊》示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目的是希望《手冊》日臻完善,成為學術期刊或出版行業的引注體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