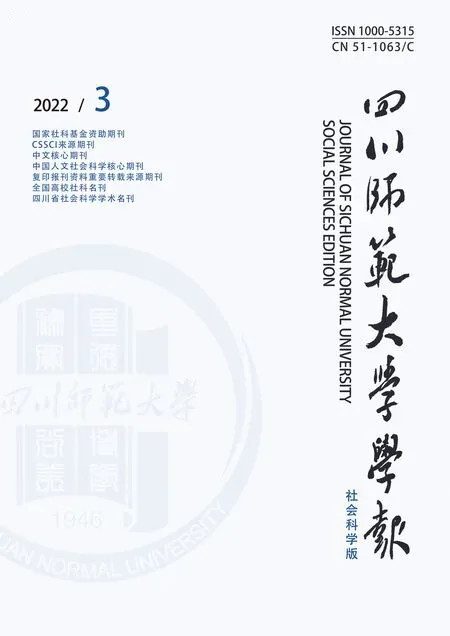歷史的鏡像:梁啟超“新史學”的多元想象
楊志遠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鏡中所投射出的影像,能否真實地反映自我?我想這個答案有著許多可能。追求歷史真實性的諸多史家,對此各有其定義與理論陳述,進而衍生出各種不同的歷史解釋。小自個人,大到群體、民族或國家,不同背景的人群,于鏡中所見,總不免為人的各類偏見與成見所遮蔽,然而如何才能獲取真實的歷史實景呢?似乎唯有回到歷史的語境中,透過自塑與他塑的行為,在其歷史場域中,去理解歷史之為歷史的可能性。歷史非靜態的歷史,而是變動不居的時間歷程,討論在此時間之流中的人、事、物,不再是呆板僵化的史料記錄,而是一種被形塑建構的精神特質。作為被譽為中國現代“新史學”開山祖之一的梁啟超,其所代表的“新史學”觀念,這個被歷史形塑的符號,在歷經120年的歲月洗禮后,究竟至今仍具有何種特質?確實是值得深思的大哉問!不同的闡釋者對于梁啟超“新史學”的主張,均無法避免種種主觀因素及由此所產生的誤讀與曲解。然而,在不斷被歷史化的過程中,梁啟超的史學或明或顯地呈現出歷史時間中的不同意義。如何將被遮蔽的歷史予以重新思考,將習以為常的論點翻轉,成為吾人理解梁啟超史學觀念的重要課題(1)有關梁啟超戊戌變法后東渡日本的學思經歷,可參考: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2003年第32期,第191-236頁;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書店2003年版。。
一 “梁啟超式”的輸入及其意義
何謂“梁啟超式的輸入”?梁啟超自述說:“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于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版,專集之34,第71頁。梁氏的“學問饑荒”促使形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學派,然而此一“新學派”為無根底的拼湊之學,企圖用一種“嫁接”的方式,在傳統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化品種。這種文化上的嫁接實驗,從其后歷史的發展來觀察,顯然是水土不服的,但是否代表著失敗呢?按梁氏自己的說法,“梁啟超式”的輸入乃“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的輸入方式。若按時人用語,則可稱之為“拿來主義”,充滿實用功利性格。但人離不開時間與空間下的環境制約,若不考慮梁氏所處的晚清民初時空背景,則其所謂的“輸入”將淪為對西方學理的仿效,但梁氏的輸入不是簡單的復制,而是某種具“創造性”的改造(3)宋學勤《“梁啟超式的輸入”的真意義——兼論中西史學文化的接軌與融合》,《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 年第2期,第114-122頁;楊念群《梁啟超〈過渡時代論〉與當代“過渡期歷史觀”的構造》,《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第48-58頁。。梁啟超在日本期間,透過其獨特的“和文漢讀法”(4)“和文漢讀法”為梁啟超與羅普編寫的日語閱讀速成指南,主要為借日本訓讀之法學習與翻譯日語書籍,然而此法對日文虛詞的處理方式有誤解原意之嫌,并非可靠的學習日文文法書。可參閱:夏曉虹《梁啟超與和文漢讀法》,載夏曉虹《文章與性情——閱讀梁啟超》,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237頁。,閱讀日籍文獻,故其對史學的吸收,主要來自日本明治時期盛行的文明史觀及其影響(5)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2003年第32期,第191-236頁。。以《新史學》為例,過往論者有質疑其主要襲自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或《史學通論》),但梁啟超不是照原書翻譯,而是在章節安排與內容選擇上經歷了一番重整,然后以之與本國歷史文化之例相互對應,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解釋。李孝遷則認為梁氏《新史學》的來源,除主要受浮田和民影響外,亦受福澤諭吉《文明概略論》,田口卯吉《支那開化小史》、《日本開化小史》,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等的影響,故其《新史學》具有多元特征,無論《中國史緒論》還是《新史學》均無固定藍本,乃博采眾家后形成自己的論點(6)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91頁。。又如關于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杜維運認為梁氏綜合中西史學的能力卓越,“他不是稗販,不是籠統的將西方史學方法移植過來,朗、瑟二氏之說,有時正面的加以采用了,而細節處則加潤色;有時反轉過來采用,而更見奇縱;有時約略采用,而另建完密的系統,以致絲毫不著采摭的痕跡,渾若天成,圓而多神”(7)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0年版,第323頁。。杜維運“渾若天成,圓而多神”八字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姑且不論梁氏的新史學論述是否已達傳統史學“圓神”的境界,但其所產生的后續學術效應如漣漪般的擴散卻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黃進興也有類似杜維運的看法:“梁氏文史涵養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學問水乳交融,絲毫未見窒礙之處。……換言之,《中國歷史研究法》之普受矚目,歷久未衰,便是能將西方史學與國史知識溶鑄一爐,這項成就迄今仍罕與倫比。”(8)黃進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7年新第6期,第268頁。黃氏對梁啟超的新史學評價很高,贊其能將中西史學溶鑄于一爐,成就罕有匹敵者。然而,事實是梁啟超雖然能快速掌握西方史學的風潮,并非常有效地將其論點與國史知識綰合,但對于西方學理的深層結構與分析之認識則闕如。這并非梁氏個人的問題。整個近代中國輸入西方學理時,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分處不同歷史時期的近代學者,在面向西方時,有著不同的背景與機遇。
梁啟超于1902年以《新史學》為篇名,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一系列對于傳統史學的批判及對國史未來期許之觀點,確實點燃了傳統史學的革命火種,掀起所謂的“史界革命”。梁氏說:“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9)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7頁。梁氏此處提倡“史界革命”,有其前提,即在晚清“救亡”心理下,企圖透過史學倡議民族主義,凝聚人民愛國之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于旦夕。故而有學者認為,梁氏《新史學》之揭橥,其真實意義在作為一部政治理論的宣示檄文,而非僅僅是對西方史學的闡述與發揚(10)黃敏蘭《梁啟超〈新史學〉的真實意義及歷史學的誤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9-235頁。。梁啟超以《新史學》標榜和傳統史學的決裂,其所謂的“新”,丘為君認為有兩種啟示:一是轉型時代意識,二是新中國的未來性格(11)丘為君《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1895-1925》,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59頁。。這兩種啟示形塑出梁啟超富含“造新去舊”的學術性格。梁氏《少年中國說》曾說:“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12)梁啟超《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5,第11頁。無疑,在梁氏的觀念中,“少年中國”與“老大中國”隱含著“新/舊”對立的兩極化觀點,在時間軸上新將取替舊,此一時間的進程,充滿了對未來的想象(13)梅家玲《發現少年,想象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象》,《漢學研究》2001年第19卷第1期,第249-276頁。。時間仿佛被擠壓在歷史的瞬間,所有的一切作為有著時間的急迫性,出現一種近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焦慮感”。此種“焦慮感”主要來自對西方線性化歷史時間觀所帶來的對現代性認同的焦慮,要擺脫此種焦慮的糾纏,往往賦予“未來”極大的希望,采一種超越性作為,以調適轉型期的陣痛(14)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未來”》,《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9期,第64-71頁。。在“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思想主導下,“亡國滅種”的憂心,始終縈繞在梁氏及其同時代青年的心頭,故以新思維掃除一切舊思維,成為梁啟超及其前后輩學人思考的重心所在。《新史學》的諸多觀念,也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展開的。
二 “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梁啟超的專文于1902年首次集結時,題名為《飲冰室文集》。梁氏取《莊子·人間世》“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之意,將其書齋命名為飲冰室,自署為飲冰室主人,此乃梁氏流亡日本心情的寫照。其后出版的梁氏文集,亦多冠以“飲冰室”之名(15)夏曉虹《十年一劍?——〈飲冰室合集〉集外文序》,載夏曉虹《文章與性情——閱讀梁啟超》,第272頁。。文集的名稱正反映出梁氏內心對國族危亡的心理焦慮感,時刻縈繞心頭的是揮之不去的救國渴望。在此心態背景下對西學的追求,自然充滿著焦躁不安的情緒,故梁啟超《新史學》諸多觀念的倡議,被壓縮在極短時間與局促空間里,瞬間爆發開來。梁氏早年拜于康有為門下,始開啟梁氏學問的新天地。梁啟超曾說:“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16)梁啟超《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6頁。不難想象梁啟超在會見康有為后,所產生的思想上的震撼效應。于是,梁啟超盡棄舊學,轉而追隨康氏,服膺“三世說”、“大同之義”諸理,主張變法維新。其后,變法失敗,梁啟超東渡日本,對西學展開大量的學習,致使其思想再度產生巨大變化。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回顧其學思的變化說:“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然其保持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于胸中,隨感情而發。……啟超自三十以后,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17)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4,第63頁。事實上,梁氏30歲左右(約1903年)仍在日本,雖受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禮,但其學思尚未完全脫離其師康有為公羊三世進化的經今文學觀點。康有為將傳統三世說與西方進化論相結合,用以作為其解釋歷史的觀念,深深影響梁啟超此時的論點(18)相關研究,可參閱:鄭師渠《梁啟超與今文經學》,《中州學刊》1994年第4期,第100-106頁;宋學勤《梁啟超〈新史學〉的當代解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3頁。張朋園認為,此時的梁啟超對進化論仍是半信半疑,東渡日本后,隨知識開展與對進化論的理解,逐步擺脫其師康有為的影響,進而形成自己的論述體系。參見:張朋園《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現代化——嚴復、梁啟超的進化觀》,載《食貨月刊》編輯委員會編《陶希圣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202頁。。1899年,梁氏在《論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說:“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據亂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據亂,漸進而為升平,又漸進而為太平。今勝于古,后勝于今,此西人打撈烏盈、士啤生氏等所倡進化之說也。……故漢世治春秋學者,以三世之義,為《春秋》全書之關鍵。誠哉其為關鍵也。因三世之遞進,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時而異,日日變易焉。”(19)梁啟超《論支那宗教改革》,《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58頁。很明顯,梁氏此時仍受經今文三世進化的影響,但已接受打撈烏盈(達爾文)、士啤生(斯賓塞)等人的進化觀念。
梁啟超將傳統公羊變易史觀與西方進化論相結合,成為其改革舊史的新主張。梁氏對進化論的接受,是漸進式的。早在1896年,梁啟超便收到嚴復尚未出版之《天演論》的譯稿,而逐漸向進化論靠攏。他曾說:“今而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20)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6-107頁。此言充滿對嚴氏的孺慕之情,但此刻其學思尚在整合之際,對嚴氏“天演”之說仍有微詞與辯駁(21)梁啟超《與嚴幼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8頁。梁啟超在信中以“三世之義”反駁嚴氏“中國歷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等觀點。參見:王文仁《進化思想與梁啟超的“史界革命”》,《東吳中文學報》2010年第19期,第309-328頁。,尚未全盤接受進化論的觀念。
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表達自己對國史的看法,其言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其明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榮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為過。”(22)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頁。梁氏此言基本上已接受西方史家對史學的看法與定義,諸如對史實的追求、尋求歷史的因果關系等觀念。梁啟超認為,史學不該等同于朝代興亡與一家一姓之譜牒,史家關注的歷史對象,必須是國民之全體,以此律繩舊史,則中國無史矣(23)有關中國近代史學在西方史學的標準下是否能稱之為史的問題,曾引發中國“有史”、“無史”的爭論。劉開軍指出,梁啟超、鄧實、羅大維等人主張中國“無史”,而陳黻宸、馬敘倫、盛俊等則反駁其說,主張中國有史,雙方針鋒相對,形成論戰,馬敘倫并作《中國無史辨》正告我同胞“中國固有史”。參見:劉開軍《晚清史學批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169頁。!至今對《新史學》的研究而言,往往忽略梁氏所受傳統史學的影響,尤其是接受康有為經今文學的影響,從公羊三世變易觀一變而為西方進化史觀的歷程。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中指出:“于今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24)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1頁。梁氏于此開宗明義,將傳統乙部之學上綱至“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的高道德倫理標準,正體現其對史學所賦予的社會責任的認識,仍具有傳統“史學致用”的現實意義。在這一點上,梁氏的史學與其師康有為相類似。無論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還是梁啟超的《新史學》,均帶有某種現實的目的性,并藉由學術著作傳播其政治理念。梁氏評論其師說:“然啟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慊于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同。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25)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34,第5頁。此一“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的做法,有著傳統變法思想“托古改制”的理念。然而,在詭譎多變的晚清時局中,面對排山倒海的歐風美雨,傳統學術顯然無法再用過去的思維應對。但如何變?用何種方法變?梁啟超選擇了一條與乃師及過往傳統不同的道路前行。他采用自身熟悉及擁有傲人歷史紀錄的史學領域作為改變的起點,但由于初接受西方史學的觀點,尚無法精確掌握西方史學的發展脈絡與內涵,在快速攫取其史學梗概后,便勇于對傳統史學提出“四蔽”、“二病”、“三惡果”的沉痛控訴與嚴厲批判:“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26)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3頁。梁啟超此處重申了《中國史敘論》中的論點,強化了對舊史批判的力度。舊史對朝代興亡的更替敘述,已無法滿足梁氏對新史的追求,二十四史不再是國史的驕傲,一變而為令人怯步的“相斫書”,充滿負面的意涵。其實,梁氏對舊史的抨擊,有得之于日本與西方近代史學界對國史的批評,亦有其本身與同儕間共同的觀感(27)李孝遷認為,梁啟超將國史喻之為譜牒說,西人早已有之,而日人中村正直在石村貞一《國史略》的序文中已提到“國史者,譜牒行狀之集大成者也”;而康有為編纂的《日本書目志》列有此書,此文序為漢文書寫,故梁氏所說的譜牒之說,極有可能在萬木草堂期間,間接或直接得自康有為處。參見:李孝遷《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頁。。姑且不論梁氏“革命式”的史學宣言,是否對舊史的打擊取得成效,其破害之功不容小覷,但如何重整支離破碎的傳統史學,卻又是一段漫長的旅程(28)路新生《梁啟超“史界革命”再審視:對〈新史學〉線性進化論與“四弊二病”說的批判》,《河北學刊》2013年第5期,第53-61頁。。汪榮祖稱梁氏的《新史學》,借用西方史學學理,以改革傳統史學,故國史在其眼中遂成鏡中之妖!《新史學》是一篇激情的革命宣言,而非理性之改良宣言,且多誤謬。有論者視梁啟超《新史學》具啟蒙與實證精神,為科學史學的提倡者。此說非也。梁氏無意使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其所主張之“史界革命”與“民族主義史學”,其精神乃“浪漫”而非“啟蒙”(29)汪榮祖《論梁啟超史學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24頁。。
梁氏在《新史學·史學之界說》中替歷史下定義: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氏此處的定義,主要從進化論的視角來看待歷史的發展過程,其言曰:“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循環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于此類者,謂之歷史學。”(30)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7頁。在梁氏看來,歷史敘述的現象有二種:一為自然界的四時變化與天體周而復始運行的循環觀,一為歷史界人類社會的進化觀。他舉孟子為例說:“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茍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循環,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31)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8頁。梁氏認為孟子的“一治一亂”循環說,非歷史學的觀點,將歷史螺旋狀發展的史觀,誤以為是一封閉的圓形循環,此說足以迷惑百千年來的傳統史家,導致史學的真相不明。不過,梁氏此時仍未放棄傳統“三世說”的學理,故仍采三世進化說法來補充對孟子以降循環歷史觀的否定。梁氏這種線性進化歷史觀,具有時間上的不可僭越性,每個歷史階段均無法跳躍,必須按時間的進程前行,故梁氏認為唯有明進化之理,中國史學才能擺脫舊史的影響,達到所謂“新史學”的理想(32)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0-108頁。。梁氏這種對歷史抱持某種進步觀點的看法,顯然對進化觀念持有樂觀主義的想象(33)王中江《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進化主義在中國》,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76頁。。
三 “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梁啟超的學生張蔭麟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將梁氏的一生學思歷程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為戊戌變法以前,是為通經致用之時期;第二期至辛亥革命成功時,是為介紹西方思想之時期;第三期為歐游之前,是為純粹政論家時期;第四期為歐游歸后以至病歿,是為專力治史之時期(34)張蔭麟(素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學衡》1929年第67期,第1-8頁。。張氏的四期分法說,簡要說明了梁啟超一生“流質易變”的特質,其多變、善變的學術個性,促使他的學說充滿許多不確定性,也許正是這種不確定性,造成其學思的多元想象。梁氏曾說自己保守與進取兩種心態常隨感情游移,故所論往往前后相矛盾,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故有論者認為,若無其“善變”、“能悔”之品格,也就沒有梁啟超這位獨特的歷史人物(35)劉東《未竟的后期:〈歐游心影錄〉之后的梁啟超》,《中國學術》2011年第30輯,第74頁。劉東認為,梁啟超思想有一突出的風貌,即強調調適與調和。因此,海內外研究梁氏思想者,如張灝、黃宗智、黃克武等學者,都抓住梁氏思想上企圖尋求平衡的特點,來凸顯其力圖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革新、啟蒙與轉化、儒家與自由、中學與西學間的種種調和。。梁氏的這種品格,在學術上的表現,則是對其所論的反復性。1918至1919年,梁啟超赴歐考察,經由留歐學人及與西方知識界的密切接觸,梁氏敏銳地觀察到歐戰后所遺留下的諸多問題。他認為,即使在西方也無一所謂完整的文化體,更多的是彼此的差異與矛盾。中西文化各有長短,如何調適中西方文明以創新文明,當是吾人面向西方之際的大哉問!回國后,梁啟超重新思考早年學術的論點,對其史學觀點作出許多修正。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對于進化原理與尋求公理公例深信不疑。此時,梁氏所謂的“公理公例”,主要是依循進化原理以求歷史中的“因果律”。1922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開始質疑此種因果律,認為無法用純自然科學的因果律求得:“宇宙之因果律,往往為復的而非單的,為曲的而非直的,為隔的伏的而非連的顯的,故得其真也甚難。……嚴格論之,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于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3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第110-111頁。梁氏此時已將自然與歷史科學分開對待,但仍未放棄用因果律來解釋歷史。至1923年,梁啟超又開始修訂他對因果律的看法。他說:“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系’一語。我近來細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復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37)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40,第2-3頁。梁啟超此時接受新康德主義(Neukantianismus)的觀點,開始強調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李凱爾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論點(38)H.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李超杰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7頁。,強調自由意志下的心力作用才是歷史的本質,并引佛家的“互緣”來解釋歷史的諸多現象(39)梁啟超《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40,第4頁。。采用佛學的觀點,作為其論證的資源,成為梁氏后期學術的特色。但也不可否認,這種學術思考缺乏對某種學術的全盤理解與認知,故其論述常出現漏洞而無法自圓其說。黃克武論述梁啟超后期史學思想的變化時說:“固然受到叢翁特和立卡兒特以后所提出的‘文化’概念,以及歐洲唯心哲學之影響,但是他卻以源于佛學的‘心能’‘共業’‘業種’‘業果’‘熏感’‘識閾’‘互緣’等概念,‘業力周遍不滅’的原則,以及儒家‘既濟未濟’‘立人達人’的想法,說明科學現象與人文現象,亦即自然系與文化系的區別,以及歷史文化現象的獨特性,和人類自由意志、主體抉擇在歷史演變過程中的關鍵地位。”(40)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02頁。黃氏的說法是,梁啟超如何面對西方的學理,如吸收的問題等,梁氏所實行的方式是以傳統儒、佛思想去思考其所感興趣的理論,故在自歐返國后的20世紀20年代國內外局勢丕變之際,梁啟超特別突出史學為文化的觀念,重新理解“何謂史學”的大哉問!然而,不爭的事實是梁氏此時大量采用佛教本體論的觀點來分析西方學理,其所獲取的結論自然不夠深化,對西方哲理的吸收也不完整。表面上,梁啟超擷取了新康德主義對于自然與文化的區分,但與此主張的理論基礎卻不相同(41)黃克武《梁啟超與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139-141頁。。
梁啟超對“方法論”情有獨鐘,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社會日復雜,應治之學日多,學者斷不能如清儒之專研古典。而固有之遺產,又不可蔑棄,則將來必有一派學者焉,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將舊學分科整治,擷其粹,存其真,續清儒未竟之緒,而益加己精嚴,使后之學者既節省精力,而亦不墜其先業。世界人之治‘中華國學’者,亦得有藉焉。”(42)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34,第80頁。梁氏謂用科學的方法整理舊學的方式,主要是運用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去改造中國乾嘉考據學的方法。他說:“夫吾固屢言之矣,清儒之治學,純用歸納法,純用科學精神。”(4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34,第45頁。梁氏對于清代考據學派所實行的“歸納法”,頗為贊譽,認為深具西方近代科學的精神,并做出值得稱贊的學術成績。姑且不論清代學者是否與西方近代的學術運用了相同的科學方法,顯然在此時梁啟超的觀察是認同的。因此,如果要明史學之義,不明史法,則無法更深入地理解歷史,故梁氏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作。胡適在民國學術史上被視為“新派”,不見得對梁啟超的學術論點均表同意,但他卻稱許此書為“任公最佳作”(44)《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2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版,1922年2月4日條。。杜維運認為,《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作,為近代中國史學界的一件大事(45)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冊,第315頁。。此書的撰述過程,依杜維運的考證,可能始于梁啟超游歐之際(46)杜維運據李宗侗的記載,認為梁啟超在歐洲時請了很多留法學生給他講述各門學問,恐怕《史學方法論》亦是其中之一。參見:《前言》,《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人文科學部“史學”》,臺北正中書局1966年版,第1頁。。《中國歷史研究法》發表之際,體例與內容均屬草創,但與西方和日本當時流行的史學方法書籍相類似。杜維運認為,梁氏此文中富啟發的突破性見解,大半來自法國史家朗格諾瓦與瑟諾博司所著的《史學原論》以及另一位德國史家伯倫漢《史學方法論》的影響(47)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冊,第317頁。。梁啟超從何獲取其史學的觀點,除杜師的推測外,似乎還有其他的管道。李孝遷認為,可能是來自日本的譯本,如坪井九馬三的《史學研究法》以及伯倫漢改寫《史學方法論》為供一般民眾閱讀的《歷史學導論》(Einleitung)日譯版(48)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345頁。。
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已與他1902年所寫的《新史學》有很大的變化。1902年,梁啟超提出史界革命說、史之公理公例說和統在國非在君說,并據此三原則,基本上是以進化的原理原則來定義歷史。然而,隨時間推移與對西學的漸深理解,梁氏開始修正其早先對于史學的論述,重視史料搜集與鑒別之法,他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學可言。”(4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第36頁。梁氏接受近代西方史學對于“史料”的定義,認為史學的成立與否,與史料的有無和真確與否直接關聯。關于“史料”的取得,梁氏擴大了過往歷史遺存的部分,而加大不同價值的史料搜集。他舉例說:在尋常百姓家故紙堆中往往可以得極珍貴之史料,如將同仁堂、王麻子等數家自開店迄今之賬簿,用科學方法研究整理,則百年來物價之變遷,可從此得知(50)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第51頁。。梁氏在此將眼光向下,尋求歷史中不經意的史料存遺,所謂“流水賬簿”入史,頗為后來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梁啟超的史學方法中有關辨偽的部分,顯然受到清代以來乾嘉考證學派方法的影響,并配合其對西方史學中“史料”的理解而來。他說:“吾非謂治史學者宜費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證,尤非謂考證之功,必須遍及于此等瑣事。但吾以為有一最要之觀念為吾儕所一刻所不可忘者,則吾前文所屢說之‘求真’兩字——即前清乾嘉諸老所提倡之‘實事求是’主義是也。”(5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第99頁。梁啟超在此反復強調“史學求真”之義,必須采西方科學的方法駕馭史料,不能步宋、明以降學術的誕渺,站在乾嘉考證學者“實事求是”的為學態度上,對吾國史學之批評別開一新局面。梁啟超對史學方法的探討,若論其所本,仍以他最熟悉的舊史作為爬梳的對象,鮮少以西方史學之例舉證。這非他個人的問題,而是那個時代的通病或稱之為特色。欲將中西史學溶鑄于一爐,不是一代人便能完成的理想,有太多的矛盾需要解釋,而其中的差異性,能否藉“格義”、“附會”、“想當然耳”便可成事?梁啟超開了頭,為中國之舊史界開辟出一方新天地。
然而,由于梁啟超的學術性格使然,其不斷變化的觀點充斥在他的著作之中。《中國歷史研究法》完成后不久,他的另一篇講稿《研究文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對于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修正》文中,又再次推翻其中的某些論點。到了1927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出版,梁啟超又再一次對其論述進行反思。梁啟超始終很敏銳地注意到民國學界的風氣,其先前提倡對史料的高度稱許,或導致民初史學傾向專注史料的學風,其主流為“史料學派”,強調“考史而不著史”、“史學即史料學”的研究方法。梁啟超對此風潮所形成的學派,或感與有責焉,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想導正此種學術風氣,并認為當時的中國急需一部好的通史,通過他所倡的個別專門史之作,整合成理想的新史(5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99,第168頁。。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梁啟超對于近代史學主、客觀的問題也提出了看法,說:“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我國人無論治何種學問,皆含有主觀的作用。……夫史之性質,與其他學術有異;欲為純客觀的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志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53)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73,第31-32頁。梁氏對于歷史活動中的主、客觀因素已有一定的理解,所謂“純客觀”的學術活動,在其理解中無法排除主觀的作用,故梁氏不敢將此理說透,但如何避免在史學中因個人的知識、情感等主觀的成見滲入史學的研究之中,他提出了采一種“鑒空衡平”的態度,在可能的范圍內忠實地搜集資料與敘述,使歷史的書寫“恰如其本來”。汪榮祖認為,此語和德國近代史家蘭克被人廣為傳引的名言“歷史要寫得像過去已發生的事一模一樣”(wie es eigentlich genwesen)頗為相似(54)汪榮祖《論梁啟超史學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26頁。此語為蘭克《羅曼與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中所言。胡昌智將此語前后文譯為“它只想呈現,過去原本是如何”(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nwesen),認為此語不是在討論研究方法以及處理史料的地方出現,它是在說明歷史發展主軸的論述脈絡時所說。參見: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第33頁。。然而事實上,梁氏深知難以達成。如何抑制史家主觀判斷及其價值立場,而達所謂“信史”的層次,這是欲為良史者的重大考驗。其實,梁啟超受新康德主義李凱爾特等人的影響,在史學的研究中,強調心力與自由意志的表現,這種依靠直覺與個性的視角,有陷于歷史相對主義的可能性。雖然梁氏一再提醒史家要避免主觀而趨于客觀,但在理論上往往落入兩難的境地(55)美國史家貝克爾(Carl Becker,1873-1945)強調歷史學家在重構過往的過程中無法克服社會的制約性,故相對主義者會把客觀性視為一個高貴的夢,為不可能實現之夢。參見:董立河《西方史學理論史上的歷史客觀性問題》,《史學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4頁。。
四 結語
在梁啟超生命的最后時光里,其思想上的轉變是有目共睹的。這個轉變是向傳統文化的復歸,對中國文化價值的重估與肯定。當五四時期,新派進步思想家主張全面清算中國文化之際,他卻主張“讀經”,但不是要回復過往以“經學”為主導的意識形態領域,而是認為所謂的“經學”實則為國族文化的源泉所出。對于疑古學派的態度,梁氏不全然排斥,他認為這是作研究的一種基本精神,其所反對的是“疑古太過”,因為將疑古視為目的,便失去學術求真的意義。梁啟超晚歲對早年服膺科學主義及進化之理的立場進行了修正。胡適曾將歐戰后中國社會反西方科學思潮的風氣歸因于梁氏,他說:“中國講維新變法以來,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科學的,直到民國八、九年間梁任公發表他的《歐游心影錄》,科學方才在中國文字里正式受了破產的宣告。……我們不能不說梁先生的話在國內確曾替反科學的勢力助長不少的威風。”(56)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頁。胡適給梁啟超扣上“反科學”的大帽子,這非真實的梁啟超。雖然梁氏在《歐游心影錄》中有許多悲觀的論調,卻是來自戰后面對歐陸殘破的現狀所引發的心理沖擊。故梁氏稱科學非萬能,但卻未否定科學,也未否定西方文明,而是回過身來重新思索傳統文明能否為此世界有所貢獻。
但如何才能做到中西文化的互補呢?梁啟超早在1902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佛學時代》中說:“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中國學術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茍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為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于我為斷。”(57)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63頁。類似的論點,陳寅恪也說過,他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說:“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58)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84-285頁。無論是梁啟超或陳寅恪,他們對中西文化的態度,均采一種開放的精神,甚至是一種“調和論”的論點。梁啟超于1927年撰《儒家哲學》時,企圖將自己的學術淵源與師承關系,重新安置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脈絡里。他稱自己近于“粵學”,其特色為遠紹戴震,考據與義理并重,近承陳澧、朱次琦,主張“漢宋調和”(59)梁啟超《儒家哲學》,《飲冰室合集》專集之130,第67頁。。梁氏在此將自己的學術師承,重新安放在早歲學海堂的學統之中,這是一種對傳統學術的認同與復歸的渴求。然而,梁啟超不是單純的回歸,而是得時代之賜,將新知與舊學雜糅,以某種融攝回應中國傳統文化。
梁氏的學術思想及其史學觀念,始終處于某種發展性狀態,隨其各階段而產生變化,但各階段非起滅的關系,而是往復的關系,彼此呈現正反激蕩的螺旋辯證過程(60)周昌龍《梁啟超思想中知識結構的轉移與深層變化》,《中國文化》2010年第31期,第79頁。。作為中國近代思想的拓荒者,梁啟超史學的種種觀念,開啟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多元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