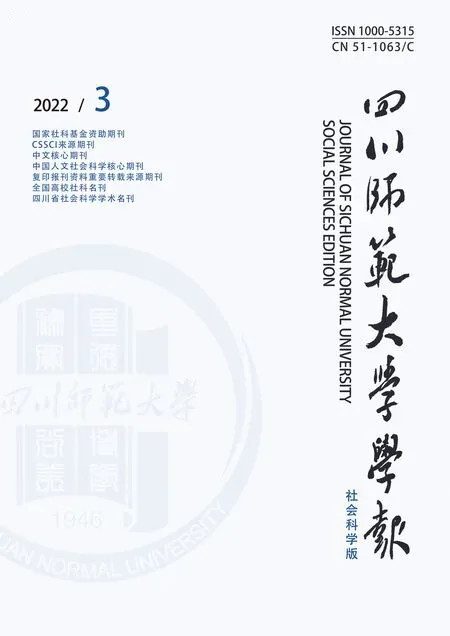司馬相如文論與武帝朝政治
許 結
司馬相如在漢代的地位,基本是以文章顯,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論漢武帝朝之得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地理志》記述“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634、1645頁。。所言“文章(辭)”,多指辭賦之文,特別是《漢書·揚雄傳》載錄揚雄自序仿相如賦而為“四賦”,以及班固稱頌相如為“辭宗”,迨至宋明時代有關“賦圣”說的形成(2)許結《司馬相如“賦圣”說》,《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已成批評定式。論詞章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相如巧為形似之言”(3)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778頁。,說思想如裴度《寄李翱書》云“譎諫之文也,別為一家,不是正氣”(4)裴度《寄李翱書》,董誥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461頁。。但也有不拘辭賦一體者,如常璩《華陽國志》稱贊曰:“長卿彬彬,文為世矩。”(5)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頁。特別是明人王祎虛構《司馬相如解客難》文,其中假托“相如”答“客”討論“文之時義”一段云:
文之時義大矣哉!經緯天地,黼黻造化者……是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弟,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方今大漢道躋燧庭,德儕羲軒……昭然乎宇宙之聲靈也,粲然乎官府之儀章也,秩然乎朝廷之等威也。(6)王祎著、顏慶馀整理《王袆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98頁。按:引用時標點略有改動。
如果出于“文之時義”來看相如辭賦以外的論述文,將其文論置放在武帝朝的政治生態中,則有值得發覆之義。
相如今存議論文字,除《諫獵書》與其“天子游獵之賦”中類似言說,另有三篇值得關注,分別是《喻巴蜀檄》、《難蜀父老》與《封禪文》,皆與武帝朝政治緊密關聯。
一 《喻巴蜀檄》與開邊政略
在武帝朝,司馬相如曾兩度出使西南巴蜀之地,一次以皇帝身邊郎官的身份前往,為彌補唐蒙出使西南處事不當的過失,一次是以“中郎將”身份仗節前往。前者留下《喻巴蜀檄》,后者則有《難蜀父老》。這兩篇重要的議論文均作于相如出使西南時期,而此行又是他唯一一次改變作為宮廷言語侍從獻賦邀寵,真正為朝廷施行政略的事務。對此,《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述很簡單: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余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044頁。
其中宜關注幾個字或詞語:一是“使略”,指唐蒙作為使者往巴蜀之地行朝廷政略;二是“責”,武帝再派相如出使巴蜀的任務,就是責備唐蒙的行為過失;三是“非上意”,在相如喻示巴蜀父老的“檄文”中,明確將唐蒙的作為與武帝分割,其“使略”的責任或后果全推卸給唐蒙個人。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早在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時,唐蒙隨行,在東越獲知蜀地及西南物產豐富,就向武帝提出在西南置郡縣的主張。其后武帝命唐蒙為中郎將,從巴蜀筰關進入,會見了夜郎侯多同。對唐蒙入西南的經歷,《史記·西南夷列傳》記云:
蒙厚賜(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余縣,屬蜀。(8)司馬遷《史記》,第2994頁。
可知唐蒙因提出在西南置郡縣,被武帝遣往喻“威德”,并為“置吏”,被后世稱為“西南絲綢之路”的開拓者;而相如也是在西南置郡縣的倡導者,只是后于唐蒙以“郎官”職出使,故無此“開拓”之名,但兩人出使西南的任務相同,都是為武帝的開邊遠略服務。唐蒙于時“發巴蜀卒治道”,既為功績,亦生禍端,而相如出使正是代表武帝去糾正唐蒙因修道路而造成的當地官民的恐慌,及由此潛伏的亂兆,以安撫巴蜀民眾。這一“反”(啟禍端)一“正”(平事端),是兩人相繼出使之因,對后來大西南完成郡縣式管理的歷史功績,相如功勞絕不亞于唐蒙。
對相如來講,這次出使是他人生軌跡上重要的一段歷程。大約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9)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五年(前130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對應相如《喻巴蜀父老檄》文中所言“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可推知相如往巴蜀并作喻父老文當在元光五年秋季。參見: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唐蒙為迎合武帝的野心,急功近利,在巴蜀地區征調了千余吏卒和兩萬多民工,日夜修造由今四川宜賓經云南昭通、貴州咸寧、再到昆明的“石門道”,當地有少數民族首領不聽調遣,唐蒙就用“軍興法”,即戰時軍事法,誅殺多名首領,引起了巴蜀地區民眾的恐慌,潛伏著“民變”的危險。漢武帝遣派相如往巴蜀安撫百姓,應該是深思熟慮,推測其用意有三:其一,相如為蜀郡人,根系深,人脈廣,便于權宜行事;其二,相如是他身邊的近臣,以“郎官”出使,僅為皇帝負責,回護其短而彰揚其長,為其職責;其三,相如確有行使政略的才能。尤其是第三點,在相如以檄文告喻巴蜀父老的文字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這篇被后世編相如文集者命名為《喻巴蜀檄》(或稱《喻巴蜀父老檄》)的文字(10)按:全文載《史記》本傳,《文選》題名《喻巴蜀檄》,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題名《諭巴蜀父老檄》。,共分三段,也是相如告喻巴蜀父老的三層意思。文中首先告喻蜀地最高長官太守,以高屋建瓴之勢彰明“蠻夷”之亂必治,以及武帝即位后平四方、一中國的膽識、策略與作為,接著才批評唐蒙辦事的誤差。其中稱贊武帝開邊統一各民族的決心,文筆婉轉,卻氣勢雄厲: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后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11)司馬遷《史記》,第3044頁。
這對“圣作”的贊美,鋪寫了伐匈奴、平西域、征閩越、吊番禺等,既有歷史事實,也有為文夸飾之處。比如匈奴單于請和親是建元六年的事,而興師北伐宜指《史記·匈奴傳》、《漢書·武帝紀》及《通鑒》卷十八所記載: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從大行王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等將軍騎材官三十余萬人匿雁門的馬邑谷中,陰使人引誘匈奴騎兵進入埋伏圈。匈奴有十數萬騎入雁門郡,離馬邑尚有百余里,覺察而引兵退走,漢軍大隊人馬追擊,結果無功而返。至于衛青等挫敗匈奴是元光六年以后事,所言匈奴“怖駭”,“屈膝請和”,是具有想象成分的(12)參見:司馬相如著、金國永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有關《諭巴蜀父老檄》的注釋,第149頁。。但相如作為武帝“一統中國”并綏遠四方的堅定支持者,文中張大漢勢,前提是告喻巴蜀太守的話,“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13)司馬遷《史記》,第3044頁。,這就確立了他的基調,朝廷“使略”西南地區方針的正確性;于是再由對漢略四方的夸張之詞,引出這段文字的重點:朝廷派遣中郎將唐蒙以及“發巴、蜀之士”興修道路沒有錯誤,錯在“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失于“時”而謬于“法”。結論是這些做法“非陛下之意”,及“非人臣之節”,既斥唐蒙之誤,也暗喻巴蜀父老的抵觸不合時宜。
由此相如進入他檄文的第二層次意思,緊接“非人臣之節”暢述“人臣之道”,要在“急國家之難”。相如先樹立起為國奮不顧身的榜樣: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后,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14)司馬遷《史記》,第3045頁。
開發與平定“西南夷”是國策,這與抗擊匈奴,用兵閩越一樣,豈能“與巴蜀異主哉”?這文勢一轉,已由責備唐蒙而變為責備巴蜀父老,逗引出“恩”“威”兼施政略。先看“恩”,相如用鋪陳之法歷敘“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遺顯號于后世,傳土地于子孫”,“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甚至做到“肝腦涂中原,膏液潤野草”,至上的國家意志與至高的道德綁架,使受“喻”者無地自容。再說“威”,與前述反證的是“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恥及父母,為天下笑”,這些絕非“獨行者之罪”,而與“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相關,“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乃至“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這又把過錯由個別行為轉嫁給整個巴蜀父老,使唐蒙“誅其渠帥”行為也變得理所當然了。這種極盡利誘威逼之能事,行之相如文字,已將朝廷“使略”造成的難堪,解脫干凈,“喻”詞轉變成了“訓”詞。
言至此而意未盡,相如在“喻”文的第三段繼“非陛下之意”,再強調“陛下之意”:一則是因唐蒙“方今田時,重煩百姓”之過錯,昭示地方,以彰顯皇帝的恩德;一則是派“信使”(相如自謂)以曉喻百姓解決“發卒之事”,既責斥唐蒙,更在于教喻巴蜀父老,即“讓三老孝弟(悌)以不教誨之過”擔負責任。可以說,相如巴蜀之行,解決“發卒之事”是實,而喻示教訓為虛,觀其檄文,則斥責唐蒙是虛,告喻巴蜀官民為實。這其中顯示出相如不辱使命且善于文詞的高超技藝。劉勰《文心雕龍·檄移》評曰:“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379頁。雖名稱《難蜀父老》,實亦兼含《喻巴蜀檄》的文意。宋人樓昉《崇古文訣·評文》說此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16)樓昉《崇古文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頁。按:有關論述,可參見:許結《漢代“文術”論》,《文學遺產》2020年第6期。所言文法得“體”,是一方面,而“文字委曲”與“善為辭”則是另一方面,其中因“術”而彰“用”,是相如常用的手法。
相如為何寓“術”于“文”,要在迎合當時的開邊政略。在漢武帝一朝,征東越、伐匈奴、服南粵,包括對大西南諸國的置郡縣管理,皆與其大政方針緊密聯系。概括起來有兩大視點。
第一個視點是大一統思想的主導作用。這一思想最突出地體現在《漢書·董仲舒傳》載董氏上“天人三策”之第三策的建議: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7)班固《漢書》,第2523頁。
董氏所論,是思想的大一統,這與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18)班固《漢書》,第212頁。文化政策相契合。如果將此“大一統”落實于行政,在武帝一朝最大的政略就是“抗匈奴”與“削藩國”。從漢高祖“平城之圍”受困于匈奴,經漢文帝相繼頒發的《與匈奴和親詔》、《遺匈奴和親書》,到漢武帝頒布的《欲伐匈奴詔》、《征南粵詔》、《巡邊詔》等,特別是與匈奴的戰事,改變了漢初以來的漢匈關系。由此而來的一系列開邊,成為武帝時最顯眼的政略。這期間相如曾兩度出使西南,就與武帝的這一政略緊密聯系。有關開邊,漢初學者已有論述,如晁錯的《言守邊衛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其中多言“秦時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貪戾而欲廣大”(19)班固《漢書》,第2283-2284頁。的過失,其與相如《喻巴蜀檄》對開邊施政的歌頌大相徑庭。當然,不同于漢匈戰事,武帝朝對西南的開發,奉行的是懷柔政策。
這又引出我們說的第二個視點,就是為了集中精力抗擊匈奴,武帝朝施行了“欲北先南,經略三越、西南夷”的政略(20)莊春波《漢武帝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9頁。。
有關西南諸國,《史記》、《漢書》均有《西南夷(列)傳》,可觀其大概。所謂“西南夷”,據張守節《史記正義》說,“在蜀之南”(21)司馬遷《史記》,第2991頁。,也就是相如家鄉的更南端的廣大地區。對這一片區域,《史記·西南夷列傳》開篇就作了簡要的介紹:“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這是接近蜀地的西南諸少數民族地方邦國,多有城池,其中以夜郎、滇、邛都規制較大。《史記》該傳接著記述:“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所說的“椎結”、“編發”,皆民族發飾,所謂“隨畜遷徙”,即游牧,在古代西南地區有“游耕”的生活方式。由于流動性強,沒有“君長”(政權機構),確實存在管理的困難。接著傳文又記述更為廣遠的區域:“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冄駹最大。……在蜀之西。自冄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22)以上所引《西南夷列傳》,均見:司馬遷《史記》,第2991頁。其中提到的“徙、筰都”與“冄駹”,在當時都是較大的邦國,合前面敘述的各區域,被統稱為“巴蜀西南外蠻夷”。
這廣袤的大西南區域,正是漢天子遠略之地,尤其是與巴蜀郡縣鄰近的地區,更是宜加管轄與治理,以防范邊陲之患。在武帝執政時期,連續出現了幾次影響西南穩定的事件。例如武帝因西南地區多次反叛朝廷,曾遣公孫弘前往視察,欲平其情而通其道,公孫弘審時度勢,勸武帝先致精力以伐匈奴,暫緩西南之事,結果武帝放下西夷事,僅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而已。又如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出使西域大夏,見市場有蜀布、邛杖,得知“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23)司馬遷《史記》,第2995頁。,于是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出使西夷西,欲往身毒國,至滇,被滇王滯留,未能開通前行道路。后來南越反叛,武帝征發南夷兵助戰,又因且蘭君不愿勞師伐遠,聚眾反叛,殺了天子使者與犍為太守。迨至征伐南越的戰爭勝利后,武帝才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也隨之入朝,朝廷任命其首領為夜郎王。相繼置郡有越嶲、沈犁、汶山、武都等。于是再使王然于以兵威勸喻滇王入朝,直至元封二年滇王始舉國降服,西南廣大區域得以平定。
居此期間,尤其在武帝欲伐北而先平南的政略指導下,相如初使西南以及所作《喻巴蜀檄》的功用,顯而易見。這也就有了他第二次出使西南及發布《難蜀父老》文的緣故。
二 《難蜀父老》與漢德建構
有了初使西南的成功,武帝對相如“復通”道路、開辟“西夷”的建議完全接受。據史書記載,在武帝對解決西南問題舉棋未定時,相如提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兩大建議:首先是反對用武力征服西南,采取和平通商的方法進行互市融通,并建議朝廷派漢人官吏去參加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權管理;第二是在靠近蜀郡的一些西南少數民族人群聚集區域設立郡縣,直接收歸朝廷管轄。這兩條建議均合武帝心意,于是委派相如為中郎將前往巴蜀及西南地區行使朝廷威權,相如也因此開始了第二次出使西南的征程。
對相如再次出使西南的身份、作派以及蜀地人歡迎的程度,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著較為詳細的記述:
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于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歡。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24)司馬遷《史記》,第3046-3047頁。
史載“蜀人以為寵”,這一“寵”字,是富貴歸故鄉的形象寫照。其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司馬貞《史記索隱》:“亭吏二人,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亦守宰無定,或隨輕重耳。”(25)司馬遷《史記》,第3047頁。其二,諸公“獻牛酒以交歡”,示尊重以饋贈(26)有關“賜牛酒”,清人王先謙結合漢昭帝始元元年、漢元帝初元元年、漢章帝元和二年的三次“賜牛酒”舉動,頗有考論,詳參:朱雪源、李恒全《“賜民爵”“賜牛酒”與漢代普惠性社會福利研究》,《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其三,卓王孫悔“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以其戲劇性的行為變化,反襯出相如再返蜀郡的榮耀。至于相如這次出使的效績,史遷的記述是:
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27)司馬遷《史記》,第3047頁。
他不僅采取懷柔政策使邛、筰等地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內附,而且西至沫水、若水,南至牂柯邊塞,修零關道路,架孫水橋,直達邛都。正因此,“還報天子,天子大說(悅)”(28)司馬遷《史記》,第3047頁。。這次相如出使西南留下的文獻,就是《難蜀父老》,文章主要是駁斥蜀中長老的觀點,借以堅定武帝開邊拓疆的決心,由此折射出武帝朝的政治生態和其文論價值。
對這篇文章,《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想反駁他們,卻因自己身處其境,于是作此文字,“以風天子”(29)司馬遷《史記》,第3048頁。。這個“風”(諷)不同于他獻賦“諷”皇帝奢侈,而是為了堅定武帝開發西南的決心,完成其一統疆土的政略。如果說他前一篇《喻巴蜀檄》偏重實際事務,則此文更多地提升到政治思想的高度(30)前人對此文頗有評述,如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卷12評相如《難蜀父老》“深陳百姓之苦,以成人君悔過之美”,乃一隅之見。參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呂祖謙全集》第8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83頁。。相如此文采取“欲擒故縱”法,以假托蜀中的“耆老大夫”和“縉紳先生”的二十七位弟子之口,詰問使者開頭。繼以“使者”的長篇大論,宣示漢廷政略,既標舉“賢君”(有為之君)理應如何,又彰顯“漢德”的意義所在。最后復以諸老弟子(諸大夫)折服其言,唯諾其事而告終。先看冠首文字: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穢濊,郡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31)司馬遷《史記》,第3049頁。按:以下所引《難蜀父老》均參《史記》,第3049-3053頁,不再一一注出。
闡明自高祖到武帝“六世”的功“德”,特別是漢興七十八年后武帝的一系列政治舉措,這才引出“命使西征”的行徑與“罔不披靡”的成績。由此再引出蜀中諸大夫對使臣的質疑,形成一種不諧的論調。比如“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32)這里說的“羈縻”,意聯絡、維系,指三代以來華夏與夷狄的關系。《史記索隱》:“羈,馬絡頭也。縻,牛韁也。……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司馬遷《史記》,第3050頁)。可見這一詞是具有貶義的。,意思是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只需保持正常的朝貢關系即可,不必要設郡縣以加強統治。又比如指責使者:你要通夜郎,三年有何成效,現要開通西南夷道,士卒疲倦,百姓力屈,其失敗難免。作為使者的代言人,相如對這些論點一一反駁,比如他說,如果照你們這樣安于現實、不求進取的邏輯,巴蜀之地又怎么能夠像今天過上文明生活呢!作為一個有作為的賢君,絕不應因循守舊,委瑣齷齪,而應有強烈的責任感與進取心,不管是“夷狄殊俗之國”,還是“遼絕異黨之域”,哪怕是“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只要缺少文明教化,都是朝廷的恥辱,何況西南人民對漢天子如“枯旱之望雨”?所以從長遠眼光來看,眼前巴蜀之地百姓的辛苦,只是暫時的,有何怨望?相如不僅暢談當下的形勢,還列舉歷代賢君如夏禹治水等功績加以佐證,為武帝“討強胡”、“誚勁越”的功業張目。其文勢縱橫,議論洋溢,既可見為辭之精彩,更能看到個中強烈而廣大的政治抱負。
在這篇文章中,最凸顯的是一段話語和一大理念。一段話語就是文中傳誦千古的名言: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33)班固《漢書》,第3050頁。
緊接的話語是說大漢皇帝應該“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從歷史的結果來看,前一句很似漢武帝這個人,后一句很像漢武帝所做的事。如果說對“創業垂統”的話,漢武帝是以此自勉并終身履行,那么有關“非常之人”、“非常之事”的說法,堪稱是武帝難以忘懷的記憶。在相如說此話二十三年之后的元封五年(34)按:據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章開頭說“漢興七十有八載”,可以推算出作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距離“元封五年”(前106),已是23年。,漢武帝頒布《求賢詔》有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35)班固《漢書》,第197頁。
不僅用相如之詞,亦取其義,使“非常之人”由衡“賢君”到求“賢臣”,關鍵是“非常之事”與“非常之功”,這與武帝朝的政治運作是共脈動的。如果我們將相如的提法對應賈誼于文帝朝《上疏陳政事》(亦稱《治安策》),雖然也是談治國理政大事,但其立論“前車覆,后車戒”的警示,故為之痛哭、流涕、太息(36)班固《漢書》,第2237-2258頁。,與相如“非常”之說不能同日而語。如果我們再比較與相如同朝為官的東方朔,他在《答客難》中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圣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37)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629頁。,其“自得”之論,正與相如反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潛符默契。而綜觀當朝思想,比較董仲舒與公孫弘,前者于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中大談“天人相與”、“禮樂教化”與“養士”、“求賢”等(38)班固《漢書》,第2495-2523頁。,重在“道”,后者于元光五年《舉賢良對策》中則強調“因能任官,則分職治”等“八事”為“治(民)之本”(39)班固《漢書》,第2615頁。,重在“治”。相形之下,相如之論顯然是由“治”而“道”,這也是他《難蜀父老》提出的一大理念,就是由“漢業”觀“漢德”。
考“漢德”一詞,初由相如《難蜀父老》提出,文中反復強調漢朝皇帝之“德茂乎六世”、“德洋恩普”、“至尊之休德”等,而關鍵語在論漢武帝功業的一段話:
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愿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途,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誅伐于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40)司馬遷《史記》,第3051頁。
如果對應漢初婁敬《上書諫高祖》批評其“欲與周室比隆”,“而欲比隆成康之時”(41)班固《漢書》,第2121、2122頁。,到東漢學者經王莽之亂倡言“大漢繼周”,其間相如提出的“繼周氏”的“天子之急務”,是特別值得關注的。正是因為彰顯了武帝執政前期已有一系列功業,所以相如在該文收束處托言諸大夫臣服而贊嘆“允哉漢德”。繼后《漢書·夏侯勝傳》記載漢宣帝即位初,為褒揚武帝,對丞相、御史說:“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于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圣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后;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功德茂盛。”(42)班固《漢書》,第3156頁。這是回顧前朝,將武帝的功業與功德結合起來。到西漢末年,揚雄《法言·孝至》再次提出“漢德其可謂允懷矣。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43)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46頁。,結合其《長楊賦》中繼歌頌高祖之“天德”與文帝之“儉德”,對武帝的“功德”更是濃墨重彩,所謂“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眥,閩越相亂,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44)揚雄著、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頁。。這些評價,傳承了相如之說,只是經漢宣帝、元帝之后,外戚勢熾,討論漢德更傾向于漢統。而基于武帝功業的漢德觀,在相如《封禪文》中有著進一步的闡發。
三 《封禪文》與帝國新宗教
相如兩使西南,是他生平從事政務的重要階段,也成就了關乎當朝政治生態的《喻巴蜀檄》與《難蜀父老》這兩篇政論之文。遺憾的是他因“使時受金”而“失官”,雖然不久復職郎署,又做了幾年“孝文園令”,其遭受的冷遇造就了他人生中與獻賦邀寵完全不同的一面,即“稱病閑居,不慕官爵”(45)司馬遷《史記》,第3053頁。。也正因為他介乎參與朝廷政治與游離官場俗務之間,于晚年稱病閑居茂陵時,又留下了一篇具有極強當朝政教意義的《封禪文》。
有關《封禪文》及武帝經眼的過程,《史記》本傳有段記載:
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書;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46)司馬遷《史記》,第3063頁。
武帝派所忠取書,得“遺札書言封禪事”,而“天子異之”。或謂“異”指不同意見,據武帝后來施行封禪大典事,此“異”當取本義,即奇異、驚異,有贊美義。對應相如每上文武帝的反應是“善之”(《子虛賦》、《諫獵書》)、“大悅”(《上林賦》、《大人賦》)等,可為旁證。而武帝為何派所忠取書且得獲《封禪文》以獻?史書未予說明,但結合所忠生平,卻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有關所忠的記載,《史記》除了《司馬相如列傳》,計有三處,分別是《孝武本紀》、《封禪書》、《平準書》。《平準書》載有所忠進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47)司馬遷《史記》,第1437頁。一事,而《孝武本紀》則記述其參與國家宗教及祭祀: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功,申功已死。”(48)司馬遷《史記》,第467頁。按:《史記·封禪書》、《漢孝武故事》記述基本相同。
由此記載可知所忠乃皇帝近臣,參與有關方士進獻神方及祭祀活動,但他又與方士不同,故有“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的質問,但拗不過皇帝的喜好,自然也就順從了有關的宗教活動。于是我們聯想到相如與所忠的兩大共同點:其一,兩人都曾是皇帝身邊的近臣;其二,兩人均不偏信方士神鬼游仙之說,相如上《大人賦》帶有明顯的反對“游仙”的目的,但都不反對當朝國家宗教的建設,并參與其事。
“封禪”詞語在先秦就有,但完整討論封禪之事則始于相如的《封禪文》。例如司馬遷《封禪書》引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49)司馬遷《史記》,第1361頁。,相如《封禪文》開篇即謂“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50)司馬遷《史記》,第3064頁。,雖亦征引前人之說,卻早于史遷書多年。班固《白虎通》引孔子說“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余君”,并彰明其義:“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51)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78頁。而封禪大典作為國家宗教的禮儀,漢武帝之前多為“虛像”,其后則成為制度,歷代傳承。封禪作為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具功隆德合的盛世的象征:所謂“封”,指培土,在泰山上培土為壇祭天,以報天之功;所謂“禪”(本作“墠”),指除地,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場祭地,報地之功。相如之所以倡導報天地之功的祭祀大典,實不同于方術諸神祇以及三代的廟祭(祭祖宗),而與武帝朝國家新宗教的建立有關。
考察三代(夏商周)的國家祭祀,以“廟祭”為主,《漢書·郊祀志》記周公相成王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52)班固《漢書》,第1193頁。,說的是“廟”(如后稷廟、文王廟)。而建立漢代的劉邦作為平民皇帝登基,因不同于前代的尊貴血統,所以在建立國家宗教時不斷進行造神活動,雖亦承續秦祀“四帝”傳統,而為“五帝”祭祀,但因巫風盛熾(53)詳見《史記·封禪書》中有關“梁巫”、“晉巫”、“秦巫”、“荊巫”、“九天巫”、“河巫”等各司神職的記載。,未定一尊。到漢武帝時,因其耽于方術,或祭“神君”,或祀“太一”,是漢初以來造神方式的延續,也可以說是建立國家新宗教的探索。武帝本人信仰的不確定性,并不影響國家宗教建立的進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事對》中有關國家祭祀,就有答廷尉張湯問:“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于人也。”(54)《春秋繁露》,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66頁。有關古代的郊祭,可參見:李學勤《釋“郊”》,《文史》第36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以祭天(地)之禮(郊)重于宗廟,以“天尊于人”,是漢代新宗教的重要標志。相如的《封禪文》是從歷史淵承與思想價值來倡導尊天敬地的國家祭祀,其中既有對盛世制禮的渴望與提倡,也內涵了對武帝迷戀方士泛神傾向的擔憂。
《封禪文》可分為五段文字。首段寫軒轅氏前有關封禪的傳說,以治世為尚,以逆行為戒,所謂“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次段自軒轅(黃帝)歷述三代,重在由“周”朝而及于“漢”世。其說有二:一是列述圣君所為,如“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公劉發跡”,“文王改制”等;二是引述《六經》以證事,如謂“《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舉例有《尚書》之“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等。從而引出“大漢之德”一節文字,極言符瑞臻至與成功而封禪的意義: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敷霧散;上暢九垓,下溯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暗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55)司馬遷《史記》,第3065頁。
此以符瑞襯托盛德,批評“不敢道封禪”的現狀,進一步突出文中的重點即第三段文字。
這段文字假托“大司馬”進言,頌武帝之功,言封禪之要。所托“大司馬”,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大司馬,加于將軍號上,有此尊稱者武帝朝僅二人,一是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一是霍去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相如文中假其職以為借重,類似賦家假托人物的寫法。在“大司馬進曰”的語詞中,相如先排比“陛下仕育群生”,“陛下謙讓而弗發”,進謂“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以封禪之事為“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所以祈請“陛下全之”,成此盛舉。為付諸實行,這段文字的收束處用“前圣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移交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的繼往圣絕學話語,實開新章。所謂“圣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其中包括因禮敬神、緣神尊德的思想。
繼后四、五兩段皆收束,第四段以“天子沛然改容”承接“大司馬”的話,以“愉乎,朕其試哉”作答,歸于“詢封禪之事”。這段文字結以諸“頌”文作贊美之意。頌文有五首,或言“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或言“萬物熙熙,懷而慕思”,或言“般般之獸,樂我君囿”,或言“濯濯之麟,游彼靈畤”,或言“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皆為祥瑞。后再束以“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托寓,諭以封巒”(56)按:《封禪文》以“頌”附“文”,東漢班固《兩都賦》系以《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正是相如文法的嗣效。。文章第五段收結,以“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喻“興必慮衰,安必思危”的憂患。
很顯然,相如《封禪文》既有感世之憂,更多盛世之頌。朱熹《楚辭后語》批評相如“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為言”乃“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57)朱熹撰、蔣立甫校點《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頁。。姑不論相如文中諷意,就是頌“漢德”的文字,也是切合當時武帝初盛期招賢俊、尊儒術、興學校、崇禮樂、潰匈奴、擴疆土的顯赫功勛。相如臨終遺留下的《封禪文》,是他對盛漢國家新宗教建設的思考,其中核心思想及影響,又體現于王朝后續的宗教事務與漢德由“功業”歸于“正統”的問題。
有關《封禪文》的后續事務,《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僅記一句:“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58)司馬遷《史記》,第3072頁。說的是元封元年武帝率群臣登泰山行封禪大典禮。對武帝行封禪,《史記·封禪書》錄有武帝泰山回駕“制詔御史”詔書:
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59)司馬遷《史記》,第1398頁。
其中除了尊重國家封禪大典,有兩點值得關注,即帝王自己的怵惕之心與普惠生靈的愛民之意,而這也恰是武帝八年前所讀到的《封禪文》中所極力倡導的。在詔書中,武帝特別提及“自新”與“更始”。因為在施行封禪大典之前,如何制訂祀儀,武帝曾詢問諸臣,兒寬有段較長的回答,以為“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并謂“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乃至“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60)班固《漢書》,第2630、2631頁。。其中關鍵在“自制儀”,誠如顧頡剛記述的,早在元封之前,濟北王已將泰山獻出,到元封元年封禪時,諸儒生又以古禮說事,難以實施,所以武帝采用祭“太一”禮來封泰山(61)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6頁。。無獨有偶,在相如拜孝文園令時因武帝好游仙而上《大人賦》以諷喻,其中有關仙界的描繪即以“北極”(太一所居)為重點(62)有關太(泰)一(壹)星與太一祀,參見:錢寶琮《太一考》,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234頁。。如賦中述“北游”云:
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狹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于玄闕兮,軼先驅于寒門。(63)司馬遷《史記》,第3062頁。
其“幽都”(西北方地名)、“北垠”(北極之地)、“寒門”(北極之門)均為傳說中的極北之地。作者在賦中描寫“乘虛無而上征兮,超無友而獨存”的精神,表達的正是一種仙游的至極境界。值得注意的是,賦家以此為行游之終結,標示著到達的“極地”,如果結合漢武帝信奉“太一”尊神,以及設置神廟和相關祭祀活動,特別是后來以“太一”法修封泰山,其間的關聯也是有跡可尋的。
如果說在《難蜀父老》中,相如論“人道”所述“漢德”是基于武帝朝的“功業”,那么在《封禪文》中論“天道”(帝國宗教)所述之“漢德”,又在“功業”之上構設了諸多符瑞,以成就其天道圣統即“漢統”的意識。該文中所述武帝“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以及“首惡湮沒,暗昧昭晢”等功業,無不涂飾以“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昆蟲凱澤”,“乘龍于沼”等瑞兆,彰顯“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的神統與道統。只是相如強調的“漢統”與“漢德”的關系,與西漢中后期因外戚干政、東漢懲“新莽”教訓所大倡之“漢統”不盡相同,屬于當時朝廷改制中的神道構設,是武帝朝新宗教的體現。《漢書》引錄吾丘壽王于武帝朝汾陰得寶鼎群臣恭賀時說: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于公劉,大于大王,成于文武,顯于周公。德澤上昭……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64)班固《漢書》,第2798頁。
“漢寶”非“周寶”,“漢德”亦不同于“周德”,這既在行政,又緣于學理。周人重禮尚德,視“德”為“禮”的核心,到春秋末世,禮樂崩壞,仍尚禮以尊德,如《左傳·文公十八年》記魯史克代季文子釋“事君之事”謂:“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65)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33-634頁。這是發展周公制禮以觀德的思想,孔子將“德”歸于“仁”,孟子將德歸于“義”,是對原始“禮德”觀在學理的解析與提升。而到了漢武帝朝始倡“漢德”,實際上是與“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文化政策相關,內涵了以儒術為經術,以經術代行政的思想內核,與武帝朝改制政治契合,這才是相如推述“漢德”的意義所在。
四 頌漢:文學書寫的政治義涵
從相如明確闡發政治見解的文章來看,其文論中對當朝的態度,顯然是以肯定與贊述為主的。因為他的生存發展期處在景、武之際,作為言語侍從在武帝朝,親見武帝早期的改制作為,在開邊政策、新宗教的建立,特別是他由武帝功業以論漢德的頌漢思想,無不與當朝的政治發展大勢合拍,或者說是武帝朝政治的積極參與者。但是,由于相如是朝廷的文臣,所以對他以賦為主體的文章批評,嘗偏于“虛辭”與“諷諫”,尤以“諷諫”為主要精神所寄。究其因,發端于西漢時期司馬遷與揚雄的評論。史遷以《詩》之傳統衡“賦”,評相如賦作“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66)司馬遷《史記》,第3073頁。。揚雄經西漢成、哀亂世,為賦雖效相如,但卻無不標明“諷”,其言相如賦“勸百諷一”、“曲終奏雅”等,是屬于以己心度前賢的一種批評方式,卻掩蓋了相如文章“頌漢”的現實性。雖然,相如文章有諷諫意識,如上“天子游獵之賦”及上《諫獵書》,但皆為防“佚游”過度,且常以天子“大奢侈”的自省方法表述,這是回護,而非責難。考查相如作為宮廷言語侍從而有極大的政治抱負,又在于兩點。其一,相如非單純侍文之士,對此,宋人晁說之《揚雄別傳》引述揚雄評枚(皋)馬(相如)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67)晁說之《嵩山文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602頁。“高文典冊”,才是其擅長之藝。其二,相如文雖用儒家經義,然非儒生,頗似王充所言“文儒之業,卓絕不循”的“文儒”。王充《論衡》梳理漢代學術,提出與經學博士為主體的“世儒”并存的“文人”,且稱頌“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超奇》),“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佚文》),所謂“鴻筆之人,國之云雨也,載國德于傳書之上,宣昭名于萬世之后”(《須頌》)(68)劉盼遂《論衡集解》,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0、412、406頁。。相如為文正在道與治之間,重在“貴今”、“文德”與“文采”。
如果我們從《封禪文》回溯相如賦“上林”,其假托“亡是公”宣揚朝廷大業與董仲舒倡《春秋》公羊學贊述王朝“一統”思想相近,體現了當時“削藩”與“抗匈”的政略,那么在相如臨終的上書中,顯然是對王朝新宗教的建立擘畫獻猷,其思想一以貫之。我們讀《子虛賦》中楚王行獵一段,當與《國策》楚王游云夢、結駟千乘類似,而《上林賦》“天子校獵”的描寫,全為新造,思想的關鍵在假托“亡是公”的說話:
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御,所以禁淫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69)司馬遷《史記》,第3016頁。
緊接著賦中描寫的統一氣象,如“張樂”一節: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70)司馬遷《史記》,第3038頁。
由氣勢到德性,相如《上林賦》中的表達或被稱為“曲終奏雅”,具體到文本就是賦文收束處的一段話:“游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途,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云,掩群《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71)司馬遷《史記》,第3041頁。這是以“六藝”述“禮德”,來呈現行仁政之君主的形象。
這種德政思想在相如的另一篇作品《哀二世賦》(或作《哀秦二世賦》)中得到另一方式的呈現。漢承秦制,卻又以秦亡為教訓,這到身處武帝朝盛世的司馬相如,其觀點也是如此。《史記》本傳記載他曾侍上出行,“還過宜春宮”(72)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又按云:“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之也。”參見:司馬遷《史記》,第3055頁。舊址,“以哀二世行失”而作此賦。指斥秦政的過失,是漢初立國借鑒的直接教訓,其中的代表言論有賈誼的《過秦論》與賈山《至言》中的過秦之說。如賈誼《過秦論》歷數秦之所以興、所以衰、以至所以亡的教訓,如謂“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等言說,興亡之鑒,人們耳熟能詳。其中賈誼又認為,“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天下集矣……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73)《賈誼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6頁。,正是承續文帝朝諸臣子進言“儉德”以鑒“秦亡”。相如在武帝朝功德盛時,以“哀秦”為賦,開創這一題材的文學書寫,是極有歷史意義與思想價值的。對此,《文心雕龍·哀吊》認為:“自賈誼浮湘,發憤吊屈……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嘆息。”(74)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第241頁。從文體分類看,這篇文章既屬辭賦,又屬“哀吊”類,而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哀二世賦》的確是對賈誼《吊屈原賦》的繼承。如賦中寫道:“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75)司馬遷《史記》,第3055頁。這里有兩點:一由賈誼之“哀臣”(吊屈)而變為“哀君”(二世),以“持身”與“失勢”論,有著更強的“新政”意識;二由漢初的“過秦”轉為“哀秦”,前者更多指向秦的暴政,后者偏向于個人的失誤。這種思想的轉變同樣體現在相如開邊意識、削藩問題上,他不同于漢初人反對“貪戾而欲廣大”,“前車覆,后車戒”,反而強調“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治道。換言之,倘秦二世用賢臣,出新政,又何需“過秦”,又何至于“墓蕪穢而不修”,“魂亡歸而不食”?以“功業”論,秦漢沒有根本的區別。由相如的《哀二世賦》開辟了以賦文“哀秦”的題材,后繼者紛紛。可以說,漢代賦家的“建德”觀,以及“大漢繼周”的德教傳統,多與懲秦亡教訓相關。
誠如前述,相如倡導“漢德”,基于武帝朝的“功業”。到宣、元之后更重“漢統”,實因“外戚”政治,如清人趙翼論《兩漢外戚之禍》說“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推原禍本,總由于柄用輔政,故權重而禍亦隨之”(76)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67-68頁。。由此上溯到對武帝得失的評價,典型的是元、成廟議對“武廟”之尊毀的討論。《漢書·韋賢傳》引錄劉歆《武帝廟不毀議》,列舉其南滅百越、北攘匈奴、東伐朝鮮、西伐大宛,以及“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后,定諸侯之制”,稱贊武帝“功德皆兼有焉”(77)班固《漢書》,第3126、3127頁。。如此肯定武帝功業,實與相如的文論銜接,是以“漢業”彰“漢統”。這到了東漢政教昌明期又有了回響,如班固《西都賦》以“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78)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24頁。,張衡《東京賦》以“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79)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64頁。,表彰天子“王會”禮儀的氣象。如果再對應相如《封禪文》中假托大司馬言的一段話,即“仁育群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這對武帝朝政教的贊美,顯然為漢人頌“德”奠定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