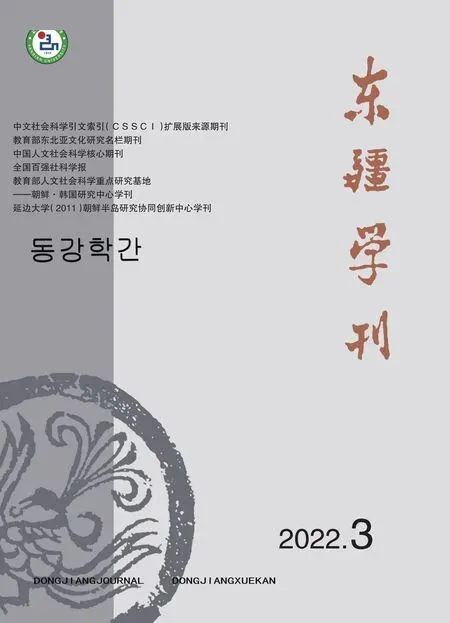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研究
滕 馳
2021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對內蒙古自治區在民族團結和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做出的貢獻給予了肯定,他進一步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1947年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成為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成功實踐,為其他民族地區樹立了典范;新中國成立后,內蒙古創造了“齊心協力建包鋼”“三千孤兒入內蒙”等歷史佳話。內蒙古自治區之所以成為“模范自治區”,是各族人民在民族工作實踐中團結一致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時代背景下,從民族學學科視角探索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踐路徑,不僅能夠為我國民族工作理論研究提供重要智力支撐,同時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現實命題。
本文總結內蒙古自治區在民族團結和邊疆治理方面的成功經驗,提出了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五條實踐路徑。
一、構建穩定統一的治邊理念是堅實保障
我國長期以來能夠維持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思想基礎是蘊藉于各民族文化形態中的“大一統”理念。簡言之,“大一統”即是對天下一統的認同和崇尚。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理念包含豐富的內涵:“大一統”的地域觀、“大一統”的政治觀、“大一統”的文化觀、“大一統”的民族觀等。[1](91-94)“大一統”的形成是由中華民族在地緣環境上的同種同源和生活方式上的共生互補所決定的,中國的歷史實踐反復證明了“天下一統”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大一統”的理念和實踐深受中國人的認同和推崇,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立國思想和踐行根本。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無一例外都是邊疆穩定和國家統一。“天下一統”的觀念經過悠久的歷史洗禮后深入人心,進而對邊疆治理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期以來形成了邊疆統一觀、國家認同觀以及“以和為主”的治邊思想,[2](32)在中國歷代王朝邊疆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指導作用。“中國古代王朝對邊疆地區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輔相成的兩種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與邊疆內地一體化。”[3](38)可以說,正是因為長期堅守了守中治邊、因俗而治、守在四夷的治邊方略,中國才能夠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最終發展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構建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大一統”的治邊理念仍然具有啟示意義。對于中國而言,“大一統”是國家觀,對于全球而言,“大一統”是全球觀。近代以來,中國遭受的屈辱史和自力更生的奮斗史表明,只有各族人民凝聚起來,牢固樹立和不斷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對內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程度,決定著對外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成效。所以,創新推進中國的民族工作,解決好中國的民族問題,直接關系到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中‘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的前景。”[4](106)趨于一致的思想觀念能夠為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和不同民族國家提供穩定的思想根基和治理環境,進而為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提供統一的觀念信仰、價值導向和思想保障。
二、夯實共生互補的經濟基礎是內生動力
經濟狀態決定文化狀態,民族經濟的特點即是民族文化的特色。共生互補的經濟生活能夠增強民族間交流交往,共生互補的經濟意識有助于形成趨同的文化價值觀,共生互補的經濟共同體能夠促進各少數民族文化融入中華文化。歷史上我國各民族間的貿易互動和經濟往來在客觀上促進了文化上的聯系,雖然文化上的交流交往并不局限于經濟貿易往來,然而也不可否認,一個民族的文化輸出與傳入主要是沿著貿易往來的商路逐漸普及并深入的。費孝通先生曾對歷史上漢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經濟貿易往來進行考證:“中原和北方兩大區域的并峙,實際上并非對立,盡管歷史里記載著連續不斷的所謂劫掠和戰爭。這些固然是事實,但不見于記載的經濟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貿易卻是更重要的一面。”[5](311)在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和往來接觸中,漢族和少數民族逐漸建立起共生共存的經濟基礎,少數民族不斷給漢族輸入新的血液,漢族同樣充實了少數民族,在語言和生活各方面互通互融,日漸趨同。“導致民族融合的具體條件是復雜的,看來主要是出于社會和經濟的需要,雖則政治的原因也不應當忽視……政治的優勢并不就是民族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優勢。”[5](332)經濟交流本身即承載著文化互動,如絲綢之路不僅是經商貿易之路,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之路,現存和出土的壁畫、器物、銘文等文物均說明了這一點。文化成為超越民族的精神紐帶,對社會整合和民族團結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建國以來,黨和國家對民族地區實施了資金投資、財政照顧、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政策扶持,其目的在于加速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縮小與經濟發達地區的差距。如今,內蒙古各族人民已將內蒙古建設為國家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輸出基地和能源基地,經濟一體化成為不折不扣撬動文化認同的杠桿,從經濟結構、經濟需求或經濟增長點等方面彰顯了各民族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事實。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拓展,榮辱與共的利益共享將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凝聚注入源源不斷的動能,而共生互補的經濟基礎則是多民族國家構建利益共同體的基本前提,多極共治、互惠互利、共享共贏的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的相互依存,能夠匯聚優勢、彌補不足,激發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使各民族、各地區日益成為更加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三、打造牢固互嵌的地緣環境是客觀需求
“所謂地緣環境就是指國家、國家同盟或國家之下的部分區域形成的地緣體間的地緣關系,以及由地緣關系組成的地緣結構和影響地緣體間的地緣關系、結構的所有內、外部地理環境的綜合。根據地緣環境的定義,可以看出地緣環境由三個部分構成:地理環境、地緣體間的地緣關系和地緣結構。”[6](8)多民族國家的民族格局總是反映著一定的地緣環境特點,盡管地緣環境并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環境無疑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7](440)一方面,國家、民族和地區總是受到地緣法則的支配,地理環境、地緣關系和地緣結構可以促進或阻礙社會發展的進程,特別是在生產力水平較為低下的地區,社會生活在地緣環境的支配決定下,呈現出迥然不同的特殊風貌。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和戰略的實施必將對地緣環境產生深遠影響,這已是國內外學界的基本共識,如“一帶一路”的實施,“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毫無疑問將涉及到沿線參與各國之間利益的協調,也會影響到國際格局的調整,因而必然也是一個地緣政治格局變化的過程。”[8](622)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人口流動性增大,其分布格局、發展實力、人口數量和輻射能力等因素成為研究地緣環境的新視角。“從發達經濟體和國內發達地區來看,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高級形態,是現代技術創新和產業集群的主要平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發育程度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是各地參與區域合作和競爭的主體,也是國家層面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主要載體。”[9]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不但成為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參與競爭的重要平臺,同時也對達成主體間共識和打造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內蒙古幅員遼闊,向西與甘肅、新疆地區連接為絲綢之路,西北觸及青藏高原,東南有大漠戈壁,和黃土高原接壤,東北部有茂密的森林,中部則是滔滔黃河和無際的大草原。草原文化之所以能升華到中華文化之中,原因之一在于地緣環境上和祖國其他疆域是渾然一體的,雖然處于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卻能夠使各民族產生交集。2020年,內蒙古按照中央的部署,以呼和浩特市為中心,在原有呼包鄂榆城市群一體化基礎上,打造了一個同心圓式的牢固互嵌的地緣體系,推進黃河“幾”字灣都市圈協同發展,向東逐漸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向西緊密聯系蘭銀城市群,借助國家“八橫八縱”的高鐵運輸網及信息網,力圖構筑一個政策協助、產業協同、交通聯動、生態互補的祖國北疆城市群與網絡圈,為促進區域發展、民族互嵌、邊疆穩固提供功能保障。
四、整合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是核心內容
文化既是人創造的“意義”,同時也是人行動的“意義框架”,能夠使人的行動按照既定的目標軌跡運行。從中華文化的歷史演進與功能特點來看,正是因為其特有的包容能力和整合功能,才成為一個有巨大生命力的整體。“作為情感聯結的橋梁和精神傳遞的紐帶,中華文化始終能夠將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華兒女緊密地團結凝聚在一起;中華文化對各民族群體社會化功能的發揮,使得中國得以成為通過文化認同進行國家內部整合的成功范例。”[10](52)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所以能夠共處,其根源在于文化能夠整合和調適,文化的排斥性、沖突性與適應性、融合性是同時存在、并行不悖的。“雖然不同文化呈多樣性的特點,但不同的文化之間是可以溝通、相互交融的。文化具有普遍性的特點,文化的普遍性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任何一個民族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擁有相同的文化內容,而是指文化為人類的基本生存、生產生活需要和社會組織服務的特性,這種特性不因種族、民族、地域、階級、時代而有所區別,因為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的生命存在及其社會活動是具有相同的本質和特征的,文化整合正是建立在這種共同性基礎之上的。多元的文化形式在相互接觸中相互影響、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和而不同’的新文化,才會呈現出豐富多彩和生機勃勃的活力。”[11](35)“和”的觀念成為中國社會內部結構各種社會關系的基本出發點,“有教無類”“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等智訓均說明了這一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化體系,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質,就愈豐富,愈有生命力,而一個文化體系愈豐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強……中國文化所以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具有無限的生命力,正是它能夠在各個歷史時期不斷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質的結果。文化整合既可以使文化不斷更新發展,也可以使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立于不敗之地。”[12](240)
內蒙古自治區與八省區為鄰,是中國行政區劃版圖中省(區)際鄰最多的地方。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除了蒙古、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少數民族語言外,漢語方言堪稱最多,東北、華北、晉陜、蘭銀方言官話植根生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此地話”(方言),多種語言共聲、諸種方言交響,展示著草原熱土廣闊的胸懷對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共榮的包容和相互滋養;內蒙古譜寫了“3000孤兒”是“國家的孩子”等經典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烏蘭牧騎”長盛不衰,為各族人民所喜愛;馬頭琴、長調、呼麥、安達組合和無伴奏合唱在國內外音樂殿堂中悠遠回響;一曲《鴻雁》唱遍大江南北,為各民族喜愛,一部《騎兵》舞劇獲得第十二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獎,等等。內蒙古之所以能夠整合不同的文化形式,除了上面所說的政治、經濟、地緣因素之外,還有便是因為文化本身能夠敞開胸襟,秉持平等和尊重、摒棄傲慢和偏見,寬待和容納異文化的博大,而不是與世隔絕、固步自封、畫地為牢。交流、理解、融合、共享是不同文化共存共榮的根本出路,也是惟一出路。
五、建設和諧融洽的民族關系是根本途徑
黨中央關于民族關系的重要論述指出:“和諧”是新時代民族關系建設的必然要求和終極目標。民族關系作為多民族國家最重要的社會關系之一,其和諧與否直接決定著民族團結與邊疆穩固。“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的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13](101)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的概念,并進一步強調:“要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促進各民族群眾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14]即以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來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設并鞏固和諧融洽的民族關系。經過長期歷史發展,內蒙古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形成了分布上交錯雜居,經濟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親近的民族關系。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三順店社區是典型的多民族聚集區,社區常住居民4097人,少數民族人口占38%,其中蒙古族居民648人,回族居民711人,其他少數民族居民共41人。一個聚居著漢、回、蒙、滿、達斡爾族、鄂溫克族等眾多民族的社區是如何做到和諧相處、美美與共的呢?
首先,交錯雜居的居住格局是互嵌式民族關系的物質基礎。三順店社區屬于老舊社區,始建于20世紀60年代,在長期的日常生活與族際交往中,民族身份已經不是首先被考慮的因素,這與我國部分民族地區民族身份模糊和淡化或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互化”不同,是指在不斷的交往互動中,各民族增進了解和認同,彼此不再刻意對自己和對方的民族身份進行識別并以此作為交往的障礙,從相遇、相知到協調、適應再到整合、認同,這是一個從自律、自在到自覺的過程。社區的居住格局逐漸由區隔型向接觸型、融洽型過渡,最終實現了深層次的嵌入,即不分彼此的交融型的互嵌社區。近年來,三順店社區在政府部門總體布局規劃下,在社區居委會與開發商的通力合作下,以國內外經典案例為樣板,打造“鄰里中心”(Neighborhood Center)模式的社區商業,社區現有小型商鋪168家,周邊毗鄰大型商場和生活超市,秉承兼收并蓄的規劃思想、鄰里中心的布局業態,將各個階層不同民族的居民融合在一起,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和民族特色,既為社區居民提供了必要而便利的公共服務,也為各民族交流、理解、融合搭建了平臺。
交錯雜居是實現各民族交融與共的底層基礎,思想文化方面的精神融合才是最終目標。在長期的交流交往過程中,各民族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習俗。漢語普通話和呼和浩特地區“此地話”(方言)成為三順店社區各民族共同的交流語言,語言是思維的外殼、思想的外衣,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采取了有利于或加速彼此理解的語言形式,在生活習慣、思想習慣上也會向對方學習,客觀上縮小了文化的距離感。
在飲食習俗方面,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牧區,漢族和蒙古族的飲食習慣、飲食結構和烹調方法已呈彼此借鑒、相互融合的態勢,“吃蒙餐還是吃漢餐”已經不是一種民族禁忌,而是禮儀謙讓之舉;非穆斯林與穆斯林相處時,能夠明確穆斯林的習俗禁忌,尊重穆斯林的生活習慣和飲食習俗。三順店社區內有一幢獨具特色的“宗教樓”,里面居住的多為宗教人士,藏傳佛教的活佛、伊斯蘭教的阿訇、基督教的牧師等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居民能夠在同一居住環境中和諧相處,不僅因為社區是居民生活所依賴的利益共同體,還因為能夠在差異中尋求共同:所有宗教都尊重生命,認為生命是有尊嚴的,其共同的價值觀和目標取向是充滿善意的包容和勸諫。這便是“多元”和“一體”的相互依存關系,多元和差異不是相互折損、相互否定,而是相互補充、相互成就,在求同存異中體諒海涵、共同發展。
除了日常交往,三順店社區還通過舉辦一系列豐富多彩的主題活動,為各族居民提供多元文化交流,“民族講堂”“社區烏蘭牧騎”“傳統美食節”等已成為社區特有的宣傳品牌,以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幫助大家了解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使其逐漸認識到中華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歷史,使各民族居民相互欣賞、相互包容、相互尊重,形成和諧共濟、手足相親、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使各族群眾在寓教于樂中受到了潛移默化的民族團結教育,由居住互嵌上升為心理互嵌。
三順店全稱為三順車馬大店,解放前這里是呼和浩特市南來北往的必經之地,店主取名的用意為“來順去順生意順”。三順驛站在當時架起了一座交流物產、連通人心的橋梁, 豐富了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增進了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今三順店社區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心相通—— 社情順,情相融—— 民心順,力相合——民族團結事業順。通過多年的努力,三順店社區先后被授予“全國和諧社區示范社區”“內蒙古自治區黨建示范點”“內蒙古自治區先進基層黨組織”“內蒙古自治區先進文化社區”“內蒙古自治區人民團結進步示范社區”等榮譽稱號,2021年,獲得中共中央“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殊榮。三順店社區的成功經驗表明,和諧融洽的民族關系是實現民族團結的根本途徑,而和諧民族關系的構建需要一定的空間基礎支撐。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指出,空間的社會屬性遠比其物理屬性具有實質性意義,缺乏一定空間基礎的支撐,諸多社會行動必然無法開展。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區環境,可以從居住空間、學習空間、娛樂空間等方面入手,營造各民族共居、共學、共事、共進的空間環境。
六、結語
本文以民族團結模范自治區內蒙古為例,探討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徑。需要指出的是,這五種實踐路徑不可能是一刀切式的,它一定是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條件和特點而定。從“治理”的角度講,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研究屬于邊疆治理范疇,“除了安全因素外,必須兼顧文化、宗教和發展上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總之,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邊疆地區在治理上還是應該‘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而且必須是在民族文化的語境中來這樣做。”[15](120)這也正是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的基本特征:尊重歷史、符合國情、順應人心,承認民族多樣,在多樣中求統一,在差異中求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