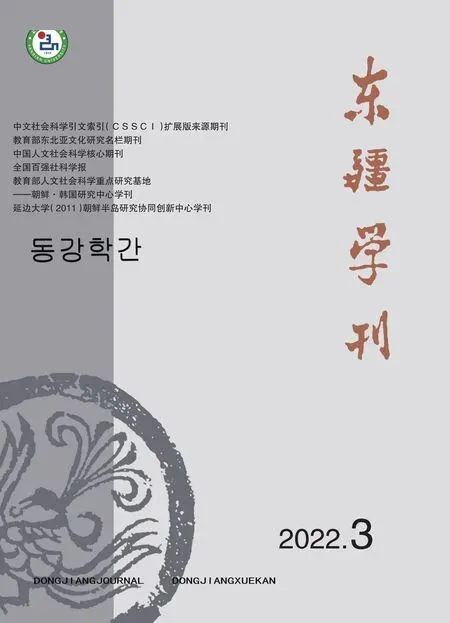近現代韓國翻譯小說《二十春光》的發掘與其原作考證
車勇
目前關于近現代韓國的中國文學接受史的諸多研究,大多集中在“純小說”的中國新文學題材上,而對中國通俗小說的影響卻鮮有提及。在近現代韓國,各種單行本形式的中譯本重譯小說、中文古典小說被連續出版并且深受廣大韓國讀者喜愛,足以說明中國通俗小說對韓國文學的影響并不亞于中國新文學。作為本文考察對象的《二十春光》,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查明其是否為翻譯或改寫的作品。筆者通過考證首次確認了《二十春光》是中國清代才子佳人小說《駐春園小史》的翻譯之作這一事實。
《二十春光》是以《駐春園小史》為原作翻譯而成的,兩部作品的故事主線和情節基本一致,兩部作品均以明代嘉靖年間為時代背景,以男主人公黃階與兩位女主角曾云娥與吳綠筠結緣及婚事障礙的故事為中心展開。筆者認為,對《二十春光》這一作品翻譯事實的發現和認定,可以視為中國原創通俗小說在韓國接受的一個重要部分,對完善和補充韓國近代翻譯文學史研究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論及始于開化期的韓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翻譯與改寫”問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一方面是一種意識形態傳播的手段,另一方面又意味著韓國新小說風格的嘗試。1930年以前,韓國的翻譯或改寫作品大多是經由日本的重譯作品,相關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韓國與日本的影響關系上。《二十春光》是韓國對中國原創小說的翻譯,本文將以《二十春光》為譯作的事實為基礎,探討其與原作《駐春園小史》之間的影響關系,并通過兩個文本的比較,考察其中的“翻譯與改寫問題”,揭示該作品作為翻譯小說的特殊地位和意義,進而揭示中國近現代原創通俗小說對韓國近代文學的影響,補充和完善韓國的中國文學接受史研究中的缺失部分。
一、《二十春光》與《駐春園小史》的基本影響關系
《二十春光》是1925年12月20日大成書林發行的韓文活頁本小說, 封面上標有“戀愛小說”一詞。版權頁上標注的著作兼發行人是大成書林的社長姜殷馨,然而正文首頁上注明的卻是樸萬熙(字謙齋)的名字。當時在韓國新小說版權頁中,通常用受讓著作權的發行者或其他所有者的名字代替原作者標記為“著作兼發行者”。[1](303)由此看來,這部作品的實際作者應該是樸萬熙,作品篇幅約2萬字,共50頁,每頁13行。
《二十春光》中的人物、時間、地點都是以中國為背景,可以推斷它是中國小說的翻譯作品,但目前為止,從來沒有人提及過這部作品以及它的原作,也就是說還沒有人對于該作品是原創小說還是翻譯、改寫的小說進行論證。筆者通過考證首次確認了這部作品是中國清代才子佳人小說《駐春園小史》的翻譯本這一事實。這兩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主線基本一致,描寫的都是黃階與曾云娥以及吳綠筠結緣的愛情故事。其主要情節為:父母早亡的男主人公黃階在他和吳綠筠早年定下的婚約告吹后,與相鄰而居的曾云娥邂逅并結緣。云娥因家禍避難到嘉興,黃階為了尋她選擇離鄉并淪為他人家的仆人,其間甚至被小人誣陷為殺人犯,但最終克服種種困難后與云娥以及綠筠結成良緣。
《二十春光》的原作《駐春園小史》,是一部章回體才子佳人小說,又名“一笑緣”“綠云緣”“雙美緣”“三合劍”“雙美緣前傳”“駐春園外史”。《駐春園小史》的各種版本有:乾隆三余堂簡本(1782年)、乾隆戊申簡本(1788年)、乾隆癸卯萬卷樓刊本(出版年代不詳)、嘉慶十六年刊本(1811年)、忠華堂簡本(出版年代不詳)、道光元年寫刻精刊袖珍本(1821年)、光緒丙子惟女堂刊版本(1876年)、光緒丙申點香閣石印本(1876年)、進步書局石印本、廣西戊中中華圖書館石印本(1908年)、光緒甲午君玉山房石人本(1894年)、光緒丙申中西書局石印本(1 896年)、宣統更戌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1910年)、宣統二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1910年)、上海書局石印本(1920年)、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鉛印本(1935年)等。[2](49)關于作者,雖然在作品中可見“吳恒野客 編次”“水若山人評悅”等字樣,但對于其準確身份至今難以確認。在現傳的《駐春園小史》版本中,最古老的是1782年的三余堂簡本。從其序言中記載的“乾隆壬寅年菊月上浣水箬散人書于椀香齋”等字樣來看,這幅作品的創作時期應該是在1782年左右,至于撰寫序言的上浣水箬散人,還沒有翔實的記錄。《駐春園小史》共24回,開頭有序言、開宗明義,每回的前首有“開頭詞”,末尾部分有“回評語”,“回評語”是對相應章節的大意說明。
彼正在癡想之間,忽見司墨上樓,對司翰道:“明日公子訂李相公諸公往印峰溪舟遊,命弟同兄偕往”。生道:“公子此命,誰敢不從。”到次日,生與司墨遂跟周公子大家入船。正登舟時,忽把舟人細認,似曾經會過,又不敢記憶,恐露事機。不逾時,諸少年俱已登舟。[3](31)(《駐春園小史》第5回)
有一天黃公子與周公子的諸友同去“印峰溪”仙游,忙著安排飲食,忽聽背后有人說:“這不是黃玉史嗎?怎么會在這兒?”黃公子大驚,回頭一看,原來是從未見過之人。[4](14)(《二十春光》第3回)
通過對兩部作品中段落的對比可知,《駐春園小史》里的空間背景及地名與《二十春光》的如出一轍。比如周尚書和黃階一起前往的地點“印峰溪”。此外黃階受難、王慕荊被營救的地點“大義山”,以及黃階與曾云娥相會的“紅螭閣”等地點指稱也相同。由此可見,《駐春園小史》和《二十春光》的影響關系還是比較明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春光》出版之前的1916年,韓國匯東書館出版了一部活頁本小說《雙美奇逢》,它是《駐春園小史》的另一個譯本。《雙美奇逢》的作者為李圭容,發行者為高裕相。《雙美奇逢》和《駐春園小史》一樣,由24個章回組成,每回都有標題。《雙美奇逢》省略了原作的序言、開宗明義、開場白、評語等,也省略了很多詩詞文本。另外在內容上,《雙美奇逢》采取了縮譯的方式,但大體上忠實于原作的故事情節。《雙美奇逢》是目前韓國已知的第一個關于《駐春園小史》的翻譯版本,而《二十春光》相當于《駐春園小史》的第二個翻譯版本。
那么,《二十春光》究竟是以原作《駐春園小史》為底本還是以《雙美奇逢》為底本進行翻譯的呢?從結論上說,《二十春光》是直接用原作《駐春園小史》作為底本進行翻譯的,事實可以從下面的引文例子中得到證實。
卻說云娥母舅葉總制,素與部將蘇廷略有隙。不期邊人犯境,葉公臨陣被擒乃與族兄廷策疏葉公通某叛逆。旨下,以葉公擬罪當族[3](17)(《駐春園小史》 第3回)
話說云娥的舅舅葉總制早與部將蘇廷有隙,正好葉總制被邊疆夷人俘虜。 此時,蘇廷趁機誣陷葉公與夷人私通,刑部遂抄了葉府。[4](11)(《二十春光》 第2回)
卻說,小姐的舅舅葉總制與部將蘇廷略有嫌隙。此時正遇盜賊犯境,葉公御敵戰敗,蘇庭略同其族兄蘇廷策誣告葉公與賊通謀,刑部密行公簿至本部,捉其家屬。[5](16)(《雙美奇逢》 第3回)
上面的引文是解釋作品中葉總制受難原因的一段,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蘇廷略是蘇廷策的弟弟。在翻譯蘇廷略的名字時,《雙美奇逢》完全遵循了原本的指稱,而《二十春光》則誤譯為“蘇廷”。“與部將蘇廷略有隙”一詞,僅就其本身而言,既可譯為“與部將‘蘇廷略’有嫌隙”,也可譯為“與部將‘蘇廷’略有嫌隙”。《二十春光》的譯者因誤譯而選擇后者,這是對文章整體脈絡和漢語語句缺乏了解所致。如果《二十春光》是以韓文版《雙美奇逢》為底本,就不可能存在這樣的誤譯。因此,通過以上翻譯案例的比較,可以確定《二十春光》是直接以原作《駐春園小史》為底本翻譯而成的。
二、《二十春光》的翻譯態度
《駐春園小史》有24個章節,而《二十春光》共有13個章節。從大體情節上看,譯作的一個章節相當于原作兩個章節,可以看出《二十春光》的譯者在翻譯原作的過程中省略了不少內容,其特征之一就是刪除了原作中單獨插入的漢詩、詞,以及主人公們來往所用書信等大部分文本。原作《駐春園小史》中插入了43首詩詞,而《二十春光》只插入其中的5首。例如穿插于《駐春園小史》第六回的《南歌者》和《念奴嬌》在《二十春光》中就被省略,這兩首詞是單純強調云娥和綠筠才藝的部分,即使省略也不會對作品的大體情節產生影響。除此之外,周公子和他的朋友們在游樂時一起創作的詩、云娥和綠筠表達愛慕黃階的詩等,同樣被刪除。原作中插入的漢詩被大量刪除,可以判斷是譯者考慮到了韓文讀者更注重小說情節的推進以及人物的刻畫,而不是詩歌在小說中起到的形式意義。當然,譯者對部分原作中的詩歌還是有所保留,比如:
綠云倩翦舞春衣, 斜拂紅梨度翠微。細雨捲簾情脈脈,清風歷檻影依依。
妝樓愛結同心夢,畫閣曾期比翼還。縱有煙波分去路,暹君一水伴干飛。
芭蕉樓 曾云娥 題。[4](9-10)(《二十春光》第2回)
此詩是黃階第一次見到云娥時從她那里得到的。通過此詩,黃階對云娥第一次感受到了愛意,從而促成了他們的邂逅。《二十春光》保留了這首詩,是因為它在黃階與云娥結緣中起著重要的契機作用。即譯者為了將焦點放在男女主角的結緣上,選擇性地刪除或保留了原作中的插入文本。
大部分清代才子佳人小說都是以大團圓結局收場。才子佳人相遇之后遭遇小人,他們的婚事遇到障礙,最終才子佳人克服困難并終成眷屬,同時小人也得到懲戒,這就是其慣用的敘事模式。《駐春園小史》和他的譯作《二十春光》莫不是如此。不過與其略顯單調的敘事模式相比,這兩部作品的具體情節推進過程卻相當復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性。除了主人公黃階、曾云娥、吳綠筠以外,云娥的侍婢愛月,云娥與綠筠的母親,黃階之友歐陽穎和王慕荊,周尚書與周公子等功能性人物也對故事情節的發展起著重要的銜接作用。而《二十春光》與原作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對這些人物的敘述。
關于人物敘述,改動最大的屬綠筠的部分。《二十春光》刪除了原作第一回中提到的綠筠和黃階的婚約談。原作在第一回就已經向讀者道破了綠筠的身份以及她與黃階的關系,但在《二十春光》中,直到中半部才能發現這一事實。
根據《二十春光》中不同于原作的設定,綠筠與黃階早年有婚約的事實直到綠筠偶然收到黃階寫給云娥的信后才得以揭示,在綠筠親口說出自己和黃階的故事之前,只有她本人知道真相,而讀者是無從得知的。以讀者的視角來說,這一事件被解釋為是偶然發生的,而不是敘述者直接披露的。這一事件是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直到小說的中間部分才被讀者們認知。這種偶然性的設置雖然不足以改變故事主線,但自然可以成為增加小說興趣的要素。《二十春光》的譯者在意識到讀者的同時,有意介入到作品敘事中,以改變敘述時間的手法對原作進行改編,從而使作品的敘事在中半部獲得了新的動力,這種改編手法可以有效地體現譯者的翻譯意圖。另外,《二十春光》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原作里部分反派人物的結局進行了改動。例文如下:
葉總制流放歸來,辭官隱居,葉夫人母女不時去探望。[4](49)(《二十春光》 第13回)
未幾,而葉總制亦以奉赦回朝,旨以蘇廷策誣諂罪,亦發戍邊。葉總制回朝,遂乞假歸家。即于舊居,重新府第,與生第宅俱見輝煌相映。而云娥小姐亦往慶賀,不勝歡喜。[3](138)(《駐春園小史》第24回)
上面的引文是結尾部分中關于葉總制和蘇廷策的一小節。蘇廷策作為反派人物,對整體敘事進程起銜接作用。因為他對葉總制的誣陷,才使得男女主人公結緣的故事情節得以發展。在《駐春園小史》中,葉總制得到赦免重回故土,同時,陷害他的蘇廷策也受到了處罰,但在《二十春光》中,蘇廷策的結局被省略。這種改動,使原作中懲惡揚善的格局在譯作里被削弱,也使得原作中慣用的古典小說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了。當然,像蘇廷策這樣的人物只能算是功能性人物,他的存在是情節需要,對作品的主題以及主要情節是無關緊要的。[6](88)
總而言之,《二十春光》的譯者為了推進敘事進程,突出作品的趣味性元素,大體上保留了原作情節,還大量刪除了對主要故事情節并非必要的詩歌等文本。而對于原作中人物的改動也只限于其敘述方法,譯者的主要翻譯目的還是為了突出原作的娛樂性而不是其主題。
三、結論
本文首先闡明了韓國大成書林出版的活頁本小說《二十春光》(1925)是中國清代才子佳人小說《駐春園小史》的翻譯作品這一事實。通過兩部作品的對比不難發現,兩個作品的主要故事情節和人物類型基本一致,《二十春光》大體上照搬了《駐春園小史》的故事情節,但也省略了很多內容,應屬于縮譯本。《二十春光》和《駐春園小史》都是以明代嘉靖年間為時代背景,故事以男主角黃階和兩位女主角曾云娥、吳綠筠結緣及婚事障礙情節為中心展開。
在《二十春光》出版之前的1916年,韓國匯東書館出版了一本小說《雙美奇逢》,它是《駐春園小史》的另一種譯本。《雙美奇逢》是目前已知的韓國第一個關于《駐春園小史》的翻譯案例,而《二十春光》相當于《駐春園小史》的第二個翻譯案例。通過對上述三部作品的比較,確認《二十春光》是直接以《駐春園小史》為底本翻譯而成的。
《二十春光》的譯者為了迅速開展主要故事情節和突出作品的趣味性元素,在選擇大體保留原作情節的基礎上,大量刪除與主要敘事情節無關的文本部分,并且采用了改變敘事時間等翻譯方法,使原作中慣用的“古典小說元素”在譯作中被削弱,進而使得譯作的娛樂性質更加突出。
在開化期及日帝強占期的韓國文學作品中,翻譯及改寫作品占很大比重。迄今為止,韓國近代翻譯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與日本的影響關系,很多文本的直接參照物都來自于日本。不過近來的研究表明,韓國近代翻譯小說的輸入途徑遠比想象中豐富,越來越多的文本被證明受到了中國的影響。如韓國近代初期具有代表性的“新小說”作家李海朝的大部分所謂原創小說其實都是受了明代小說《今古奇觀》的影響。而筆者所發現并探討的文本《二十春光》也屬于此類。此類文本被不斷發掘,也說明了中國文學對韓國翻譯文學及原創文學發展初期的影響比想象中要大。可以說,《二十春光》是一部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它雖非韓國所認為的“本國原創小說”,而是一部中國通俗小說的譯作品,但對它的研究,對進一步探究韓國近現代所謂“創作小說”的真實來源及虛實有著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