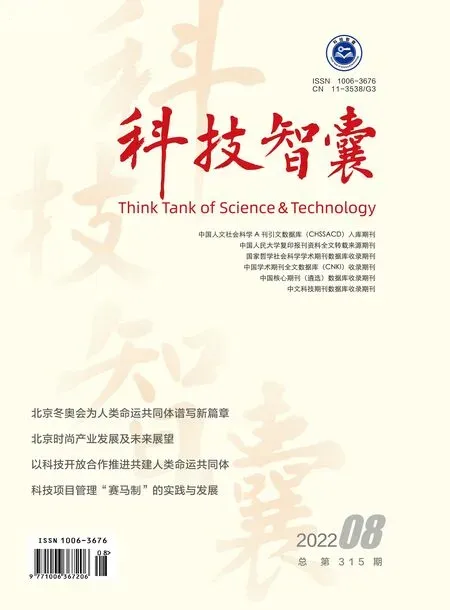數字化背景下學術期刊編輯隊伍的規范化建設
——基于合規性視角的考察
廖吉廣
《山東社會科學》雜志社,山東,濟南,250002
學術期刊作為呈現研究成果的平臺、溝通作者讀者的紐帶、集結學派同人的陣地和學術潮流的特殊推手,在學術研究建制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認為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中處于樞紐地位。[1]可以這樣說,學術期刊的發展和繁榮,已經極大改變了傳統意義上學術生產和知識傳播的路徑、機制和效率,成為衡量學術現代化、專業化程度的重要參考項。學術期刊的編輯直接負責學術期刊的日常運作,他們的學術眼光、學術品位以及編輯隊伍的構成直接關乎期刊創辦的好壞,這無疑對期刊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影響,可謂責任重大。
目前,學界圍繞學術期刊編輯的職業素質培養、職業認同與焦慮困惑等問題已經做了大量探討,但這些研究多是基于編輯個體或是期刊社(編輯部)整體來討論的。學術期刊編輯隊伍建設發展現狀如何,還存在哪些不足,行政管理與業務實踐之間如何有效平衡,這些問題仍有待深入討論。鑒于此,筆者嘗試立足數字化的時代背景,結合202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技部發布的《關于推動學術期刊繁榮發展的意見》以及其他相關部門發布的各類文件要求,從合規性角度來探討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問題,并立足學術期刊出版環境提出可行性建議。
一、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現狀與不足
系統梳理政府出版管理部門長期以來發布的各項規章制度不難發現,國家在學術期刊編輯隊伍管理方面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于相關規定發布時間較早且期刊出版環境已發生較大變化,特別是在數字化發展日新月異的當代社會,這些規定在具體貫徹落實過程中往往不盡如人意,亟待重新厘清、加以規范。
(一)學術期刊編輯的資質問題
學術期刊編輯的資質,主要是指期刊出版單位負責人和各級審校人員符合有關資質要求,編輯隊伍的專業素養和編校力量能夠支撐期刊正常出版。對此,政府出版管理部門有著明確的規定。例如,2008 年,我國新聞出版總署印發的《出版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管理規定》第四條明確強調:“凡在出版單位從事出版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員,必須在到崗2 年內取得出版專業職業資格證書”“在出版單位擔任責任編輯的人員必須在到崗前取得中級以上出版專業職業資格,并辦理注冊手續,領取責任編輯證書”。而對于在出版單位擔任社長、總編輯、主編、編輯室主任(均含副職)職務的人員,《關于報刊社社長、總編輯(主編)任職條件的暫行規定》《關于規范報紙期刊主要負責人任職資格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出版單位總編輯工作的意見》等文件都分別對其任職資格作出了規定。
在具體的業務實踐中,出版管理部門對“三審三校”制度的貫徹有明確規定。例如,2019 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在開展“三審三校”制度執行情況專項檢查時指出:初審應由出版單位具有編輯職稱或具備一定條件的助理編輯人員擔任(一般為注冊責任編輯);復審應由出版單位具有副編審以上職稱的人員擔任,復審人員應為出版單位中層及以上負責人;終審應由具有正、副編審職稱的社長(副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或報刊編輯部主編擔任。“三審”中任何兩個環節的審稿工作不能同時由一人擔任。[2]校對人員亦有相應的任職要求。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受管理模式和單位規模的制約,不少學術期刊編輯存在資質與崗位不符的情況,這主要體現在3 個方面:1.期刊負責人主要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投入期刊業務管理的時間精力有限,履行終審職責不到位,存在“掛名”“缺位”問題;2.編輯人員多參與教學、科研序列職稱評審,不具備出版序列職業資格;3.學術期刊編輯隊伍普遍規模較小、學科方向比較分散,難以形成滿足“三審”需要的人員結構。
(二)學術期刊編輯職業教育培訓的落實問題
編輯隊伍的職業教育培訓帶有普遍性,對此國家有明確的規定,學術期刊編輯自然也不例外。就編輯繼續教育培訓來說,2020 年9 月由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印發的《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定》第十三條規定:“出版專業技術人員參加繼續教育的時間每年累計不少于90 學時。其中,專業科目學時一般不少于總學時的三分之二。”在此之前,編輯參加繼續教育時間要求是每年累計不少于72 學時。就期刊負責人的培訓來說,2005 年,我國新聞出版總署印發的《期刊出版管理規定》第五十五條明確規定:“期刊出版單位的社長、總編輯須參加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組織的崗位培訓。期刊出版單位的新任社長、總編輯須經過崗位培訓合格后才能上崗。”也就是說,期刊負責人不僅要參加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還應該接受政府出版管理部門組織的崗位培訓。
就具體情況而言,雖然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實行的是統籌規劃、分級負責、分類指導的管理體制,但是學術期刊編輯的職業培訓在實踐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其一,少數學術期刊負責人對職業繼續教育培訓重視不夠。學術期刊負責人多為研究型學者,部分主編忙于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處理行政事務,沒有精力組織和參加政府出版管理部門的培訓。其二,繼續教育培訓供求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現有的培訓無法滿足需要。以“第六十七期全國期刊負責人崗位培訓班”為例,《關于舉辦第六十七期全國期刊負責人崗位培訓班的通知》明確培訓對象為未參加過期刊主編崗位培訓班或取得《崗位培訓合格證書》已滿5 年的期刊主編、編輯部主任(均含副職)。[3]但是報名系統剛剛開通,報名人數就已經達到上限,說明全國范圍內需要參加培訓的期刊負責人尚有不少,學術期刊同樣面臨此類問題。其三,繼續教育學時認定缺少必要的操作指引。2020 年印發的《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定》明確了編輯參加繼續教育的形式及學時計算標準,這對學術期刊編輯來說更是政策利好,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學時認定標準不明確、權責劃分不清晰等難題,可操作性不強。
(三)數字化轉型與學術期刊編輯的自我認同問題
辦好學術期刊,離不開既敬業又專業的編輯隊伍。當前的學術期刊編輯隊伍存在自我認同問題,嚴重制約著學術期刊的長遠健康發展,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編輯人員的自我認同危機之所以存在,與主辦單位的辦刊模式密切相關。[4]在現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出版單位中的出版社是主體和主流,相關政策的制定也多是基于出版社的實際情況,而對期刊特別是學術期刊來說,適用性有些不盡如人意;學術期刊被邊緣化,學術期刊編輯被定性為輔助性工作人員,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術期刊普遍規模有限,編輯隊伍多由教學科研崗位工作人員兼任,無法形成穩定的專職編輯隊伍。特別是隨著數字化出版的興起,學術期刊編輯面臨嚴峻的角色挑戰,必須從傳統認知中的學術編輯、文字編輯向數字化編輯轉型,這極大沖擊了學術期刊編輯工作內容的純粹性,致使他們的自我認同度持續降低。
二、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的路徑
客觀來說,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存在不足,是多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針對前文所述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存在的問題,相關部門應積極順應數字化發展的時代潮流,考慮學術期刊編輯隊伍的實際和工作內容的特殊性,從以下方面著手加以解決。
(一)明確崗位考核側重點,優化職稱評審程序
對于學術期刊負責人,應加強任職資格的前置審核把關,嚴格按照崗位職責履行情況進行評價考核。應著重考核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期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等情況,并將考核結果與工資待遇掛鉤,切實起到對編輯群體的激勵促進作用。針對學術期刊編輯從業資質不合規問題,應明確參與教學、科研序列職稱評審的編輯亦應參加繼續教育培訓、取得責任編輯證書,并以期刊年檢為抓手倒逼推動學術期刊編輯合規化。在繼續完善不同序列職稱轉評的基礎上,開展第二職稱評審新探索(即在取得一個職稱的基礎上,根據工作需要申報第二職稱),突出以出版實績為價值導向,注重評價出版專業技術人員的能力素質和工作業績,方便具備其他序列職稱的編輯參加出版序列職稱評審。
(二)完善繼續教育配套措施,打造數字化出版培訓平臺
針對職業教育培訓標準提高、相關配套措施不足的問題,應逐步搭建全國統一的數字化出版培訓平臺,完善學術期刊負責人崗位培訓和從業人員繼續教育培訓體系。一方面,加大培訓供給。利用數字化手段開展行業調查,摸清學術期刊和學術期刊編輯“家底”,系統梳理學術期刊負責人崗位培訓和編輯繼續教育培訓需求,基于大數據算法合理劃分培訓職責,確保各項培訓需求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增強政策可操作性。例如,針對出版專業技術人員參加繼續教育的不同形式,明確不同形式學時認定需提交的證明材料,盡可能簡化學時認定程序。建立完善各級出版協會、期刊協會、編輯學會等,使其能夠在政府出版管理部門指導下有序開展工作,合理分解培訓任務,提高培訓內容針對性,滿足學術期刊編輯的學習和實踐需要。
(三)暢通職業發展渠道,促進人員雙向流動
學術期刊在學術評價和學術生態鏈條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從這個角度上講,學術期刊編輯的職業發展也應得到足夠的重視。應把編輯工作擺在與教學、科研同等重要的位置,暢通學術期刊編輯職業發展渠道,適應數字化轉型需要,轉變編輯角色定位,增強編輯職業認同感和價值獲得感。與此同時,還可探索教學科研人員與辦刊人員定期交流輪崗制度,鼓勵人員雙向流動,進而推動學術發展與學術出版深度融合。為此,應適當修改相應的管理規定,如實行以崗定責,針對工作人員在不同崗位的職責適用不同的考核標準,確保考核結果客觀、合理、公正,解除人員流動、崗位變動的后顧之憂。
三、結語
學術期刊的繁榮發展離不開專業穩定的期刊編輯隊伍,梳理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的情況不難看出,編輯隊伍在規范化建設上還存在不足,如學術期刊負責人對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重視不夠,編輯在從業資質和職業教育培訓方面還存在與政策規定不符的情況,相關評價標準導致編輯自我認同感較低等。從合規性的角度加以審視,以上問題的解決需要政府出版管理部門、期刊主管主辦單位、學術期刊編輯等通力合作。為此,應積極順應數字化發展的時代潮流,充分利用各種數字化技術手段,在完善制度配套、強化崗位考核、暢通人員流動等方面下功夫,將政策規范與期刊實際相結合,實現學術期刊編輯隊伍規范化建設有序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