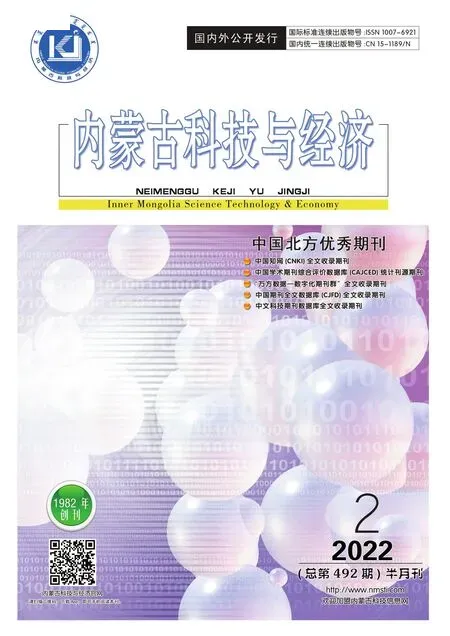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研究
——來自內蒙古的實證
尹 璐,劉玉春
(內蒙古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年—2022年)》提出加大金融扶貧力度,把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金融普惠增強了貧困人口的資金可得性,對貧困問題的持續解決起到了重要作用。國內外相關組織致力于金融機構扶貧業務的開發,普惠金融的實踐也證明了通過為有需要群體提供恰當有用的金融服務,為貧困家庭供應資金扶持,擴大投資與生產,提高自身收入水準,能夠達到減貧的效果。自2005年聯合國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來,普惠金融成為各國學術界和政界高度關注的一個新的重要范疇。2013年,中國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通過資金在金融媒體上的有機良性流動,利用金融支持促進農民收入增長,抑制農民貧困回退。金融是經濟的血液,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流轉融通。我國一直大力發展脫貧事業,不斷加大金融扶貧力度,至2020年底我國完成脫貧攻堅任務。惡劣自然環境狀態下的貧困人口在2020年全面脫貧以后,面臨了諸多新的問題與挑戰:進入后脫貧時代,貧困人口的脫貧效果能否保持?金融扶貧的效果是否能持續為積極正向的?環境惡劣條件下的貧困人口對于金融的需求怎么滿足?所以進入后脫貧時代,脫貧工作更需要思考金融支持如何發揮作用。
內蒙古位于我國西北部,緯度高、屬于半干旱干旱氣候地區。內蒙古農牧交錯帶的降水量低,風沙大,自然生態環境脆弱,資源環境的承載力低,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較差,農牧民生產方式單一,經濟來源較少,經濟生活抗風險能力薄弱,致貧返貧可能性大,是我國集中的貧困地帶。要想實現可持續脫貧,持續的金融支持必不可少。筆者基于實地調研,采用DEA方法,測算了內蒙古農牧區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為內蒙古農牧區普惠金融減貧策略提出政策建議,為后脫貧時代的普惠金融減貧發展提供思路。
1 文獻綜述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口多、收入低,金融需求潛力大(星焱,2015)[1],有關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的相關研究較為豐富。閆述乾等(2015)分析甘肅省財政支持和金融支持的效果后發現農民使用自有資金的農村扶貧效果最顯著,其次是財政支持,最后是金融支持[2]。郭小卉,馮艷博(2020)探索了后脫貧時代金融扶貧向普惠金融的轉型問題,指出現有扶貧模式的核心在于政府主導,金融為輔助,脫貧成效顯著但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能力不足[3]。薛曜祖等(2019)研究發現,投入規模不足和創新不足制約了我國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導致我國各區域農村金融扶貧效率差異顯著,空間上呈現“中部>西部>東部>東北”的格局[4]。金融包容性對減少貧困和增加收入的影響具有異質性,非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減貧效果明顯高于貧困地區,貧困地區金融政策明顯抑制農村金融扶貧效果,貧困程度越深抑制程度越大,總體上農村金融有利于扶貧但部分貧困縣扶貧效果不顯著。(王漢杰等,2020;鄭秀峰,朱一鳴,2019)[5,6]。
在研究方法和構建指標體系上,張晴,龔亮(2020)采用工具變量雙固定效應模型,利用基于扶貧縣的普惠金融指數實證分析了金融普惠政策對減貧的異質效應,認為普惠金融政策對增加農村可支配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定向扶貧貸款政策更有益于減貧;非貧困縣、省級貧困縣和國家級貧困縣的減貧力度呈下降趨勢[7]。黃敦平等(2019)基于中國金融普及指數(IFI)構建了農村貧困人口扶貧理論框架,指出中國金融普及水平在2010年—2016年期間不高但呈上升趨勢,金融普及發展水平達到拐點值后,其遞增效應減弱[8]。馬菲,杜朝運(2017)利用我國各省2005年—2013年的數據構建普惠金融指數,認為通過促進普惠金融增長可以對減貧起間接作用[9]。武麗娟,徐璋勇(2018)運用模糊斷點回歸方法對農村普惠金融扶貧和經濟增長效果進行了實證驗證。結果表明:東部地區金融普及的發展在降低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程度的同時還促進了經濟增長;在中部地區,發展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絕對貧困水平和相對貧困水平,但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在西部地區,發展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絕對貧困水平,但相對貧困增加,抑制經濟增長[10]。所以在農村金融普及過程中應注意區域差異,最大限度地發揮金融的積極作用,這也印證了前人的觀點。盧盼盼等(2017)基于貧困家庭空間結構,構建了理論分析框架,分析表明享受普惠金融服務的貧困家庭可以跨越貧困線進入非貧困家庭,無法獲得金融服務的貧困家庭就會陷入“貧困陷阱”。從各個維度來看,增加貸款密度的扶貧效果更加明顯[11]。因此,要更好地發揮金融普及在扶貧中的積極作用,適當發揮金融服務的普及效應。
研究者們對于普惠金融減貧問題從不同領域、方法、理論分別印證了普惠金融幫助窮人增收的積極作用,普惠金融是發展經濟學和金融發展理論的重要延伸。現有的文獻在理論和實證上奠定了一定基礎,但是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普惠金融減貧對于農牧戶而言是否切實有效?普惠金融在中國進入后脫貧時代以后怎么可持續地發揮作用?
2 普惠金融減貧發展
金融扶貧的最終呈現方式是金融機構向農戶發放貸款,農戶減貧依賴于農業產業的發展與振興,農戶向產業所需的固定資產投資量是發展產業的重要支撐,因此金融機構涉農貸款數額和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可以反映金融減貧投入的指標。貧困發生率可以直接反映出多年來農戶減貧的動態變化趨勢,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支出可以檢驗貸款是否帶動了農戶家庭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表1 2012年—2018年內蒙古農牧區普惠金融減貧情況
2012年—2018年,隨著內蒙古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力度不斷加大,農戶固定資產投資程度總體持續加深,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不斷上升,貧困發生率快速下降,普惠金融減貧效果明顯。截至2018年末,照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內蒙古農村牧區貧困人口為14萬人比2017年減少23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0%,比2017年下降1.7個百分點,減貧速度為62.7%,是近年來減貧速度最快的一年。內蒙古31個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農村牧區貧困人口為13萬人,比2017年減少20萬人;貧困發生率為1.9%,下降2.9個百分點。內蒙古貧困地區農村牧區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達到10 965元,同比增長11.3%,增速比2017年提高1.5個百分點。

表2 2018年內蒙古貧困地區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況
2018年,內蒙古貧困地區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比全區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1.6個百分點;收入水平比全國貧困地區農村平均水平高594元。十八大以來,內蒙古貧困地區農牧民可支配收入累計增加5 395元,累計增長96.9%,年均增長10.2%,高于同期全區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0個百分點,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與全區農牧民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收入比由2012年的1∶1.43下降為1∶1.26。內蒙古貧困地區農牧民人均工資性收入2 095元,同比增長13.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19.1%,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2.4個百分點;人均經營凈收入5 773元,同比增長11.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52.6%,拉動農牧民可支配收入增長6.1個百分點;人均財產凈收入226元,同比增長2.4%,止跌回升,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0.1個百分點;人均轉移凈收入為2 871元,同比增長10.4%,占可支配收入比重26.2%,拉動可支配收入增長2.7個百分點。
3 普惠金融減貧效應的DEA分析
DEA是一種線性規劃模型方法,計算結果是產出對投入的比值。得到100%效率的一些單位被稱為相對有效率單位,而另外的效率評分低于100%的單位稱為無效率單位。筆者采用DEA中BCC模型,假定規模收益可變,把技術效率深入分解為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的乘積。相比應用同樣廣泛的CCR模型,BCC模型應用范圍更貼合實際,而且有利于判斷目前我國農村金融扶貧效率是受純技術因素的影響還是受規模因素的影響。此外,DEA模型在實際運用過程中,導向選擇包括以投入為導向(產出一定)和以產出為導向(投入一定),根據本研究目的為測度普惠金融減貧效應,優化內蒙古農牧區金融扶貧資源投入,實現農村金融扶貧資源最佳的投入產出比,以期提升內蒙古農村金融扶貧資源利用效率,所以選擇以投入導向的BCC模型作為內蒙古農牧區金融扶貧效率分析模型。
BCC模型原理為假設有n個評價單元,每個評價單元都有m種輸入變量以及s種輸出變量,Xij(Xij>0,i=1,2,…,m)表示第j個評價單元的第i種輸入的投入量,yrj(yrj>0,r=1,2,…,s)表示第j個評價單元的第r種輸出的產出量,那么第j個評價單元的投入變量可記為Xj=(x1j,x2j,…,xmj)T、產出變量可記為Yj=(y1j,y2j,…,ysj)T,j=1,2,…,n,得到DEA的BCC模型如下:
λj≥0;j=1,2,…,n;s+=0;s-=0,θ∈E1
minθ=[θ-ε(eTs-+eTs+)]
λj≥0;j=1,2,…,n;s+=0;s-=0,θ∈E1
式中:θ為有效值,s+、s-分別表示產出、投入松弛變量。
根據模型,指標中n=535。筆者從農戶角度出發,利用內蒙古農牧區農戶調研數據分析2018年度普惠金融對農戶減貧的效應。
3.1 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筆者選取內蒙古農牧區農戶作為本次研究樣本,所用數據來自內蒙古中東部農牧區實地調研的535份有效問卷,調研期間通過訪談真實具體的了解了農戶貸款脫貧減貧情況。總體上,該區域自然條件局限,農戶收入以農業、畜牧業為主,農牧區的農村基礎建設基本完整但村里無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郵儲等金融機構。調研的農戶中,年齡在31歲~50歲占比56%,51歲~70歲占比41%,18歲~30歲占比3%;男性占比38%,女性占比62%;能決策人數占比82%;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戶僅31%;風險厭惡者占31%;風險偏好者僅占11%,絕大多數農戶的風險偏好處于保守穩健狀態。距離最近的金融機構均在10 km以內,到達所花時間在30 min以內,農戶的借貸業務辦理完畢整體所花費時間長達到2.5 h。農區農民的主要家庭收入來源多為種植業和養殖業;牧區牧民的主要家庭收入來源為養殖業。農戶經營蔬菜大棚和養殖牛的資金來源基本完全來自銀行貸款,借款渠道單一。借款規模集中于1萬~3萬, 5萬~10萬這兩個區間,具有借款規模小、還款期限短、借貸頻率高的特點。
3.2 指標選取
調研地區農戶主要收入來源為自家農業、畜牧業收入,貸款用途主要為農業或畜牧業持續投資,因此農戶家庭年收入總額作為金融支撐產業的投入指標;除生產以外,金融機構貸款用途占比第二位的是生活需求方面,因此金融機構借款數額作為另一個投入指標。對應的,資金流出即消費支出作為產出指標,具體由農戶家庭年支出情況表征。
3.3 實證分析
運用DEAP(2.1)軟件,基于BCC模型的輸入導向型,計算535份農戶調研問卷。

表3 農戶調研問卷DEA計算結果

表4 樣本效率平均值
根據DEA計算結果表示,綜合效率等于1占3.0%,純技術效率等于1占3.7%,規模效率等于1占3.0%。由此可知:從純技術效率來看,金融支持對于3.7%的農戶來說是DEA有效的;又由于綜合效率受規模效率的影響,從綜合評價角度來看,金融支持對于3.0%的農戶來說是DEA有效的。即金融支持對農牧戶的減貧效率在金融機構貸款獲得情況的有效率為3.7%,在此基礎上考慮具體借款數額因素后,減貧效率降低了0.7%。樣本效率平均值的綜合效率、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小于1,總體上非DEA有效。

圖1 規模收益變化占比情況
根據表3得到金融對農戶減貧效率的規模收益變化,如圖1所示:規模收益遞增占89.1%,規模收益遞減占7.9%,規模收益不變占3.0%。對于近90%的農戶來說,金融支持增加導致消費支出的增加程度更大;而對于7.9%的貧困戶來說,金融支持沒有帶來更多的消費能力;剩下3.0%的貧困戶,金融支持力度和消費支出能力變化持平。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研究結論
筆者基于DEA方法對內蒙古農牧交錯帶普惠金融減貧效率進行測評研究,通過實地調研數據分析得出以下結論:農戶利用金融貸款減貧程度不高,綜合考量效率僅為3.0%,金融支持對農戶的減貧作用從規模收益來看總體上處于遞增階段,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是幫助減貧的首選方式。
4.2 政策建議
為提高內蒙古農牧區普惠金融減貧效率,結合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4.2.1 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扶貧工作是一項公益性強、長期性強的社會工作,財政是扶貧工作的核心和不可缺少的支撐力量。完善財政扶貧政策,整合利用金融發展支持資金特別是扶貧專項資金,防止挪用和濫用。財政扶持基金由單純補貼貧困群體向多種形式、綜合補貼發展,培育和提高貧困家庭自我發展能力,促使農戶減貧能力內生化。
4.2.2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強涉農貸款金融支持和擔保。金融機構應降低貧困家庭貸款的門檻,鑒于金融貸款、利率高的現象,實施相應減少金融部門和財政資金貼現利息的措施,以減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貸款壓力,增加生產發展的積極性。金融機構靈活調查和運用其他擔保手段,對質押困難的貧困家庭發放貸款,建立和完善信用評估制度以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損失。從實際出發,嚴格審慎審批“三農”金融貸款,解決資金不能及時滿足需求、貧困地區融資難等問題。鼓勵金融涉農資金投向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保證高產的經濟作物、畜牧業等產業。
4.2.3 強化農戶財務管理意識,促進農戶合理使用自有資金。除了住宅、醫療、教育等必要的投資外,種植業、養殖業也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減貧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產業產生的收入,引導農民合理利用貸款資金進行生產投資是實現農民從單純的“輸血”向自我“造血”轉變的重要途徑。反貧困是一項持續性的工作,農民自身生產能力的提高是其核心。因此,要加強農村教育培訓,逐步消除知識貧困、文化貧困、觀念貧困,提高農民自身發展能力,避免出現反貧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