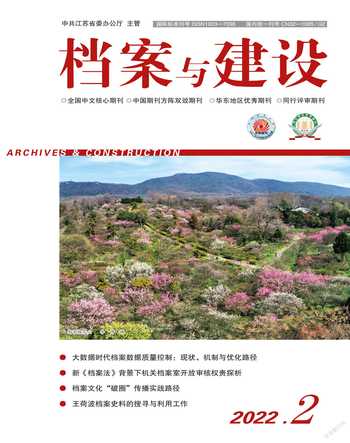由一份檔案看徐悲鴻的人品與畫品
秦靜
近日筆者發現一件來自臺灣地區的檔案,內容是1947年“國立北平藝專學生自治會”呈報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的秘密報告,報告指控徐悲鴻掩護共產黨及民盟追隨者而解聘國民黨籍教授,經與吳鑄人商榷,要求速將徐悲鴻撤換、續聘國民黨籍教授。吳鑄人(1902—1984),原名壽金,江蘇盱眙縣人。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并成為骨干分子。1946年,作為國民黨中央派系的代表,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中統”)的支持下當選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任內,利用過去國民黨中央訓練團高級班學員的人脈以及“中統”的力量積極反對中國共產黨。

報告以“呈為呈請國立北平藝專校長徐悲鴻營私舞弊掩護奸匪排擠國民黨籍教授請速予徹查并特請教部立即撤換另委適當人選以利教育事”為標題,列舉了徐悲鴻為解救被國民黨抓捕的李宗津等4名進步教員,向李宗仁“情愿以家身擔保始得釋放”等事,報告中還稱“教部曾有兩密電致徐悲鴻,請其速為解聘奸匪李宗津、馮法祀、齊振杞、沈士莊等四員。徐接電后即對國民黨籍教授懷恨,極思有所報復,故本期即將教授王靜遠……等先生解聘”云云,要求徹查并撤換徐悲鴻先生。此報告共兩頁,墨筆書寫于“毓東紙店”紅格信箋紙上,信箋紙高23.2厘米,寬39厘米。首頁上部鈐印公章兩枚,上有“三處”等字,右側上部墨筆書“三科2/8”,另有批示但被涂抹無法辨認。第二頁末尾署名“國立北平藝專學生自治會”并印有陽文朱色“藝專學生會章”一方。從其所印公章“三處”二字分析,報告應存于原國民政府教育部三處,后流出并于2011年中國書店春季拍賣會拍出。
這份檔案中所提及的相關事宜,實際發生在解放戰爭期間。真實情況其實是,1947年“反內戰、反饑餓的學生運動爆發了,進步的教師和學生們走上了街頭,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游行,事后,國民黨教育部堅決要悲鴻解聘參加示威游行的三位教授:馮法祀、高莊、李宗津,但是又被悲鴻頂了回去……當悲鴻獲悉北平警備司令部要逮捕參加游行的學生,悲鴻又立即通知他們趕快離開北平”[1]。在這期間,徐悲鴻冒著巨大政治風險,找到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表示“誓與諸君共存亡”。
報告充分展現了徐悲鴻保護愛國師生的歷史功績。檔案中提及的四位教員李宗津、馮法祀、齊振杞、沈士莊實際都是德藝雙馨的愛國青年。
李宗津(1916—1977),江蘇常州人,曾師從顏文梁、呂斯百等中國第一代油畫家。因徐悲鴻賞識其才華,1946年被聘為北平國立藝專講師。一年后,北平學潮風起云涌,李宗津因不同意開除參與運動的學生學籍而憤然離職,于1948年轉到清華大學營造系執教。他的作品立足現實,具有濃厚的人文氣息,是中國早期油畫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馮法祀(1914—2009),安徽廬江人,曾受業于徐悲鴻、顏文梁、呂斯百、潘玉良等大家,1937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到過延安;參加過抗敵演劇隊;抗戰期間堅持繪畫創作,舉辦過6次個人畫展,作品多為愛國主義題材。1946年與徐悲鴻一起到北平參與了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創辦。徐悲鴻對他的作品的評價是:“以急行軍之做法,描寫前后方動人的景象,做法深刻。”[2]
齊振杞(1916—1948),出生于北京,青年時期就讀于北師大,其間爆發“九一八”事變,他以抗日救國為己任,曾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他毅然投筆從戎,加入了國民政府軍,擔任陸軍第十二軍司令部上校秘書,直接參與抗日。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他用畫筆作武器,記錄下了日軍的暴行和中國軍民奮起反抗侵略的英勇場景。他對抗日救國的貢獻,在一份資料里是這樣描述的:“先生抗戰初期在豫、皖等地服務第五戰區,擔任戰地寫真,與目下二、三野戰軍并肩作戰,以思想前進,為劉、陳兩司令所器重。”[3]
沈士莊(1905—1986),上海寶山人,1927年畢業于上海中華藝術大學。讀書期間,他多次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游行;抗戰期間參加了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曾任教于北平藝專陶瓷系。1947年因參加“五二〇”游行,受到當時反動派的迫害,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來到解放區,任冀察熱遼聯大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
徐悲鴻積極援救愛國人士,源于一顆愛國之心。他一生為國家興亡而畫,為人民安危而畫,創作過許多鼓舞人心的畫作。
1937年,徐悲鴻創作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時徐從海外歸來不久,國內正面臨抗戰危機。此畫用淡墨渲染風雨,墨竹順應著筆勢,仿佛在風雨中飄搖擺動,沙沙作響。一塊堅石赫然佇立,向畫面右側傾斜,增加了整幅畫的危機之勢。一只雄健的大公雞昂然站立于危石之上,引吭高鳴。雞身的羽毛黑白分明,朱砂點綴的雞冠分外奪目,令人看后精神不覺一振。畫左上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丁丑始春,悲鴻懷人之作,桂林。”題詩出自《詩經·鄭風》風雨篇的第三段。作者運用象征手法來隱喻當時的國內形勢,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是以風雨象征國家、民族正處于風雨飄搖的危機之中,大公雞象征著要喚醒國人團結抗日的大號角;所謂“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是指目睹大家齊心協力共同抗日的形勢,心中不免感到慰藉欣喜。
1940年,國內戰場節節敗退,許多人對形勢持悲觀的論調,抗戰進入了極其艱難的階段。然而,徐悲鴻不為所懼,以飽滿的樂觀主義精神投入了創作。他創作出了聞名于世的《愚公移山》,在這幅畫作中,徐悲鴻獨具匠心,將西方寫實手法融于中國畫托物言志的意境之中,對古老的神話故事進行了全新的闡釋。畫面右端幾個高大魁梧的壯年男子手持釘耙奮力砸向土堆的場景,象征著中華民族的萬眾之力,傳達出一個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決心,即便這困難猶如一座大山一樣不可撼動,他們也決不放棄。
1943年,抗戰出現了勝利的曙光,徐悲鴻又創作了《會師東京》。畫中題款:“會師東京,壬午初秋繪成初稿,翌年五月寫成,茲幅易以母獅及諸雛居圖之右,略抒激憤,雖未免言之過早,旦意其終須實現也,卅十二年端陽前后,悲鴻,靜文愛妻保存。”畫中威風凜凜的群獅,象征著中國在內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雄獅個個矯健威武,英姿勃發,怒視前方,仿佛預示著一場搏殺。他們聚攏于日本富士山山頂,預言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占據勝利的制高點,迎接著斗爭勝利的曙光。
抗戰期間,徐悲鴻的藝術創作因國內形勢的需求而變,不僅有取材歷史、借古喻今的作品,更有關注現實民生的創作。他的畫充滿了民族關懷,始終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1938年至1942年期間,他多次前往香港、新加坡、印度、馬來西亞等地開辦畫展,將其所賣畫款10萬余美元全部捐獻給抗戰前線。據統計,徐悲鴻是為抗戰捐款最多的畫家。[4]在那段山河破碎、戰火紛飛的日子里,徐悲鴻以一位畫家的身份默默支持著國家,令人感佩。無論作為一位教育家還是畫家,他的人品與畫品都值得我們后人學習。
注釋與參考文獻
[1]廖靜文.徐悲鴻傳[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422.
[2]韋啟美,侯一民.急行軍的戰斗風格——看馮法祀畫展[J].美術研究,1980(03):4.
[3]密云區黨史辦.齊振杞[EB/OL].[2020-01-06]. http://www.bjmy.gov.cn/art/2020/1/6/art_4091_104995.html.
[4]黃真彥,丁英順.徐悲鴻的“抗戰畫”[N].重慶政協報,2019-08-2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