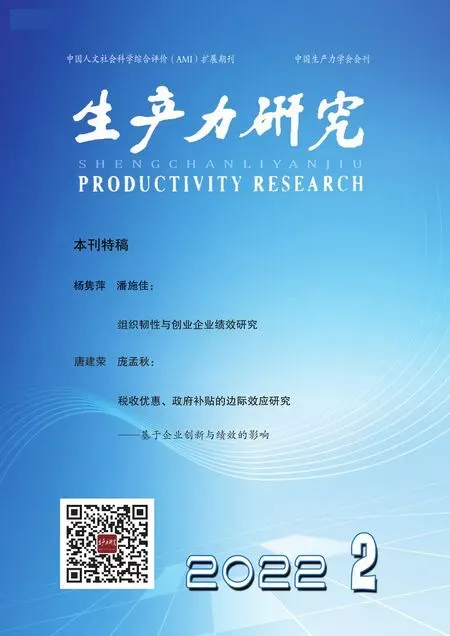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測算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供給側改革的視角
劉 嵐,徐 超
(武漢科技大學 文法與經濟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5)
一、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我們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對供給側進行結構性改革,其核心在于,重新調整錯配的生產要素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創新等要素,使其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從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指的是經濟系統的總產出量與總投入量之比,是GDP 增長主要的貢獻因素之一,解釋了GDP 變化中由傳統生產要素投入諸如資本和勞動力變化所不能解釋的部分。在人力、資本等要素一定的前提下,若全要素生產率仍然能夠增加,即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大于0,說明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內生性,能夠依賴于創新以及制度等優勢實現經濟增長。因此,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與供給側改革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息息相關。
對于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徐生霞等(2020)[1]指出,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經濟發展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路鳴(2018)[2]研究表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手段,茹少峰和魏博陽(2018)[3]文章指出,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以及宏觀效率變革的重要的測算指標;在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面,潘丹丹和張巖宏(2018)[4]用索羅殘差法探究了全要素生產率與青海省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王路(2020)[5]采用了索羅殘差法測算了全要素生產率,并以此為基礎分析其對貴州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Van Beveren(2012)[6]采用了半參數法(semiparametric)改進的索洛殘差法測算了全要素生產率;Miller 和Upadhyay(2000)[7]在分析經濟開放程度和人力資本的投入這兩個因素是否會影響全要素生產率時,也是采用索羅殘差法進行測算。黃圣雯(2020)[8]采用了數據包絡分析中的DEA-Malmquist 指數法分析了全要素生產率對我國貧困地區經濟績效的影響,李媛恒等(2020)[9]就我國制造業的TFP 增長率,使用了DEA-Malmquist 指數法進行了測算。
本文選取湖北省進行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從地理區位來看,江漢平原的存在,使得湖北成為中國北方與南方陸運交通的連接通道,同時長江與漢水使得湖北的水運交通也十分便利,因此從地理區位上分析,湖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能夠通過陸運、水運交通來帶動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二是從經濟區位來看,在我國中部崛起的戰略中,湖北省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其處于長江經濟帶,發達的水運交通網使得湖北對于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有著“承東啟西”的作用;而京廣沿線經濟帶的存在,使得在中部的湖北起著“接南連北”的作用,同時處于經濟帶以及陸運、水運中心位置的湖北,其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沿線經濟帶的經濟發展活力能產生的貢獻不容忽視。三是湖北的制造業基礎強勁,但是近幾年湖北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接下來湖北省的發展任務之一是要推動湖北省制造業高質量、良性發展,諸如推進光電子信息、汽車及零部件、醫療器械等產業集群建設,說明湖北省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遇到了瓶頸,效率趨緩,因此測算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其影響因素有利于我們了解從哪些方面推動供給側改革下湖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國內外許多學者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采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對于具體某一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文獻較為有限,對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本文采用索羅殘差法,并用卡爾曼濾波算法進行改進,來對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從而針對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結果及影響因素分析提出相應的湖北省經濟高質量發展對策。
二、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測算分析
(一)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模型選取
索羅殘差法是建立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基礎上來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考慮柯布-道格拉斯函數:

式(1)中,Yt代表經濟系統的總產出,At代表綜合技術水平,Kt代表該經濟系統的投入資本,Lt代表投入的勞動力,a 代表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1-a為勞動產出的彈性系數,0≤a≤1。
兩邊取對數我們可以得到:

式(3)~式(2)可以得到:


式(5)中,yt代表人均總產出,kt代表人均資本存量。
但是索洛殘差法有一個缺陷,即它是假設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在樣本年份期間內是保持不變的,勞動產出的彈性系數也如是。在分析湖北省2007—2019年全要素生產率變化時,這種假設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因此本文在索洛殘差法的基礎上,利用卡爾曼濾波算法檢驗湖北省這13 年間資本和勞動產出彈性系數的變動情況,決定是否可以用平均的產出彈性系數來計算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

對應的協方差矩陣為:

我們假定當前年份人均資本產出彈性系數由上一年的資本產出彈性系數和該系數的變化情況決定,即:

假定(8)式中,vt的變化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也就是,△v=0,那么,t+1 時刻的狀態向量與t 時刻狀態向量的關系用矩陣可以表示為:

即t 時刻狀態向量的協方差矩陣變換為:

考慮真實世界對湖北省相應年份全要素生產率的噪聲干擾為Wk,并假定該噪聲的分布服從正態分布,均值為0,方差為Qt,則式(9)、式(10)最終形式為:

利用極大似然估計法估計卡爾曼濾波算法中狀態轉換矩陣Fk的參數,即可了解2007—2019 年湖北省資本產出彈性系數的變化趨勢。
(二)指標體系構建和數據處理
根據可獲得性、完整性、系統性和可靠性的原則,參照國內外知名學者的有關研究以及湖北省的具體情況,本文構建了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指標體系
表1 中評價指標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湖北省統計年鑒(2007—2019 年)》和湖北省統計局官網(http://tjj.hubei.gov.cn/),為了評價指標更具合理性和可比性,對GDP 和資本存量進行以下調整:
1.國內生產總值:在官方數據的基礎上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以2007 年為基期,對之后年份的湖北省GDP 以2007 年的價格指數為基礎進行折算,得到實際總GDP。
2.資本存量:由于資本額沒有直接的統計數據,獲取較為困難,采取較為流行的永續盤存法對資本存量進行計算:

式(13)中,Kt表示第t 年的資本存量,It表示第t 年投資額,Pt表示第t 年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δt表示第t 年的資產折舊率。對于2007 年的湖北省基期的資本存量,本文采用李珂等的方法,以1978 年湖北省的固定資產額為基礎,除以當時折舊率和固定資產的平均增速之和得到資本存量,并將結果利用式(13)折算得到2007 年湖北省的資本存量估計值;δt借鑒李珂等的研究,將折舊率確定為11.1%。
(三)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具體測算
1.平穩性檢驗。首先假定資本產出彈性系數不變,根據式(5),我們可以得到人均總產出和人均資本量的理論回歸式以便求得資本產出彈性:

首先對時間序列lnyt以及lnkt進行平穩性檢驗,確定其沒有隨機的趨勢或者確定的趨勢,防止產生“偽回歸”問題。對lnyt進行ADF 單位根檢驗得到p 值為0.0131<0.05,說明該數據平穩;對lnkt進行ADF 單位根檢驗后得到值為0.0103<0.05,在5%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原假設,說明該數據也平穩,從而可以對人均總產出和人均資本存量進行回歸分析。
2.模型結果。對數據進行回歸處理,得到回歸方程:

從式(15)可以得出資本的產出彈性為0.632,即式(1)中參數a 的值為0.632,接著利用極大似然估計法估計參數v 狀態轉換矩陣中Fk的參數,得到結果如下:

即at=0.92at-1+0.04+wt,β 的p 值為0.095 17,在10%的顯著性可以接受該值。
通過式(16)計算,得出湖北省資本產出彈性系數的變化如圖1 所示,從圖1 中可以看出,2007—2019年,該系數的變動不顯著,在0.61~0.635 的范圍內波動,離散程度小,呈現出規模報酬基本不變的狀態,且基本上接近于式(15)中的α,因此可以用式(15)中計算所得資本產出彈性系數作為近似替代,以此來計算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

圖1 湖北省資本產出彈性系數變化
3.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湖北省經濟增長的貢獻。通過Matlab 軟件和(15)式計算,得到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見表2)。
從表2 中我們可以看出,2007—2012 年,湖北省的TFP 的增長均為正值,說明湖北省在這個階段內對生產要素的利用率較高。而2012—2019 年湖北省的TFP 的增長基本處于較低水平的負增長,可能的原因是我國已由過去的高速發展逐漸轉變為高質量發展,創新驅動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主線,湖北省面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如果依賴于傳統的要素驅動發展模式,還會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進一步放緩,不符合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表2 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率貢獻
三、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分析
(一)指標選取
本文基于對國內外學者所研究的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選擇了如下指標研究其與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
1.教育支出與財政支出之比。在索洛模型中,由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MPK)是遞減的,如果存在持續的內生性增長動力也即技術進步,那么會使得人均資本邊際產出大于資本折舊,從而促進經濟增長。而技術進步離不開高素質的人才;Alvi S 和Ahmed A M(2014)[10]利用面板數據分析26 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時,發現教育對于這些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正向且明顯的作用。因此本文將湖北省教育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作為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用xedu來表示。
2.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年度GDP 總值之比。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中,全要素生產率是通過勞動力和資本間接測算的,Turner 等(2013)[11]在測算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中發現,要素投入的增長占產出增長的四分之三,但是要素投入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不足三分之一,說明要素投入對于產出增長的驅動作用是存在邊際遞減的效用的。而固定資產投資額作為體現經濟系統中物質資本的投入,我們需要衡量其現行水平是否合理,即判斷繼續加大固定資產投資是否能促進湖北省經濟增長,因此選取湖北年度固定資產投資額與湖北省年度GDP 總值之比來作為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用xfix來表示。
3.科學技術支出與財政之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現代社會中,理論逐漸取代了經驗的重要性,科技對未來事物及走向的強大預測能力正在逐步摒棄人工重復試錯的低下效率,科技以其難以想象的加速度不斷地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工業變革。從這個角度來看,科學技術支出與財政支出之比能夠反映湖北省新技術、新工藝的研發活力,了解湖北省對于科技發展的投入情況,科技是經濟增長內生性動力的重要來源,因此將科學技術支出與財政支出之比作為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用xtec表示。
4.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占湖北省生產總值的比重。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能反映注入湖北經濟系統的外來資金,外資的注入也會帶來一些先進的科技成果,進而影響湖北省經濟發展,也是會間接影響到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方面,因此將其與湖北省生產總值的比值作為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用xinvest表示。
5.第二產業(工業)與第三產業(服務業)的增加值之和占GDP 比重。湖北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增加值能夠反映湖北工業與服務業的技術含量與技術水平,因為技術含量、技術水平上去了,相應的產品附加值就會增加,因此筆者將湖北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之和占湖北省GDP 比重作為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用xval表示。
對影響因素進行歸納,如表3 所示。

表3 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
表3 中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湖北省統計局(http://tjj.hubei.gov.cn/)、國家統計局官網(http://www.stats.gov.cn/)以及中經網(https://db.cei.cn/)。
(二)模型建立
關于湖北省2007——2019 年全要素生產率以及其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式(17)中,y 代表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
(三)數據處理
1.平穩性檢驗。本文首先利用Eviews8 軟件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如表4 所示。從表4 中我們可以發現,變量在一階差分、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示平穩。

表4 數據平穩性檢驗
2.協整檢驗。變量之間長期穩定均衡關系通過協整檢驗來分析,若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是協整的,即可在一階差分平穩的條件下進行OLS 回歸。經過Kao 協整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Eviews 8 得出的p 值為0.029 7,因此可以進行回歸。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回歸后模型結果及相關系數如表5 所示。

表5 模型回歸結果
由于變量xval沒有通過5%顯著性檢驗,因此,在10%的顯著性檢驗下,回歸結果如下所示:

寫成微分形式為:


關于式(19)所蘊含的各個因素對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在教育投入方面。教育投入占比每提高1%,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就提高0.256 015%,該結果說明增加教育投入能促進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增加教育的投入,有利于提高人才的質量和數量,而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隊伍的擴大,能充分利用、有效研發各種新技術從而促進生產技術的提高。
2.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固定資產投資額占比每提高1%,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反而降低0.408 887%,因為在固定資產投資初始階段,增加固定資產的投資能夠有效地利用相應的技術,此時全要素生產率會相應較高;但隨著邊際效用遞減,以及受限于技術進步的速度,此時再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額占比,反而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這與我國近些年經濟進入新常態也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湖北省也需要將傳統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
3.在技術投入方面。科學技術支出占比每提高1%,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就會提高0.116 39%,驗證了科學技術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新技術的研發能夠更好地利用已有的社會資源,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經濟產值,而一部分新的科技成果如果轉換為市場產品,會在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的推動下自發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反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使其提高,形成良性循環。
4.在經濟開放度方面。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總額每提高1%,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就提高0.264 008%,可能原因是外商投資湖北省企業,不僅會給湖北省注入外資,還會帶來新技術以及新的管理理念,這些都有利于對于勞動力、資本的利用,從而使得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
5.在產業結構方面。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每提高1%,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就提高0.209 639%。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越高,意味著湖北省相應產業技術的進步,而相應的技術進步有利于降低相關產品的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符合新常態下改善供給側的要求。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
通過索洛殘差法對湖北省2007—2019 年的經濟數據進行分析,本研究發現2007—2012 年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同時期經濟增長速度也較快;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的變緩趨勢日漸明顯,傳統要素驅動經濟發展模式的效率逐漸走低;因此在供給側改革的大背景下,湖北經濟由粗放轉向集約增長,核心要義是要改善供給側,轉變增長動能,提高效率。同時,由于新冠疫情對湖北省經濟沖擊巨大,經濟快速恢復與高質量發展,能夠有效地提升產業增加值,彌補疫情對于湖北省經濟的負面影響;湖北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通信、人工智能以及醫療器械等高科技成果如果能通過市場轉換為經濟成果,無疑會推動湖北省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不僅使經濟恢復得“快”,又使經濟恢復得“好”。
(二)建議
因此,本文就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提升湖北省經濟增長水平,從以下幾個角度提供建議:
第一,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防止進一步的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產品時,要堅持質量第一、效率優先的原則。同時,要優化要素配置,調整生產結構,使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有其結構性“土壤”,進而推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加大人力資本的培養力度,高素質的人才隊伍是科學技術得以進步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各行各業的精英人才的作用不容忽視,而人才的涌現恰恰反映了教育取得的成果,進而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提升教育支出可以使得湖北省各個相關產業都有其相應的“人才儲備庫”,人盡其才,從而使得配置在產業上的生產要素得以充分利用。
第三,要繼續健全科技創新體制,加大科學技術投入占比,保護科技工作者的專利成果,鼓勵相應的發明專利成果應用于實體經濟,以科學技術創新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反哺科學技術創新的良性發展模式。
第四,進一步拓寬經濟開放度,鼓勵外資在湖北省投資及設立企業,將外資企業的管理模式和發展模式借鑒至湖北省實體經濟,推動本地企業治理結構的發展。
第五,淘汰高耗能、低效益的企業。湖北經濟結構轉型時會面臨發展的“陣痛”,但是只有淘汰這些低效率的企業,才能使得生產要素得以釋放,新舊動能的接續轉換才能更加快速,釋放出的要素資源能在效率更高的產業中得到利用,從而提高湖北省的全要素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