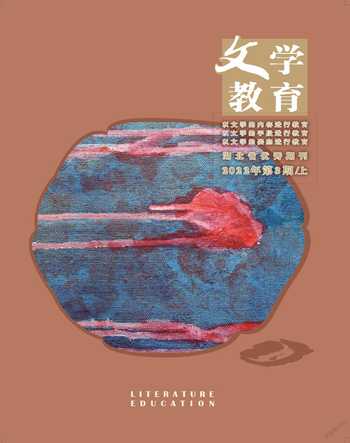精神分析視閾下的《白鹿原》
敬文靜
內容摘要: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中,將人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文將《白鹿原》看做一個整體,將其中的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看做本我的代表,白趙氏,仙草和白孝文看做自我的代表,朱先生和白嘉軒以及白靈看做超我的代表。其中將田小娥、白趙氏和仙草以及白靈視作這個整體關于女性觀的分支。
關鍵詞:白鹿原 精神分析 女性觀 潛意識
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結構分為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或稱無意識、下意識),并且他將潛意識提到無比重要的地位,他認為人物潛意識甚至比意識更加重要,潛意識才是真正的精神現實,并且他就潛意識給出了自己獨特而嶄新的解釋。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與本我》中將其早期的“潛意識”、“前意識”、“意識”的心理結構進一步完善為為“本我”、“自我”和“超我”。
實際上,作者陳忠實先生通過《白鹿原》的創作來構建了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如果將《白鹿原》看做一個整體的話,那么弗洛伊德的心理結構,即自我、本我和超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相應人物形象。
一.本我
在弗洛伊德在其潛意識理論中提出,“本我”處于人格心靈的最底層,由人類與生俱來的動物性本能所驅動,特別是性沖動,相當于“無意識”。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它具有不斷地要求滿足的基本本能,同時它又不斷地企圖使自己獲得機會,以便在意識中表現出來,它是一種被壓抑而又不斷地表現自己的東西。它是混亂的、毫無理性的,只知按照“快樂原則”行事,盲目地追求滿足。
鹿子霖、黑娃和田小娥可以看作是本我的代表。鹿子霖的身上理性因素很少,其一生都受欲望的驅使,不停地放縱欲望。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權欲和性欲的放大表現。鹿子霖就任國民政府白鹿鎮鄉約,奉史縣長之令在白鹿征稅,引起村民不滿;在“四·一二”政變后就任第一保障所鄉約以及就任白鹿保公所保長等可以看出其對于權力的不懈追逐,在鹿子霖的觀念中,其沒有是非對錯的衡量標準,沒有道德觀念的約束,甚至鹿子霖就是白鹿原上的惡的代名詞:強奸田小娥,設計白孝文,調戲兒媳等。在他的身上我們看不到克制等理智因素和內疚等道德因素,他追求的是欲望的放縱,他只按照快樂原則行事,盲目的追求滿足。他的一生是混亂的,無邏輯的,他是人類最低心理結構——本我的象征。
黑娃的身上具有一種野性,在其身上最突出的特點便是對于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欲望——暴力的放縱。黑娃一生經歷了“將軍案”,就任農民協會主任和國民革命軍習旅長主任,后上山為匪,后歸順保安團等,而其打斷白嘉軒的腰桿,回鄉為田小娥復仇等行為更是將其身上占據主導地位的的暴力因素展現的淋漓盡致。但黑娃的欲望放縱又區別于其他類似行為,作者在黑娃身上設置了未被封建倫理綱常閹割的原始野性,作者在探索封建傳統文化的前進道路和先進力量。作者在環顧周圍時發現,以白鹿原為縮影的社會人民早已深受封建傳統文化的控制,在這些人身上作者看不到傳統文化的出路,于是作者寄希望于帶有原始野性,從未被封建傳統文化閹割過的黑娃身上。
田小娥作為白鹿原上最為鮮活的傳奇悲劇女性,在她身上交織著“天使”與“妖婦”兩種形象,她既有善良順從的一面,也有叛逆墮落的一面,但其在作者筆下其最為突出的是作為白鹿原上“性”的代名詞。田小娥先是引誘黑娃,其次是被鹿子霖強奸,緊接著是受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尤其是白孝文在封建傳統文化的壓抑之下出現了性無能,但在和田小娥的性事中隱疾不治而愈。如果說鹿子霖代表的是人類原始貪欲(或是權欲),黑娃代表的原始暴力的話,那么田小娥代表的則是深受最高道德標準的象征——超我的壓抑的性沖動。
弗洛伊德認為本我是心理活動的原動力,是個人存在的動力,其潛在力量是巨大的,可以毀滅個人和種族存在。如若人的心理潛在力量被激發,任由本我主宰個體,那么整個機體就會陷入重重困難之中,甚至由于同整個外界的對抗而導致自我毀滅。所以在實際生活中,“本我”只能作為心理活動的導火線而存在,絕不能讓它代替或占滿整個心理世界。從鹿子霖、黑娃和田小娥身上可以看出他們身上保留著未被閹割的原始活力,白孝文通過田小娥找回了長久受到壓抑而喪失活力的原始性欲,白鹿原通過黑娃看到了新的活力注入。但由于他們身上缺乏理性和道德因素,所以在這個“導火線”點燃以后,只能退居幕后,或被壓抑到內層去,然后,再讓一種比“本我”更高級的心理——“自我”或“超我”來占領心靈舞臺。
二.超我
在弗洛伊德心理結構理論中,“超我”處于最頂層,是理想化的自我,其理想化主要表現在能進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與“本我”相對。與其“理想化”相對應,“超我”的作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具有道德約束力,即在長久的道德規范中形成的個人道德規束,對個體起到規范和懲罰作用,也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良心”;二是理想的自我,并以理想化的原則來制定個體所遵循的道德行為標準。“超我”以道德規范來指導“自我”的活動,并限制、壓抑“本我”的原始的本能沖動,從而使其按照符合規束的原則活動。“超我”代表著一個力求完善的維護者,被描述為人類生活的高級方向。
朱先生在作者筆下是“智者近妖”的存在,其可謂是白鹿原上文化和道德標桿,甚至族長白嘉軒根據朱先生的思想修立了鄉約,并使其很快成為白嘉軒治理鄉族的法寶。在朱先生身上有很多超越現實的存在,如:僅靠三寸之舌替張總督勸退方巡撫20萬大軍;對縣長的人生預言,對天下的歸屬預測等。在朱先生身上我們幾乎看不到欲望和原始沖動,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和道德。可以說朱先生是超我的真理象征,是客觀規律和社會道德規范的人格化,也就是認識和掌握了客觀規律的、富有經驗的年長者在人心內部的投影,是客觀權威的內部化。他是客觀規律的化身,是真理的化身。
白嘉軒雖其智慧不及朱先生,但在白鹿原人的心中,如果說朱先生是神一般完美和無欲無求的代表的話,那么白嘉軒則是理智和道德在現實生活中的榜樣和楷模。相較于朱先生,白嘉軒多了幾分七情六欲,多了幾分人情味,但在白嘉軒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高級的理智和道德等心理因素和低級的欲望和沖動等心理因素矛盾斗爭的身影。白嘉軒代表了在人類社會中的超我。超我的范圍包括:客觀規律、在客觀規律指導下的權威性人物、以及客觀地存在社會上、帶有強制性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白嘉軒用朱先生撰寫的以封建倫理綱常為核心的《鄉約》來治理宗族,讓鄉親背誦,甚至修祠堂,豎牌樓,刻石碑,建戲樓,并借以祠堂為核心的權力建筑群來進一步加強以《鄉約》為代表的封建傳統文化道德標準。通過這一些舉動都可以看出白嘉軒有意引導人們走向自我約束的道路。
白靈在《白鹿原》中是白鹿精魂的化身,雖然相較于朱先生及白嘉軒等超我的代表,白靈明顯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白靈卻是出生于宗法之家里的叛逆之魂,是在重壓之下奮起反抗的另類女性,白靈是白鹿原上最光彩照人的形象。她身上既有野性十足的活力,又有經過都市現代文明熏陶而明辨是非的大氣。她的每一次出現,都給晦暗的封建世界帶來不一樣的色彩。白靈從小便表現出了與封建傳統文化統治所不容的叛逆個性:當父親在讀完私塾后不讓她繼續讀書時,她一個人偷偷地跑到西安城投奔二姑家和兩個表姐一起上學;當白嘉軒找到她時,她不惜以死抗爭換來父親的妥協;逃婚;參加革命等。可以說白靈是《白鹿原》所有女性形象的超我代表,其具有理性因素,是女性的“理想自我”的化身。
三.自我
處于本我和超我二者中間是“自我”,它從“本我”中分化出來,但有受到“超我”的規束和陶冶而表現出漸識時務的一部分。“自我”受到“超我”的指導,并監督“本我”的活動,充當本我與外部世界的聯絡者和仲裁者。與“超我”的理想化和“自我”的沖動化不同,“自我”可以根據周圍環境的實際條件來隨時調節“本我”和“超我”所產生的矛盾,并根據當下環境條件來決定自己行為方式的意識,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理性或正確的判斷。它的行動原則是“現實原則”,既能從道德規束下獲得滿足,又能避免過于理想化的道德規束對于壓抑本能沖動所產生的痛苦。
“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經常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特別是“超我”和“本我”經常處于不可調和的對抗狀態。在超我面前,自我對于超我發出的命令必須服從和執行。在超我和本我發生矛盾沖突時,自我還需要依據超我的命令對本我進行壓制。由于有些壓制是帶有長久性和反復性的,所以它也帶上了習慣的性質——也就是說,是無意識的。白趙氏在以朱先生和白嘉軒為代表的超我面前,白趙氏自覺承擔起了自我的責任。在黑娃“勾搭”上田小娥后,鑒于黑娃的嚴峻教訓,白嘉軒愈加嚴厲地注視著兒子孝文的行為規范。在男女之事上,祖母白趙氏自覺承擔起了自我的監管者的職責。祖母白趙氏在通過明里暗里各種方式嚴格監管孝文的房事,最終導致了孝文的性無能。這種監管由于長期重復,最終變成了白趙氏的無意識表現。
處于中間地位的自我,比本我更處于緊張的焦慮狀態。因為超我的命令是無情的、冷酷的。當超我發出這樣或者那樣的指令時,它是沒有什么道理可講的。超我多多少少地沾染上“霸氣”。自我生怕沒有盡到看顧和控制本我的責任而違背超我的命令,必須時時密切注視本我和超我的動靜。白趙氏和白嘉軒的妻子仙草便充當了自我的角色。她們“聽命”于白嘉軒和朱先生,時刻注意周圍人的動向,一經發現便立刻向超我報告,如黑娃的叛逆,白孝文欲望的萌動等。
白孝文可以說是自我復雜性的最好印證。白孝文出生于“耕讀傳家”的族長之家,被當作族長繼任者的白孝文從小受到以朱先生和白嘉軒為代表的超我的壓抑,但白孝文并不是沒有欲望的萌動。其實從白孝文的成長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在重壓之下,白孝文身上還殘留著一絲原始欲望。白孝文在初行房事之后便沉溺其中,后經白趙氏的監管和壓抑之后,轉而將這種欲望轉化為為超我所容許的看戲。在分家之后,白孝文對這種原始欲望放縱可謂是達到了極致:首先表現在對性欲的放縱與沉迷。自與媳婦房事被把控之后,白孝文一度處于性無能的狀態,哪怕面對田小娥。但在賣地挨打之后,孝文開始真正品嘗到性欲的滋味。白孝文開始沉迷于被閹割掉的性欲。其次是對鴉片的沉迷。在田小娥第一次拿出煙槍時,白孝文第一時間想到的時朱先生在講禁煙時的失態。為向超我進行報復加之鴉片煙的誘惑,白孝文開始吸鴉片并一發不可收拾。最后是淪為乞丐,沿街乞討。為填飽肚子,白孝文開始沿街乞討。此時,相比于同情與救助,周圍早已將超我統治融為無意識的人對白孝文更多的是奚落和嘲諷。真正促使白孝文向自我轉變的是長輩鹿三的嘲弄。鹿三深受白嘉軒的影響,更像是超我的衛道者,其對白孝文的奚落更是超我對本我的無情奚落。正是此次奚落,讓原本軟弱的白孝文認識到了超我統治的根深蒂固。可以說前期的白孝文身上有本我的影子,且這種本我的因素受到了超我和自我的壓抑。
后期的白孝文找到了平衡本我和超我的方法,那就是成為自我的一員,他一方面慰撫超我,另一方面給本我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間接的表現,其以世俗的圓滑為法寶,借此來協調本我和超我的關系。其利用自己的圓滑最終成為縣長,他一邊安撫身為超我代表的白嘉軒,一方面又設計殺害了自我的代表黑娃,并實現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一類的自我是“識時務者”,他們不一定完全服從客觀的要求,更不一定完全放棄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使自己遭受太大的損失。他們主要是表現出“混”的樣子,擺出一副順從的樣子,但實際上又在察言觀色,等待時機,一旦客觀上的“超我”不注意的時候,即可蒙混過關。這樣自我便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使超我以為自我順從了它的命令,二是偷偷地使自我某些要求得到滿足。
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和“超我”有助于人們認識人們的潛意識,開創了新的精神研究領域。而將《白鹿原》看做一個整體,加之以弗洛伊德的自我和超我理論,我們會發現在《白鹿原》中都可以找到對應人物: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可以看作本我的代表,白趙氏,仙草和白孝文可以看作自我的代表,朱先生和白嘉軒以及白靈可以看作超我的代表。這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白鹿原》。
參考文獻
[1][高宣揚.弗洛伊德及其思想.[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04.
[2]陳忠實.白鹿原.[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07.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自我與本我.[M].林塵,張喚民,陳偉奇譯.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09.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reud,S).夢的解析.[M].花火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3.03.
[5]高夢圓.“天使”與“妖婦”形象的交織——《白鹿原》男權話語體制下的田小娥形象分析[J].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19,3(15):59-60.
[6]朱言坤.鄉賢·鄉魂·鄉治——《白鹿原》鄉賢敘事研究[J].江蘇社會科學,2018(01):187-194.
(作者單位:西安工業大學文學院;指導教師:馮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