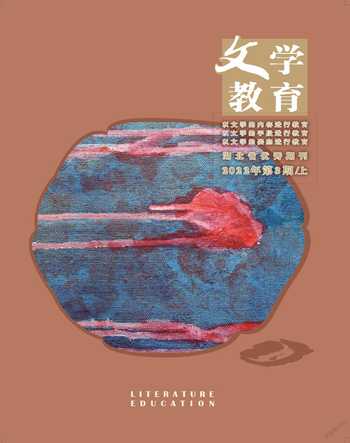埃瓦雷斯托《金色的根》的歷史內涵
高鈺
內容摘要:英國黑人女作家伯納丁·埃瓦雷斯托在其創作的奴隸敘事小說《金色的根》中重新探討了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歷史及影響問題。作者在本書中通過假想黑人和白人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的身份發生顛倒的故事,重新書寫歷史。本文將該小說放在戰后黑人書寫潮流的背景下,從小說的非自然敘事手法為切入點,探討小說中不可能的故事世界和非自然的敘述行為,繼而探討該小說所表達的歷史內涵。
關鍵詞:伯納丁·埃瓦雷斯托 《金色的根》 非自然敘事 歷史內涵
尼日利亞裔英國女作家伯納丁·埃瓦雷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于2008年出版了一部或然歷史小說《金色的根》(Blonde Roots),該小說假想黑人和白人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的身份發生顛倒,探討奴隸貿易的歷史和影響。該小說在出版的次年,就榮獲了“橘子青年小組獎”(Orange Youth Panel Award),也入圍多個獎項。同時,該小說也受到評論家們的廣泛關注。朱迪·紐曼(2012)稱這部小說想讓人們思考如果歷史發生對換,人們該如何看待歷史問題,同時也對現代性的內涵提出疑問。羅森博格(2010)則對小說中的歷史書寫進行探討,并分析了作者埃瓦雷斯托關注歷史話題的時代根源。小說《金色的根》的創作,不僅是再現黑人歷史問題,也是思考奴隸貿易對英國乃至歐洲的影響。
目前,不少學者都關注到了該小說的反諷和戲仿的藝術特色,以及歷史與現實問題,但對小說的非自然敘事的探討還不多見。自理查森于2006年出版《非自然的聲音:現當代小說的極端化敘述》一書后,非自然敘事學便迅猛發展(尚必武,2015),成為重要的后經典敘事學派之一。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非自然敘事更新了對敘事文本研究時的固有觀念(尚必武,2015),也為文本的解讀提供了新的方法。敘事學家將敘事分為故事層和話語層,而敘事的非自然性則體現在故事和話語這兩個部分。理查森在《非自然的聲音》(2006)一書中區別了幾種非自然的敘事,瑞安(Marie-Laure Ryan)在《不可能的世界》一文中從非自然空間、非自然時間和非自然人物等五個方面討論了非自然的世界,即不可能的世界。本文擬從《金色的根》中的非自然的事件和非自然的話語兩方面對小說進行分析和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小說所承載的歷史內涵。
一.非自然事件:或然歷史
上文提到,《金色的根》這部小說通過假想,顛倒了黑人和白人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的身份,即黑人變成了奴隸主,而白人變成了奴隸。顯然,小說中黑人和白人身份逆轉的故事在真實世界中不可能發生,或者說,這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而作者卻采用戲仿和反諷的手法,將白人女性奴隸多麗絲(Doris)的為奴經歷娓娓道來。敘事學家揚·阿爾貝(Jan Alber)認為非自然敘事是指物理上、邏輯上和人力上不可能的場景與事件(Alber,2012),而赫爾曼則指出,故事世界是“被重新講述的事件和情景的心理模式,即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時間、地點,出于什么原因,同什么人或對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情”(轉引自尚必武,2015:102)。可見,在故事世界中,必然出現時間、空間和人物。而作者《金色的根》這部小說中,對時間、空間和人物都進行了非自然化的處理。此外,小說講述的非自然事件與真正的歷史事實相悖,這也使得該小說成為一部“或然歷史小說”(Alternate History)。或然歷史并不是真的歷史,而是一部虛構小說,只不過把熟知的歷史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進行改寫,并能產生一種諷刺的效果(Duncan,2003)。埃瓦雷斯托在采訪中表示,她一直都想寫一部關于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小說,但她想讓人們以一種新的視角去思考,而不是講述一個和歷史相似的故事(Gustar,2015:438)。事實上,小說敘述中出現的反諷,挑戰盛為流傳的種族優越性觀點,重新審視殘暴、野蠻和原始的內涵與美、婚姻和文化的理想(438)。下文將從人物非自然、空間非自然和時間非自然三個方面對《金色的根》這部小說中的非自然事件進行解讀,并探究其背后的歷史內涵。
非自然的人物從身份上質疑種族優越論。“人物”在《敘事學手冊》中被界定為“故事世界中基于文本或媒介的一個角色,通常是人或者像人”(轉引自尚必武,2017:135)。而在非自然敘事中,這樣的人物在物理上、邏輯上和人力上都具有不可能性。顯然,不論是白人女性奴隸多麗絲還是黑人奴隸主卡加(Kaga)都是這樣的非自然人物。小說中將人物身份進行顛倒,變成與歷史事實相反的兩個種族,而這兩個種族在小說中的境遇也是對種族優越論的一種質疑和反思,小說中最典型的就是對美的思考。多麗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被販奴者抓走,賣作奴隸。在黑人奴隸主的社會中,多麗絲所代表的白人形象——如勻稱的體型和纖細的金色頭發——是丑陋的。而多麗絲在從小到大的為奴經歷中,都遭受到了外貌上的歧視。多麗絲的第一次奴隸經歷是在一個顯貴的人家里作名叫小奇跡(Little Miracle)的小女主人的玩伴,雖然同為十一歲,但多麗絲比小奇跡更高。而多麗絲卻因此受到了小女主人的辱罵,“你長得丑”,“我才是漂亮的”(Evaristo,2009:97)。長大后的多麗絲,看到了很多人剪掉自己原來的金色的、紅色的和棕色的直發,花十來個小時裝上黑人的頭發。還有白人會去做鼻子變平手術,雖然一個變平肥大的鼻孔在白人的臉上看起來十分可笑。這些違和的審美標準毫無理由,多麗絲也意識到對此唯一的解釋就是“因為我生活在他們的世界,所以我當然就有了外貌缺陷”。雖然面臨外界的審美歧視,但多麗絲仍堅信:雖然她是白人,但她也是美的。
以上多麗絲對審美標準的思考,是一個白人女奴隸對黑人奴隸主的世界中對美的定義的看法。從她的思考中,讀者很容易聯想到現實世界中對美的定義。多麗絲的思考,是對種族優越論的質疑。埃瓦雷斯托在《“美”絕非你所想的那樣》一文中寫道,一直以來,人們對美的定義都太過狹窄,而她也通過作品不斷地去呈現美的更多可能性。顯然,小說中多麗絲的思考,正是這一觀念的體現,也是對讀者的提問和啟發。
非自然的空間從地理上顛覆歐洲中心的觀念,同時強調奴隸制度對文明發展的貢獻。空間對于理解敘事十分重要,讀者通過人物流動、居住或體驗不同的空間和地點,能在腦海種構建起復雜的世界(Bridgeman,2007:52)。阿爾貝區別了四種類型的非自然空間,其中一種就是地理上的不可能性,即把現實世界的空間融合進一個新的整體(轉引自尚必武,2017:136)。在《金色的根》的正文開始之前,作者附上了一張地圖,這是小說種大西洋奴隸貿易發生的場所。但不同尋常的是,這張地圖打亂了現實世界中真實的地理位置。實際上,該地圖不是隨意的把歐洲的位置位移,而是以非洲為中心,將位于北半球的歐洲大陸平移到了南半球。小說中創造的非自然地理背后,是對歐洲中心論的顛覆。長久以來,歐洲中心論者一直將其置于宗教、環境、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性之上,一面強調西方對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的發展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也歪曲和貶低非西方世界的成就和貢獻。而小說在對非洲和歐洲地理位置的處理上,將非洲置在世界的中心,而歐洲則變成了非核心的地位,其含義不言而喻。
不僅歐洲的位置發生改變,小說中虛構的非洲殖民地中心艾博薩聯合王國(U.K. of Great Ambossa)及其首都倫敦(Londolo),也是英格蘭和倫敦的翻版。在地圖上,英格蘭被平移到了赤道上,并更名為艾博薩聯合王國。顯然,作者的這一篡改,強調了英格蘭是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參與者的身份。小說中,艾博薩聯合王國的富貴人家生活愜意且悠閑,究其原因,是奴隸們把所有的生活瑣事和勞作都承擔了,奴隸主人才能生活輕松。多麗絲的主人卡加通過參與大西洋奴隸貿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他還擁有一個甘蔗種植園,種植的奴隸們不分晝夜的辛勤勞作,為卡加創造了巨大的利潤。以卡加為代表的諸多奴隸主甚至艾博薩聯合王國的財富來源都是來自奴隸貿易,而其后續的文明發展,離不開奴隸制度下奴隸的悲慘一生。作者對地理的重置既是對歐洲中心論的顛覆,也是強調奴隸制度對文明發展的貢獻作用。
非自然的時間連接起過去和未來,從歷史來思考當下。在非自然敘事中,時間的線性維度遭到破壞,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固有界限被打破(尚必武,2017:135)。誠然,《金色的根》這一小說并不是按照線性時間發展,而是在歷史時間中不斷穿梭。小說沒有完完全全地再現大西洋奴隸貿易這段歷史,而是融入對中世紀歐洲封建農奴制以及21世紀的甘蔗種植園進行思考。多麗絲在第一次逃跑的過程中回憶了自己被抓賣為奴隸之前的生活,她的父母種植卷心菜(Evaristo,2009:7)。多麗絲也透露,她家的地是從領主那里租來的,作為條件,所有的男性農奴都要在領主作戰的時候充當步兵。按照多麗絲的自述,她來自中世紀的一個農奴家庭。顯然,作者并沒有按照線性的時間順序對奴隸貿易進行敘述,而是把早于奴隸貿易的西歐農奴制時期也融入小說。這一做法的用意也不言而喻,奴隸制度并不是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甚至世界,而是在歷史上早已有之。歐洲的發展,早已與奴隸制度結下了深厚的聯系。
小說中的時間不僅向前推到了中世紀,同時也向后看到了21世紀。作者在小說的后記中說道,“在21世紀,主人的子孫們仍坐擁那些甘蔗種植園,他們也是艾博薩聯合王國最顯赫、最富有的人家。而那些甘蔗種植工人很多都是奴隸的后代,他們現在是付薪工作”(261)。小說在關注大西洋奴隸貿易這段歷史之外,也把目光看向了當下。奴隸貿易是一個跨種族、跨文化的活動,它是現代社會概念和隱喻范圍的基礎(Burkitt,2012:408)。非裔美國研究學者卡比(Hazel V.Carby)認為,大西洋奴隸貿易是理解當代各種復雜問題的關鍵,可以解釋很多當代現象(1989:126),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身份問題。然而,奴隸貿易不僅影響了黑人的身份構建,也對歐洲特別是英國白人的身份建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此外,小說后記中提到的21世紀的甘蔗種植園工人也正是作者對奴隸制度影響的探討。小說中的非自然性將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這段歷史同過去的過去,即中世紀農奴制,和21世紀甘蔗種植園的付薪工人連接在一起,表明不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人口買賣和奴役都是存在的。從這一層面來看,《金色的根》既是對過去的回顧,也是對現實的反思。
在小說《金色的根》的故事層中,埃瓦雷斯托講述了一個黑人奴役白人的非自然事件。通過對非自然的人物、非自然的空間和非自然的時間分析和解讀,能看到這一事件背后埃瓦雷斯托對種族優越論、歐洲中心論和現實的思考,以及對黑人奴隸制度的歷史真實性和其對人類文明貢獻的肯定。
二.非自然話語:并置
《金色的根》除了在故事層上具有非自然性,在話語層上同樣也是非自然的。小說并沒有遵循傳統的奴隸敘事小說程式化的文本模式,而是在繼承了傳統的第一人稱敘事策略的基礎上,通過并置的策略,從多個角度和聲音對同一個事件進行敘述。這種多聲部的復調結構,是兩個敘述者之間的對話,也是沖擊單一歷史的建構話語。
小說中女奴隸多麗絲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的為奴到逃離的經歷,中間卻穿插了奴隸主卡加回顧自己憑奴隸貿易發家經歷的敘述。二者敘述的交叉點是多麗絲第一次逃跑后,卡加懸賞追捕她的公告。尚必武指出,在敘事中,話語是為建構故事或表達故事服務的,而在非自然敘述中,話語顛覆了故事,話語顛覆故事的手段就是反常的敘述行為(2015:100)。理查森在《非自然的聲音》(2006)一書中集中討論了幾種典型的反常敘述行為,其中兩種便是“不可靠敘述者”和 “多重人稱敘述”。顯然,小說中的敘述者多麗絲就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首先,她十分清楚自己的敘述者身份,例如,她在講述自己在第一任主人家當差的事情時,她說道“故事是這樣的…”(Evaristo,2009:17)。其次,多麗絲有意識地把個人經歷加入了奴隸貿易歷史的構建,她講述自己為奴和逃離經歷的各種軼事,并把大西洋奴隸貿易歷史的建構建立在自己的個人經歷之上。但通過這樣不可靠的奴隸敘事,埃瓦雷斯托在《金色的根》中質疑了單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歷史話語。同時,在多麗絲第一人稱單數(“I”)敘述的過程中,偶爾會出現第一人稱復數(“We”)的敘述。理查森認為,“多重人稱敘述”具有不確定性,且具有向心文本的效果,即一開始就出現的很多聲音和立場最后都減少到一個敘述位置(轉引自尚必武,2015:100)。在多麗絲的第一人稱敘述過程中,穿插了一些如“我們大家都開玩笑說…”(30),“我們那里的男性…”(32)和“我們女性都在家…”(106)這樣的第一人稱復數的敘述,但歸根結底,這兩種敘述聲音最終都可以歸結成多麗絲的聲音,敘事聲音“我們”所包含的經驗,也是多麗絲的個人經驗。
小說中除了敘述者多麗絲,還有另一個敘述者,即奴隸主卡加。小說的第二部分由卡加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講述了他自己憑奴隸貿易的發家經歷。卡加的敘述一方面,在奴隸貿易中以奴隸主的經驗和話語對奴隸貿易歷史進行建構;另一方面,卡加的敘事是同多麗絲的對話,解答了多個在多麗絲的敘事中沒有得到答案的地方,串聯起了多麗絲一家的命運。整部小說采用“多聲部”的復調方式,多麗絲和卡加的聲音同時發生,他們直接講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但二者都沒有講述出全部的事實。兩種敘事聲音并置,建構多重敘事話語,既是奴隸和奴隸主兩種立場的代表之間的對話,也是對奴隸貿易歷史穩定性和真實性的沖擊。哈琴指出,歷史和小說都是話語,兩者構建了表意體系,我們借此制造過去的意義(2009:121)。多麗絲和卡加的話語,都各自代表了一種對歷史的建構。歷史的意義或真實,全都存在與話語之中。埃瓦雷斯托通過不可靠的敘述者和兩種敘事聲音并置的手段,對單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歷史進行了解構,通過多麗絲敘述在種植園中的生活經歷,講述了奴隸之間的互幫互助、家人之間珍貴親情,破除了奴隸主對奴隸的不懂感情和冷漠的固有印象。
三.埃瓦雷斯托小說的歷史內涵
埃瓦雷斯托在采訪中表示,她對探索英國歷史的根源十分感興趣,在英國尋找黑人存在的證據,而這些興趣都來自她獨特的家族歷史(Munoz-Valdivieso,2004,13)。早在埃瓦雷斯托的前三部小說中,她就表現出了對歷史的極大關注。她的第一部小說《拉拉》講述了女主人公在英國社會中尋找自己的雜糅身份,第二部小說《皇帝的寶貝》則探討了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中黑人的存在,第三部小說《幽靈旅伴》則是一部公路小說,主人公在旅途與歷史中的黑人幽靈對話而逐漸認識到自己的黑人身份。固然埃瓦雷斯托本人對歷史問題的關注極具洞見性,但她所處的時代文化潮流也對她的創作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埃瓦雷斯托不是唯一一個對歷史話題感興趣的作家,戰后的英國族裔作家如卡爾·菲利普斯也在從事戰后英國黑人的書寫。此外,戰后英國的藝術家都在尋找一個新的方法,去展現黑人在歷史發展中的成就,而不是一味地把黑人塑造成被害者的形象。一些藝術家通過視覺藝術的手段破除黑人的刻板影響,而去展示黑人在藝術上的成就。與此同時,一些博物館開始展出大量有關奴隸經歷的展品,強調了非洲文化對西方文明的貢獻(Rosenberg,2010)。在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埃瓦雷斯托繼承了傳統的修正主義歷史小說和女性歷史小說,同時進行了個人的文學創新,運用幽默和反諷的手法,加之將多種體裁融為一體,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Rosenberg,2010)。埃瓦雷斯托在訪談中表示,自己喜歡打破傳統,喜歡在小說中探討人物身份問題,但這不是在探討自己的身份,而是對整個英國身份進行思考。從《金色根》這部小說中也能看出,作者納入思考范圍的并不單單是黑人群體的歷史,而是整個英國乃至歐洲在當下的問題。
此外,埃瓦雷斯托的歷史小說更多的是喚起讀者對歷史的記憶。長期以來,英國社會為保持“純潔性”的種族文化神話,一直有意地忽視黑人的歷史,直到二戰后大量的黑人乘“帝國風馳號”涌入,英國才正式承認他們的存在。但戰后英國黑人同英國社會產生激烈的沖突,直到近三十年,英國黑人研究漸熱,涌現了大量黑人研究作品,英國黑人的歷史才得到關注。而埃瓦雷斯托的的作品,正是以與黑人相關的歷史事件為切入點,如《金色的根》所敘述的大西洋奴隸貿易,對黑人歷史進行重構。一方面讓讀者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另一方面,也是對黑人群體的提醒,不要犯民族健忘癥(艾瓦雷斯托,2010)。
在戰后英國族裔學者和藝術家都關注黑人歷史在英國,以及歐洲的存在的背景下,埃瓦雷斯托在文學創作上,以獨樹一幟的方式,探討黑人的歷史以及歷史事件對當代黑人身份建構的影響。在或然歷史小說《金色的根》中,通過對小說中不可能事件和不可能話語的分析,探究其背后想表達的歷史內涵,既是對西方中心論和種族優越思想的解構和顛覆,也是對當下黑人甚至是白人的身份建構的反思。閱讀埃瓦雷斯托的歷史小說,不論對何種膚色的讀者,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
參考文獻
[1]Alber,J. 2012. What is Unnatural about Unnatural Narratology A Response to Monika Fludernik[J]. Narrative 20,(3):371-382.
[2]Burkitt,K. 2012.Blonde Roots, black history:History and the Form of the Slave Narrative in Bernardine Evaristo’s Blonde Roots [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48):406-417.
[3]Bridgeman,T. 2007. Time and Space [A]. Herman,D(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Carby,H. 1989. Ideologies of Black Folk: The Historical Novel of Slavery [A]. McDowell,D & Rampersan,A (eds.). Slaver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C]. 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Duncan,A.2003. Alternate History [A]. James,E & Mendlesohn,F(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Evaristo,B.2009. Blonde Roots [M]. London: Penguin Books.
[7]Gustar,J. 2015. Putting History in its Place:an Interview with Bernadine Evaristo[J].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9(3): 433-448.
[8]Munoz-Valdivieso,S. Interview with Bernardine Evaristo [J]. Obsidian III:Literature in the Africa Diaspora,(5):9-20.
[9]Rosenberg,Ingrid Von. 2010. Bernardine Evaristo’s (Gendered)Reconstructions of Black European History [J]. ZAA, (58):381-395.
[10]伯納丁·埃瓦雷斯托.2010.張瓊譯.幽靈旅伴[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11]尚必武.2015.非自然敘事[J].外國文學,(2):95-111,下轉159.
[12]尚必武.2017.什么是敘事的“不可能性”——揚·阿貝爾的非自然敘事學論略[J].當代外國文學,(1):131-139.
(作者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