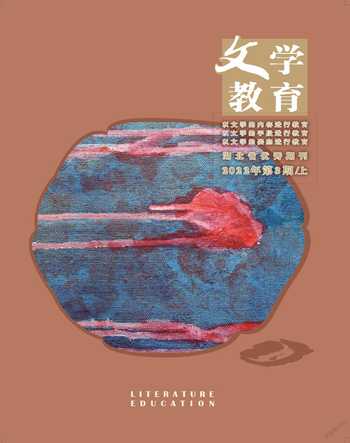論《時光倒流的女孩》中的死亡敘事
藍婉禎
內容摘要:美國當代作家加布瑞埃拉·澤文的《時光倒流的女孩》通過對死亡浪漫化的想象敘事,展現作者對生命的思考,從而探求人生的意義。文章認為,小說通過講述已逝的人們離開人間后,在一個名叫“另界”的島嶼上重新展開一段“逆生長”人生的故事,表達了在作者持著直面死亡的理性態度同時也使死亡“去陌生化”,讓讀者透過表面觸及更深刻的人生哲理。本文將從死亡體認、亡靈歸屬、死亡情緒三個方面論述小說的死亡敘事中體現的人物成長及人生哲理,以期豐富該小說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時光倒流的女孩》 死亡敘事 人生哲理
《時光倒流的女孩》是美國作家加布瑞埃拉·澤文的成名作。小說講述了一個意外喪身于車禍的十五歲少女莉茲來到“另界”,盡管她想盡一切辦法想要回到人間,但她都沒能成功實施計劃,因此她開始接受,學著成長。在“另界”里,莉茲收獲了親情、友情、愛情以及一份她擅長的工作,她在人間的“遺憾”都以另一種形式在“另界”得以補償。由于“另界”是莉茲死亡后才來到的地方,而小說運用大篇幅來描繪莉茲在“另界”中的生活,因此本文將從小說的死亡敘事角度切入,從死亡體認、亡靈歸屬、死亡情緒三個方面論述該小說死亡浪漫化敘事的意義。
一.死亡的體認——以另一種存在形式感受現實世界
作者在小說中為死亡賦予了附加意義,這體現在小說人物對死亡的體認——死去的人只是以另一種存在形式在另一個世界感受著人生。
在引子部分中,小說通過莉茲生前養的一只哈巴狗露西的心理活動與莉茲弟弟阿爾維的自言自語,來討論莉茲死后會去哪里。阿爾維“相信她在天上,相信天上有天使、豎琴、云彩、白色絲綢睡衣,什么都有”,露西“相信會有一只哈巴狗走來走去”[1]。作者通過死者的家人和狗對死亡的美好想象,淡化了一個年輕的生命因意外車禍而喪生的悲劇色彩,同時也從還活著的生物角度展現了對死亡的體認,為下文“另界”的描述做鋪墊。
在正文部分中,莉茲先從一艘通往“另界”的“尼羅河號”上醒來,她保留著在人間的所有記憶,因她在死前被家人剃光了頭發,所以她也保留著光頭的造型,她還在這艘船上遇到和她同時間段死亡的人,這些都說明了作者筆下的死亡不僅意志生命并未消失,而且肉體生命也依然存在,這些死去的人只是離開了人間,正前往一個叫“另界”的島嶼重新生活,等待再次輪回到人間。
莉茲在“另界”感受到親情。當莉茲到達“另界”后,她和生前從未見過面的外婆生活在一起。因為在“另界”的人們從死的那天起,年齡就往回倒退,所以莉茲的外婆在“另界”的年齡為三十四歲,此時她外婆的年齡與莉茲媽媽的相仿,因此莉茲在外婆身上不僅彌補了她生前無法見到外婆的遺憾,而且還在“另界”感受到母愛的溫暖。
莉茲在“另界”體會到愛情。因為在“另界”中,年齡會倒退,當莉茲認為她再也無法遇到愛情而感到失落的時候,歐文出現了。她在某次試圖通過“海井”與自己在人間的家人取得聯系中,被“另界”偵探歐文抓捕,但當歐文得知她想聯系活人的原因是想將她精心準備的禮物送給她爸爸時,歐文以被停職一個月為代價幫助莉茲用“海井”告知她弟弟禮物所放之處,并成功幫助莉茲將禮物送給了她爸爸。歐文與莉茲在相處中碰撞出愛情的火花,最后他們都成為陪伴彼此余生的人,莉茲盡管已離開了人間,但她在“另界”仍能品嘗到愛情的甜蜜。
莉茲在“另界”收獲了友情和工作。在“另界”里,莉茲還遇到了與她在人間最好的朋友佐伊個性十分相似的桑迪、遇到了她生前最喜歡樂隊里的成員柯蒂斯、遇到了她在“另界”的輔導員阿道司,這些人都成為莉茲在“另界”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她在“另界”仍能感受到友情的美好。莉茲在人間還未到達可以擁有一份獨立工作的年齡就已經離開人世,但她在“另界”擁有一份與自己愛好結合的工作。
小說中作者借莉茲輔導員阿道司之口說出了對死亡的體認——“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到時候,你還會把死亡看作新生的”[2]。每個去世的人都會以另一種存在形式在感受和建構另一個現實世界,在另一個世界彌補生命中的遺憾和缺失,這樣對死亡的浪漫化想象,緩解人們對死亡的恐懼,讓人們對失去的事情得以釋懷,因為我們所逝去的東西都會以另一個形式補償回來。這與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死亡觀不謀而合,叔本華認為,“對死亡的恐懼是先驗的,這種恐懼源于生命意志。死亡是個體的終結,是表象的終結,而生命意志不會就此消逝,它將重新在時間軸上得到新生。”[3]
二.亡靈歸屬——在“另界”里正視死亡
小說中對死亡的浪漫化想象敘事并不是對死亡的否認,“另界”與人間的契合并不是盲目地淡化死亡的現實感。作者為死去的人們構建了理想化的“另界”,但也時刻在提醒著亡靈要正視死亡這一事實,若想回人間必須遵循自然輪回的規則,一切人為的“復生”都是不允許的,亡靈的歸屬是正視死亡,等待輪回。
莉茲作為“另界”的新成員需要參加適應儀式,適應儀式包括觀看介紹“另界”錄像片、與適應輔導員見面、確認自己的遺言等等,這一系列的過程與在人間入學的程序相當,因此莉茲發出感慨“死亡跟上學沒有太大的差別”。“另界”里的景觀與人間也無較大的區別,莉茲坐在車里觀光時心想“這里的一切太像人間了”。“另界”的一切都太像人間,讓莉茲感受不到自己是已死之人,也讓讀者覺得莉茲只是到另一個地方旅行,這樣的死亡敘事使死亡“去陌生化”,淡化了死亡對于死者及讀者的現實感。
“另界”呈現的外表與人間極其相似本就容易麻痹死者對死亡的感知,然而在“另界”里還有地方可以觀察人間的舉動或與人間取得聯系,例如有一個叫“瞭望臺”的地方,在這里花一個“伊特尼姆”就可以觀看人間五分鐘;還有一個叫“海井”的地方,通過“海井”不僅死者可以看到人間所發生的事情,活人也能通過身邊某個出水口看見和聽見死者。這就更加拉近了生與死的距離,讓無法直面死亡的亡靈極易受誘惑,從而想要通過人為手段去“復生”。
作者將死亡敘事做了藝術化的處理,淡化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從而讓人們能夠接受得失無常,但她的死亡書寫呈現出的是一種直面死亡的理性姿態,她在小說中多次借人物之口強調“沒有任何辦法能使你(莉茲)返回到原來的生活中,你也不應該返回到原來的生活中去,你原來的生活已經終結,你永遠也回不去了。”[4]
莉茲曾多次嘗試回到人間,但都沒能成功。一次是想要將肇事司機告訴家人,還有一次是想告知家人她精心為爸爸準備的生日禮物所放位置,前一次是被外婆阻攔,后一次則是傳遞信息有誤,而且還因為傳達信息有偏差,導致她弟弟阿爾維被爸爸扇了耳光。不止是莉茲,歐文剛來到“另界”時,也非常留戀人間的妻子,他有規律地“拜訪”妻子,使妻子從醫學院退了學,整天待在家里等待著歐文,后來當歐文得知自己毀了妻子的正常生活后,便知道得停止了。
凡此種種,作者想要表達的就是“活人得繼續活人的生活,死人也得繼續死人的生活。”[5]一個亡靈并不能改變活人的生活,也不能改變死亡的事實,他只能是人間的旁觀者,在“另界”好好生活,等待輪回。作者既將死亡浪漫化敘事,同時又理性地強調亡靈的歸屬就是要正視死亡,在“另界”重新展開自己的生活,兩者交相呼應既減輕了死亡的沉重感,又加深了作品的思辨性。
三.死亡情緒——在適應中成長
莉茲從一開始的不相信、抵觸自己已經死亡這個事實的情緒逐漸轉變為開始適應“另界”到最后完全接受并釋然的積極情緒,這個過程也是莉茲追尋自我、實現自我價值的成長過程。莉茲在“另界”的適應中成長,對人間所逝去的一切釋懷,感悟出“人生不能僅僅用時間來衡量。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長短,而是生命的質量。”[6]這一人生哲理。
作者筆下的死亡與活著對于莉茲來說沒有任何區別,因此莉茲不相信自己已經死了。莉茲在那艘通往“另界”的“尼羅河號”上就一直堅信自己在做夢,她不相信自己在車禍中喪生,直至她通過“瞭望臺”的“望遠鏡”看到家人在人間為自己舉辦的喪禮,她才明白自己已經離開了人世。因為莉茲的身體并沒有死的感覺,她的身體跟往常完全一樣,所以她第一次產生抵觸情緒體現在當“尼羅河號”抵達“另界”全船人必須下船時,莉茲一直不愿意下船,她懷著僥幸心理認為船會有返程,能將她再次送回人間。
莉茲留戀人間,不愿接受已死亡的事實。當她得知生活在“另界”的人將越“活”年齡越“小”,直至七天大的嬰兒就會再次輪回到人間時,她非常不甘心,她不想經歷一個能看到結局的人生,因此她對“另界”產生著厭惡情緒。莉茲外婆叫她起床時,她說“我死了。還起床干什么呀?”此時的她對生活已經沒有了希望,懷著消極的情緒看待問題,她只想回到人間生活。
莉茲消極情緒的產生源于她對死亡的恐懼,而“人們對死亡的恐懼是人之最本己的心理狀態,我們害怕的不僅僅是死亡本身、死亡的過程,更害怕因死亡而孤立于社會之外”[7]。所以她將所有時間都花在“瞭望臺”上,每天都觀看她家人、朋友在人間的舉動,試圖從他們聊天會提到她這件事情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感。在某一次觀看她父母的談話中,莉茲得知肇事出租車司機畏罪逃跑了,她一定要讓司機付出代價,于是她想通過“海井”與家人取得聯系,但她通過觀察這個司機的日常生活發現他并不是一個壞人,也許這個司機也有苦衷,她最終放棄了報復,并有了第一次對自我認知的覺醒“即使讓他坐牢我也不能復生,什么都無法讓我復生”。
莉茲想要復生卻多次碰壁后,她開始學著適應。莉茲開始接受一份符合自己愛好的工作——幫助死去的狗適應“另界”的生活。這份工作讓她在“另界”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并且讓她能夠不去牽掛人間的生活,這時歐文給予莉茲的愛情可謂是錦上添花,讓莉茲能夠逐漸接受這段新的人生。莉茲本為自己在人間沒能考到駕照、沒能擁有一份工作、沒能遇到愛人而感到遺憾,卻不曾想能在“另界”得到補償,莉茲開始適應在“另界”的生活了。
莉茲性意識覺醒后產生了困惑,她再次在尋找自我中迷茫。“另界”有一個為難以適應“另界”生活的十六歲及以下亡靈專門制定的“遣返條例”,即在另界居住滿一年后便可以輪回到人間,但最終的決定權是在亡靈手里。在一切似乎都步入正軌時,莉茲卻選擇成為嬰兒重新輪回到人間,因為歐文在人間的妻子意外去世,來到了“另界”,歐文因為曾經對妻子的誓言而選擇放棄莉茲,莉茲在愛情上倍受打擊,她說“埃米莉是歐文的初戀,而我也想成為某個人的初戀。”[8]莉茲再次對“另界”的生活失去了激情。歐文和莉茲的愛情危機實際上是莉茲在成長過程中性意識覺醒帶來的困惑,莉茲對性的認識是對純真愛情的向往,然而復雜的環境因素會讓莉茲在困惑中迷茫,所以她本能地選擇逃避。
莉茲從迷茫中自我解脫,她掙脫開遺憾的束縛,完全接受在“另界”的生活。莉茲被包裹成一個木乃伊狀放進一條通往人間的河,順著潮流,莉茲將重新投胎成嬰兒回到人間。在漂流的這段時間里,作者通過莉茲的一段心理活動描述她對生命意義的感悟,這同樣也是莉茲明白自我生命價值、自我成長的過程。“莉茲意識到,一次生命就是篇很好的故事,哪怕是像她現在所經歷的這樣一次返老還童的古怪的生命。繼續留戀自己原先那種由小到大的生活毫無意義。她永遠無法找回以前的生活。”[9]莉茲明白了她不能執著于自己已經失去的東西,她不能為了追求已失去的事物而錯過當下擁有的,這就是她在適應中成長的體現。
《時光倒流的女孩》采用對死亡浪漫化的想象敘事,同時也理性地直面死亡,通過小說中女主人公莉茲在適應“另界”生活的情緒變化展示一個女孩尋找自我生命價值、自我成長蛻變的過程,旨在告訴讀者“人的生命因凌亂而美麗”,對已失去的東西釋懷,專注當下。《時光倒流的女孩》死亡敘事將理想化和理性結合,淡化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陌生感,同時作者寓深刻道理于平凡語言中,通過亡靈的世界探求生命的意義,使得人生哲理深入人心。
參考文獻
[1](美)加·澤文著,路旦俊等譯:《時光倒流的女孩》,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2]徐威:《叔本華死亡觀探微》,《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1期,第22-24頁。
[3]陳民:《西方文學中死亡敘事的審美風貌》,南京師范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
[4]岳麗:《在生命的盡頭尋找愛與希望——讀<時光倒流的女孩>》,《出版廣角》,2017年第20期,第89-91頁。
[5]劉軍霞:《<時光倒流的女孩>中莉茲的成長之旅——從成長小說的視角解讀》,《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34卷第11期,第57-58頁。
注 釋
[1](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頁。
[2](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74頁。
[3]徐威:《叔本華死亡觀探微》,《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1期,第22-24頁。
[4](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73頁。
[5](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141頁。
[6](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62頁。
[7]陳民:《西方文學中死亡敘事的審美風貌》,南京師范大學2005年博士論文。
[8](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07頁。
[9](美)加·澤文:《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218頁。
本文所引用的《時光倒流的女孩》原文內容均來自于《時光倒流的女孩》,路旦俊、胡澤剛譯,江蘇: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