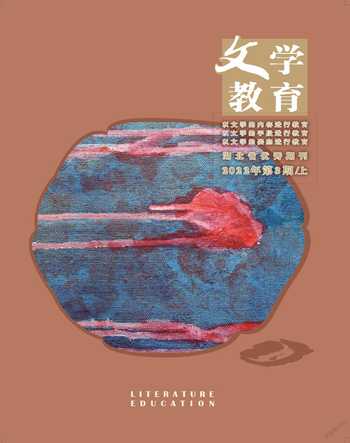樋口一葉小說作品中的父母形象
胡利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對樋口一葉作品《十三夜》《大年夜》中的父母形象進行相關的研究,探討了明治時代在新舊思想的交鋒中、社會制度的變遷中人們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態。
關鍵詞:樋口一葉 十三夜 大年夜 父母
樋口一葉(1872-1896)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職業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印在紙幣正面的日本女作家,在日本具有極高的國民知名度。樋口一葉出生于日本東京都一個下層官吏家庭,自幼酷愛讀書,立志成為作家。命運多舛的她先后經歷了父親亡故、未婚夫毀婚等變故,飽嘗生活的艱辛。二十歲時開始發表作品,在“一葉的奇跡十四月”中寫出《青梅竹馬》《十三夜》《大年夜》《濁流》《岔路》等,她的文學才華得到了許多文豪的稱贊,當時被尊為“文壇之神”的森鷗外稱其代表作《青梅竹馬》為“當代名作”,著名作家幸田露伴也因自己沒有寫出如此出色的作品而嘆息、遺憾。2004年,日本發行新版紙幣,樋口一葉的肖像出現在五千元紙幣上,成為第一位印在紙幣正面的日本女作家,這是對樋口一葉文學貢獻的最高贊譽,充分反映了她在日本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樋口一葉的作品多以那些出身卑賤、生活困苦、命運凄慘的女性人物為描摹對象,但她的作品不僅僅局限于描寫女性的哀怨與愁苦,而是以女性的命運為視角客觀描述明治時期的社會百態。明治時期,日本社會正經歷著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識開始萌芽,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男權至上、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明治維新后,日本的社會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平等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而金錢成為人人追求的目標,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本文通過對樋口一葉作品《十三夜》《大年夜》中的父母形象進行相關的研究,管中窺豹去了解明治時期整個日本社會,探討了明治時代在新舊思想的交鋒中、社會制度的變遷中人們的生活狀態和思想狀態。
一.慈祥的母親和封建的父親——《十三夜》中的父母分析
《十三夜》講述了出身平民家庭的阿關嫁入官吏家庭后,飽受凌辱,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娘家,希望能在父母的幫助下離婚。遭到父親反對后,阿關乘坐人力車離開娘家,沒想到人力車夫竟是阿關的初戀,兩人感嘆命運的不幸,卻只能各奔東西。
在《十三夜》的開頭,描寫了阿關的一番思想斗爭。一方面,她擔憂著父母的期望、孩子的成長以及弟弟的未來,另一方面,她又拒絕回到那個冰冷的家庭和鐵石心腸的丈夫身邊,在多番前思后想后,還是決定離開丈夫。從這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出阿關是一個性情溫柔、愛護孩子的母親,她不是毫無勇氣的懦弱女性,她渴望做自己命運的主宰,希望能靠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
阿關的母親是一個慈祥而傳統的母親形象,她非常關愛女兒阿關,雖然女兒阿關已經長大成人,嫁到了原田家,變成了尊貴的原田夫人。可是在母親心中,阿關還是以前的阿關,是從小在身邊長大的小女孩。母親時刻想著阿關的飲食起居,她做了糯米團子,想讓弟弟給阿關送過去,因為弟弟的難為情,沒有給阿關送過去,母親感到很遺憾。當看到阿關回到家里,母親覺得這是個彌補遺憾的好機會,所以第一時間就拿出來,想讓阿關吃個痛快。在母親與阿關的對話中,不難看出母親十分體諒阿關的難處,對阿關說著許多體己的話。希望阿關能在原田家當好原田夫人,照顧好丈夫和孩子,還告訴阿關不必補貼娘家。母親還擔心卑微的娘家會讓阿關難堪,所以克制心中對阿關的思念,路過阿關家的時候只遠遠地看著而并不進門去探望。以上種種細節,無不刻畫著一個慈祥、溫柔、愛女兒的母親形象。
當阿關把自己在原田家的遭遇向父母傾訴后,疼愛女兒的母親心痛得如同刀割一般,無法容忍女婿的行為,她回憶結婚前原田多次上門提親、不嫌棄阿關家的貧寒,對結婚后原田的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表示十分憤怒。慈祥溫和的母親不再覺得阿關的溫順是性情上的優點,對阿關說,因為你太老實了,所以丈夫才會得寸進尺,越來越不講理了。讓阿關不要再遷就了,也不必再忍受丈夫的凌辱,希望阿關離開原田家,回到娘家來生活,還讓阿關的父親去原田家評評理、算算賬。可以看出,母親雖然清楚地知道原田家有權有勢,可當女兒的尊嚴受到踐踏的時候,母性的本能讓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站在女兒的立場,心疼女兒,維護女兒。在母親心中,沒有什么比女兒的開心和快樂更重要的事情了。
與一心疼愛女兒的母親不同,阿關的父親則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踐行者,處處表現出了一個封建家長的行為做派,是明治時代社會現實在父親身上的真實投射。明治時期,日本《戶籍法》中明確規定,男性為上位,女性為下位。女性沒有公民權,只是隸屬于丈夫的附屬品,必須在丈夫的監視下才能行使財產權。而1898年實施的日本新民法更是繼承了日本的傳統家庭制度——家父長制,即父親是一家之主。“在明治初期的法律中,極少有專門保護女性的條款,妻子不僅是丈夫的附屬,丈夫更可以單方面決定離婚。”(張雅君,從樋口一葉的文學表現看近代日本女性的猶疑與搖擺[J],學術論壇,2011,(3):156-159,196.)除了沒有保護婦女權益的條款,對婦女離婚也有著嚴格的規定。“明治時代的民法對女方離婚有著嚴格的規定,而女方要擺脫婚姻的枷鎖必須先征得娘家的同意。此外,當時的民法還規定,女方離婚后六個月內不得再婚。……她們的幸福幾乎完全掌握在別人手中,女性為爭取幸福,就要面臨著來自家庭和社會各方面極大的阻力,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決心。”(王天然,從《十三夜》淺析樋口一葉反封建思想的局限性[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3,(10):89-91.)婦女離婚必須先征得娘家的同意。婦女離婚后,半年內不得再婚。另外,婦女的財產權利也沒有任何保障,婦女一旦離婚,立刻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在社會思想方面,“延續數百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還十分頑固地扎根在明治社會的土壤中,順從、貞操、奉獻、忍耐仍被視為女性最根本的義務。”(林敏,樋口一葉文學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
當阿關的母親希望父親能去找原田去評評理、算算賬時,希望父親能為阿關討回公道,可深知法律制度和社會規則的父親卻交抱著胳膊、閉著眼睛聽著,對母親說“不要胡說八道些沒有的話”,并且十分明確地表示了自己的態度——反對阿關離婚,充分地表現出了一位封建權威男性家長的做派。雖然父親也心疼女兒的境地,希望女兒能擁有幸福的生活,但腦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以及他對社會規則的了解仍使他勸說女兒放棄離婚,狠心而不近人情地勸阿關要多多體諒丈夫、好好伺候丈夫,告訴阿關,妻子的責任和本分就是設法讓丈夫開心,勸阿關為了孩子、父母以及弟弟的前途隱忍下去。在父親眼中,阿關是原田家的太太、太郎的母親、亥之的姐姐、齊藤家的女兒,唯獨不是她自己——一個活生生、有感情的女性,一個渴望家庭溫暖、父母關愛的女兒,一個在婚姻中受盡虐待和折磨的妻子。父親“堅決反對阿關離婚,只考慮到了阿關周圍許多人的利益,而對于一切事情的中心人物,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阿關卻采取無視的態度。”(王天然,從《十三夜》淺析樋口一葉反封建思想的局限性[J],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3,(10):89-91.)父親一味只讓阿關忍讓,可對丈夫的責任和本分卻只字不提。而母親在聽到父親反對阿關離婚后,同為封建社會制度受害者的母親也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只能無助地陪著女兒哭泣。
在《十三夜》這篇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中,樋口一葉刻畫了一對非常典型的父母形象——父親封建專制,母親慈愛善良。阿關的父母深受明治時期社會文化的影響,通過阿關父母的性格特征,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現實和社會文化的特征。而父母對尋求幫助的女兒的態度是如此的冷酷和不近人情,更進一步證明了日本女性生存境況的凄慘與悲苦。阿關貴為有錢人家的太太,試圖沖破封建制度的束縛況且如此,更遑論那些社會地位低下、經濟條件困苦的平民女子了。《十三夜》中父親的思想以及母親態度的轉變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男權至上、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萬分痛苦、已決意離婚的阿關聽從了父親的勸告,做出回到原田家的選擇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刻薄的母親和冷酷的父親——《大年夜》中的父母形象分析
《大年夜》講述了女仆阿峰為了維持生活忍受著主人家的刻薄,大年夜這天,答應借錢的女主人抵賴反悔,阿峰只得偷竊了主人的錢以幫助貧病交加的舅舅度過難關。阿峰向主人坦白之時,卻發現玩世不恭的大少爺石之助無意中幫助了她。
《大年夜》中有兩對父母形象,第一對父母是阿峰的舅舅舅母,第二對父母是山村家的老爺和太太。阿峰的父親去世,母親帶著阿峰投靠了舅舅。母親去世后,阿峰在舅舅舅媽的撫養下長大成人。阿峰的舅舅,外號叫“實在人安兵衛”,他是個做小生意的小販,由于本錢有限,只能販賣茄子蘿卜之類的一些廉價的蔬菜,從來不賣一些新鮮名貴的物品。因為做人實在,常常有老主顧的光顧,所以生意還能維持,也能勉強送兒子去學堂讀書。可后來由于身體疾病,安兵衛不能繼續做生意了,連家里的菜秤都賣掉了。一家人搬進只有六個榻榻米那么大的小屋生活。安兵衛雖然并不富裕,但卻很憐愛阿峰。雖出身貧苦,卻不忘自己對親人的責任,毫無怨言地照顧父母雙亡的阿峰。對于舅媽,文中雖然著墨不多,但僅有的幾處描寫如“熱情地拉著阿峰的手,招呼她進來”不難看出舅媽與舅舅在品行上的一致,都將阿峰視如己出。與此同時,阿峰也將舅舅舅媽一家視為自己唯一的親人,將舅舅舅媽視為自己的父母。安兵衛一家雖然貧窮,但全家人都有善良的品性,充滿了對家人的關懷,互相體恤,互相關愛,長輩對晚輩愛護,晚輩對長輩理解,不難想象,如果走出經濟的困境,安兵衛一家一定會是一個其樂融融的大家庭。
《大年夜》還著重刻畫了山村家的老爺和太太這一對父母的形象。與善良樸實的安兵衛一家截然相反,山村一家是刻薄的、吝嗇的。山村太太傲慢霸道,喜歡阿諛奉承,雖富甲一方,但卻吝嗇小氣。所以在山村家做女仆的阿峰日子并不好過。寒冷的冬天,大清早阿峰就得起來干活,因為打水不小心弄壞了主人家的水桶,太太就對阿峰橫眉冷對、大加指責。阿峰撥弄柴火取暖,也被主人家責罵浪費時間、偷懶不干活。于是山村家的女仆一月換兩個是平常事,甚至有住了一晚上就跑掉的。山村太太的刻薄吝嗇、不近人情由此可見一斑。
山村家的大少爺石之助長得一表人才,眉清目秀,因為是老爺的前妻所生,所以太太對他非常苛刻和厭惡,還曾有意將他送給別人做養子,讓太太所生的妹妹當家里的繼承人。這件事情讓石之助和老爺、太太的關系變得十分緊張,也讓石之助徹底看清了老爺、太太的真實面目。為了故意與家人置氣,石之助游戲人間,吃喝玩樂,恣意游蕩,揮霍家財。老爺氣得幾乎要與他斷絕父子關系。太太對這種行為自然也是不能容忍,擔心他將家里的財產揮霍一空,所以在老爺面前故意挑撥,希望老爺能讓石之助離開家庭,自立門戶,實際是想將石之助掃地出門。
在太太的影響下,太太所生的幾個妹妹對石之助也非常冷漠,聽說石之助回家了,嚇得仿佛見了膿瘡似的,唯恐避之不及。大年夜這天,妹妹們穿著漂亮的綢襖,本來想在一起玩鬧一番,可討厭的大哥石之助回來了,太太和妹妹們心里一直不住地想“快滾吧,快滾吧”。石之助看到妹妹們與老爺、太太如出一轍的行為,反而得意洋洋,甚至越發任性妄為。當石之助從老爺那里拿到錢后,太太懷著滿腔的恨意像送瘟神一樣送走了他,還對石之助的母親進行諷刺和挖苦,“真想看看他母親長什么嘴臉”。
為什么富有的山村家會有石之助這樣一個“逆子”呢?《大年夜》下篇一開頭就給出了交代。由于石之助是老爺的前妻所生,所以老爺待他日益冷淡,清晰準確地描述出了父子關系的狀況。父子二人關系交惡并非完全是太太的挑撥,而是父子關系一直非常糟糕,繼母的行為只是將不好的父子關系雪上加霜。當兒子石之助找老爺要錢的時候,雖然老爺知道石之助拿到了錢只會去揮霍和花天酒地,可老爺為了保全家族的聲譽和面子,回避了教育兒子的責任,希望兒子拿了錢快滾,隨便去哪兒都行,只要不要丟了家族的臉面。在老爺心中,家族的面子和自己的面子遠甚一切,遠比兒子的成才重要。這天是過年,在這個全家團圓的快樂的日子里,老爺對兒子也沒有一絲溫情和關懷,只有嚴厲的責罵和滿心的厭惡。
俗話說,養不教,父之過。不可否認,石之助是個浪蕩公子,可如果細想一下,他究竟是如何變成現在這副模樣,恐怕身為親身父親的老爺也難辭其咎吧。父母關系交惡,年幼的石之助失去了疼愛自己的母親,這對于年幼的孩子來講,是多么傷心的事情,可老爺不僅不加倍疼愛、憐惜年幼的兒子,還把對前妻的厭惡轉移到兒子身上。可以想象,年幼而無辜的石之助受到了多少不公平的冷遇和虐待。后來,老爺又娶了太太,又在太太的影響下,與石之助的關系越發交惡,對待石之助越發冷酷無情,毫無一絲父子間的溫情。父親的冷酷,繼母的刻薄,加上妹妹們對石之助的厭惡,讓石之助絲毫感受不到來自父母的關懷和家庭的溫暖,讓石之助不斷遠離家庭,終至走上了破罐子破摔的浪子之路。
山村家雖然是富甲一方的有錢人家,卻沒有一絲家庭的溫情,在這個家庭里,有刻薄、挑撥離間的繼母,冷酷、不負責任的父親,放浪、揮金如土的長子以及冷漠、功于心計的妹妹,家庭成員之間雖有血緣關系,卻沒有親情聯系,所有的家庭成員之間只有相互的算計和利用,金錢只給這個家庭的家庭關系帶來了極端的異化和扭曲。
(作者單位:萬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