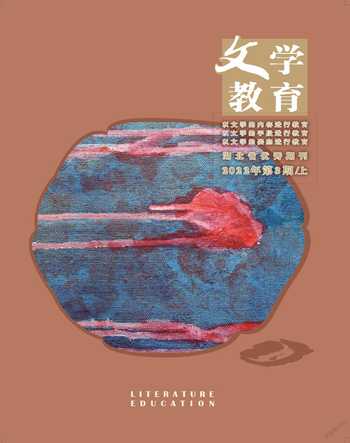香港特區文化認同意識探究
徐小雙
內容摘要:始于2019年上半年的香港暴力活動深受以下兩個意識的推動:一是背后涌動著的“香港本土意識”及其引發的“香港民主”“香港獨立”等思潮,反映了當前部分港人在后殖民文化滲透下與內地間強烈的觀念沖突;二是某些港人對自己的國家沒有文化認同意識。帶有西方殖民主義色彩的香港本土意識和文化認同意識使得回歸后的香港對同處于大中華文化圈下的中國內地和中央政府產生了離心力,進一步導致其本土意識被利用,激化了以謀求香港獨立為目的的分離意識,為今日香港之困境埋下了導火索。為此有必要正視香港與內地的觀念差異,發揚中華文化,尊重各自文化意識,不斷加強文化自信以增進香港同胞對中華文化和祖國的認同感,逐漸減少沖突和對抗,實現真正的人心回歸。
關鍵詞:文化圈 香港本土意識 文化認同意識
1997年,在舉世矚目中香港順利回歸祖國,然而由于歷史、地域、政治、經濟發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香港與內地在融合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但這些問題不足以造成2019年上半年“反修例”風波以來香港暴力活動的不斷升級,亦不足以促使香港陷入危險的境地。況且從根本上而言,香港與內地同屬大中華文化圈,彼此存在著天然的文化認同性。有鑒于此,有必要將相關問題,特別是港獨風波背后的本土意識和文化認同意識問題,置于文化圈語境中進行深入研究。
一.文化圈
1.文化圈概念的提出
文化圈(culture circles)概念最先萊奧·弗羅貝紐斯(Leo Frob é nius,1873-1938)提出。在文化神話學理論中,文化人類學家弗羅貝紐斯將非洲劃分成不同的文化圈,發現每一個文化圈都具有一系列物質文化特質,地理環境相同的地方會產生相同的文化。文化圈理論既能運用于個別文化中,也能運用于整體文化中。1911年,德奧傳播學派代表人弗里茲·格雷布納(Robert Fritz Graebner,1877-1934)對文化圈概念做出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每一種文化現象都是在某個地方一次性產生,向四周傳播,從而形成了以該地文化為中心的‘文化圈’,而一個文化圈的邊緣又與另一文化圈相交叉”[5]。
2.文化圈有關空間和時間的規定
文化圈可以從空間角度強調文化特質的分布狀態,即地理空間上的相同文化特質在一起構成文化叢,特定文化叢結合的特定空間構成文化圈。與此同時,在縱向的時間維度上,文化圈內還存在著不同文化特質出現的時間順序,即共處于一個文化中的不同特質所顯示出來的時間上的先后順序[4]。文化圈根據時間維度可劃分為原始、古代、近代等文化圈,按地區可劃分為東方、西方等文化圈,東方文化圈是東方文化中最大的一個文化圈,以中國儒學文化和佛教文化為代表。“中國內地和香港同屬于大中華區,具有大中華區文化圈的共同本質屬性,如使用漢字、崇尚儒學等”[3]。西方文明源于兩希(希伯來和希臘)文明,其主體思想基本圍繞著人、欲望、宗教而展開,自由民主意識根于其中,引領當今西方世界的主流價值取向。殖民時期的香港就深受西方文化圈的影響,形成了與內地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次文化圈。
二.香港的特殊歷史與其本土意識的形成
“‘本土意識’是指屬于某個地方……”[1],從本質上來講,本土意識作為一種地域意識存在,表現為對某一地區的熱愛和歸屬。中山大學區鉷教授認為:本土意識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意識,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個人身上又會表現為不同的時代意識和主體意識[2]。可見,“香港本土意識”體系的形成離不開歷史的積淀,同時又與當今形勢有一定的關系。
1.香港殖民地歷史與其本土意識的產生
香港的歷史可以追根溯源至5000年前,秦軍南征百越,香港一帶正式歸入中國領土,此后一直置于中華主體的管轄之下,直至1841年鴉片戰爭清朝戰敗,才于1898年被迫割讓,成為英國的殖民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與發展停滯的內地相比,香港經濟騰飛,本土文化逐漸興起,香港人逐漸確立起一種具有優越感的本土意識。與此同時,香港社會興起的諸如“六七反暴運動”“金禧事件”等一系列反殖民運動成為香港本土自我意識覺醒的有力推手,然而這些社會運動并沒有撼動英國殖民文化在香港的影響力。“在‘香港本土意識’中,既有體現香港精神、能夠凝聚香港社會‘愛國愛港’、‘愛鄉愛土’情懷的本土意識,也有刻意突出所謂‘主體性’的本土意識”[8]。為獲取香港精英階層和市民的支持,港英當局隨之采取行政吸納政治精英、教育培養“親英”力量、文化扶持淡化國家認同等一系列“柔性殖民”政策,后殖民主義意識不斷被融入到香港的本土意識中,香港人民因此不斷受到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熏陶,在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念上與內地形成差異甚至對立,香港也從最初的“反殖民主義”本土意識逐漸轉向了“反中”的本土意識。
2.香港回歸20多年中本土意識的逆向崛起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的中心地位在“一國兩制”的保駕護航中始終保持不變。但是,回歸后的香港并沒有真正地開展“去英化”“去殖民化”的教育工作,在西方殖民文化占上風的情況下,任受到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滋養的香港青年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國情的教育還停留在空白期,部分港人的“戀殖”現象日益突顯,將內地視為文化落后的“他者”。隨著內地的迅速發展壯大,部分香港人骨子里的自我認同和優越感受到沖擊而產生被邊緣化的感覺,反華情緒日益高漲,對中華文化和國家的認同感日趨消減。在這種形勢下,本土意識伴隨著“偽主體”意識在香港崛起,香港社會日益夾雜著更強烈的“小香港”狹隘思維,缺乏“大中華文化圈”的宏觀視角。
3.保守主義的抬頭和本土意識的激化
201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風云變幻,英國脫歐,北愛爾蘭與蘇格蘭站出來也想脫英,歐盟的凝聚力和一體化受到巨大沖擊。2017年特朗普在第45任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中大肆宣揚“美國優先”的口號,此后美國“毀約退群”的單邊主義行動層出不窮,促使西方文化逐步走向保守主義,歐洲分裂趨勢也愈發明顯。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保守主義的抬頭和香港本土意識的崛起,促使部分香港人在國際舞臺一片“退”“脫”聲中跳了出來,涌現出了大量不滿特區政府和反感內地的青年之聲。部分情緒化、非理性化的香港青年對內地產生情感扭曲,街頭游行示威和暴力抗爭活動頻繁密集,反政府、反權威意識泛濫。這種“新常態”的背后是躁動不安的社會和暗流涌動的西方反華勢力,香港的本土意識由此激化,逐步淪為反對派謀求香港獨立的分離意識和極端主義的推手。
三.香港歷史與其文化認同意識
1.港英政府的文化政策
港英政府在殖民期間除了對香港進行軍事、經濟和政治上的控制,還通過宗教、媒體對香港實現奴化教育。這種奴化教育以權利為導向,“強調公民的權利與責任及其統一關系,崇尚‘人權高于主權’,個人的自由權利神圣不可侵犯”[6]。在教育方面,出于利己動機,港英政府推行普遍的英語教育,販賣西方生活方式,西方價值觀念不斷滲透香港教育,一大批香港青年的思潮悄然倒向了西方意識形態化,而中文反倒成為了“二等語文”,在教育中常常不受重視。港英政府刻意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弱化港人的國家政治認同,這導致香港與內地在思想和文化上的隔閡甚至社會對立;為回歸后的香港種下了許多“不安定”的種子。
2.特區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無所作為
增強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根本在于提升語言、文化、歷史教育,然而香港特區教育局并沒有推行中國國民教育。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香港企業家伍淑清一針見血的道出了香港教育局的不作為:“仿佛不知道香港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從來沒有興趣去推動國民教育”[10];而作為香港最大的單一行業工會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也成為了反華勢力的“急先鋒”,熱衷于煽動學生群體罷課和發起各種亂港游行活動......可見香港的暴亂就是教育失敗的直接反映。2000年,香港取消作為必修教育科目的中國歷史,代之以泛政治化的通識教育,在教材中不僅有意炮轟中國的“一國兩制”還對西方的“占中”行為加以粉飾,激化香港與內地矛盾。相比于學生從小就接受愛國教育的中國大陸,香港地區教材中愛國教育的缺失成為當今多數香港青年缺乏文化認同意識的一大因素,香港學校沒有統一教材,教師授課自由,一些思想激進的教師對中國歷史進行歪曲,助長了年輕人的不滿情緒,培養了一代缺乏中國歷史觀和文化觀的年輕人。特區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不作為,最終使香港的年輕人丟掉了文化的根。
3.香港暴亂背后的文化認同危機
一個地域的文化形成需要經過歷史的沉淀。縱觀香港的前世今生,香港與內地地緣相近,血緣相親,兩地間文化一衣帶水,共處于大中華文化圈內。但是,英國在香港一百多年的統治使香港民眾深受其所灌輸的價值觀影響,文化也隨之西化,在文化多元性背景下逐漸形成了文化自我意識,在思維模式、價值理念上與內地民眾形成了一定的隔閡和心理界限,缺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這是很多沖突的起源。香港價值觀念里強調最多的是西方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強調個人至上和斗爭精神,與大陸傳統的家國教育理念、注重倫理道德存在很大不同。部分香港人將香港看作一個特殊的區域,很少有國家的概念,強烈的本土意識使得香港民眾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認同高于對國家主權的認同,認為香港社會自由法制優于大陸。面對內地的迅速發展他們產生了一種香港“優越感”喪失的焦慮,渴望主體性和獨特性,樂此不疲地追求西方反華勢力所謂的“自由斗士”“民主戰士”稱謂,在文化和國家認同的泥沼里無法自拔。
四.思考與建議
1.厚植和諧理念,包容文化差異
主權中國之外還架構著一個更具包容性和靈活性的文化中國。《左傳》中記載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9]?當今時代習近平主席在多種場合也反復強調“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多元統一的整體,包含著“差異”和“創新”,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以和為貴、以文化人的交往理念溫潤人心,所以生生不息。陸港地區間的文化差異由于歷史等原因而生,但這不應該成為沖突和對抗的借口,兩地人民要正視差異,尊重各自的文化圈,和諧共處于中華大文化圈內,針對不同于自己所處的文化圈內的制度、法律、社會習俗等要作出適應性改變和融入。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包容性的傳統,摒除傲慢與偏見,厚植和諧理念,用包容化解分歧。
2.弘揚中華文化,增進文化認同
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們要不斷弘揚中華文化,增進文化自信,宣傳和引導香港人民學習和了解中國文化,加強國民教育以形成兩地文化認同的最大公約數,積極利用文化融合來化解文化沖突,從思想上加強香港同胞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感,從而增進對內地的文化認同、制度認同和社會發展認同。“塑造文化認同的前提是基于血緣記憶、地緣記憶和歷史記憶的共有文化和同根文化,要積極發揮中華文化感召力強、依附力大的特點,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魅力讓香港青年主動尋求身份依附”[7]。香港與內地文化同源,無論是大陸人民還是香港同胞,他們的血液里都留存著中國人的文化記憶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港獨分子和反對派的居心叵測永遠改變不了內地和香港的大融合趨勢。
香港與大陸文化本同源,但是西方一百多年的殖民歷史人為地切斷了這條天然的文化認同紐帶,很多香港同胞缺乏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意識并產生了強烈的本土意識,這導致部分缺乏社會經驗的香港青年在港獨分子和反對派的推波助瀾下為追求所謂的“香港獨立”而不斷參與暴力襲擊事件,促使2019年下半年以來的香港暴亂活動不斷升級,多次觸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作為一座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城市,香港如少年般在櫛風沐雨中成長,彷徨與叛逆隨行,成長與希望相伴,針對香港暴亂,“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全國上下最大的訴求,香港與內地要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一國兩制”政策優越性,尊重各自的文化圈,攜手并進,在差異中尋求融合,在融合中化解沖突,以平復香港地區日益凸起的本土意識,增進香港同胞的文化認同意識,保證香港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推動“大中華文化圈”的發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1]Snyder Gary, The Real Work [M].New York:Directions Book,1980.
[2]曹山柯.近年我國的本土意識與后殖民主義研究[J].學術研究,2005,000(007):120-124.
[3]管艷霞.“一國兩制”背景下內地與香港跨文化沖突研究[J].傳播與版權,2013(02):104-105.
[4]王學基;孫九霞.文化圈視角下粵港澳大灣區旅游一體化發展機制構建[J].旅游論壇,2019,v.12;No.69,17-26.
[5]吳寧.移入與根植——中國人類學學科化進程研究[D].中山大學.
[6]楊紅柳.從歧見到共識:香港青年國民身份認同的政治價值觀探析[J].學習與探索,2017(7):79-85.
[7]姚嘉洵,孫曉暉.香港青年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困境及其增進策略探析[J].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8(4).
[8]祝捷,章小杉“香港本土意識”的歷史性梳理與還原—兼論“港獨”思潮的形成與演化[J].港澳研究,2016(1).
[9]跟著習主席學傳統文化之文明篇:溫故而知新[OL].新華網,http://union.china.com.cn/zfgl/2014-09/26/content_72655
82.htm.
[10]“修例風波”造成香港家庭撕裂,為何價值觀差異巨大[OL].北晚新視覺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24921
63548545846&wfr=spider&for=pc.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