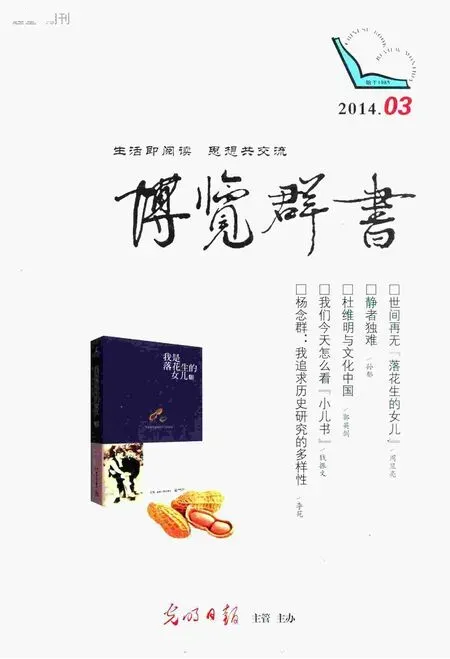高加林為什么三次進城又三次回鄉
柴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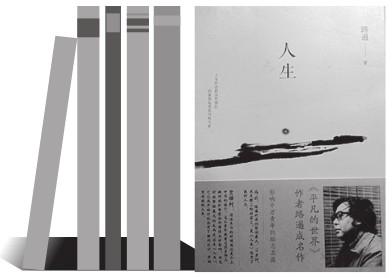
路遙是一位積極關注現實生活、努力把握社會思潮、主動把自己的人生融入歷史洪流的作家。他以自身“城籍農裔”的成長經歷和親兄弟王天樂的人生際遇為觸發點,用《人生》喚起了數代人對農村有志青年命運的關注,讓“城鄉交叉地帶”的人與事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標志性的歷史軌跡。高加林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狀況下的農村知識青年形象,像保爾·柯察金和于連·索雷爾一樣,為自己理想的生活模式而努力奮斗。他想要離開封閉、落后的農村,擺脫終身在泥土中勞碌的農民生涯,選擇一條靠知識養活自己、展現自己才華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戶籍決定知識青年職業選擇的時代,高加林錯過了三次實現理想的機會。
在小說首頁,路遙引用了柳青《創業史》中的一段話:“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引自路遙著《人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作者開頭就著力描寫高加林失業時暴風驟雨般的內心世界,接著就用他三次進城、三次回鄉的生活經歷,為人們展示了人生之路的迷霧與陷阱。
高加林失去“民辦教師”的工作,讓他過去生活中“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徹底破滅了”。他不得不再次成為耕耘在土地上的農民。這種理想身份的喪失,令他憤恨和痛苦。究其原因,高加林對生活的認識建立在學校教育和書本閱讀構建的文明世界之上。此時的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習慣與城市緊密地融合在了一起”,進而將自己想象成從里到外的城里人。
高加林第一次為解決家庭生計而進縣城賣饃,這次體驗加深了失業帶給他人生的痛苦。賣饃的過程中,他將三年前在縣城讀書的校園生活與當下賣饃農民的落魄現實不斷地進行兩極化的比較。昔日生活的豐富多彩與當下生計的艱辛枯燥形成鮮明對比,更加凸顯出他對當下生活的不滿與痛苦,也最終促使他逃進過去經常光顧的縣文化館,回避當下必須賣饃換錢的現實困境。可以說,當他挎著賣饃的籃子、走上那條通往縣城的簡易公路時,他的精神意識就沉溺在過去和當下的情感斗爭中,最終與記憶中的理想自我妥協了。
高加林在進城的路上,看見那些紛紛攘攘為生計而奔赴縣城的同鄉們,沒有一種投身于現實生活的熱情與激動,只是“感到自己突然變成一個真正的鄉巴佬”,“一個曾經是瀟瀟灑灑的教師,現在卻像一個農村老太婆一樣,上集賣蒸饃去了”。當他走進城門,電影院、商店、浴池、體育場等充滿城市文明象征的建筑,都在提醒他校園生活的美好記憶,“往事的回憶讓他心酸”。他對自我身份的認知依然停留在知識青年的角色層面。在他的思想觀念里,農民是社會地位最低、讓他羞于見人的角色。同時,他自認為讓這么優秀的知識青年成為“鄉巴佬”,會讓那些馬占勝之類的村鎮文教干部感到良心有愧。這種心態,就導致他在縣城遇見過去的熟人——中學同學和文教干事時持兩種不同的態度。
高加林搖擺在過去生活和當下現實的交錯記憶里,太陽西斜時“垂頭喪氣出了城”,巧珍為他解決了賣饃失敗的現實困境。盡管在回村的路上,突如其來的愛情讓高加林暫時“失去了任何記憶和想象”,接受了巧珍的表白,但是,回到村子后他又懊悔自己在感情沖動下與巧珍熱吻。可以說,過去的記憶不斷地提醒高加林當下生活的痛苦,也促使他要不顧一切地去實現過去設定的人生目標。
高加林一心想擺脫農民身份、生活在城里、依靠精神勞動養活自己,并沒有擺脫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理想。這種傳統理想,隨時代變遷而具體化為做“公家人”的職業理想。城市具有地方經濟、文化、政治中心的聚合功能。在高加林的想象中,進了城,也就成了靠知識吃飯的“公家人”。
不識字的農女巧珍面對農民身份的高加林,才敢于抱著實現理想愛情的希望去追求愛情。巧珍的愛情并不足以讓高加林遺忘過去的生活記憶和人生理想,只有對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幻想,才能使高加林“短暫地忘記疲勞和不愉快”。一旦往昔的記憶被當下的場景再次喚醒,就會重新激活他對理想生活的渴望。
高加林為了給村里收集耕肥,第二次在夜中進縣城拉糞。他拉著茅糞桶走在縣城的夜色里,燈火喧嘩的城市夜景和空寂安靜的鄉村生活,在他的腦海中再次形成鮮明的反差,激蕩著他不安分的靈魂。相同的地點,不同的境遇,那些存留在教室、電影院、體育場等城市空間中的記憶瞬間被激活了。高加林路過縣廣播站,馬上把想象中黃亞萍此刻的夜晚生活場景與自己當下流汗流淚的挑糞工作進行比較,之后又通過與“先鋒”隊菜農因爭搶車站公廁的糞便打架,宣泄自己此時的憤懣無奈和苦悶情緒。
但是,他還來不及平息因打架而感受到的不平與憤怒,就在副食公司家屬院里承受了更深重的侮辱。住在家屬院里的張克南母親,嫌棄高加林在夜晚納涼的時候挑糞,辱罵他是“一身糞”的“鄉巴佬”。這更是刺痛了高加林的自尊心,他只能強忍淚水,為有文化有知識的自己受到屈辱而不平。來自當下現實的屈辱體驗沉淀在高加林的思想意識里,也成為他未來人生選擇的一種無意識催化劑。
路遙深諳中國傳統文學敘事之妙,“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用了一個細節暗示高加林在不久的未來接受黃亞萍求愛的必然性。小說寫道,高加林拉著糞車在燈火映紅的河邊停下來,此時的心情“燃燒著火焰”,他“渾身的血沸騰起來”,向遠處“燈火映紅的河面”奔去,快到河邊時路過“先鋒”隊菜地,“報復性的摘了一抱西紅柿”,然后在水里憋氣、下沉、上浮,吃掉西紅柿。可見,高加林在搶糞中感受到的不滿,通過這些奔跑、游泳、偷菜的行為而得到宣泄,但是,被張克南媽媽辱罵的屈辱與憤懣并沒有得到合適的排解。
高加林通過與他有關聯的同學黃亞萍、張克南來獲取縣城青年的生活內容,并時時將自己當下的生活現狀與小縣城上層青年的生活樣式做比較。他們有同樣的教育經歷,但在社會地位、經濟條件和家庭環境方面差異巨大。這讓現實中的高加林感到更加痛苦和不平。
路遙渴望勞動改變命運,這種勞動更傾向于一種精神層面的腦力勞動,并沒有擺脫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文化觀念。同時,他認為土地是人類世界生命延續的根源,鋼筋混凝土構筑的城市空間終歸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暫時性狀態。巧珍對體力勞動和農村生活的熱愛,就體現了作者對農村生活的迷戀,這與高加林對城市生活模式的向往,形成了鮮明的沖突。因此,高加林的進城理想及現實選擇,本身蘊含著路遙自身的困惑。
路遙認為,自己是既帶“農村味”又帶“城市味”的人。“農村味”代表他過去的生活體驗,“城市味”是他當下生活狀態的寫照。這兩種味兒也在第三次進縣城后的高加林身上此起彼伏。過去農村生活形成的人生理想和當下城市生活習慣之間的沖突,促使他不得不在前途理想和真實情感之間做出抉擇,最終導致悲劇性的結局。
高加林第一次進縣城賣饃回到高家村時,感到自己在困境中匆忙地與一個農村姑娘發生愛情,是墮落和消沉的表現。在他的內心深處,“和巧珍結合在一起,他無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可見,高加林的思想意識里依然沿襲著傳統文化中“門當戶對”的婚嫁觀。但是,在他第二次進城拉糞前,身處農村艱苦生產勞動中的高加林想象未來的人生方向,渴望將來能離開農村去外面務工或當干部,希望也能把巧珍帶去。這時的他,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憧憬和希望。高加林第三次進入縣城,從一個青年農民變成縣委宣傳部的通訊干事,從過去生活經驗里城市的過客暫時變成城市中的一員。對這種轉變,他感到激動和滿足,并決心努力工作,展現自己的才華。當黃亞萍向他表白愛情,并許以省城電臺記者的未來職業發展方向時,他認為這將是決定自己命運轉折的機會。更讓他自得的是,他戰勝了出身縣城干部家庭、經濟條件優越的城市青年張克南,贏得縣委干部家庭出身的“城里的小姐”的愛情。
此時的高加林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習慣,在會場、體育場、國營食堂等城市空間里贏得人們注目與尊重。報刊、廣播等媒介更是讓他成為縣城的名人,自尊心得到最大的滿足。他也滋生出超越縣城獲得更大光榮的愿望。他的生活習慣、戀愛方式和人際交往原則,都隨著新的生活環境發生了改變。黃亞萍按照“現代”化的大城市生活標準去裝扮、改造高加林,塑造自己心中的“完美愛人”形象。高加林也以為,他接受黃亞萍的愛情,可以無視輿論和良心而融入這種新奇而激動的愛情,是追求自己的“活法”。
高加林想要的謀生方式是用筆耕耘在白紙上的精神付出。他向往白底黑字上描畫出的世界,忽略了真實的現實世界。身為通訊干事的高加林,面臨的問題不是能否擺脫農民身份,而是能否進入省城那樣更大的城市空間。他已經暫忘了那段失業在農村生活的困境,遺忘了那片養育他的鄉土。
高加林以為他與巧珍之間出現交流障礙,是由于巧珍無法理解文字編織的幻象世界帶來的精神愉悅。實際上,這主要是因為巧珍對于他將要實現的人生未來理想,沒有權力、經濟上的幫助。高加林理性權衡巧珍帶給自己的現實生活和黃亞萍將帶給自己的未來理想,感情的天平就傾向于選擇命運轉折的機會。但是,他忘記了,當時在失業困境中接受巧珍的愛情,雖是對傲氣十足的巧珍他爸的報復和打擊,但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可見,高加林兩次接受愛情的心理狀態,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每一次他都從自身當下所處的現實出發,選擇更有利于自己的機會。
普魯斯特認為,人類經驗之真理,只有通過理解記憶和時間,才能加以把握。人永遠難以認清當下自我存在的真相,只有經歷過后才能看清來時的路。高加林在當下的迷霧中,做出錯誤的選擇。等他意識到一個人“千萬不能拋開現實生活,去盲目追求實際上還不能得到的東西”時,注定已再次墮入絕望的深淵。
路遙說,作家的作品要接受現實的檢驗,更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鄉村和城市是人類文明進程中兩種基本的生活方式,在時代發展的今天,“城鄉交叉地帶”的邊緣日漸模糊,遺落的鄉愁漸漸游走為城市空間的老街舊巷。新一代的“城籍農裔”人,也只能在記憶中追尋泥香,在時光之城中體會人生的局限與漂泊。
(作者系文學博士,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