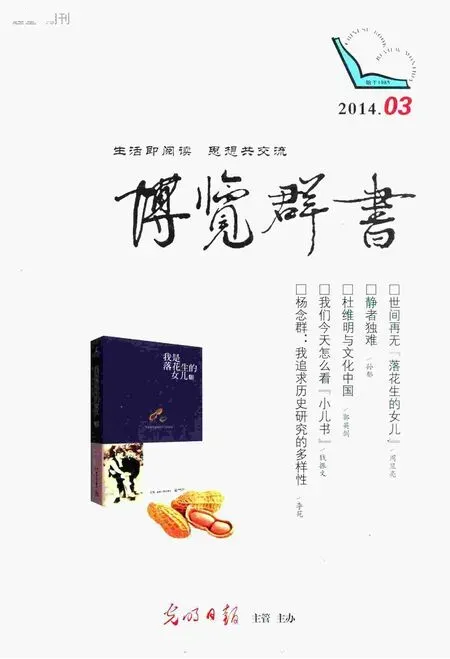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職業認同”這一概念為何“不見了”
樊亞平
《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心態史研究(1912-1949)》一書是我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心態史研究(1912-1949)》的最終成果,也是我在攻讀博士期間開啟的新聞史人物研究領域持續耕耘的又一成果。
攻讀博士期間,我曾以職業社會學領域的“職業認同”概念及相關理論為視角和基本框架,對近代報刊出現至北洋軍閥統治末期這一歷史時段內的新聞從業者職業意識發育史、職業成長史和職業心靈史進行了研究,試圖探尋職業社會學意義上的“記者”“報人”在中國的早期成長歷程與發展足跡,感知他們從事新聞職業的理想與困惑、激情與無奈,探求他們篳路藍縷、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當時的研究應該說是頗為成功的。博士論文送審、答辯時得到了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教授和諸多著名學者——如陳力丹、楊保軍、李彬、黃旦等的相當高評價和美譽,出版后更是得到了圈內眾多相識和不相識的師友、同仁、學生的好評。當時的我為此頗有一些自得,自認為挖到了一個學術研究的富礦,尤其為自己在該研究中所引入的“職業認同”這一源自其他學科的理論視角與框架而得意。眾多學者的贊譽強化了我在確定此選題時已暗自下定的準備按此路子將新聞史人物職業認同研究進行到底的決心。當時的研究最終凝結為《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認同研究(1815-1927)》這本出版后經常脫銷的著作。按我當時的想法,接下來的第二本書的題目顯然是明擺著的,即,《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認同研究(1912-1949)》,研究視角和路子當然與前一本書完全一樣。
然而,現在擺在各位同仁與讀者面前的這本書的題目卻是《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心態史(1912-1949)》,之前研究中曾讓我頗為自得、自以為能體現自己研究的視角創新的“職業認同”這一核心概念不見了,代之以“職業心態”。由“職業認同”到“職業心態”,看似只有兩字之別,實則蘊含著前一本書出版后的十年中我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的認識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在研究中國新聞傳播歷史與現實問題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切實深入到中國新聞傳播豐富、多樣、鮮活的歷史情景與現實邏輯中去,發現根植于這種歷史情景與現實邏輯的真實情狀與問題,對其進行不帶任何固定套路和現成模式的實實在在的研究,而非使用某個源自其他學科或西方的概念及其理論框架對中國特有的現象與問題進行簡單闡釋或驗證式研究,更不能照搬西方或其他學科理論來研究中國特有的現象與問題。
就我所開啟的新聞史人物職業意識發育、職業成長和職業心靈研究來說,我之前引入“職業認同”概念及其理論框架所做的中國新聞從業者職業認同研究,雖然并非簡單闡釋或驗證式研究,更無照搬西方或其他學科理論之色彩和意味,而是將“還原歷史情境”“回歸歷史現場”作為研究的基本理念、追求,在研究中力求回到人物所處的個人生活情景與社會歷史情景,但該研究畢竟是從職業社會學領域考察職業認同的四個主要視角出發對每個人物的職業意識發育與內心世界進行關照和呈現的,因此不免給人一種較為刻板的印象。如果說當時引入“職業認同”概念及其理論在新聞傳播學領域還屬于一種引領風騷的學術創新的話,今天繼續沿用十年前的研究路徑與模式無疑就顯得有點老套和刻板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變化,在這次研究開始之前,我便開始了謀求研究創新的努力。
這種認識轉變和謀求創新的努力是如何產生的呢?說到這種轉變的產生,不能不說到我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的日子。在復旦新聞學院做博士后期間,我原本準備按之前研究新聞史人物職業認同的模式和路子對范長江新聞生涯與職業認同進行研究,但最終卻放棄了“職業認同”概念及其理論視角,決定回歸范長江人生歷程與職業生涯,對其人生追求與職業求索中的心態進行直接的、不帶任何固有框架的研究。這一變化的產生緣于與黃旦教授的碰撞和李金銓教授的間接啟發。
黃旦教授在我博士后報告開題時對我繼續沿用“職業認同”概念和理論框架研究新聞史人物提出了非常明確的不同意見,認為借用其他學科概念和理論框架必然會對自己的研究產生牽制乃至轄制,必然會影響自己對所研究人物內在心靈與心態的自由呈現。當時我并不認同黃旦教授的看法,我“爭辯”說,我并沒有簡單套用“職業認同”概念及其理論框架,并沒有把“職業認同”作為一把價值評斷的標尺,用它去一一度量所研究的人物,并沒有用職業認同與否作為尺子對所研究的人物進行價值評判,我只是將它作為考察所研究人物內心世界的一種視角和進入其內心的一個出發點,它并未,也不會對我的研究產生轄制。開題報告后,就此問題黃旦教授還曾與我交流過不止一次,但我并未完全心服口服。
過了一些日子,我看到了一篇李金銓教授在蘭州開會期間接受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訪談的文章。在這篇訪談中,李金銓教授在談到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時,非常明確地表達了其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新聞傳播歷史與現實問題的路徑與方法的反對,認為西方理論自有其產生的特殊時代、特殊土壤,自有其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它們大都是為了解決西方特殊時代、特殊文化土壤上產生的特定問題而產生的。因此,試圖用它們來解釋中國特殊歷史或現實問題,往往隔靴搔癢,牛頭不對馬嘴。要想提升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層次,就要深入到中國新聞傳播的歷史與現實中去,發現真正屬于中國新聞傳播歷史與現實的真問題,對其進行實實在在的研究。
正是受到黃旦教授和李金銓教授的啟發,我決定拋棄“職業認同”概念及相應的研究框架與視角,以探究人物心態為目標,深入到范長江成長和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與時代情景中,深入到范長江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生境遇與個人生活情景中,對其探求個人出路和國家民族出路的歷史過程及在此過程中的心態變化進行客觀的全景式呈現,以此展示作為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上的標桿式人物的范長江豐富、鮮活、獨具特色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正因為有了研究思路的變化和研究路子的革新,這部以“范長江心態研究”為題的博士后報告完成后收到各方面的積極反饋與評價。參加我博士后出站答辯的包括黃旦教授在內的五位專家、新聞史學界諸多前輩和中青年實力派學者等,均對報告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贊賞。
由于我明白這部博士后報告之所以能獲得這樣的評價與反響,主要是因為拋棄了“職業認同”概念及相應的理論框架,不帶任何框框地直接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對其心態進行不帶任何“有色眼鏡”的研究和呈現,因此,由此開始的我的新聞史人物研究便十分明確地將“職業心態”確定為研究過程中的關鍵詞和核心目標。以此為目標對從中華民國成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期間最主要的五類新聞從業者的職業心理、職業情感、思想理念及心路歷程等進行“還原歷史情境”“回歸歷史現場”式的研究之后,便有了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去除了“職業認同”這一之前曾令自己自得的概念、代之以“職業心態”的書。
由于放棄了之前熟悉的研究路子,研究過程中“毫無憑藉”,只能抱著盡力深入每個人物個人生活情景與社會歷史情景的目標,獨自摸索,再加上研究所設定的人物較多,對每個人物的研究又不僅僅限于對其新聞從業活動的關照,而且涉及其整個人生求索及其他活動,故工作量可以說非常大,因此,擺在大家面前的這本書肯定存在不少問題和不完善之處,我只能在此請求各位同仁與讀者批評指正,以便我能在接下來的研究中盡力改進了。
(作者系蘭州大學“萃英學者”,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聞傳播學本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新聞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新聞史學會地方新聞史研究委員會副會長,甘肅省新聞傳播學類專業教學指導、認證與教材建設委員會主任,“甘肅省領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