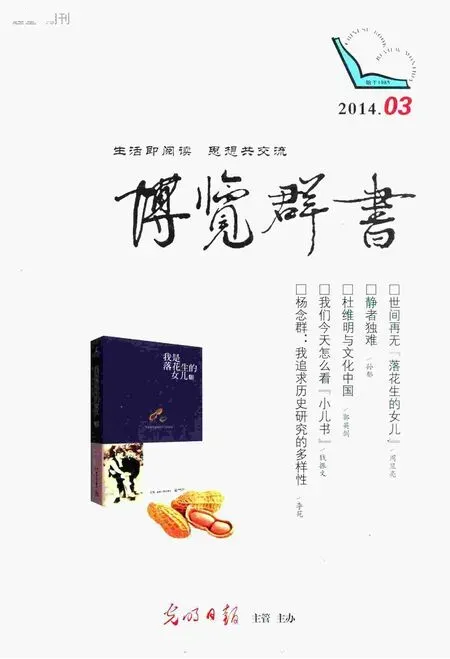該感謝逝川還是詛咒逝川
石鐘揚
20世紀末旅京訪勝,朋友有詩《比目魚》紀之,我也湊了首《蝶夢》與之呼應。前幾天我向他索《比目魚》以助記憶,他悵然作答:流失在逝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該感謝逝川還是詛咒逝川呢?它淘洗了諸多舊痕,留下的或更珍貴。此刻我尤想在逝川中撈回若干蝶夢,當然是關于《性格的命運》的。是自戀情結作祟還是老無長進所致?我也搞不清,反正不算“朝花夕拾”。
20世紀80年代確為激情燃燒的歲月,《性格的命運》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書中探討的雖是古典小說的審美奧秘,其間也澎湃著我的激情。本來在鋪紙振筆之余心造一個讀者促膝案前,與之作心靈對話,也不失為賞心樂事。然而在當代中國“爬格子”并不是什么輕松的生存方式。世事紛擾,人心不寧。往往只得在夜深人靜,妻孥鼾唱聲起,才勉強坐在案前,在燈花月色陪伴下去尋找屬于自己的那點境界。可是沒爬上兩頁紙,就有瞌睡蟲來請安。每每帶著悔恨躺下,又期待第二日帶著興奮爬起。
當年在那僅可容膝的蝸居里,我夜以繼日地書寫著,雖苦猶樂。
書拖到上世紀90年代末才得出版。自跋中“我雖早過不惑之年”云云改了三遍,初曰“已屆不惑”,再曰“已過不惑”,到某年夏出版在望就寫成“早過”,沒想到又過三年多才真的見書。可見其出版何等艱難。即使如此,我仍感激那個時代。中學、大學時代受擾難以安心讀書,盡管我酷愛讀書。20世紀80年代終于能心安理得地讀書、教書、寫書,樂何如之。
我從小愛讀小說,也曾做過小說創作的夢。然而在我生命最富夢幻的歲月里,往往苦于“想寫的不能寫,能寫的不想寫”。寫不成小說,就千方百計地將別人寫的小說弄來昏天黑地地讀。被放逐到“廣闊天地”的日子里,在故鄉昏暗的煤油燈下,小說(當然不限于中國小說)幾乎成了我的精神伴侶。20世紀70年代,我在師友的協同下,借得圖書館一隅,竟引經據典地寫了本《〈紅樓夢〉詩詞評注》。那本書雖極其丑陋,并早消逝在書的海洋中,但它畢竟不是“從幾十條人命看《紅樓夢》主題”之類的東西。因而我視之為自己從事小說研究的起點。
或許是曾有的那點創作意識在鼓蕩,或許是曾勉強讀懂幾部小說的那點審美經驗所支撐,我在研究中(包括上課)從不愿人云亦云,總喜歡講些“自己所找到的東西”。當它們陸續訴諸報刊時,竟意外地獲得了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的稱許(有相當一部分為一些有影響報刊所轉載,所評述),當然也有善意的批評與爭鳴。我無法判斷自己所言種種有多少科學性,只是努力地投身到追求科學的過程之中去。
已發的文章,涉及中國小說的方方面面。1989年暑假,有友人極力慫恿我將其中關于中國小說審美藝術方面的文字,揀出匯成一本書,說是它們遠較那些正經八百的論文有“靈性”。有這錯愛之譽,加上有出版社愿玉成此事,我就真的操練起來了。
全書分上、下兩編。
上編探討中國小說中具體的人物性格及其命運,下編探討中國小說自身的藝術性格及其命運。
“性格就是命運”這名言,雖出自西哲之口,卻似富有禪味。我蠻喜歡它,因而生吞活剝出個“性格的命運”作為全書的總標。只不過在西哲是個肯定的話頭,到我卻成了個朦朧的意象。
書的副標更換過幾次,先名為“中國小說審美趣談錄”,朱光潛先生之學術助手朱式蓉老師當時正在籌措《朱光潛全集》的編輯出版,他以美學法眼視之說有媚俗之嫌,賜名“中國小說的審美構成”。自忖他對拙著期待過高,而拙著實難拿出嚴謹的體系以副其名,因用了今題:中國古典小說審美論。而實為中國古典小說審美片面觀。其間不免有鄙薄圓潤的“面面觀”之意,卻并不意味著我已達到了“深刻的片面”。只是希望從自己最感興趣的角度切入中國小說的審美世界,從若干可串連的側面,去尋求中國小說的行進線索。
在寫作過程中,我只求一吐為快,力避學究程式與宏觀空談,即使是大題目也從細部著手慢慢道來。《世說新語》式的審美片談,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我對之心儀已久,只恨自己永遠寫不到那“氣韻生動”的境界。
本書的寫作與平日的小說研究,都得到過恩師朱一玄先生的熱情鼓勵和幫助。
一玄先生是中國小說史料學大師。他早年遭厄,晚年以極其頑強的毅力,銳意窮搜,在一個相當荒涼的基地上筑起了一座中國小說史料的長城,嘉惠后學,功不可沒,是那些輕視史料的空論家們所無法比擬的。先生每有新編問世,總先行賜我,甚至尚未刊行的編著,也允我先用,惠我良多。
先生在為我另一本關于《西游記》的書所寫的序言,對我更是鼓勵有加。他說:
我與鐘揚同志相交數年,80年代初鐘揚同志曾來南開大學中文系進修,朝夕切磋,情誼日篤。當時我正在從事古典小說資料的編輯工作,鐘揚同志經常提出中肯的意見,如對虞集《〈西游記〉序》的看法,便對我幫助甚大。以后書信往返不斷,并多次拜讀其寄贈的著作,深感其學術成就日有進益,必將推動古典小說研究的發展。
這實令我愧莫能當,唯有努力筆耕,以報答先生厚愛之情。
本書寫成后,我有機會赴京拜請序于舒蕪先生。舒蕪先生當時正在寫關于周作人的系列論文,忙得很。原以為先生看看提要,聽聽介紹,就可寫序。豈料先生看了我帶去的大半部書稿猶嫌不足,問我為何不帶全稿?對帶去的稿子,先生是逐一細看了。稿子原是請學生謄清的,我校勘不精,先生則為之糾謬十數處。這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令我敬佩不已。
舒蕪先生是當代中國首倡“回歸五四”的學者,其畢生的學術堪稱“回歸五四”主旋律下的三部曲:一鳴驚人的《論主觀》、世說新語式的《說夢錄》、大徹大悟的《周作人概觀》。舒先生看好的恰是拙著中的“五四”氣息或余韻。其序以理論家的敏感,一語破的,有點石成金之妙,尤為令我感動的是,先生對拙著中某些觀點不同意,也能直率指出,而不同于某些一味以美言應景的序言。
《性格的命運》被舒蕪先生謬贊為“寓熱量與養分于滋味中”“有趣有益的好書”,我不敢應承,只求與朋友作“心靈的溝通”。與獲得什么獎項相比,我更在乎同學們在課堂上專注之余的笑聲(安師中文系93級王立群、99級許金萍等皆有文記之,南財財管李娜在選修課后竟一口氣寫了五篇有“片面的深刻”的短文)、諸位同道不吝賜教的評說(朋友們在報刊上發表書評有八九篇),學術會上某些初次謀面的朋友竟視之為我的名片:“我讀博時看過您的書……”也因此結識了不少新朋友。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轉眼三十多年過去,感謝仍有朋友惦記著這本小書,新版也應運而生。當年與我一樣出走“圍城”的胡繼華博士,聞之欣然在其佳評后添了一段詩性文字,讓我在庚子之冬憑增抗寒的溫度。《性格的命運》首版責編張丹飛說:“這是我博士畢業入職編的第一本書,有品位,我至今記憶猶新。”并設法找出了它的電子版,為新版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文人陳獨秀》責編劉景巍說:“《性格的命運》文字太美,我當初就是為之打動了才向你約稿的。”(我也成了陜西社的老作者,在那里出了幾本書。)
寧宗一先生年屆九十,仍不辭勞苦為《性格的命運》新版賜以佳序,他將心靈美學與五四精神結合起來言說之,對不才鼓勵有加。令我無比感激且惴惴不安,愿步履蹣跚地向先生期待的境界靠攏。
《性格的命運》新版增加了插圖,以光篇幅。原版內容未動,只改了若干錯別字。附錄了三篇書評,三位朋友各有文化幽懷,從不同視角評說拙著,在讀者可作參照系,在我當然是珍貴的歷史留念。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