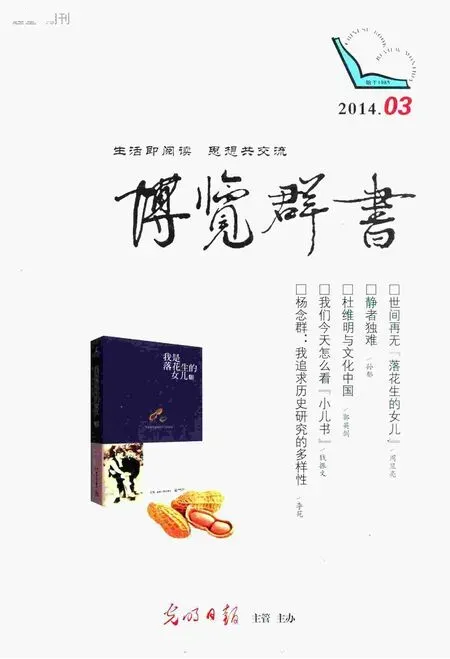歲月被梁鴻鷹寫成怎樣的“顆
劉金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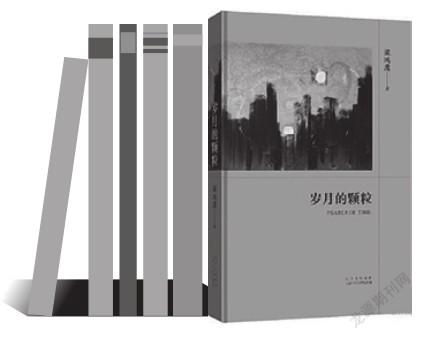
作為一種自由不羈且極具情感表現力的文學體裁,散文最需要也最能體現作者的性靈和情愫,可以說充分發掘、適度調控與合理運用性靈、情愫等自我感受,對于個性化散文創作至關重要,僅以懷戀故鄉題材的散文為例,作者對摯愛親人的朝思暮念、對故人舊事的魂牽夢系、對離愁別緒的沉潛品嘖,這些自“我”感受需要在散文中自然流露和真誠表達,就此而言,是否有“我”無“我”,就成為檢測散文品位高下的一個重要標尺。著名學者、作家梁鴻鷹寫就的《歲月的顆粒》(北京出版集團2021年3月版),就是一部抉發和詮釋有“我”的個性化散文作品,是一部以“我”為觀照主體和敘述核心的“精神自傳”。
散文集《歲月的顆粒》輯錄了作者近年創作的18篇散文,幾乎每篇散文都刻錄“我”的生命萍蹤和情感印記,都涵納“我”的生活經歷和人生感悟,這些散文通過鉤沉和反芻“我”的故鄉情結和生命點滴,勾勒出“我”故園生活的行蹤軌跡,通過聚焦和描述“我”前塵往事的明媚與憂郁,摹繪出“我”青春年少時的生活圖景,可以說《歲月的顆粒》是一種打開“我”早期精神履歷的文學方式。莫言說,一個作家難以逃脫自己的經歷,而最難逃脫的就是故鄉的經歷。散文集《歲月的顆粒》的主調和底色是追憶故鄉,這也是作者的敘述策略和言說理路,更是作者建立與故鄉精神聯系的載體與路徑,正是在多層多維的深摯回憶中,作者娓娓敘及“我”來自何方的隱情,款款道出“我”成為今日之“我”的秘籍。事實上,幾乎每位作家都有一個精神原鄉,都有一個牽系情感和扯拽心魂的地理圖騰,這個精神原鄉和地理圖騰如同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留存著作家兒少階段的生命體驗,盛裝著作家難以忘卻的情思和夢幻,珍藏著作家不諳世事時的樸素愿望和殷殷企盼,見證著飄然而逝的歲月滄桑和酸甜苦辣的人生起落。摹寫過去生活的背影,撿拾消逝歲月的顆粒,將精神原鄉和地理圖騰在“我”身上留下的種種痕跡,精妙而獨到地書寫出來,這是《歲月的顆粒》的創作題旨和審美要義。梁鴻鷹的故鄉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磴口縣城,那是一個被稱作九曲黃河第二曲的要津渡口,也是一座地處河套平原西端與烏蘭布和沙漠東側的塞外小城,如果將巴彥淖爾的多彩風光比作一幀精美畫冊,那么磴口便是這本畫冊的亮麗首頁。正是這個歷史基脈深厚、自然風貌殊異的塞外小城,成為梁鴻鷹精神成長的發祥之地,成為作家寄寓無盡鄉愁的生命起點。解讀散文集《歲月的顆粒》,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于作者而言,歲月悠長但人生苦短,回首故鄉是一種珍視,書寫故鄉是一種致意。磴口小城在《歲月的顆粒》中是一種詩意的存在,書中的生活背景和人物故事與磴口小城形成一種對象化審美關系,“郵票般大小”的磴口是“我”“精神的依傍之所”,是“點燃作家文學想象”的最初場域。作者筆下的磴口小城寧靜、恬淡、悠然,充溢著濃郁的母性氣韻又不乏濃重的父性氣息,溫存和滋養著“我”孱弱的身體和孤寂的心靈;小城中的父母、親朋、老師、同學,以及火車站、理發店、書店、學校,是故鄉的肌理和表情,傳遞著故鄉體溫和故鄉神態,寫下他們既是安頓和慰藉,更是感恩和酬答;他們不僅構成“我”追溯和詮釋的文學母題,而且嬗變為人文符碼和文化隱喻,換言之,磴口小城已超越地理學意蘊而成為一種情感意象,那里諸多纏結“我”靈魂的人與事,演化為“我”的追思、緬想和渴念,呈現出醒豁的書寫意義和鮮明的詩性價值。
作為散文寫作的最高境界,詩性精神是散文體現個性價值的內在底蘊,“詩性精神”所倡導的“深情兼智慧”“立象以盡意”也為梁鴻鷹所秉持。散文集《歲月的顆粒》不僅葆有純真的詩感、繽紛的意象和靈透的語言,而且呈具一種詩性向度和詩意追求,對自身成長形而上的思咐深蘊于作品結構中,直逼事物本質的感悟貫穿在作品字里行間,如“悵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頹然,衰敗、老去、寥落,最終迎接命運對自己最后的審判”(《最初的年頭》),再如“愛是生活的前提,是幸福的基石,是陶醉、戰栗、痙攣、發呆,是情欲的愛撫,是巨瀾般的波動,是風暴般的席卷”(《母親與我的十二年》),“有的人一輩子主要以人生鑒賞家而存在,有的人主要以人生價值評論家出現,人生正確的參與者總是那樣的稀缺”(《父親零章斷簡》)等,靈感飛揚,意蘊悠長,既不矯情造作,也不偽飾空泛,這是詩性智慧的律動,是詩性稟賦的表達,也是詩性精神的揚厲,書中不乏內曜詩性精神的唯美篇章。社會心理學表明,男性成長大體要經歷懵懂、叛逆、覺醒、救贖四個階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美國作家福克納說“每個男孩都是一部偉大的成長小說。”當下變動弗居的社會里,小城與都市、過往與現實互為鏡像,因而,回憶懵懂、叛逆的兒少時代,對于多年負笈在外的“我”來說,不失為一種情感補償和精神救贖。在《歲月的顆粒》中,樸實懇摯的文字律動著思鄉之情,簡潔誠篤的敘述傳達著戀鄉之意,這種散發溫潤與暖意的散文書寫,是作者“精神還鄉”的形象實錄,是作者尋找精神成長依據的文學見證。與梁鴻鷹理性深刻的文學評論相較,《歲月的顆粒》中的散文更見溫情和真摯,更能顯現個體生命的真實刻度。林語堂曾經說:
凡方寸(散文)中一種心境,一點佳意,一股牢騷,一把幽情,皆可聽其由筆端流露出來。
久遠的記憶、徹骨的往事,總會在夜闌人靜之時輕叩心魂,喚醒“我”文學書寫的自覺與能動,于是作者以曼妙筆觸不動聲色地講述,以樸拙語言坦然平靜地敘說,使關涉故鄉小城的記憶片段充滿情感張力。《母親與我的十二年》一文輕舒慢緩、淡墨濃情,作者以至情至真至純的文字,描繪了母親通達、純樸、善良的品性,讀罷心頭酸楚、淚眼婆娑;《被歲月和父親所塑造》一文深描細繪、語密心澄,作者以本然純摯清爽的語言,刻畫了父親隱忍、坦蕩、持重的一生,閱畢心情沉郁、五內交集。這兩篇回溯父母多舛人生際遇的散文,不僅揭示了命運無常對“我”精神成長的微妙影響,而且表達了創傷記憶蘊含著或深或淺的精神隱痛。作者在追憶故鄉或美好或憂郁的前塵往事的同時,也在品味前塵往事之于“我”的人文意義,表現在作品中,作者將“品味”還原為生動場景和鮮活故事,真切展現那些漸行漸遠的人與事,使故鄉小城凝結的文化意蘊更多地顯示出生命的自然狀態。《最初的年頭》一文呈現了姥姥慈愛、仁厚、豁達的心地,《遙遠的奶媽和她的孩子們》一文書寫了奶媽一家人淳樸、和善、熱誠的心性,《世上最寒冷的那個早晨》追念了母親去世那天“令人愁腸寸斷的場景”,抒發了源自“我”內心深處的悲傷、愴然和依依不舍,成為全書最動容最感人的篇什,也許是情到深處意更篤,只有當“優雅”“堅韌”“無畏”的母親離開人世時,作者的筆下才掀起更為急驟的波瀾。
懷念親人固然是一種鄉愁表達,而記述故鄉風物和友朋也是一種鄉愁傾訴,《火車進站》點繪出小城車站忙亂蕪雜卻又不失恬靜安然的姿態,《書店不完全往事》展現了塵世某些點面的渾濁污穢和人性深處的詭異幽秘,《哦,那一年的高考與假日》和《夏季的愛與欲》兩文,通過重溫高考前后“我”的幽微心事和回放大學任教時的真純戀情,印證著青春芳華期“我”的躁動心理和健康心智,表明作者對人性、情愛、責任的思考、踹度和審慎。細節展示散文個性、體現散文韻味、彰顯散文風范,決定著散文的品相和成色。關注和留心既往生活河流中的波紋漣漪,以及發掘波紋漣漪背后別有意味的思想玄機,是散文集《歲月的顆粒》個性化的又一突出表現。正如作者在其文學評論中經常將“西部”“鄉村”“黃土地”“大漠”“高原”“白楊”作為文化符號進行寓意解析一樣,在散文寫作中,作者也頻頻用細節作為精神表達的通孔和機關,如《父親零章斷簡》中的收音機、自行車、菜肴是現實情境中的細節,而站臺則是人生旅途的一個隱喻;再如《史上最寒冷的那個早晨》中的樹木也許讓人有些親切,而冬日早晨的寒風則使人徒生悲傷和孤獨。書中散文的諸多細節,不僅述說陳年往事,而且蠡測世道人心,使得“我”的童年生活變得飽滿、真晰、明澈,既帶著體溫又掛著淚痕,引領讀者深切體會故鄉記憶的歡愉和欣忭、悲苦和落寞。細節更見功力和性情,而細節的選擇取決于作者的氣度和素養。涉獵廣泛、學養豐湛的作者,借助對知識細節和生活經驗的積累、打磨和整合,辟建一種屬于自“我”的文學樣式,書中的《聲音考》《毛發的力量》《執子之手》和《我們照相吧》是四篇悅心怡情、養性增趣的學術隨筆,作者在庸常中發掘神奇,從陋見中開發新意,使讀者在生氣灌注的文化語境中獲得智性愉悅。情愛中的細節是一份真誠、一縷溫馨、一種感動,書寫愛情的散文離不開對細節的撿拾、觀審和描摹,書中的《盈盈尺素》一文,以云錦鯉素作為牽系綿綿情感的介質,宣示了一個真摯溫婉、一波三折的愛情故事,為“我”的情感旅程留下一段甘之如飴的佳話,收到周振甫先生所說的細節由“搜間傳神”到“推微知著”的審美效果。
創意性散文寫作是一種觀念變革行為,無論何種形式的散文創新,都是在藝術精神的引掖和促動下的文體嬗變。為了讓敘述更妥帖更自然更豐盈,梁鴻鷹對散文文本做了些許技術調整,通過變換敘述人稱延展觀察視野,通過延展觀察視野豐富追憶內涵,書中一、二、三人稱的不斷變化與適時轉換,意味著主體敘述視角的交替與更迭,形成一種多維敘述模式,開闊了散文文本的敘事空間,彌補了敘事之“我”和經驗之“我”的認知缺失。同時,不同人稱出現在散文集《歲月的顆粒》的不同篇什中,不但沒有使作品產生內容疏離感和邏輯違和感,相反使“我”的往事回憶變得更加客觀立體真切,并增加了讀者的閱讀經驗和審美享受。作為一種探究生命本質的文學樣式,散文是精神解放和文體開放的產物,其先天便同歷史、哲學、美學等學科糾集在一起。在《歲月的顆粒》中,很多散文開篇除了摘錄古今中外作家詩人的精彩表述和精辟論述外,還引用了一些哲學家、歷史學家的經典論斷,這種“鳳冠明珠”式的運思,不僅為整篇散文確定了基調和意旨,而且在與正文互辭過程中起到統攝和引領作用。優秀的散文作品能夠超越時代框限和地域拘囿,引發不同年齡不同地域讀者的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文質俱佳的散文集《歲月的顆粒》,無疑也會擁有眾多跨時空的精神知己。對于我這個出生于東北邊陲的同時代讀者而言,作品在我心中激揚起澎湃的記憶浪花,鼓蕩起壯闊的往事波瀾。品讀《歲月的顆粒》,如同與作者共同行走在塞外邊城的街巷里,一同寓目和篤守北方天空下的精神家園,一道領受和承納命運的安詳、灑脫與超然。
(作者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