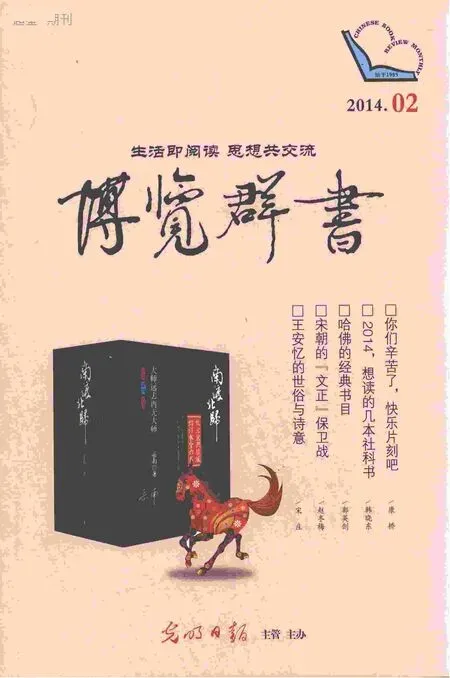第一個中文版《魯迅全集》送審之后
北塔
第一個中文版《魯迅全集》是許廣平以魯迅遺孀的身份去國民黨內政部送審的,現在所見內政部批文上寫的是“周許景宋”。
許廣平是何時開始送審的呢?
比較明確的說法有兩種。
1.1936年11月說。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如,早在1978年,葉淑穗和張小鼎在《浩大的工程 卓越的勞績——紀念三八年版〈魯迅全集〉刊行四十周年》一文中說:“許廣平同志在魯迅生前友好的協助下,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就將全集目錄編好,報送國民黨內政部審核登記。”“十一月”指一整個月。我們能把時間定位得更準一些嗎?王錫榮在《許廣平為出版〈魯迅全集〉奔忙》一文中說:
從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在短短的一個月里, 許廣平強忍悲痛, 竟然主要依靠自己個人的力量, 已經把《全集》草目初步擬出來。……于是一面向內政部報審,一面落實出版單位。
“草目”比“目錄”更準確,因為后來有修改。我們可以據他的這幾句話推斷:如果許廣平是在把草目初步擬出來后馬上送審,那么是在11月下旬;如果稍稍耽擱,那么可能是12月初。
1936年11月說之所以被大多數人支持,是因為它來源的渠道非常權威,來自魯迅的遺孀許廣平和三弟周建人這兩位當年的直接當事人。陳漱渝和張小鼎他們沒有交代他們所持的“1936年11月說”的來源。它最早起源于1937年10月19日《大公報》的《紀念魯迅》一文 。該文是《大公報》為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訪問許廣平、周建人的“本報特寫”。
支持這個說法的還有一條旁證。許壽裳在1937年1月6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說:
三先生來平,得唔見三次,甚慰,并知豫兄譯著登記事,南京方面已經大部分通過,甚望其全數亦通過無留難。此間已托齊先生轉托京友設法,未知現在究竟如何?乞示知。
“三先生”就是周建人,當時就職于上海商務印書館。周建人由上海去北平見到許壽裳之前,就得到了“南京方面已經大部分通過”的消息;這個好消息應該還是許廣平首先得到,然后傳給周建人的;因為出面跟南京方面聯系的不是周建人,而是許廣平。也正因此,許壽裳接著直接問許廣平:“未知現在究竟如何?乞示知。”周建人與許壽裳“唔見三次”得需要三五天吧,那之前他由上海乘坐火車去北京也需要一兩天。我推斷他此次離開上海的時間應該是1936年12月底,即那時他已獲南京方面的消息。而南京方面用以審讀約需一個月,所以說許廣平開始送審的時間是1936年11月,符合推理。
2.1937年2月15日說。這種說法是由祝肖因在對第一種說法提出質疑否定之后提出來的。早在1989年9月12日,他就寫完了《〈魯迅全集〉》送審述略》一文,但直到6年后才在《上海魯迅研究》雜志上發表。祝肖因在文中說:
不知是當年許廣平對記者的介紹語焉不詳,還是記者記述有誤,總之,這個數十年來被公認為的權威性的說法已經受到懷疑。最新披露的資料表明,確切的送審日期應該是1937年2月15日。
他所謂“最新披露的資料”指的是1987年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魯迅之子周海嬰編的《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更具體說是書中1937年2月25日一個署名“何玨”的人給許廣平的信。那信上說:
逸塵先生:很抱歉的,將魯迅先生著作登記事拖延了許久,因為李先生月初出發,鄙人也入院割治痔瘡,轉托人代辦,又因手續不合,為內政部所拒。直待月半鄙人出院,始辦理送部手續并與負責者接洽,但已勞先生盼望半月矣。
“逸塵”是許廣平的別名。“月半”是“2月15日”。祝肖因據此認為,“‘送審’的確切日期是‘月半’即1937年2月15日,從而明白無誤地否定了歷來所傳1936年11月‘送審’的說法”。我以為,何玨說“月半鄙人出院,始辦理送部手續”的真正含義可能是:15日是出院的日子,而辦理送部手續的日子可能會晚一兩天。
這種說法涉及另一個相關的時間問題,即許廣平在1936年11月初步擬出草目之后,為何不顧當時各方翹首以盼的緊急情勢和焦急心理,要拖到1937年2月15日之后才送審?
此間涉及第三個時間點問題。許廣平是何時開始委托“李先生”的?“李先生”指李秉中。許廣平不是自己直接從上海跋涉去南京送審的,而是委托了魯迅的弟子李秉中代送。那么,是不是在初步擬出草目之后就委托了呢?祝肖因的回答是“否”。他推斷說:
許廣平委托李秉中的時間大致在1937年1月底,而不是此前的其他時候。因為信中明確指明“已勞先生盼望半月矣”,此語是與前面“拖延了許久”相照應的拖延了多久呢?“半月”就是準確注腳。反之,如果李秉中不是于1937年1月底受托而是在1936年11月,則使許廣平“盼望”的時間就不止“半月”了。
如果許廣平委托李秉中的時間在1937年1月底,那么我們還是繼續要問:從1936年11月到1937年1月,整整兩個月時間,她為何遲遲不送審?是一時找不到可以委托的人嗎?還是另有原因?這有待于進一步考證才能回答。
那么,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呢?
我無意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兩者都有道理和證據。祝肖因抓住一點關鍵證據而試圖推翻第一種說法,恐怕也難。但如何解決兩者之間的不一致問題呢?筆者想假設性地提出第三條思路,即許廣平他們是把材料分批送審的。
這是有“據”可循的。1937年6月8日,國民黨當局對許廣平他們送審的材料審查結束之后,把有關材料、內政部批文和中宣部審查意見等一并原渠道給了李秉中,李在給許轉寄材料時所附的信中說:“續送譯書三種,尚未批下。聞有問題,不識確否?”許既然可以在大批量送審之后,“續送譯書三種”,為什么不能先送譯書若干呢?請注意,許壽裳信中所說的也是“譯著”。許廣平之所以先送一些譯著去受審,可能是因為她認為,與魯迅那些與當局勢不兩立的匕首性著作相比,譯著是外國人寫的,針對的也不是中國,所以會比較容易通過。許壽裳信中所說的“南京方面已經大部分通過”,指的就是他們所預期的效果。當然,我的這個假設有待于小心求證。
我推斷,《全集》的少量材料送審的時間是11月下旬或12月初;大部分材料的送審時間是1937年2月15日稍后不久。最后又送了一次,總共是分三次送審。
2月25日何玨此信前半封的內容要點是:登記事拖延了許久,原因幾點。一是,2月初,李秉中出京,不能親自辦理,委托給了何玨;二是,何玨剛剛受托還沒去開始幫辦,就突發痔瘡入院割治,于是轉托第三人代辦。第三個原因則是公家的,即“手續不合,為內政部所拒”。但何沒有明說手續到底哪里不合即內政部所拒的具體理由。不過,應該不是非常嚴重的關鍵問題,因為登記只是履行手續而已,無非是交款交材料;這個問題可能是受托人辦事不周所致。此信后半封的內容要點是:2月中旬,何玨出院,“始辦理送部手續并與負責者接洽”,又10天左右,登記手續算是辦妥,然后他給許廣平寫信報告結果。“已勞先生盼望半月矣”,實際上許廣平盼望的時間何止半月?哪怕從1月底許廣平委托李秉中辦理起算,到許廣平收到這封信,也已經快一個月了。
至此,1937年2月下旬,登記手續才算辦完;接下來,許廣平他們就開始等待更加漫長復雜的審批過程。
足足兩個月之后,即4月30日, 內政部領導終于做出了“警字第二九七二號”批示,即關于此案的第一份批文。內容大概是:《兩地書》和《墳》兩種原本注冊過,不用審查;《南腔北調集》《二心集》《毀滅》三種出版當時就被查禁,“未便準予注冊”;其余《吶喊》等書31種要函請中央宣傳部審查。根據這份批文,第一批次五種過內政部這一關時,準予注冊的只有兩種,只占五分之一。如果后面31種過關的也是這個比例,那么,只能準予注冊6種。全部能合法出版的才8種,如何稱得上全集?
許廣平應該是通過南京政府里的人提前知曉了這個批文的內容。在正式拿到批文之前,4月27日晚她就急忙給許壽裳寫信,及時匯報這個糟糕的情形。由此,筆者推斷,她是27日就得知了批文的內容。
1937年4月29日,許壽裳給許廣平回信,說“全集注冊事,既已全部由內政部轉致中央黨部,自當從速接洽。裳擬致函熟人方君,請其竭力設法,邵、荊二君已有回信否?”“中央黨部”這里指的是“中央宣傳部”,“由內政部轉致中央黨部”指的就是批文中所說的其余《吶喊》等書要函請中央宣傳部審查。請注意29日這個日子比批文落款的30日還早一天,許廣平給許壽裳寫信匯報的時間更要早幾天(當時京滬之間所需要的通郵時間);因此,我推斷她從內部渠道提前了解到了批文的內容。
得到這個消息后,二許就甚為擔心、著急。在這種緊要關頭,許壽裳沒有以費辭安慰或鼓勵,而是直接出謀劃策。首先他說要“從速接洽”。接洽誰呢?他想到了三個人。
1.“方君”。這是何許人呢?許壽裳在1937年5月3日致許廣平的信中說:“裳已馳函蔡先生及中央黨部方希孔(治)。”由此可知,此人姓方名治號希孔。1934年年初,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率先在上海將過去的出版后“書刊檢查”制度改為出版前“原稿審查”制度。“圖審會”設立主任委員一人,就是由方治兼任。方在升任副部長之前,按照夏衍《懶尋舊夢錄》中的說法,“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不管誰換當部長,實權都操在方治手里。”更何況,1935年12月,國民黨五大后,中央宣傳委員會又改為中央宣傳部,部長為劉蘆隱,方治升為副部長。1936年2月24日,劉蘆隱因“蔣介石首席智囊”楊永泰案被捕,6月5日被判處十年徒刑。7月,方治代理部長。此后,他以為自己肯定能轉正。但是,1937年7月,蔣介石卻讓浙江老鄉邵力子出任部長,方仍任副部長,不過,他在部內地位有所抬升,相當于次長(常務副部長)。邵力子碰到重大的或棘手的事呢,也盡量找他商量。方希孔作為掌握實權的副部長,很可能分管的就是他之前負責的熟悉的圖書雜志審查業務。許壽裳找的是有可能幫得上大忙的人。
2.邵君。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的專家注解說是邵銘之。此君也是紹興人,也曾留學日本,與許壽裳、魯迅是終生摯友。許壽裳找邵銘之幫忙,是否有可能是因為后者與同為紹興人的邵力子有什么家族關系?待考。
3.荊君。指的是魯迅的另一個庶出弟子荊有麟。此人曾擔任國民黨中心黨部上海宣傳委員會秘書兼聯系總干事。或許因此,許壽裳認為,此人在國民黨中央宣傳系統有些關系,也能幫上忙。
事實上,早在1937年4月29日許壽裳給許廣平寫這封信之前,早在27日許廣平得知批文內容之前,許壽裳自己或讓許廣平已經向邵、荊二人寫信求助,所以他才會在這里問許廣平:“邵、荊二君已有回信否?”
給許廣平寫這封信之后,最晚不超過5月3日,許壽裳就馳函方希孔,“請其竭力設法”。
這是情勢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候,許壽裳精神百倍,火力全開。除了請求以上三人幫忙疏通。他還寫信給陳大齊、沈士遠求助。5月2日,他又與馬幼漁見面,聽聽后者的意見。許壽裳在1937年5月3日致許廣平的信中繼續說:
注冊事,時機不可失。裳已馳函蔡先生及中央黨部方希孔治,請其設法,予以通過。陳大齊、沈士遠二兄處亦同樣函托,并征求其加入為紀念會委員。昨與幼漁兄談及,渠謂大先生與胡適之并無惡感,胡此番表示極愿幫忙,似可請其為委員,未知弟意為何如?希示及,湯爾和為委員已得其允。
我們且來看許壽裳四面求助的效果。
1.方希孔這條線。5月7日,方治給許壽裳寫短信說:
季茀先生大鑒奉讀 手教至慰馳念關于魯迅先生遺著呈送登記事候轉到本部時當遵囑注意以副雅望肅此奉復即頌時祺 弟方治上。
許壽裳4月29日致許廣平信中說“全集注冊事,既已全部由內政部轉致中央黨部”。方信中“候轉到本部時”云云說明:已過了一周,送審件還沒有到中宣部,至少沒有到方希孔這位中宣部副部長的手上。差不多一個月之后,還沒有結果。許廣平非常焦慮。
6月3日,許壽裳又致信許廣平說:
方希孔前月初有回信,茲附上,中宣部審核結果想不久即可發表。閱報蔡先生已返滬,弟可去一訪,并將經過情形簡單報告。適之有回信否?
前月初回信指的就是5月7日方治給許壽裳寫的這封短信。哪怕5月7日方治說他還沒看到送審件,但畢竟過去這么多日子了,許壽裳估摸著事情辦得差不多了,所以他一方面給許廣平安慰打氣,另一方面鑒于好消息還沒有到來,他還巴望著請蔡元培和胡適這兩位大人物幫忙。此時,他聽說蔡回到上海,所以建議許廣平專門登門去拜訪蔡,當面匯報有關情況。
2.荊有麟這條線。5月21日,荊給許廣平寫信說:
周先生著作事,經有麟托王子壯先生、周先生老友沈士遠先生托陳布雷先生分向宣傳部各負責人及邵力子先生處接洽。
可見,荊有麟自己出面委托王子壯幫忙,王1917年入讀北京大學,也算是魯迅的弟子。1936年11月,王調任銓敘部政務次長,其間迭兼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政工考核委員會黨務組副主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銓敘部成立于1930年1月,負責掌管全國文職公務人員和考取人員的登記、銓敘及各機關人事機構之管理事項。因此,王子壯是中央里的實權派人物。
3.沈士遠這條線。沈收到許壽裳的函托后,就去找他的得意門生陳布雷。據《陳布雷回憶錄》載,沈士遠是他極敬仰的老師,師生關系十分親近。17歲的陳布雷常去沈先生的宿舍請求指導。“沈先生常以《復報》《民報》《新世紀》密示同學,故諸同學于國文課藝中,往往倡言‘光復漢物,驅除胡虜’,毫無顧忌。惟有時以某某字樣代之而已。”沈士遠也十分欣賞陳布雷,說陳年紀輕輕,就已接受并信仰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達其革命意志。陳布雷收到恩師的請托后,馬上去找了宣傳部各部門負責人及邵力子。陳布雷與蔣介石交厚,最初還是邵力子牽的線。所以他跟邵力子可以坦率交談。邵力子、方希孔他們本來就同情、敬佩魯迅,支持《魯迅全集》的出版;之前,鑒于魯迅與政府之間的緊張甚至敵對關系,他們可能還有點猶猶豫豫、畏手畏腳;現在,既然“總裁智囊”陳布雷都出面來說項了,那么就相當于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他們何不做這個順水人情呢?
許壽裳為了打贏這場審查仗,猶如一名統帥,獨坐中軍帳,發出一道道金牌,請(不是令)各種人物從不同方向和路線“進攻”中宣部尤其是邵力子部長。而且他把蔡元培這邊作為主力軍。因為他深知,正如沈士遠與陳布雷師生情深,蔡元培也是邵力子的恩師。1901年,上海南洋公學為實現從速培養人才的教育訴求,開設經濟特科班,邵力子是第二批錄取的學生,而出任特班總教習的正是蔡元培。邵力子極為尊重蔡先生,稱蔡是“最有影響的兩位老師之一(另一位指馬相伯)”。蔡元培也很賞識門生邵力子,稱“善為文,努力革命”。論國民黨內部關系,陳布雷位高權重,說話有分量。但從社會聲望和個人關系而言,無人比蔡對邵更有影響力。
1937年5月13日,蔡元培收到許壽裳的求助信。這次蔡不僅沒有推脫,而且當即寫信給邵力子。邵也不敢耽誤,馬上了解了情況并做了當面匯報。5月20日,蔡元培復函許壽裳說:
魯迅先生遺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傳部邵力子部長,力子來談,稱:內政部已轉來呈文,當催部員提前檢查。
請注意“來談”的意思是,邵力子接到蔡先生的函托之后,馬上到蔡府畢恭畢敬地“趨謁”。也因此,許壽裳相信,蔡出面找邵,事情必成。5月21日,許壽裳在給許廣平寫的信的最后,告知許“蔡先生已函托邵力子也”。5月25日,在許壽裳致許廣平的信中,為了讓后者放心,他還引用了蔡元培給他的回信的有關內容。兩天之后,5月27日,他給蔡元培再寫信,充滿感激和感情地說:
魯迅遺著事,承先生親與力子部長一談,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誤解,使一代文豪,榮于身后,亦全國文化之幸也。
許廣平收到許壽裳5月21日來信的時間是23日。一天前,即22日,她就收到了荊有麟21日的來信,荊說:
現已得到結果,邵力子部長與方希孔副部長已下手諭,關于政治小評,如有與三民主義不合之處,稍為刪削外,其余準出版全集,惟印刷時時,須絕對遵照修改之處印刷,一俟印刷稿送審與刪改無訛,即通令解禁。邵力子部長并諭: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云云。
這兩封信仿佛是給許廣平吃了定心丸,而且是雙保險。這是陳布雷和蔡元培的雙保險,也是邵力子與方希孔的雙保險。因此,許廣平很激動,很高興。5月23日當天,她讀完許壽裳的來函后,馬上回信,詳細報告這個來自國民黨中央的好消息。除了全文抄錄荊的信的內容之外,她又說:“關于迅師遺著,因先生等各方努力,似有很好效果(以前邵先生對李秉中言,似不大能寬假)。”
然而,荊有麟21日的來信中所說的好消息是許廣平盼望了許久的,所以她喜歡聽,而且不假思索就信了。筆者卻生疑竇。邵力子與方希孔已下手諭準許出版全集,恐怕只是一個面上的初步表態。“邵力子部長并諭:對此一代文豪,決不能有絲毫之摧殘,云云。”恐怕是一句漂亮話,講給來說情的幾個大人物和魯迅的千萬粉絲以及后人聽的。這些手諭下發時,中宣部根本還沒有開始檢查許廣平送審的材料呢。“手諭”只是“紙條”——內部指示,并不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文(即批文)。
蔡元培給許壽裳的那封回信中接下來引用邵力子的話說:
當催促部員提前檢查,現尚未斷言是否全部都無問題,萬一有少數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幾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蔡轉述邵的真心話,魯迅的作品是否全部都能通過檢查,準予出版,連邵本人都說不定。他只建議說:如果真的有幾部不能通過,那么要忍痛割愛,丟車保帥,委曲求全,犧牲局部以保全集。這跟許多人包括許廣平的想法是一致的。許壽裳一開始的理想是盡可能全部收入魯迅的作品,但事已至此,他知道固執堅持沒有多大意義,反而連累全集盡早出版,所以他在這信的后面就不再堅持前說,而是說邵的說法“亦持之有故,止可俟其檢查后再說”。可見,邵力子作為部長,并沒有(或許身不由己)在部里搞一言堂,而是要等部下對許廣平報送的材料檢查完畢后,再定哪些可以通過,哪些不能通過。
總之,在許壽裳他們竭盡全力動用最強社會關系找到邵等中宣部要員疏通之后,中宣部的態度由“不大能寬假”轉而同意出版不全之全集,已經是相當不容易的巨大轉變了。
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給許廣平寄寫信說:
月余未緘候,無任抱歉!因離京兩次,行色匆匆,心緒不寧,未能執筆。內子又入院生產,一切煩瑣之事,令人頭痛。昨始自廬山返京,得內政部批及執照九紙,已囑何君先將執照寄呈,想已收到。
內政部批文的落款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八日”,也就是說,1937年6月8日,批文終于下來了,離許廣平開始報送約半年。6月10日批文就被送到了李秉中處,而他6月21日才寄給許廣平,耽擱了整整10天;原因是10日他在廬山出差,返回首都南京時適值他妻子在醫院生孩子,他大概是直奔醫院,沒有去辦公室,所以未見執照和批文。他從廬山跑回南京,大概就是因為妻子生孩子的家里大事;廬山的事還沒有辦完,所以孩子出世之后呢,他又去廬山。6月20日,廬山事了,他又回到南京,返回工作崗位,才拿到內政部批文及執照。大概當場他就請同事何玨先將執照寄給許廣平。為何不讓何一起寄批文呢?可能是因為批文中有相當大的問題,可能會讓許廣平看了之后悲憤失望;所以,李秉中覺得自己應該給許廣平寫信說明或安慰一下。況且,他還有別的事要跟許廣平說。
李秉中點到的關于政審的實質性的問題有兩個:一,《不三不四集》可暫時抽出,將來有機會時再加入全集;二,續送譯書三種,尚未批下。如果只有這兩個小問題的話,鑒于魯迅生前就有不少書被禁,對此許廣平不至于悲憤;但實際上,批文中或者說審查的意見多得多,多得讓她受不了。
在總共送審的36種魯迅著作中,國民黨當局的審查意見分為三類。
1.全然不予放行的有4種:《南腔北調集》《二心集》《毀滅》和《不三不四集》。占比為九分之一;
2.全然準予發行的有11種:《兩地書》《墳》《魯迅自選集》《故事新編》《小說舊聞鈔》《十月》《俄羅斯的童話》《桃色的云》《小約翰》《死魂靈》《表》。其中,前兩種是內政部初審時就通過的,因為“曾經呈準注冊”,照例放行。再,其中《十月》《俄羅斯的童話》《桃色的云》《小約翰》《死魂靈》《表》等六種為譯著,超過一半;這說明譯著通過的比例確實相當高。全然準予發行的11種占所有送審總數的比例僅為十分之三。
3.要求刪改后才予以放行的多達21種,占比將近六成。如果把全然不予放行和要求刪改后才予以放行的合在一起,則比例高達將近七成。這離眾人所期盼的全集相差得太遠了。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