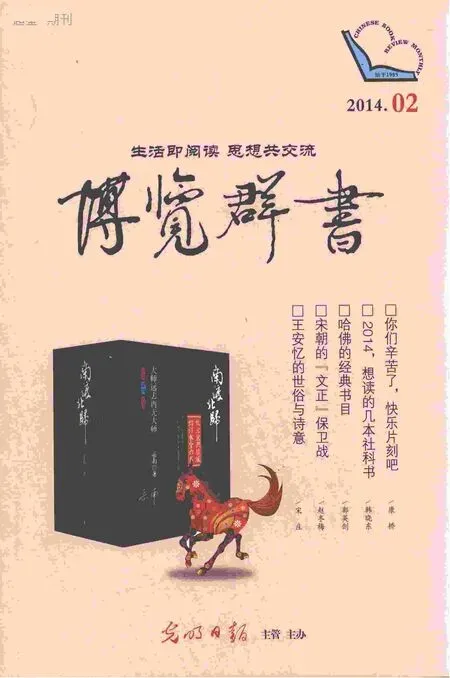對動物傲慢意味著人類的災難
林科吉
美國學者博里亞·薩克斯的《神話動物園》一書,為我們介紹的動物將近百種,包括空中飛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解,細分為18個類別,匯集了神話、傳說與文學中的動物故事,因此,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精彩紛呈、饒有趣味的堪稱“文化動物學”或“象征動物學”的專著。
人類生存于自然環境中,組成這個環境的除了東、西文化公認的宇宙基本元素如地水風火、或金木水火土之外,恐怕跟人類關系最為密切的當屬動、植物界了,它們是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基本生存之所恃、所需。相比而言,動物更是跟人類相伴相隨、相助相依,它們充當過人類的祖先、兄弟,也是人類的親密伙伴與忠實助手。初民社會崇拜的圖騰大多是動物形象,特別是那些龐然大物,總是令人敬畏,中國古典文獻記載有“鑄鼎象物”之說,意即在青銅大鼎上鑄塑神圣之物的圖像,掌握了神物的圖像,就控制了此類物種的能量,“象”與“物”的“原型”即神圣之象和牛,該著中提到的熊、獅、豬、鹿、野牛、老虎、豹子、大象、河馬等,也都因為塊頭巨大,擁有令人驚異的力量和速度,與之相比,人類往往感到自慚形穢。在原始分類觀念中,人們常常將這些動物與人類劃為同一個種類,而且動物是長兄,人類則甘當小弟。中國古人崇拜的“四靈”,代表的是各自類別中的最高典范和“老大”,人類中的圣人與之同級,具有同等的象征價值。但是,并不是說那些小小的動物就會被人們輕視和忽略,其實它們自有天賦異稟和神奇之處,都擁有令人羨慕的神秘力量,如公雞召喚太陽,燕子帶來春天,青蛙是雨水的使者,蝴蝶則是再生的象征,等等。這些大大小小的動物共同形成了人類的世界,雖然達爾文早就告訴我們,猿猴才是人類的親戚,但是在人類的感覺里,遠親不如近鄰,人們對身邊的動物感到親切和親熱,比如我們視之為家庭組成部分的“六畜”,以及房舍周圍的蜘蛛、蜻蜓、蛤蟆和蟋蟀等,已經完全融入人們的飲食起居和情感思維,它們與人類一起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共棲環境”。
地球的年齡長達40多億年,地球上生命存在有35億年以上,人類的出現也有200萬年之久,在這樣漫長浩渺的宇宙時間里,各種生物最終使地球變成一個充滿生機的世界。仰觀俯察,宇宙之大,品類之盛,經過自然大化繁衍出了萬千生命形式和樣態,人類作為其中的一個種類,與之和諧相處、共存共榮。正如每一種動物都有各自喜好的食物,都有其搭窩筑巢的特殊材料,及固定的疆界,有它們自身的生命成長的周期、節律等,其天性模式是經過精確的調節而獲得適應的。人類同樣依其性命,與環境的時空協調、合拍,并與他周圍的生命建立起廣泛的聯系,這樣方可盡力擴展其生命的幅度。我們必須在各種生命的聯系中,才能參悟人類自身生命的本質;只有當我們深刻體察到自身的動物本性,生活才會更加踏實。
宇宙大化至為神秘莫測,眾人只知其然,但圣人能知其所以然。《文心雕龍》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虎豹,云霞草木,皆天地之文,圣人靜觀默察,正是通過為諸物立象,才“有以見天下之賾”,最終領悟到自然萬物的幽深微妙。圣人的工作就是在自然與文化之間進行協調,將自然事物予以人文化、象征化,而又不傷害其天性。人類學家、神話學家一般都會承認,人類是處于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動物,像榮格那樣的心理學家也發現,理性只有跟本能相協調,一個人才可擁有完整的自性。有理由相信,人類最早的智慧并非通過近代哲學家所謂的“我思”而獲得的,而是在對身邊之物的觀照和模仿中逐漸有所領悟。因此,可以說動物發揮了最早的人類“鏡像”的功能,我們在青蛙身上看到了多產和豐沛,在野豬身上見到了勇敢和剛烈,知了和蟋蟀的彈奏使整個秋季滲透了詩歌的韻味,鷹類意味著溝通天地、陰陽和生死……這些都是人類想要擁有而又缺乏的能力。馬文·哈里斯曾提到有些動物比如豬、牛等,對于人類來說不但“好吃”,而且“好想”,它們的肌肉可供人類的肉食所需,皮毛供我們御寒之用。更為重要的是,人類通過它們建構了自身的文化,它們不但滿足了人類的生物性需求,也通過象征意象參與到人類的精神生活中。如果我們要問:一種文化為什么在不可勝計的事物中,偏偏揀選出某些特別的種類作為表征符號?細讀《神話動物園》也許能找到理解的線索。
人、動物與其環境,共享同一個生命網絡,共處一個生物系統,現代人類非常傲慢地將自己置于生物鏈的頂端,這其實是一種災難性的觀點,人類擁有的能力確實變得越來越強大,但也變得越來越恐怖,如果我們將其他一切生物都劃分為食物與非食物、可吃與不可吃,這樣極端的二元對立,許多動物就會因為對人類“無用”而被置于極為危險的境地。一種動物、一個物種就代表大自然的一扇生命之門,“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化生,生生不息,當人類將一種動物趕盡殺絕,也就意味著這個地球上有一扇生命之門對我們關閉了,當地球上只剩下人類時,也就代表所有的生命之門徹底關閉,這將是一幅恐怖的景象。
閱讀這本著作,不禁令人想起弗雷澤及其《金枝》,因為材料收集范圍從西到東、自古及今,涵蓋了神話、傳說、童話、小說、詩歌、戲劇,乃至科學調查報告、宣傳畫、早期印刷品、卡通、影視作品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這個工作看似簡單,其實“研究難度超乎想象”。文學人類學研究也正是提倡用這種方法研究神話:不但要求全球視野,還要有廣泛的收集、海量的閱讀與深刻的沉思。最后,除了感謝作者帶給我們如此豐富和有趣的動物象征知識外,也還有略感遺憾的地方,作者雖然偶爾也有涉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動物形象與故事,畢竟只是蜻蜓點水,比如熊、豬、燕子等這些動物意象,在中國傳統中應該潛存著更加精彩的、更為深邃的文化信息。相信《神話動物園》這本專著作為開端,可以啟發中國文學人類學者在此主題上有更深的發掘。
(作者系文學博士,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