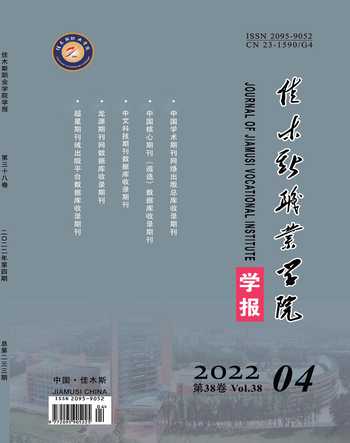格日勒其木格·黑鶴鄉土作品的流浪敘事
劉羿含
摘? 要:作為當代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以鮮明的草原文化立場描寫內蒙古草原與黑龍江興安嶺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遷,通過兒童、動物等敘事視角進行文化闡釋與民族歷史的書寫。作者創作兒童文學、動物文學和鄉土文學等題材時以流浪者的形象和符號對作品整體加以建構。流浪敘事既有對人性美的精神期待,也有對草原游牧游獵文化的追問與思考,以及對自然、城市和草原等空間維度不斷交互的探尋。流浪敘事在鄉土題材作品的運用表現出黑鶴與漢族作家不同的民族性格與生命體驗,具有鮮明的審美意蘊和生態整體主義的思想指向。
關鍵詞: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流浪敘事;草原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2)04-00-03
“流浪”作為一種人類普遍的生存方式,是東西方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之一,也是中國現當代鄉土題材作品的主要敘事策略。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成長過程始終停留在游牧民族和游獵民族的草原文化場域。在他的作品中,敘事主體以流浪的行動過程完成對草原民族生活經驗與民族文化心理的詩性書寫與審美表達。與其他作家創作的流浪文學不同,黑鶴進行流浪敘事的敘事主體不僅限于人類,具有自我意識和自然屬性的動物形象也被納入其流浪寫作的形象與符號系統中。從而與他的兒童文學與動物文學相聯系,呈現出獨特的文學想象方式。
一、敘事主體:流浪者的形象類型
“流浪的基本屬性就是物質與精神生存境遇中那種失根與無歸屬感,以及與此相應的流動不定的生存狀態[1]。”流浪者被迫或主動地進行物理位置的移動與生理心理流浪,并在這一過程中完成對生命體驗的書寫、社會問題的探討與時代精神的表達。在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創作的鄉土題材作品中,流浪者形象是草原民族文化敘事的敘事主體之一。以各類人物形象、動物形象為基礎,已成為黑鶴作品譜系中完整的符號系統。其中人類流浪者的形象繼承了流浪文學以個體視角觀察社會整體動態面貌的敘事傳統。不同的敘事主體對流浪敘事的心理描寫和認知方式具有極大的影響。從敘事主體的原生空間來看,黑鶴筆下的流浪者形象可以分為草原流浪者與城市流浪者兩大主體類型。不同的敘事視角則會在兩個主要類型內部形成異質性。
(一)草原流浪者
草原流浪者即來自草原、山林等自然屬性與他者屬性較強地域的流浪者。流浪是游牧游獵民族適應草原環境變化的能動性表現,也是群體行為的顯著特征。因此,黑鶴在作品中塑造的一部分草原流浪者更加傾向于傳統意義上的流浪,即為解決現實中的生存問題的身體意義上的流浪。這類流浪者可以被概括為“生存流浪者”,通常以家庭為單位出現,流浪的空間也僅限于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內部。黑鶴的作品雖然多以動物與兒童為主要人物,但其行動軌跡與生存流浪者的行動軌跡具有重合的部分,換言之,生存流浪者所在的場域是黑鶴流浪敘事的背景與空間,動物與兒童基本的生存需要和接受的人文關懷都依附于生存流浪者。因此對生存流浪者流浪具體過程的描寫更多承載了關于民族歷史與民族記憶敘事的功能,借以展現游牧民族特有的旺盛生命力。黑鶴的作品大多從生存流浪者的流浪過程中展開,并借由生存流浪者克服惡劣環境的日常生活細節交代作品的主要角色和主要情節。
另一部分草原流浪者則側重精神層面的自我放逐與出走。通過離開既定的生活環境進行自我能力與精神的審視,這類流浪者可以概括為“認知流浪者”。當認知流浪者成為敘事主體時,黑鶴注重進行動態的敘事,即流浪主體不斷尋找、發現自我并最終完成身份確證與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認知流浪者是《黑焰》中藏獒格桑認定的主人韓瑪和福利院的盲童。韓瑪作為漢文化圈的人物,游牧民族與游牧文化對他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作品中韓瑪參與到阻止偷獵的志愿活動中,從更隱秘、更深刻的角度感受到高原獨有的生命力與自然不可抗的破壞性。而后韓瑪進入草原腹地并與草原居民共同生活。生存流浪者的流浪生活以及遭遇特大雪災的經歷使得韓瑪深刻認識到格桑體內牧羊犬的本性,進而完成了作為一名志愿者,更是作為一個牧民在草原場域的身份確證。韓瑪的認知流浪者特征主要體現在成為牧民的身份認同,是一種隱性層面的精神流浪。而生活在福利院的盲童則是顯性層面的認知流浪。孤兒院的孩子因為視力受損,認識世界與自我都有一定的缺陷。在精神與認知上一直處于流浪狀態。韓瑪暫時“拋棄”格桑的原因是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幫助殘障兒童從生理上恢復認知功能。后續情節里韓瑪將格桑帶回福利院,盲童的認知世界添加了新因素。“一個又一個孩子試著讓格桑舔舐他們的小手,每一次接觸都會逗引著這些孩子發出控制不住的真正屬于他們的笑聲。”[2]笑聲隱喻著盲童開始與現實世界產生實在的關聯。格桑代表旺盛的生命力與陌生化的體驗,同時也是盲童精神流浪的一個標志性節點。通過與格桑的互動,盲童開始認識與自身形態不同的生命并逐漸開始產生對世界的自覺認知。盲童精神流浪的重點不在于“流浪”狀態本身,而是格桑作為其流浪的節點幫助盲童從新的角度進行認知活動。認知流浪者的流浪軌跡與生存流浪者相比范圍由草原內部擴展至農耕地區和現代都市,以一種外來者的邊緣化身份進行關于草原文化的審視與審美性觀察。這一類流浪者形象更多象征著作者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諸多現象和其生態視閾下對草原現狀的思考。
(二)認知流浪者
草原流浪者的流浪經歷與身份歸屬都是來自草原空間,其流浪的隱喻意義也大多與草原民族幾千年的厚重文化相關。但與草原這種原生態且具有獨特審美價值的空間相對應的是現代都市空間。在這種空間中包含著作品的一部分敘事主體。黑鶴的作品中常見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即是城市流浪者,來自城市且在草原與山林中流浪的多是以寫作和攝影采風等為創作目的。“我”在黑鶴的作品中代表了現代文明進入原始生態區域后諸多可能的見證者與記錄者。不為人知的動物傳奇與逐漸消逝的文化遺產通過“我”的講述得以保留流傳。這類流浪敘事的情節發展大多通過“我”與牧民、老人和兒童的交流中展開敘述,增強了作品的事實真實與心理真實。同時,每部作品的第一人稱敘述者都具有一個共性特征,即敘述者的童年與青少年都在草原中度過。在生活習慣與個體經驗方面與生存流浪者存在共同點,包含了作者鮮明的個人經歷與情感,對草原民族與游獵民族的生存經驗、審美習慣和民族性格有深刻的體悟。以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為代表的城市流浪者的流浪經歷更傾向于一種回歸,即對游牧游獵生活習慣與歷史傳統回溯和對草原民族生存現狀的摹寫。以城市流浪者為敘述主體的作品中,“我”完成了主要情節的敘述后回歸到現實生活。一切具有草原特質的事物都正在消逝,原生自然環境中動物和人類等一切生靈所象征的野性的荒野逐漸成為被埋沒的棲居地。城市流浪者在追憶的同時也包含了對現代性所帶來的同質化浪潮的質疑與審視。
二、敘事意象:流浪者的意象符號
(一)狗與狼:草原精神的流浪符號
在黑鶴的作品中,狗與狼是蒙古民族與草原文化象征,二者以敵對關系表現惡劣的生存環境與嚴苛的生態循環。哈拉、諾亥和巴努蓋等牧羊犬的能力好壞的標準即能否對抗狼群等猛獸帶來的危險。狼與狗的廝殺是黑鶴的小說中常見的草原情景。狼群象征著草原生態環境的原生力量,即自然的力量與生態整體主義思想。狗則是草原流浪者在草原山林中自在生活的符號之一,此外,在狼與狗的斗爭過程中也會以馬、羊等人類游牧的牲畜群作為自然真實美感的象征符號。狼、狗、馬、羊共同構成了自然生態環境的符號系統。其中狗作為多義符號,在表現人與草原的共存狀態同時,作者將傳奇色彩的經歷加諸于符號中以承擔流浪主題的敘事功能。
黑鶴小說中的狗流浪經歷與城市流浪者類似,自出生起在原始的草原環境中接受草原環境內的生存法則,激發幾千年間積累出的放牧、廝殺、守衛等物種本能,完成游牧游獵本能的主體塑造。而后牧民會出于各種原因將牧羊犬出售或贈送。具有草原生存經驗的狗在新的空間場域中轉化成一個極端陌生化的符號,由草原遷移到城市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人類獵奇和戲仿的對象,作品中經常出現牧羊犬不適應城市空間的狀態:牧羊犬會被拴在餐館門口等封閉性質的小空間內,并成為過往路人圍觀試探的“景點”。它們得到充足食物的同時被鐵鏈和木樁束縛,被贊美的同時被當作測試同類戰斗力的參照物。牧羊犬能夠成為作者流浪敘事的主體在于牧羊犬逐漸具備兩種相互對立的生命體驗。與其他創作動物題材小說的作家不同,黑鶴塑造動物意象的重點放在了動物意象的自然屬性,即擬實性而非類人性。將動物流浪的過程作為敘事線索,以動物的思維方式與生命經驗觀察不斷變化的人類世界并在城市經歷苦難的流浪。
(二)馴鹿與熊:鄂溫克文化的流浪符號
黑鶴是蒙古族作家,但創作的內容不僅限于蒙古族的草原生活經驗。同為少數民族,黑鶴對鄂溫克族與鄂倫春族的生活習慣與文化傳統也有相當程度的關注。鄂溫克與鄂倫春民族的生活空間更為隱秘,民族文化體系的保存更為完整。如果狗與狼是作者自身生命體驗的一部分,那么熊與鹿則是作者從以“共情的外族人”視角出發觀察描寫馴鹿營地生活的隱喻符號。熊作為鄂溫克民族的圖騰之一,被鄂溫克居民賦予了強烈的神圣性與人性思想。它的每一次出場都是鄂溫克民族古老傳統與原始信仰的具象化表達。鄂溫克族與鄂倫春族與熊形成一種動態的微妙平衡,當雙方不存在關乎生存必須的利益沖突時,人與熊是可以共存甚至共處的。黑鶴對熊的生活狀態進行了戲劇性但不失真實性的描寫,其中熊在山林中的流浪象征著游獵文化的生命力。在《黑狗哈拉諾亥》中,鄂溫克老人格力什克與饑餓的熊展開生死搏斗,用先民獨有的長矛與熊同歸于盡。年輕人使用古老的民族喪葬儀式安葬老人與熊,認為格力什克是部族最后的英雄,死后將前往“美麗的世界”。作者在描寫格力什克與熊的死亡時加入了黑風暴與落雪等反季節景物描寫。正如作品最后所言“后來,鄂溫克人不再進入那片廣袤的林地[3]。”銘記民族千百年記憶的老人之間消逝,同樣意味著鄂溫克和鄂倫春民族文化的流浪與失語。格力什克的母犬死后,母犬生育的哈拉在草原營地縱情嚎叫,但被牧民從山林強制帶到草原,后途經貝加爾湖流浪幾百公里回到草原的哈拉已經失去了山林帶給它的氣息。動物之間的斷代隱喻著鄂溫克和鄂倫春民族的古老文化的動蕩與割裂。
熊是鄂溫克部族的圖騰,具有原始信仰的超驗性特征。馴鹿是游獵營地生存發展的基礎與保障,其意義不亞于牛羊馬之于草原民族。馴鹿的特殊性在于不與營地建立完全的依附關系并且保留了一定的野性。作者通過非話語方式描寫鄂溫克與鄂倫春民族樸素的生態觀念,馴鹿在山林流浪的終點是回到營地補充鹽分與水分。因此,馴鹿符號在黑鶴的意象符號系統中更多代表著原駐民對故土的眷戀和對自然的敬仰。同時,黑鶴筆下經常出現馴鹿孤兒形象。馴鹿孤兒受各種因素干擾被母鹿拋棄。成為徹底的流浪者之前,原駐民會為馴鹿唱勸奶歌以喚醒母鹿的母性,為馴鹿孤兒爭取結束流浪和死亡的機會。作者創造馴鹿這一符號不僅在于表現游獵民族的民族性格與文化底蘊,在流浪主題敘事下,馴鹿也象征了作者的家園情結以及對母愛的歌頌。
三、敘事空間:中間文化帶
草原文學的主要特點表現在通達開放的文學態度與粗獷剛勁的寫作風格,即開放型文化的文化書寫方向,農耕文明、城市文明和游牧文明同時共存于草原空間,這種創作特征為流浪敘事提供了異質的空間敘事基礎。黑鶴的作品中流浪主題下的人物形象與符號系統進行異質的空間敘事并綜合了自我與他者的雙重言說。在城市空間中進行少數民族身份的流浪者敘事是黑鶴流浪主題空間敘事的常見敘事模式。草原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并非在各個時期處于同一發展階段,存在少數民族群體進行跨時代的社會變革情況。因此時間維度上的復合性決定了城市文明等現代性對草原文化的干預,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流浪者的個體經驗以及思維定式。黑鶴筆下的流浪者大多實現了回歸,建立起“離去—回歸”的敘事模式。作品中也有徹底離開原生地的流浪形象,《黑狗哈拉諾亥》中的哈拉是代表野性回歸并得以延續的符號,而同胞兄弟諾亥則是流浪至死的符號。黑鶴在塑造諾亥形象的過程中曾坦言:“我不知道用暴殄天物這個詞語是否有些過了。但在草原上,即使是最偏僻的牧場,如此體形的牧羊犬也是鳳毛麟角,沒有想到就這樣進了湯鍋。這樣一頭不可多得的牧羊犬,當年僅僅以六百元的價格賣給了那個殺狗的人[3]。”諾亥的流浪與死亡一定程度上象征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悖論。民族文化在城市空間中極易受到同質化的壓抑,甚至成為潛在的文化體系。除了異質文化在現代城市空間的“流浪”,黑鶴的作品中另一種常見的敘事場景是代表現代文明的流浪者進入草原或山林空間中。例如,偷獵者在馴鹿營地附近種植的罌粟,馴鹿“牛仔褲”被送往鄂溫克營地附近的旅游景點充當拍照的工具。但兩種文明在他者空間的流浪都引向一個結果,現代文明的發展必然會沖擊民族文化發展的既定方向。黑鶴善于使用死亡來表現自己對草原文化發展前景的思考,如果流浪者沒有回到象征原始的民族文化的草原空間中,就會進入“流浪—離去—消逝”的敘事模式。一個部族甚至一種文化的群體流浪放置在多元異質的空間中,必然會使文化之間的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文本內部結構和鄉土文學題材下的復調性敘事。
四、結語
流浪書寫在當代文學的場域中仍然是一個具有生命力和關注度的創作維度,包含著回溯人類傳統和觀察生存現狀的現實主義觀照。在流浪敘事中,流浪者的困境也是時代與群體的困境。格日勒其木格·黑鶴塑造的流浪者形象不僅是當下時代語境下的孤立符號,也是原始的生命活力與生命境遇的生動呈現。鄉土文學敘事方式的建構與重構,關乎民族文化與民間傳統由自發的群體性行動成為自為自覺的審美創造,同時也是文學參與到族群與歷史實踐的方法,并實現對原有話語范式的創新突破。
參考文獻:
[1]陳召榮.流浪母題與西方文學經典闡釋[M].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6.
[2] 格日勒其木格·黑鶴.黑焰[M].南寧:接力出版社,2006.
[3]格日勒其木格·黑鶴.黑狗哈拉諾亥[M].南寧:接力出版
社,2011.
(責任編輯:張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