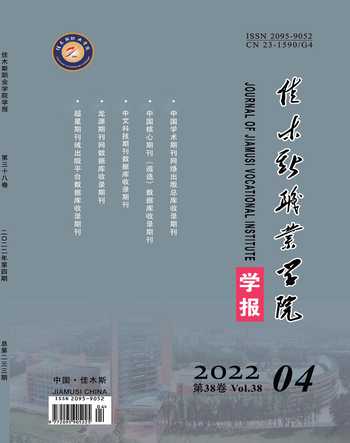踐習與能力
張滇波
摘? 要:博雅教育在中國經過近20年的實踐在取得較大成績同時,也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博雅教育的相關科目看作是知識傳授而不是能力培養。博雅教育以如何做人為首要目的,然而道德教育不僅是學習知識合道理,還必須使學到的知識和道理內化于心,就要通過不斷踐習來培正心性的內化過程,以習慣成自然,使人們在生活的言行中遵守道德倫理規范成為自覺。但是在當今的博雅相關課程的教學實踐中,大多是課堂宣講加學生互動,而沒有任何相關的踐習或者模擬訓練,這就是把道德倫理科目當作是知識而不是能力的表現。先秦儒家提出“學而時習之”的思想,與古希臘哲學家提出的身心訓練,在德育上具有很高的合理性,梳理他們的思想將給現代博雅教育提供很好的啟示。
關鍵詞:能力導向;博雅教育;道德能力;德行踐習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2)04-0-03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現代興起的教育理念,有時與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不加區分地使用。美國學院與大學協會(AAC&U)對它的定義是:“博雅教育是增強個人能力并使之準備好處理復雜性、多元性與變易性的一種大學學習方式。這種方式既強調較寬領域(如科學、文化與社會)的廣博知識,也強調在感興趣的特定領域的深入成就。博雅教育能幫助學生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強化通用于(span)所有專業領域學習的智力與實踐技能,諸如交往、分析以及解決問題的技巧等,發展在現實環境中應用知識與技能的演證能力(demonstrated ability)。”從這個定義,可以分析出以下兩點:首先,博雅教育的根本教育目的在于增強學生準備應對復雜、多元、變易的現實局面的能力,也就是說,博雅教育培養的真正核心在于學生的能力導向,而非知識導向,雖然廣博的知識是鍛煉能力的必要條件;其次,博雅教育所要培養的不是專項能力,而是在所有學科與人生階段都必不可少的通用能力。
但是,就目前國內的博雅教育實踐而言,普遍存在課程設置以知識導向為主,而能力導向訓練不足的問題。對此,如果我們回顧中西方古典時期的博雅教育史,或可以從起源處理解博雅教育的本質目的,為我們反思現代博雅教育的不足提供啟示。
一、西方古典博雅教育思想的內涵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直接來源西方中世紀的“自由技藝”(artes liberles),內容包括語言三藝(the trivium)的語法、修辭、邏輯或辯證法與數學四藝(the quadrivium)的幾何、算術、音樂、天文七種技藝,故亦稱“自由七藝”。雖然“自由七藝”作為教育的系統內容是由公元五六世紀的拉丁百科全書學家編纂而成,但就其每項內容與形式特征而言,則都來自古希臘以來的古典傳統[1]。哲學的起源開啟了古希臘人的理性精神,使他們試圖要找出宇宙的本原,以建立統一次序。其中畢達哥拉斯派把本原歸結為數,他們不但研究算術與幾何,而且也用數來建立音樂與天文的原理。所以,在畢達哥拉斯學派看來,音樂不屬于今日所謂的藝術,而是科學,故而它與算術、幾何、天文學一道被后人稱之為數學或科學四藝。古希臘進入民主政體后,使得演說與辯論成為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普遍方式,智者學派應運而興,向公民提供修辭、語法、辯論術的收費教育與培訓。可見,“自由七藝”的內容在古希臘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在中世紀的百科全書學家之前,各個學校的側重不同,如柏拉圖的學園強調科學四藝,而智者學派更重視語言三藝,而沒有將七藝看成一個系統穩定的教學內容。
自由教育的含義:首先,最終目的是自由;其次,自由需要能力;最后,自由能力的實現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技能有高低不同的階梯。
尤可注意的是,拉丁語artem(藝),是指經由學習、訓練或實踐而獲得的技能或技藝,今日如繪畫、舞蹈、聲樂等我們所謂藝術(art),同樣也是須經學習、訓練才能獲得的技能;這意味著“七藝”教育不僅是知識教育,更是能力教育,以今日而言就是培養人最基本的語言與邏輯能力。因此,自由七藝的教育目的就是培養人們可以超越自己達到自由的最基本能力。人們在奠定這些最基本能力之后,就為日后突破自身限制,進行更高能力的學習與訓練提供了必要條件。可見,美國大學協會對博雅教育的定義是在西方博雅教育傳統上發展而來。
古希臘的教育就其總體目的而言,是要培養“集善與美于一身的人”。各個學派雖然具體的教育目標各異,但都只是各自賦予了善與美的不同含義而已。具體而言,“善”是指人的心靈能力,而“美”則是身體能力,故古希臘“人文主義之父”伊索克拉底認為需要哲學與體育這兩類技藝來分別訓練心靈與身體,以使身心和諧而成為健全的人。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教育就不能停留在知識,而需要實訓。他說:“當學生們熟悉這些課程并能融會貫通時,老師們便讓他們置于實際生活中,讓他們習慣于努力工作,這需要學生將學到的特定事物密切聯系實際,從而更扎實地理解理論,并將理論更為貼切地運用到所需的場合。這里強調‘理論’(theories),是因為沒有任何知識體系能取代這些實際運用[2]。”
柏拉圖為古希臘教育提供了一種基于人性的系統理論基礎。他在《理想國》中將人的靈魂由低到高分為欲望、激情與理性三個部分,若人被后兩者主宰,則言行會自相矛盾突,不能自制。而自制正是理性的特征,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讓人的理性、激情、欲望達到和諧,這樣人才能才言行自持、條理,人才能表現為“一”個人。柏拉圖認為,諸神給了人類兩種技藝:音樂和體育,通過它們來處理智慧和激情的問題,也就是照顧好靈魂和身體。有了音樂和體育,靈魂和身體就能張弛有度,彼此和諧。那種能把音樂訓練和體育鍛煉最佳組合起來,以最佳比例匹配于靈魂的人,我們才稱其為最完美、最和諧的音樂受訓人[3]。一個人如果經過音樂與體育的良好訓練,則可以達到較高的德行成就,只有知道了節制、勇敢、慷慨、高尚等美德的不同形式,以及它們的屬性、對立面,不管它們出現在哪里,都能辨別它們本身及其映像,且不輕視它們,不管出現在大事物中還是小事物中,均承認它們屬于同一技藝同一學科,我們才能算作進行了良好的音樂訓練[3]。應當注意的是,音樂之所能夠承擔起品德與倫理的訓練,在它本身是以數理為基礎,其中體現較強的理性。當然,柏拉圖所劃分的初等、中等、高等三級教育的科目遠不止這些,如還包括算術、幾何、天文學、辯證法等,其中理性智慧的最高訓練是辯證法或哲學,前面的一切科目訓練都是為了為辯證法做準備,能最終完成辯證法訓練的才能稱作哲學家。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柏拉圖強調教育的每一步都必須和實際鍛煉結合起來以獲得實際的經驗能力[4]。
二、儒家博雅教育思想的內涵
古人認為:大通曰博,中正曰雅。但“博雅”一詞不見于先秦,而范曄編撰的《后漢書·杜林傳》有“博雅多通”之語,故可能在魏晉時方始出現。博雅教育固然是舶來詞,卻并不妨礙中國古代有博雅教育思想的實質,而儒家尤其豐富。
孔子教育培養的理想目標是成人,即今之所謂全面發展的人,而這正是博雅教育意欲達到的教育目的之一。他認為:“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君子上達”(《論語·憲問》),即君子不應象器具那樣只有片面的功用,而應不斷向上自我超越而達到宏大與完善。孔子認為:“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即同時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寡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多才多藝,再加上禮樂的修飾,就是成人。孔子認為:“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人的全面博大,就是在效法天道。孔子本人就是一個博學多能,全面發展的人。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詩》《書》《禮》《樂》等經典,以及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其中,“六藝”本義就是指六種才能或技藝,乃是古代貫穿小學與大學的課程,而《詩》《書》《禮》《樂》等經典,則是大學的課程。而大學的教育目的在于“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本質上,對于經典的學習,也不能停留于知識層面,更在于要形成技能,這樣才能真正學以致用,如孔子曾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意思是:背誦了《詩》三百篇,授予他政務,不能通達[5];讓他出使四方,也不能獨立,背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為《詩》涉及廣泛,其雅、頌部分尤其關乎政治、祭祀等內容;同時,《詩》皆有曲,亦屬“樂”,要與禮儀相配,故《詩》三百可作政治教材之用。另外,諸侯卿大夫相交,既唱和《詩》以為娛樂,又寄托《詩》以表達婉轉之意,可知,熟誦《詩》三百乃是當時是外交人員必備的技能。而能力的提高要靠足夠的踐習,所以孔子十分強調踐習的重要性,故他提出要“學而時習之”,他的弟子曾參每日都有是否“傳而不習”的反省。這里的“習”主要是技能意義上練習、實習、修習或踐習,而不只是知識意義上的復習。孔門弟子一直傳承這種“學而時習之”的學習方法,直到西漢司馬遷還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到:“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即司馬遷游歷魯國時,還看到當地的儒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孔子的故居修習禮儀,這種風氣讓他產生了“雖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慨。
“學而時習之”是中國傳統哲學知行合一的重要內容,在儒家典籍中還有大量論述,如《禮記·儒行》的“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記·中庸》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禮記·大學》的“格物致知”;《荀子·儒效》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6];等等都在強調踐習的重要性。
古希臘中那種重視音樂來訓練人們心靈來達到身心和諧,以至于成就人們德行的作用,在儒家典籍中是以禮樂關系來論述的。《大學·樂記》有云:“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與古希臘哲人觀點類似,儒家也認為音樂訓練作用在人心之上。《樂記》又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在儒家看來,禮儀是人們言行的外在規范,合乎禮儀是人們德性的外在表現。但是,禮儀的制定主要是通過規范上下、親疏的分別,來達到社會次序的,故而需要一種通融的力量使禮儀在分別中實現和諧,儒家認為這種力量來自音樂的訓練。
三、古典博雅教育思想的現代啟示
博雅教育在中國經過近20年的討論,已在教育界形成共識,也是目前教育實踐的主流,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諸多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博雅教育的相關的科目,當作知識,而不是能力培養。比如,道德倫理是博雅教育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有學者甚至認為它就是博雅教育的首要目的[7],其實它本質上是人們正確處理自己與他人或社會關系的一項重要能力,但是在相關課程的教學大綱中,卻只有課堂宣講,頂多加上與學生互動,卻沒有任何相關的踐習或者模擬訓練,這就是把道德倫理科目當作是知識而不是能力的表現。由于認識沒有到位,體現在教學大綱或者培養計劃之中,就只有知識的學,而沒有應用的習,這就使知識永遠處于外在狀態,不能內化成人的素質。其實,古希臘哲學提出的身心訓練(且不論其具體的科目設置是否合理),與孔子提出的“學而時習之”的思想,才是為德行教育的至理。德行不僅是學習知識道理,還必須使學到的道理內化于心,這就有一個通過不斷踐習來培正心性的內化過程,以至于習慣成自然,使人們在生活的言行中遵守道德倫理規范成為自覺。
由于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獲得知識,因而在具體的教學安排中,又出現了兩個普遍的問題:
第一,普遍的大班教學。國外大學的博雅教育普遍采取小班研討制(一般都在25人以下,如果達到40人就必須配置助教,大班教學不超過總體課程的3%),而且每學期課程較少(平均每學期4門左右),這樣既能保證學生充足的能力訓練時間,也便于教師通過仔細批改學生的讀書報告、論文,以及課堂討論來檢查學生的學習情況。但是國內大學則多采取大班教學(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一兩百),這就是使得所有的技能訓練成為泡影,即便在教學大綱中強行安排,實際上也無法有效地實現。但是,如果只把博雅教育的教育目的看成傳授知識,那么大班教學是符合效率原則的,因而是合理的。
第二,課程設置中,課程門數過多,看似全面,實則每門課程安排的教學時間與教學量都有所不足,這就造成了教師與學生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經歷來保障知識應用方面實訓與作業,從普遍出現“教而不習”與“學而不練”的現象,使得大部分學生在知識把握上浮光掠影,不能將之內化為自己的能力,從而難以應用。
總之,古典博雅教育思想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要回歸博雅教育的根本任務,以能力導向來培養學生,而不僅僅將其看作是知識的傳授。
參考文獻:
[1][美]戴維·L·瓦格納.中世紀的自由七藝[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2]馮金明.古希臘演說辭全集·伊索克拉底卷[M].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
[3]柏拉圖.理想國[M].李美靜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
[4]單中惠,楊漢麟.西方教育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5]孔祥驊.“六藝”出自巫史考——兼論孔子與《六經》之關系[J].學術月刊,1992(4):63-69.
[6]張紅梅,周方昌.試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系[J].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4):5-7.
[7]楊福家.博雅教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董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