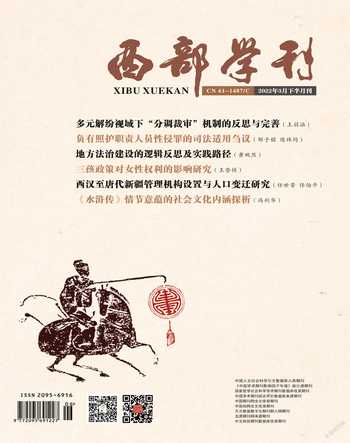西漢至唐代新疆管理機構設置與人口變遷研究
任世芳 任伯平



摘要:新疆是中國開發較早的區域之一。對西漢至唐代新疆的人口與開發歷史進行梳理和考證,發現自公元前60年至742年這800多年間,西漢最早設置了西域都護府,管轄陽關以西天山南北,西包烏孫、大宛、蔥嶺。歷經東漢、三國、西晉、十六國、北魏、隋等,直至唐朝進行正規的州、郡、縣設置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其中從十六國到北魏的230年間,中原及河西走廊的各民族向西域流動強烈,漢、氐、鮮卑、敕勒、匈奴等民族已經在新疆充分融合。研究表明,唐代極盛時期新疆諸籍人口最高達到十六萬多人。
關鍵詞:西漢;唐代;新疆;人口與開發
中圖分類號:K232;C92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6-0014-06
新疆是中國開發較早的區域之一。由于年代久遠,現存有關歷史時期新疆開發史和人口數量的記載很少,僅存的史料也大多語焉不詳,加之當時的技術條件無法對游牧民族進行戶口統計,造成不同學者對歷史時期新疆人口數量的計算和解讀存在差異。研究基于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和考據,對自西漢在今新疆地區設置西域都護府(公元前60年)始,直至唐朝進行正規的州、郡、縣設置和嚴格戶籍管理的數個朝代進行人口與開發歷史的梳理和考證,希望對這一時期史實的還原有所幫助。
一、隋代以前經營簡述
(一)兩漢期間的經營
西漢以來,中原王朝為了維護本土安全穩定和開辟疆土,長期經營西域(即今新疆及其周邊地區),對邊疆各少數民族主要采取以“和撫”為方針的策略,即所謂“羈縻”,并設置州、郡、縣加以管理,這些舉措使該地區的人口有了明顯的增長。
西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置西域都護府,任命鄭吉為第一任都護,管轄玉門關,陽關以西天山南北,西包烏孫、大宛、蔥嶺。轄區內人口約一百二十六萬,其中在今天中國境內的約五六十萬人(《漢書》96卷《西域傳》)[1][2][3]。
此后各朝代也沿襲西漢制度。東漢設西域長史府,三國曹魏及西晉因之,同樣設西域長史府,轄區與西漢大致相同,也均未設置州、郡、縣。
(二)兩漢至隋以前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中原的統一王朝滅亡,從公元304年匈奴族劉淵建立漢國起,至公元439年北魏滅北涼,這135年稱為十六國時期,中原戰亂頻繁,小國紛立,但前涼、前秦、后涼、西涼4個政權仍統治著整個西域地區(惟不包括烏孫)。而且有別于西漢至西晉僅限于羈縻,前涼、前秦、后涼、西涼、北涼5個政權還在高昌地區設置了高昌郡。鄒逸麟先生指出:“這是西漢以來大量漢人入居開發的結果,到了前涼時期就很自然采用了與內地農業區同樣的地方行政制度進行統治,這是中國疆域史上第一次在新疆地區設置與內地同樣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西北開發史上具有重要意義。”[3]
北魏于公元439年滅北涼,統一中國北方后,與柔然為爭奪西域常有戰爭,互有進退。新疆西部的的龜茲(今阿克蘇、庫車一帶)、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烏孫、悅般(均在今巴爾喀什湖東南)、渴槃陁(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一帶)、于闐(今和田一帶)、鄯善(今若羌一帶)等小國,均有歸附北魏的愿望,因柔然所阻,未能如愿[3]。
5世紀中葉,北魏曾于焉耆置鎮、鄯善置西戎校尉府,但統治均不穩定[3]。
二、隋代對西域的經營
隋朝統一中國本部后,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大軍進駐伊吾城(今哈密),設伊吾鎮。公元610年置伊吾郡。此前曾于公元609年置鄯善(治今新疆若羌)、且末(治今且末)二郡[4]。這三郡均位于今新疆東部,中原王朝西部郡縣的設置如此之遙遠,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十六國以來中原文化在西部開拓的結果。
但上述3個郡的戶口數字卻是個疑問。查《隋書·地理志》得知,該志的鄯善、且末二郡有郡、縣之名而無戶數,而伊吾郡連郡名也未列入。據凍國棟先生在論文[5]中指出:按宋本和十通本《通典》卷7《食貨典》歷代盛衰戶口條的隋代戶口統計年份作“大業二年”,即公元606年;“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已據隋志改為大業五年”。
作者認為,《隋書·地理志》的前文并未明確表述它所記的戶口數字之統計年份,僅僅只是寫道“(大業)五年平定四郡”,此處所稱四郡,即今新疆境內的鄯善、且末,青海境內的西海、河源。前文接著敘述全國郡、縣、戶、口的數字。由此可見,大業五年是指隋代開疆辟土的截止年份,而并不是一定指戶口統計年份,細讀該前文,即能理解隋志編撰者的原意。舊本《通典》既作大業二年,必有所本,不宜貿然否定。
按隋代戶口統計制度,據《隋書·食貨志》云:大臣高熲(熲音窘)建議:“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文)帝從之。”
綜上所述,如隋志戶口為大業二年數,新疆三郡尚未設置,戶口自然無從統計;如為大業五年,則按《隋書·煬帝紀》[4],當年六月“癸丑才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不可能馬上調查戶口,向隋朝廷中央“上計”。因此,《通典》和《隋書·地理志》均缺四郡戶口就是可以解釋的了。
三、隋代之前中原人口遷入新疆的線索
隋及隋以前,新疆境內郡縣無人口記載。
西漢經營西域,似自武帝元鼎六年秋(公元前111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徒民以實之”(《漢書·武帝紀》)[1]。張掖、敦煌位于今甘肅省河西走廊西端,尚未入新疆境(見文獻[6]),作者認為這是武帝經營西域的前期準備步驟。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秋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1],大宛為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之費爾干納盆地,都城位于今烏茲別克斯坦(或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內,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大宛降漢,這次西征歷時將近兩年。又據顏師古注:“庶人之有罪謫者也”,看來李廣利是征集了全國不少因罪而謫放的平民。據《漢書》卷61《李廣利傳》云:“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余而出敦煌六萬人。”[1]而太初四年(公元101年),即出兵后的第二年,李廣利“軍還,入玉門者萬余人”,則未入玉門關的至少有五萬人,這樣多的人未必死亡在大宛。gzslib202204041649《漢書》卷94《匈奴傳上》記載: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廣利又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漢兵物故什六七”,中原又有約二萬人未能返回酒泉。
以上兩項合計七萬人,作者認為并非全部死亡,更可能的是滯留或定居新疆,其理由如下:
1.李廣利第一次西征的戰果是大宛降漢,說明戰斗還算順利,不至于有83%以上的兵卒戰死,否則只剩下一萬人,大宛一個反擊就可將其部殲滅,因為大宛也是大國而非小的城邦。
2.《隋書·西域列傳·高昌》云:“昔漢武帝遺兵西討,師旅頻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意思是最疲倦困乏的士兵就留居高昌。實際上更可能的是,這些有罪的囚徒,雖然朝廷或許曾有戰勝則赦放的承諾,但看到高昌及絲綢之路上一些地方自然條件尚好,留下來比返回中原更好,因而定居新疆。
3.《隋書》上述文中又云:“(高昌王馬)儒又通后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愿東遷,相與殺儒,立(麹)嘉為王。”從西漢武帝到北魏(北魏太平真君十年即公元449年設有西戎校尉府),此時內地王朝控制范圍向西北已達最遠,其伊吾郡和焉耆郡已與高昌國接壤,但距西漢武帝西征大宛已有550多年,高昌居民安土重遷的情緒完全可以理解。
四、唐代以前遷入人口的族裔淺探
遷入新疆地區的民族成分,在西漢武帝命令李廣利西征時,入疆者肯定絕大多數是漢族(“天下謫民”),因此其后留疆者也應絕大部份是漢族,這是特定條件下的集體移民。
十六國時期情況有些不同,與新疆接壤的今甘肅省,曾先后有前涼、前秦、后涼、西涼、北涼5個割據政權控制著西域,其統治者族屬分別為漢、氐、漢、氐、匈奴,故遷入西域者不論官、兵和平民都可能有大量氐族、漢族、匈奴族和其他少數民族。
北魏時期民族融合更加緊密。作者在論文[7]中指出,這一時期統稱漢族和鮮卑族為華人。拓跋鮮卑統治中國北方將近150年,漢族的鮮卑化相當普遍,如東魏的實際統潔者高歡就是鮮卑化的六鎮漢人,隋文帝楊堅也是由弘農遷往武川鎮的鮮卑化漢人。反之,鮮卑人的漢化也不少,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實行漢化政策,自己也改姓元。
而東魏大將斛律金(斛律阿六敦),則是突厥語族中敕律部族人。正是由于北魏統一和治理時間長達150年,各民族(漢、鮮卑、高車、匈奴等)已經逐步融合,故《北史》統稱之為“華人”,就連“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的山胡(步落稽),也“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8]。
基于以上分析,從十六國到北魏分裂為東、西魏的230年間(公元304—公元535),中原及河西走廊的各民族流動及融合極為強烈,因此,從內地遷入西域的不可能只是漢族,而應是《北史》所稱的華人,其中包括漢、氐、鮮卑、敕勒、匈奴等已經充分融合的各民族。
五、前秦及諸涼曾對西域長期經營
(一)前涼。國主為漢人張寔,前涼奉晉朝正朔,東晉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張寔之子張駿繼位后,出兵“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并降”。寔曾任命張植為西域校尉[9]。前涼公元376年為前秦所滅,經營西域計41年。
(二)前秦。前秦于苻堅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任命呂光領兵“七萬以討平西域”,次年呂光自長安發兵出玉門,攻克龜茲,“王侯降者三十余國。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龜茲王)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前秦國主苻堅因呂光平西域有功任命呂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前秦公元394年為后秦所滅,經營西域計11年。
(三)后涼。氐族人呂光奉前秦命平定西域后,留守該地區,文獻[9]云:“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前秦敗亡后,呂光在公元389年自稱“三河王”,即王位于涼州(今武威市),自前秦滅亡之公元了394年算起,到后涼公元403年為后秦所滅,統治河西走廊及新疆大部共9年。
(四)西涼。李暠,今甘肅臨洮漢人,后涼時任敦煌太守。東晉隆安四年(公元400年),被推舉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當年“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9]西涼于公元421年為匈奴北涼所滅,統治西域計21年。
(五)北涼。北涼國主匈奴人沮渠蒙遜玄始十年(公元421年),“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9]在其先,于公元420年左右,曾任命隗仁為高昌太守。可見北涼早已設置了高昌郡,而西域三十六國的臣屬在后。北涼統治(羈縻)西域約38年,公元439年為北魏所滅。
以上五國,經營西域共計達120年,占十六國統治時期(公元439—304年)135年的88%以上,時間不可謂不長,在此期間中原文化會進一步傳播到新疆地區。最典型者是北周時期漢人麴寶茂公元555年在新疆東部建立的高昌國,它存在了85年,到公元640年為唐朝統一。
六、唐代新疆開發與人口估算
(一)開發情況簡述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平高昌麴氏王國,獲戶八千零四十六,口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八”(《舊唐書》卷138《高昌傳》)[10]。這件史實有幾點值得追索其淵源。
1.三國曹魏繼承西漢和東漢的制度,在今新疆地區建立“西域長史府”,并在高昌駐戊已校尉,羈縻西域各小國。曹魏對諸小國只要求其進貢和承認宗主身份,而并不干涉各國內政。西晉因之,也設西域長史府和戊已校尉,前者駐海頭,在羅布泊西岸;后者駐高昌,在今吐魯番市與鄯善縣之間。而麴為古代漢族姓氏(三國曹魏時有麴英)。故很有可能麴氏家族是在三國時期遷入高昌。其子孫后成為高昌國王。《舊唐書》卷40《地理志》在高昌條下云:“(北)魏末為蠕蠕(即柔然——作者注)所據,后麴嘉稱高昌王于此數代。”[10]
2.《隋書·西域列傳·高昌》云:“高車……以敦煌人張孟明為(高昌國)主,孟明為國人所殺,更以馬儒為王,以鞏固、麴嘉二人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后魏(即北魏——作者注)請內屬。人皆戀土,不愿東遷,相與殺儒,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今甘肅省蘭州市東)”[4]。gzslib202204041649由引文可見,高昌幾任國王均為甘肅漢人,麴氏家族世襲罔替后,更由北魏時期延綿到初唐,立國時間近百年。《隋書》又云:高昌王宮“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象。……其鳳俗政令與華夏略同。”顯然國中絕大多數為漢人。
3.高昌國在唐政府收復后改設西州,州治在今吐魯番市,據《隋書》介紹,此地區“地多石磧”(即所謂石漠——作者注),氣候溫暖,谷麥再熟,宜蠶,多五果(即桃、李、杏、梨、葡萄——作者注)。“又在吐魯番出土文書的阿斯塔那184號墓另出件《唐請處分前件物納官牒文稿》中有句:“奴婢因茲逃避,田地無人澆溉”[5]。表明當時該地區已有灌溉農業。新疆氣候干旱少雨,灌溉全靠冰川及積雪融化供水,而新疆沒有灌溉就沒有農業,高昌等地農業的發達,與漢族移民的遷入不無關系。
4.公元640年時高昌國有人口37738人。據《舊唐書》卷40《地理志三》西州條下載:“天寶領縣五,戶九千一十六,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新唐書》卷40《地理志四》隴右道西州交河郡條:“天寶元年為郡……戶萬九千一十六,口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兩志所載口數完全相同。由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至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其間計102年,口數僅增加了31.10%,年遞增率僅2.6‰,這一數字相當之低。據凍國棟先生介紹:“……學術界已有的研究可知:唐前期(貞觀至天寶)戶口的平均年增長率在10‰左右。”[5]西州的增長率只及唐全國同期的1/4強,其中之原因,據作者推測是西州只管轄敦煌、壽昌二縣,故交河郡并非高昌國土的全部,而只是高昌城周圍的較小地區,高昌國的管轄范圍應該包括伊州、西州、庭州等與高昌城毗鄰的地區,其人口在天寶十一年時為69597人。而沙州所轄敦煌、壽昌2縣的縣治均位于玉門關和陽關之內,屬甘肅、自非高昌所能控制。因此,舊高昌國范圍內的人口由37738人增加到69597人,增加1.844倍,年平均遞增率約為6‰,與我國一般年份人口遞增率6‰~7‰的數值相一致。
(二)新疆華族戶口的估計
查閱唐代新疆地區州縣的華族戶口一般有以下幾種史籍可資應用。
首先是新、舊兩種《唐書》的《地理志》,史學界大多認為,《舊唐書》的數字比較可靠,《新唐書》補充的史實較多,內容較為豐富生動,但數字及文字多抄自《舊唐書》,難免有脫訛之處。因此作者綜合《舊唐書·地理志》所載的戶口數據,結果見表1。
第二種是梁方仲先生根據《元和郡縣(圖)志》為主,并參考《太平寰宇記》等典籍,整理而得的數據[11],見附表2。
第三種是唐代杜佑所編《通典·州郡典》[12]所記唐天寶年間各州戶口數,見表3。
比較表2和表3的數字,我們發現前者(開元數)和后者(天寶數)的戶數只相差1.3%,口數只相差6.19%。
由此,作者傾向于認為,唐代開元、天寶時期今新疆境內四州的戶數在22000戶左右,人口數在10萬人左右。另外還有一個理由,畢竟兩唐志分別是五代劉眗等人和北宋歐陽修等后人所撰,而《通典》是唐代名臣杜佑所編撰,杜佑作為唐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本朝人寫本朝事,又掌握著各種現成的檔案,他的著作可信度應最高。
綜上所述,表2(梁方仲先生綜合整理)的合計戶數和口數,與表3(杜佑《通典》記載)的合計數,分別誤差僅1.31%和6.19%,精確度相當之高,可資應用。
(三)戶口估算方法
在表1中,帶括號的數字均為估計數。不帶括號的數字:沙州戶數引自《元和郡縣(圖)志》;其余引自《舊唐書·地理志》。
各州估計戶口的方法如下:
沙州:《元和郡縣(圖)志》有天寶戶數而無口數,依舊領縣(貞觀十三年,即公元639年)戶均口數3.81算得天寶口數。
西州:《舊唐書·地理志》有舊領縣戶數而無口數,今按天寶(天寶十一年,即公元752年)戶均口數5.49算得舊領縣口數。
北庭都護府,即庭州:《舊唐書·地理志》有舊領縣戶數而無口數,故按天寶戶均口數4.48算得舊領縣口數。
表2是根據梁方仲先生在文獻[11]中,綜合《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古籍,整理出來的唐代戶數,因只有戶數而無口數,因此我們假定開元、天寶間各州戶均人數不變,用以估算當時的人口,顯然存在一定誤差,僅供參考。
但是比較兩表可見,天寶的戶數比開元戶數減少10.4%,而口數減少12.5%。
(四)屯兵及安西大都護府的人口
1.屯兵人口
《舊唐書·地理志》載有北庭都護府(庭州)屯兵事,但其記載頗有疑義,原文云:“自永徽至天寶,北庭節度使管鎮兵二萬人,馬五千匹;所統攝突騎施、堅昆、斬啜;又管瀚海、天山、伊吾三軍鎮兵萬余人,馬五千匹”。但下文只有:“瀚海軍,……在北庭都護府城內,管鎮兵萬二千人,馬四千二百匹。天山軍,……置西州城內,管鎮兵五千人,馬五百匹。……伊吾軍,在伊州西北五百里甘露川,管鎮兵三千人,馬三百匹。”由三軍分兵數合計,可知正好是鎮兵二萬人,馬五千匹而不是“三軍鎮兵萬余人,馬五千匹”,此疑點一。再者,按唐志原文,節度使管兵二萬,馬五千;“又”管三軍兵萬余,馬五千,使人感覺該使共管兵三萬,馬一萬;或共管兵四萬,馬一萬,此疑點二。據作者分析,文中“又”字應刪去,而三軍鎮兵應為二萬人。
鎮兵是否會帶家屬?鎮兵本人是否已列入當地戶籍?從《敦煌資料》所錄《唐交河郡柳中縣(天寶年代)籍》[13]殘存的康文冊,為戶主,白丁,40歲,本郡(即西州)天山軍鎮兵。因殘卷下段又缺,不知該戶共有幾口。但不可能這戶只有康文冊一人。
該書《唐交河郡(天寶年代)籍》又有:“弟知非載叁拾肆歲,勛官上柱國本郡天山軍鎮開元貳拾捌載伍月貳拾玖日授甲頭馬玄忠”。作者估計戶主應為知非之兄,可能亦身為官吏。
以上兩例表明鎮兵和官吏均為著籍人口,即已編入戶籍,因此我們不另外計入官兵戶口。gzslib202204041649《通典·州郡典》還載入天寶元年(公元742年)安西都護府的戶口,計12106戶,63168口。(戶均5.218口)。這是兩唐志都沒有的寶貴資料,說明唐政府已在伊、沙、西、庭四州以外的新疆境內設置州郡縣,并統計戶口。
《舊唐書·地理志》還記載了月氏等16個都督府的府治所在地。經與文獻[14]對照,它們都位于現代國界線以外,故不討論。
2.安西大都護府的人口
安西大都護府是唐將龜茲、于田、疏勒、焉耆四小國合并而成,四小國分設龜茲、毗沙、疏勒、焉耆四都督府。疏勒有勝兵二千;龜茲、毗沙各有勝兵數千,今均以三千計;焉耆無勝兵數,姑以二千計。四小國估計有勝兵一萬人。又據王尚義先生估計,少數民族平均每4.73人出勝兵一名[16],則估計四小國人口在4.73萬人左右(表2戶均口數為4.78,與出勝兵之比例相合)。
從四小國的自然條件來看,隋唐時期均為以農業經濟為主。《隋書·西域列傳》云:龜茲國(今庫車)“土多稻粟菽麥”;于田國(今于田)“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疏勒國(今喀什市)“土多稻粟麻麥”。《北史·西域列傳》云:焉耆國(今庫爾勒市及焉耆回族自治縣“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麥,畜有馳馬,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纊,俗尚蒲桃酒。”表明四國均為農業國而非游牧民族。
《舊唐書》在敘述北庭都護府的十六番州時云:“已上十六番州,雜戎胡部落,寄於北庭府界內,無州縣戶口,隨地治畜牧”。由此可見當時對游牧民族是不入編戶的,因為按當時的技術條件,官府根本無法對游牧民族進行戶口統計和管理。由此又可知,《通典》所記載的安西大都護府戶口,應該就是將從事農業并定居的原住民,編入戶籍,成為“華人”。
此外,文獻[10]又云:“安西都護府,鎮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試將鎮兵數與原住民口數合計,為7.13萬人,與《通典》所記63168口相差8132人,誤差11.41%,這一誤差并不算大,因為統計年限和統計口徑是有變化與差異的。
(五)天寶年代以后的情況簡述
天寶十四年—寶應二年(公元755—763年)即安史之亂時,吐蕃奴隸主入侵,隴右道全境淪陷,時間長達85年。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今甘肅敦煌)人張義潮起兵反抗吐蕃,公元851年奉唐正朔,舉河西、隴右十一州復歸唐朝,其中就包括伊、沙、西3州。
吐蕃占領期間,留居河西、隴右的唐人仍在艱難的環境下堅持生產。《新唐書》卷216《吐蕃傳》載長慶二年(公元882年)劉元鼎入吐蕃會盟事有云:“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15]
成紀在今甘肅秦安縣西北,蘭州在今蘭州市,均在唐隴右道的東部。但其先張義潮在沙州起義,“一日,眾擐甲噪州門,虜(指吐蕃官吏”)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余州“,顯示在這十一州唐人眾多。
張義潮起義收復沙、西、伊、瓜、甘、肅、蘭、鄯、河、岷、廓、涼等十二州,唐封其為歸義軍節度使。
公元867年張義潮回長安,在朝中為官,由其族侄張淮深留守河西、隴右(名歸義軍)。公元872年張義潮去世,唐朝廷任命沙州長史為歸義軍節度使。
《新唐書·吐蕃傳》又云:“后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為回紇所并,歸義諸城多沒。”回紇首領骨力裴羅在唐玄宗時受封為懷仁可汗,此后歷代可汗皆接受唐朝冊封。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汗國崩潰,諸部離散,一部分南下降唐,一部分西遷。西遷者一支至河西走廊,稱甘州回紇,為今裕固族祖先。一支至西州(高昌,今吐魯番市),以后逐漸形成維吾爾族。作者估計,回紇開始統治新疆各州,當在公元872年以后,則歸義軍至少存在了24年[17]。
結語
中原王朝自西漢開始經東漢、三國、西晉、十六國、北魏、隋等數個朝代,在今新疆及其周邊地區一直設立有專門的管理機構,雖歷經戰亂但一直傳承下來,在維護邊疆地區安全穩定的同時,也促進了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中原文化的傳播,與之伴隨的是該時期一部分少數民族和內地漢族人口的遷入。
研究表明:唐代新疆境內唐人(華人)的著籍戶口,為伊、沙、西、庭4州及安西都護府合計戶數為34329戶、人口164187人;這兩項數字比文獻[18]中表1中伊、沙、西3州合計戶數25838戶、人口75883人分別增長32.86%和116.37%,作者認為,這是唐代新疆境內唐人戶口的高峰。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西域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葛劍雄.中國人口史·第一卷·導論·先秦至南北朝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3]鄒逸麟.中國歷史人文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4]二十五史·第三冊·隋書·地理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5]葛劍雄,凍國棟.中國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時期[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6]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7]任世芳,任伯平.南北朝北方諸突厥語族及契吳考[J].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3(5).
[8]二十五史·第三冊·北史·卷九十六·稽胡[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9]二十五別史·十六國春秋輯補[M].濟南:齊魯書社,1999.
[10]劉眴,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1]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2]唐杜佑.通典·州郡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8.
[13]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敦煌資料(第一輯)[C].北京:中華書局,1961.
[14]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15]宋祁,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6]王尚義.兩漢時期黃河水患與中游土地利用之關系[J].地理學報,2003(1).
[17]張帆.中國古代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18]汪永臻.從人口變化看唐代河隴地區農業經濟的開發[J].西北人口,2009(1).
作者簡介:任世芳(1974—),女,漢族,湖南湘陰人,太原師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水文水資源及歷史環境變遷。
任伯平(1933—2017年),男,漢族,湖南湘陰人,原中國民主同盟山西省委員會研究員,原太原師范學院客座教授,研究方向為歷史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