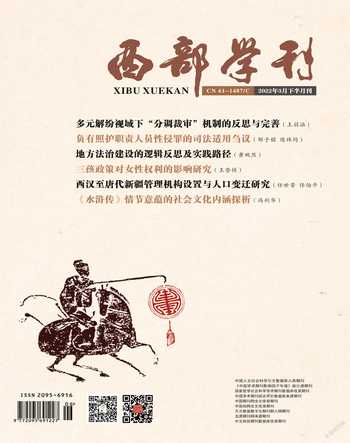國際關系中的“例外主義”探析
張鵬 周前程 張俊杰
摘要:運用到國際政治上的“例外主義”實質是“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例外主義”國家通常認為自身在道義上優越于其他國家,其價值與主張是“特殊”的;另一方面,“例外主義”國家認為自身代表的價值、政策、模式等具有“普遍”意義,超越國界,是其他國家應該追求的目標和參照的標準。“例外主義”與“民族主義”有明顯區別。“例外主義”并非都意味著“單邊主義”和“豁免主義”,其表現出多種形式,依據“典范或使命”“豁免或非豁免”兩個維度可以分為“帝國型”“文明型”“國際型”“全球型”四種類型。
關鍵詞:例外主義;美國;印度;土耳其
中圖分類號:D83/8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6-0058-04
一、引言
“例外主義”①并非只是“豁免主義”(不受國際制度、規則管轄和制約),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種形式。本文試圖從理論上梳理和界定國家外交中的“例外主義”,并依據兩個標準將“例外主義”的表現形式大致分為四個類型,即“帝國型”“文明型”“國際型”“全球型”。每一種類型的“例外主義”具有不同特征。通過對于美國、印度、土耳其外交中的“例外主義”現象進行案例分析,本文得出一些初步結論,包括:“例外主義”古已有之,并非一個新現象,也并不為美國獨有;“例外主義”并不必然與物質實力成正比,弱國也存在某種類型的“例外主義”,外交雄心是關鍵;“例外主義”并非是“單邊主義”“豁免主義”的同義語,并不必然代表著對抗性,某些類型的“例外主義”倡導多邊主義,尊重國際制度與規則;一國“例外主義”的形式隨著時空發生改變。因此,在理論上,本文有助于厘清“例外主義”與相關概念的區別,深化對于外交中“例外主義”這一現象內涵、形式等的認識;在政策上,可以在區分不同形式和類型的“例外主義”的基礎上,區別對待之,對于主張合作與多邊主義、有利于維護國際秩序的“例外主義”給予理解和支持,揭露并反對秉持霸道、單邊主義與“豁免”立場的“例外主義”。
二、“例外主義”的內涵與類型
“例外主義”是對于一國國家身份的界定,通常表現為一國在道義方面的某種優越感,認為自身的價值理念、政策主張等代表著普遍價值,是人類進步的發展方向,其實質是“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例外主義”國家通常認為自身在道義上優越于其他國家,其價值與主張是“特殊”的;另一方面,“例外主義”國家認為自身代表的價值、政策、模式等具有“普遍”意義,超越國界,是其他國家應該追求的目標和參照的標準。
“例外主義”思想的產生一般都內含對于國家、民族身份的構建,但并非所有關于國家、民族身份的構建都必然包含“例外主義”的成分,“例外主義”言行也并不存在于每個國家的外交中。“例外主義”也并非某個國家的“專利”,其存在已久。“例外主義”外交通常體現出一國自認為具有的某些獨特性,這些獨特性(尤其是價值、精神、理念層面)為該國獨有,不能被他國復制,是該國優越于其他國家的地方。但“例外主義”國家標榜自身在外交中追求一種普遍的“善”,這種“善”又是普世的。“獨特性”與“普世性”的互動關系構成了“例外主義”內在的矛盾性。
“例外主義”不同于“民族主義”。雖然二者都表現了一國強烈的優越感,但“例外主義”的優越感主要來自于道德、精神層面,“民族主義”的優越感主要來自于種族層面。“例外主義”雖然代表著某些獨特性,但“例外主義”國家通常宣稱自身標榜的價值觀、理念、政策等是一種適合于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理想追求,這些價值并不具有排他性,反而是“例外主義”國家極力倡導的。“民族主義”卻經常流露出民族中心主義的狹隘性與排他性,認為本民族天然地優越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不具備同樣“優越”的條件,甚至是劣等民族,是被征服和犧牲的對象。民族主義通常以國家邊界界定自身的優越性[1]。歷史上和現實中因狹隘民族主義而導致的慘劇和糾紛不勝枚舉。
“例外主義”包含不同類型,根據兩個重要維度“典范性或使命性”“豁免性或非豁免性”,可以將“例外主義”劃分為四種理想類型。所謂“典范性”,是指認為自身是人類發展的典范,但該國特立獨行,沒有改變他人、使他人歸附自身的沖動。所謂“使命性”,是指該國認為自身具有推廣自身價值理念、轉變他國、改變他人的義務,具有強烈的救世感和傳教士式沖動。但這種轉變的方式也存在區別,最強烈的以美國小布什政府為典型,直接以武力鏟除所謂“邪惡”政權,強制按照自身意志改造中東國家。“豁免性”是指標榜“例外主義”的國家認為自身可以豁免于國際制度、規則之外,不受它們約束,通常意味著單邊主義與利己主義。所謂“非豁免性”是指“例外主義”國家接受國際制度與規則的約束與限制,與其他國家一樣遵守國際社會公認的制度與規范。依據這兩個維度,可以將標榜“例外主義”的國家分為四個理想類型:文明型例外主義、帝國型例外主義、國際型例外主義、全球型例外主義。
文明型例外主義代表著一種典范性的價值理念與發展道路,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最發達的文明,認為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是遜于自己的、“未開化”的“蠻族”,對于國際事務持超然態度,力圖游離于國際紛爭之外,不受外部世界的牽扯,追求本國的發展與完善。因此,文明型例外主義往往與孤立主義外交相連。
三、“例外主義”的案例分析:美國、印度、土耳其
(一)美國的“例外主義”
美國的“例外主義”最具有典型性,超級大國時常出現的“例外”言行受到世人關注,也引發了學術界的濃厚興趣。美國是將國家身份與“例外主義”聯系地最緊密的國家。有學者認為“例外主義”是美國國家身份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組成部分[2]。美國的身份由“例外主義”界定,因為“例外主義”是一個強大、延續、普遍的信仰,貫穿于美國歷史,在美國外交政策辯論的時期,總能成為美國各派尋求合法性和為自身辯護的依據。美國的“例外主義”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從清教徒宣稱的“山巔之城”到美國《獨立宣言》的文本,區別于其他地區(尤其是歐洲)的“例外主義”思想在美國根深蒂固。美國的道德優越感存在已久,認為自身不同于“封建”歐洲,懷揣著當時最先進、最前沿的啟蒙思想,在一塊新大陸上實踐著前無古人的人類理想,是人類精神的燈塔。gzslib202204041904美國的“例外主義”體現在不同維度。從“典范性”上看,美國將“人人生而平等、三權分立、憲政、法治、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代議制政府、言論與宗教自由”等近代啟蒙思想家的理念付諸實踐,在政治發展上走在世界前列。這些思想、理念、制度設計被美國憲法固定下來,成為美國的立國之基、強國之本。美國精英與大眾認為其理念與制度是美國強大的主要原因,且具有普世性,是其他國家的典范,美國的“例外性”即在于此。從“使命性”來看,美國的“例外主義”體現在美國“天定命運”的思想與自信。“西進運動”②后,美國基本完成了大陸的擴張,目光開始投向海外。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以及加入列強迫使日本、中國等打開門戶,美國的勝利都令美國人更加篤信自身的“天定命運”:美國是獨一無二的“上帝選民”,美國的理念和發展道路是最先進的,代表著人類的最高水平,美國肩負著改造世界的使命與責任[3]。“典范性”與“使命性”也體現出“例外主義”內部一定的緊張關系。“典范”要求美國做好自己,與他國維持和平的貿易關系但超脫于他國事務之外。“使命”堅持認為美國應該積極協助他國,以使他國像美國一樣,包括在必要時超越美國國界完成美國的“例外”使命“解救”他國,為人類“自由”“民主”而戰。“典范”與“使命”這兩個維度沖突的典型體現是1919年伍德羅·威爾遜政府推動美國加入國際聯盟遭到參議院否決。美國國內不時出現的關于“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論爭也折射了“例外主義”的內在矛盾。
在“豁免性”與“非豁免性”這一維度,美國也是典型國家。美國的“例外”不僅體現在道德優越感上,對于國際制度與規則的選擇性加入、退出也是美式“例外主義”為人詬病的地方。美國對于一些關乎全球治理的國際制度,例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京都議定書》等一直拒絕加入,使這些國際制度的成效大打折扣。美國時常的“退約”之舉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不滿和擔憂,這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最為明顯。美國對于國際制度的肆意“退出”體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實用主義作風與美國“例外主義”的自私一面。
美國的“例外主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形式,這與當時美國的綜合國力、國際形勢、戰略需要等密切相關。根據前述“例外主義”的兩個維度,美國的“例外主義”在不同區間滑動。在不同政府時期,時而“典范性”多一些,時而“使命性”多一些;時而強調“豁免性”,時而宣稱“非豁免性”。從美國不同政府的政策實踐來看,克林頓政府與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整體上執行的是包容性的“例外主義”,即通過鞏固聯盟、建立伙伴關系、推動多邊主義等實現自身的領導,具有“典范性”和“非豁免性”的特征,因此接近于前述類型中的“國際型”例外主義。小布什政府秉持的“先發制人”戰略思想是進攻型的“例外主義”,具有“使命性”和“豁免性”的雙重特點,依照前述類型屬于“帝國型”例外主義。
(二)印度的“例外主義”
印度的“例外主義”自1947年獨立以來就充滿道德色彩。印度掙脫殖民枷鎖取得獨立、通過和平談判將五百個邦整合進自由民主的聯邦制的歷史強化了印度對自身理念與道路的自豪感。時至今日,印度一直認為自身有獨特的能力在世界事務中提供道義領導力。印度認為自身的歷史與文明在現實主義政治盛行的國際關系中是一個精神層面的引領者。印度的“例外主義”主要來自于:甘地非暴力、包容性的精神理念;尼赫魯對于世俗印度的精神引導;印度教的民族主義。這些宗教、精神有一個共同信仰:印度有能力、有義務給世界帶來道義領導,印度獨特的歷史與文化使其天生具有包容、整合、融合相互沖突的思想與信仰的能力。
印度總理尼赫魯對于獨立后的印度外交影響頗深。早在1944年,尼赫魯在獄中書寫《印度的發現》時,就曾指出:“印度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銷聲匿跡,中間地位是不可能的。”尼赫魯高超的外交技藝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對印度道義優越感的自信:印度注定要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一個關鍵角色,不論印度的物質實力如何[4]。尼赫魯標榜印度的外交以道義為原則,印度要做一個講道義、有原則、尊重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模范。這種道德優越感成為印度決策精英的廣泛共識與使命感的來源,他們都認為印度具有毫無疑義的文明與道德優勢在國際關系中引領“道義”行動。這種道義優越感在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的激烈斗爭中被強化。印度認為自身推動的“不結盟”運動是對兩大陣營殘酷的均勢政治、權力政治的批判。印度“不結盟”、注重戰略自主的外交傳統影響至今。
印度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并非意味著中立或者孤立,相反,獨立后的印度一直試圖在國際事務中發出自身獨特的聲音,在諸多事件中都扮演了頗具自身特色的角色:在聯合國的成立以及《聯合國家宣言》的起草過程中,印度提供了大量支持;公開呼吁國際社會承認新中國;拒絕簽署《舊金山對日和約》,認為其沒有充分尊重日本的主權與獨立;在20世紀60年代,印度宣稱不發展核武器并非印度沒有核能力,而是基于道義做出的自我限制。對多邊主義的重視、對新生的亞非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以及自身的道德使命感,使尼赫魯時期的印度接近于“全球型”例外主義。
(三)土耳其的“例外主義”
土耳其的“例外主義”思想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土耳其是伊斯蘭教與世俗國家相結合的典范;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輝煌歷史與多元文化;其處于歐洲與亞洲接合部的獨特地理位置。土耳其的領導人在伊斯蘭教與世俗國家之間未走極端,相反,同時強調伊斯蘭價值與民族國家的利益。土耳其認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代是多元文化共處的典型代表,其歷史經驗尤其適合當代世界的“文明沖突”與許多國家內部的民族、宗教沖突所借鑒。身處東西方交融的地理位置,使土耳其的決策者一直將土耳其視作東西方文明溝通的橋梁、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緩沖地帶,奧斯曼帝國是、現在也是其他國家的典范。土耳其在世界上擁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9·11事件后,有學者預言的“文明的沖突”成為可怕現實,土耳其的“例外主義”與優越感再次抬頭,認為自身的歷史與現實經驗體現了自身的“例外性”[5]。土耳其認為新世紀以來西方文明遭遇重大危機,中國、印度等文明也并未真正走向全球,土耳其的文明適合于解決當代全球問題,甚至有潛力超越當代其他文明。土耳其傳統上一直標榜、推崇的包容性、多邊主義以及內部多元文化共存的歷史使土耳其自視為地區國家的典范。近年來土耳其國力的增強使其更加自信。土耳其“例外主義”的這些特征接近于上述分類中的“國際型”例外主義。gzslib202204041904四、結論與思考
“例外主義”本質上是一國對于自身在道德、理念等精神層面懷有優越感的體現,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矛盾的統一,通常也是一國國家身份、民族身份構建的一部分。“例外主義”本質上并非是一國物質實力的副產品,與物質實力也并非成正比。“例外主義”并非美國獨有,某些國家“例外主義”思想的存在由來已久。“例外主義”并不一定意味著單邊主義與對抗行為,這只是“例外主義”的一種形式,且絕非最普遍的形式。大體來看,一國實力增強,其“例外主義”勃興的可能性大。“例外主義”具有多種表現形式,依照前文所述,可以分為四種理想類型。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同一國家在不同時期都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接近于某種理想類型的“例外主義”。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第一,“例外主義”思想主要與一國的政治雄心存在緊密關系,與物質實力的強弱并無必然聯系。美國建國前后早已經存在“例外主義”思想,但當時美國的實力還很弱小;尼赫魯政府時期的印度在物質實力上也并不強大,但外交雄心使其表現了強烈的“例外主義”言行。此外,物質實力的增強可深化也可削弱一國的“例外主義”傾向,不可一概而論。例如,如今印度實力的增強反而使其傳統上的“不結盟”政策有所弱化,戰略自主性相對下降,變得不那么“例外”。
第二,具有“例外主義”思想的國家普遍將自身看作是一個文明體,而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美國將自身看作是在歐洲文明基礎上改造后的西方文明的代表;印度也以自身的文明古國身份為傲,認為自身在精神層面可以為人類領航;土耳其認為曾經的奧斯曼帝國文明超越了如今的國家邊界,可以為當今世界化解“文明的沖突”提供啟示與借鑒。
本文只是對于“例外主義”的內涵和類型做了初步的界定和劃分,有助于厘清這一問題,加深對于這一現象的認識。對于國際關系中的“例外主義”,未來研究的問題包括:還有哪些國家具有明顯的“例外主義”思想?在何種條件下產生上述某種類型的“例外主義”?既然“豁免性”和對抗性并不是“例外主義”的必然特征,那么“例外主義”的良性形式在何種條件下會復興?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和回答的問題。
注釋:
①例外主義:最初是一種地理概念,后來演變為地域獨特主義觀點,即“例外主義”觀點。到后來,這一概念運用到國際政治上又有變化。美國因具獨一無二之國家起源、文教背景、歷史進展以及突出的政策與宗教體制,自認為世上其他發達國家皆無可比擬,故宣揚自己為“例外主義”及其典型。后來有關國家根據本國特點和外交方針也對“例外主義”做出不同的詮釋。
②西進運動:美國獨立之后掀起的“開發西部”的運動,始于18世紀末,終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間大批移民遷入西部。白人不僅強行占據了屬于印第安人土地、家園,還大肆屠殺印第安人。面對后來強大的美國,很多人極力贊揚它的聰明遠見,卻選擇性地忽略了印第安人遭遇的種族滅絕。
參考文獻:
[1]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M].London:Verso,1983:7.
[2]PATMAN,ROBERT G.Globalisation, the New US Exceptionalism and the War on Terror[J].Third World Quarterly,2006(6).
[3]KATE,SULLIVAN.Exceptionalism in Indian Diplomacy:The Origins of Indias Moral Leadership Aspirations[J].South Asia: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2014(4).
[4]尼赫魯.印度的發現[M].北京:世界知識版社,1956:57.
[5]BENHAIM,YOHANAN,KEREM,etal.The Rise and Fall of Turkeys Soft Power Discourse[J].European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2015(21).
作者簡介:張鵬(1988—),男,漢族,河南長葛人,博士,安徽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政治學。
周前程(2001—),男,漢族,安徽宿州人,單位為安徽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研究方向為政治學。
張俊杰(1998—),男,漢族,浙江寧波人,單位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研究方向為國家利益、數據科學與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