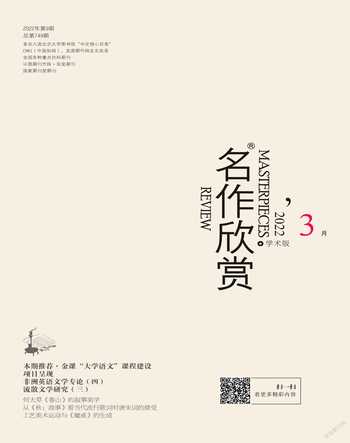死亡與新生:濟慈的夜鶯之歌
摘要:濟慈的《夜鶯頌》描摹了詩人戰勝死亡意志和逃離現實的沖動,重歸現實和詩人的使命,重獲新生的心路歷程。被詩人稱作“不死鳥”的夜鶯是詩人靈魂新生的象征。
關鍵詞:《夜鶯頌》死亡新生
濟慈的一生如流星一般璀璨而短暫,他最為優秀的詩歌絕大部分創作于1817年到1820年短短的三年間。在? 1819年,濟慈接連完成了六大頌歌的創作:《慵懶頌》《心靈頌》《夜鶯頌》《希臘古甕頌》《憂郁頌》和《秋頌》。結合濟慈寫作于1819年前后的書信和詩作,不難推斷,濟慈創作力的井噴背后有著死亡意識的推動。在創作于前一年(1818年)的題為“When I Have Fears that I May Cease to Be”(《當我擔憂生命就此停息時》)的短詩中,詩人將自己的大腦比作豐饒多產的沃土,可惜的是自己可能活不到“撿盡落穗”的那一天,也無法完成計劃中的“一堆詩書”,就像來不及用“熟透的糧食”填滿文字的“谷倉”。雖然天上變幻莫測的游云仿若“某種高級浪漫故事的巨大字符”,但是自己怕是不久于人世,沒有足夠時間來“勾勒出字符的蹤影”a。在濟慈的六大頌歌中,靈魂與肉體、生存與死亡、有限與無限、現實與想象、永恒與無常、藝術與生活這些矛盾的統一體是常見主題。濟慈在《夜鶯頌》中更是借由對夜鶯歌聲的詮釋,將這些主題容納進一首只有八十行的抒情詩之中。
《夜鶯頌》的開篇即凸顯了夜鶯的歌聲在“我”心中喚起的“痛并快樂著”的糾結情感:痛苦與歡愉相交織,對比強烈而又密不可分。詩人開篇即以“心痛”“昏沉”與“麻木”等一系列帶有消極情感指涉的語匯來形容“我”當下的心理感受,更是借助“沉向忘川”這一表述中“忘川”——冥府之河——的意象引入死亡的身影。然而緊接著,詩人筆鋒一轉,指出“我”的“心痛”并非源自對“幸運的夜鶯”所抱有的羨慕、嫉妒、憎恨等負面情緒所觸發的身體不適。恰恰相反,“我”的“心痛”乃是出于對夜鶯所代表的幸福狀態的向往和為之開心而產生的難以自抑的發自于心的強烈共鳴。詩人筆下的夜鶯宛若身姿輕盈的林間精靈,上下翻飛于綠草如茵、樹影交錯的山毛櫸樹林之中,它甜美的歌聲充盈于整個林間。詩歌字里行間處處洋溢著詩人對于夜鶯的幸福狀態的強烈認同之感與熱切的企盼之情。夜鶯“身姿輕盈”的騰飛意象寄寓了詩人對掙脫塵世羈絆、超越世俗憂思的渴盼之情。對比駱賓王獄中所作《詠蟬》一詩中“露重飛難進,聲多響易沉”的描寫,不難看出,駱賓王筆下負重前行、竭力發出自己聲音的鳴蟬是詩人愁苦心境的化身,縱然悲壯,不免自憐。而濟慈筆下飛翔的夜鶯則是詩人想要超越現實困境,企及理想世界的向上之心的化身。夜鶯翱翔的身姿將詩人的眼光引向廣袤無際的天空,引向對于無限的渴求與向往,夜鶯高亢嘹亮的歌聲更是激發了詩人對于“扶搖直上九萬里”的想象。
夜鶯的歌聲將詩人從“昏沉”與“麻木”中喚起,如同甘泉,滲入心脾。詩人接下來即用細致入微、虛實結合的筆觸描寫了窖藏多年、沁人心脾的美酒。美酒散發著田間花草的香氣,讓人不由得想起普羅旺斯的歌舞和艷陽高照下人們的歡聲笑語;酒杯里斟滿了溫暖的南方和繆斯之泉,酒杯邊緣珍珠般的氣泡在沖你眨眼,被葡萄酒染成紫色的不只是酒杯的邊緣,還有飲者的唇。有了美酒的撫慰,詩人的血液似乎也開始回暖,從麻木中漸漸轉醒,一幅有聲有色的田園風光浮現在詩人腦海之中:綠意盎然、花團錦簇的鄉野田間,以及點綴其間載歌載舞的人兒和他們不絕于耳的歡聲笑語。
雖然夜鶯的歌聲如同美酒一般令人沉醉,然而這美酒所提供的繆斯之泉在詩人心中喚起的并不是醉酒當歌、潑墨揮毫的創作沖動,而是激發了詩人不如乘興歸去的死亡意志,意欲悄無聲息地離開這個塵世,與夜鶯一起,隱遁向那“幽暗的叢林”。死亡的第一步自然是肉體的消解,故而詩人以“遠遠遁去”“消散”“徹底忘卻”三個謂語動詞的并置開始了接下來的講述。“我”所遁向的“幽暗的叢林”是文學中用以影射死亡的慣用表述,“消散”的自然是沉重的肉身,留下的則是代表不滅意志的靈魂,“忘卻”的是夜鶯“在林間從來不會知曉的/倦怠、瘋狂與躁動”。對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有所了解的讀者不難注意到,濟慈所用“倦怠”(weariness)、“瘋狂”(fever)與“躁動”(fret)的表述呼應了華茲華斯在《丁登寺》中對于時代重負的描述。華茲華斯認為浪漫主義詩人所面臨的世界是一個難以單純用理性去把握的謎團,這給詩人造成了精神的重負和心靈的疲乏。生活其間的人們躁動不安,看似忙忙碌碌,實則無所作為,這個世界不同形式的瘋狂重重地壓在詩人的心脈之上。不論是老一輩的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還是年輕一輩的浪漫主義詩人濟慈,對于英國社會痼疾的批判精神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憂患意識可謂一脈相承。濟慈接下來選取了他眼中最能代表當時英國社會現狀和人生境況的五個層面,來具體描述他眼中的塵世煩憂與磨難:人們呆坐原地,傾聽著彼此的呻吟;患有小兒麻痹癥的人頭發稀疏而花白;患病的年輕人面色蒼白、瘦骨嶙峋,直至死亡;對于人生的思考總會讓人充滿哀傷和難以遣懷的絕望;美神丟失了她的信徒,愛神日漸憔悴。在詩人的筆下,社會固然充滿了躁動不安與各種狂熱的追逐,然而也有困在原地、不知該往何處去的人們,他們哀嘆人生際遇、暗自傷懷,找不到前進的方向。雖然科學在不斷進步,但是疾病仍然難以消除,即便年輕人也會成為死神的刀下亡魂。盡管詩人所描繪的是在其所處的時代他感觸最為痛切的社會問題,然而這些社會問題并沒有隨著詩人所處時代的逝去而消散。將詩人筆下“靜坐呻吟的人們”用來描述20世紀荒誕派代表作家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也不顯突兀。疾病、衰老、死亡,以及對于真善美的界定和反思是人類社會面臨的永恒話題和挑戰。
諸如此類“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再次強化了“我”的逃離沖動,只不過這一次的逃離借助的不是美酒,而是“詩性想象力隱形的翅膀”(viewless wings of? Poesy)。即便“我”飛翔的雙翼承載著如前所述的社會問題所觸發的思想重負,“我”仍然憑借想象力這股好風的加持,直上青云,來到月亮之上。靜謐的天地和溫柔的夜色讓“我”的心也隨之柔軟,“我”有幸目睹了端坐于寶座之上的月亮女神和眾星拱月的盛況。恰如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月亮女神是初民想象力的化身,《夜鶯頌》中“眾星拱月”的月亮女神亦是被詩人賦予了統攝之力與整合之力的想象力的化身。然而,濟慈并沒有耽溺于月亮女神所代表的由想象力建構而成的理想世界,換言之,濟慈并沒有完全超越這個讓他憂心的現實世界,而是又回到了月亮之下的塵世。41256754-E997-4193-95A0-C654CF94F81D
月亮之下,除了與夜間微風一起飄散下來的月光與星光,沒有其他的光源,然而受阻的視線給了“我”聞香辨花草的機會。在香氣氤氳的夜色中,這個時令的各種青草、灌木叢和野生果樹都散發出各自獨有的氣味。在香氣的提示下,“我”仿若看到了白色的山楂花、掩映于層層疊疊的綠葉之中的紫羅蘭,以及花瓣中滾動著晶瑩剔透、清冽醉人的露珠的麝香玫瑰。聚集在麝香玫瑰周圍的飛蟲發出的不絕于耳的嗡鳴聲似乎起到了凝神靜氣之用,“我”的心神再次被“靜靜地離開人世間”的念頭所捕獲。“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詩歌的沉思中呼喚著死神的名字,期盼著他的降臨,等待著自己平靜的呼吸漸漸地消散于空中。尤其是在這個香氣馥郁、靜謐溫柔,且有著夜鶯的歌聲相伴的夜晚,死亡的誘惑比以往來得更加猛烈,讓自己的生命無痛無傷地終結于這個午夜的念頭不可遏止。然而,心念一轉,“我”想到夜鶯的歌聲并不能永伴左右。縱然歌聲永在,聽歌之人卻已長眠地下,“托體同山阿”者不過草皮一塊,再也無福傾聽夜鶯這位靈魂歌者所吟唱之安魂曲。
夜鶯在濟慈的筆下成為永恒的化身,被他稱作“不死鳥”。夜鶯的歌聲跨越歷史和階層,從古到今,不論是九五君王,還是鄉野村夫,都曾一飽耳福。對于“獨在異鄉為異客”,在鄉野田間默默垂淚的路得來講,夜鶯的歌聲也曾流淌進她哀傷的心田。即便是被囚禁于波濤洶涌、危險環伺的海中孤島之上的少女,亦有幸聆聽夜鶯的歌聲。濟慈在此處引入的路得與被幽禁的少女的意象亦可被視作詩人的自況。英美學界曾有觀點認為,詩人筆下孤獨的女性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藝術家的靈魂狀況,此處亦可適用。對于類似孤寂處境的切身之痛如同童話故事中打破幻境的午夜鐘聲,將“我”從詩性想象力織就的夢境中喚醒。與夜鶯一起翱翔九天的夜間游歷恰似黃粱一夢,而今幻境猶如破碎之鏡,映照出的仍是詩人那個“孤單的自我”。“我”曾在夢幻之境中揮別塵世,與夜鶯一起翱翔于月亮之上,而今回到現實真境,不得不再次揮別幻境。夢境之短促讓“我”不由心生感慨,想象力曾被賦予的“魔術師精靈”這一美譽是多么名不符實,詩性假象固然美好,它的易損性同樣是不爭的事實。
伴隨著夜鶯的歌聲這一幻境誘因的遠去,詩人所置身其中的不再是“充盈著夜鶯的美妙歌聲的樹林”(melodious plot),而是“靜靜流淌的小溪”(still stream)。一動一靜的對比之下,濟慈借由氛圍的轉變暗示了“我”的心境從不安到沉靜的過渡,恰如“still stream”這個頭韻/s/所傳達出的平滑與靜謐之感。在此沉靜的心境中,詩人能夠更好地聆聽華茲華斯所言“沉靜而永在的人性悲曲”(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b。故而,《夜鶯頌》始于傾聽,終于傾聽,從夜鶯的歌聲到人性的悲曲,從理想世界到現實世界,從逃離到回歸,經由夢境之旅的“訓誡”,濟慈再次背
負起時代的重擔,去直面一個詩人的使命。在他眼中,詩人只有勇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并為之做出改變的努力,才能寫出好的詩歌。《夜鶯頌》中的夢境之旅,正是濟慈的社會憂患意識和詩人責任自覺的外化,體現于詩人對于“人生的意趣”和“死亡的誘惑”之間的角力,以及從逃離到回歸的心路歷程的描述。
《夜鶯頌》的前六個詩節用相當一部分筆墨渲染了死亡的誘惑性。詩人首先用生動活潑的筆觸描寫了與自然界和諧共處、自在翱翔、引吭高歌的夜鶯,以之反襯自己作為詩人卻難以直抒胸臆的憤懣和對當時消費主義甚囂塵上、耽溺于物質追求、枉顧靈魂需求、不適合“詩意的棲居”的英國社會的批判。繼而,詩人將理想化的自然界與痛苦不安的人類社會并置,以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差。詩人歷數了人世間的萬般煩惱:疾病、衰敗、死亡、憂傷、絕望,莫不如影隨形,身體的疲憊伴隨著心靈的躁動,以美為旨歸的藝術魅力在消退,與之相伴而生的則是人們愛的能力被不斷削弱,不管是愛人,還是愛己。于是有了詩人逃離現世,與夜鶯共翔的愿望。詩人借助詩性想象力建構的幻境去逃離,去忘卻,去暢游,于是有了詩人在溫柔夜色中所嗅到與聽到的一切。月亮之上所代表的理想世界與月亮之下所代表的現實世界形成了詩人可資對比的兩重世界。月光與星光是黑暗的夜色中唯一的光源,視覺受阻,嗅覺變得更加敏銳,各種花草的香氣撲鼻而來。“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聚攏在花草周圍的飛蟲的嗡鳴聲更添一份幽靜。在如此靜謐的自然的懷抱,伴隨著夜鶯美妙的歌聲,詩人更加難以抗拒沉沉睡去的誘惑。然而,夜鶯的天籟之音亦讓詩人意識到自身與夜鶯的距離:自己不過是一介凡夫俗子,而夜鶯則是不朽的精靈,從古至今,從宮廷廟堂到山野田間,都有它的歌唱,這也是“獨在異鄉為異客”的羈旅之人的心靈慰藉。夜鶯所象征的不朽,反襯了人類個體的渺小與宿命。詩人對于個體生命的有限性與個體生命的孤單宿命的深刻體悟,仿若打破夜鶯的歌聲所建構而成的幻境的鐘聲,引領著詩人神魂歸位,從精神的漫游回到現世。就《夜鶯頌》中出現的整體意象而言,雖然詩歌中處處潛伏著死亡的身影,但生命的歡愉亦俯拾即是。詩人對夜鶯、對美酒、對歌舞、對夜色籠罩下花草樹木的描繪,處處洋溢著對于自然和人生之美好片段的悅納。
縱覽全詩,不難看出,詩性想象力所營造的詩性假象雖然短暫而易損,然而它的存在甚為必要。丁宏為在談論濟慈的《圣阿格尼絲日前夜》一詩時,針對由傳說、迷信、神話和幻覺等因素所編織的幻境對于人物現實行為的塑造之力,曾做出如下評論:“在夢幻與現實的邊界線上,人類頻繁地往來,生活即成為越界行為,而往往讓雪萊等人體味到的失敗或絕望,有時在濟慈筆下得到緩解,因為他讓真相與假象更緊密,讓現實成為夢幻空間的外延。”c這種穿行于夢幻與現實之間的“越界行為”有助于詩人實現對現實生活的“有限的超越”,它指向未盡的生命歷程,指向不斷地自我超越,既不會完全脫離現實層面,從而否定人類有限的抗爭所具有的內在價值,也不會沉溺于詩性想象力所建造的幸福幻谷。故而,讓我們再次回到濟慈在《夜鶯頌》結尾處關于“我是睡著,還是醒著?”的發問,我們可以說答案正在二者交界之處,人生即在半夢半醒之間。這夢境不僅可以帶來改變的目光,進而改變在此目光觀照下的世界,如同布萊克所言,“改變的目光使一切改變”d;而且夢境背后的詩性想象力亦可為我們平淡的日常生活附加一層審美價值,使生活中的生機趣味得益于生活與藝術之間的越界行為,從而得到激發。
濟慈曾在書信中將他從中汲取靈魂滋養的偉大的思想和作品稱作“靈魂鍛造之谷”(the vale ofsoul- making) e,而他的每一篇詩作都見證了這個千錘百煉的過程。《夜鶯頌》這首詩歌中,夜鶯的歌聲不是將人拖入有進無出的幻境般的海妖塞壬的歌聲中,而是詩人心曲所化,吟唱的是詩人自我鍛造的心路歷程。被濟慈稱作“不死鳥”的夜鶯與浴火重生、自我涅槃的鳳凰合為一體,成為詩人靈魂新生的象征。
a文中所引濟慈詩歌的譯文皆為筆者自譯,文責自負。
bWilliam Wordsworth: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見羅經國、阮煒編注:《新編英國文學選讀》(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頁。
c丁宏為:《真實的空間——英國近現代主要詩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頁。
d出自布萊克的《思想旅者》,譯文轉引自丁宏為:《真實的空間——英國近現代主要詩人所看到的精神境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頁。
eRobert Gittings, ed.. Letters of John Keat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250.
作??? 者:謝娟,博士,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趙斌E-mail:mzxszb@126.com41256754-E997-4193-95A0-C654CF94F8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