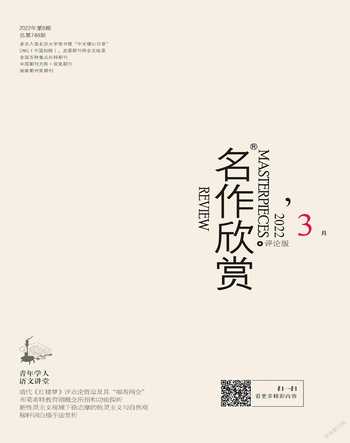民間經典的嬗變與創新
高琪
摘要:白蛇傳奇作為我國四大民間故事之一被人們所熟知,并且在不同的時代下被先后改編成戲曲、小說、電影和話劇等不同的藝術形式。20世紀80年代香港作家李碧華根據“白蛇傳”的故事改編小說《青蛇》,在1993 年香港電影導演徐克又根據小說拍攝同名電影,2013年內地導演田沁鑫將《青蛇》改編成話劇,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對這一民間傳說故事進行再敘述。不同體裁的改編對經典傳奇故事原本呈現出的人物、主題和敘事有一定的傳承,但又對其進行再建構。本文將從人物形象、敘事主題以及社會意義等方面來分析“白蛇傳”這一傳統民間故事的現代改編,并且通過這一系列成功的改編作品來思考現代改編創作的經驗。
關鍵詞:《青蛇》??? 改編??? 主題轉變??? 現實意義
“白蛇傳”和“孟姜女哭長城”“梁山伯與祝英臺”“牛郎織女”并稱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流傳至今已經變為經典“IP”,白蛇傳奇這一經典的民間傳說在不同時代的加工潤色下有了新的形式和價值體系。從香港作家李碧華對傳統的民間故事“白蛇傳”的顛覆再創作開始,隨著時代的變化進一步生成的電影和話劇都是對這一傳統故事的現代改編,并且在《青蛇》小說到電影再到話劇的改編中都有一定的時間段,除不同藝術形式下作品形式發生變化之外,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也都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民間經典在嬗變和創新中如何成功對前者進行解構重構值得關注,在改編作品背后所呈現出的不同的精神內涵以及在當時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現實意義都是可深入探究的。
一、民間故事的傳統解讀
“白蛇”這一形象最早出現在明朝洪楩《清平山堂話本》所收錄的宋元話本《西湖三塔記》中,《西湖三塔記》中跟隨在白蛇身邊的并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青蛇,而是卯奴——“白娘子”的女兒,也是一只“烏雞精”,并且白蛇是一個專門食人心的害人精,這時的蛇女被稱為蛇妖,她們不具備“人”的性格特點,這些早期的兇殘美女蛇故事主要是貶低女性和警誡男性,這些貶低主要是針對女人而非蛇。明末馮夢龍的《警世通言》中所收錄的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白蛇傳”的故事才定型,在這里出現的“青青”也就是之后白蛇故事中的“青蛇”,但是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還是一條青魚。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主要表現的是人妖沖突,其主旨是宣揚佛家禁欲思想,并且當時主要角色的白蛇是處于由惡到善轉變的過程。
傳統文本中白蛇傳說是講述一個修煉成人形的蛇精與人的曲折愛情故事,想借此表達人們對男女自由戀愛的贊美和對封建勢力無理束縛的痛憎,但是人蛇戀超越了人們認知的正常的倫理秩序,在長期封建的社會狀態下,人們認為“蛇”即為色,所以在傳統文本下無論是白蛇還是青蛇都是極具魅惑的,而且這是在男權社會下的產物,是封建社會下人們對于內心欲望渴求的表現。“情”和“理”就是傳統民間故事文本中的核心主題,《情”是指以白蛇和許仙的人妖戀情為主,以與其他角色的感情為副線的情感邏輯;“理”便指以白蛇、青蛇、許仙和法海四個角色所屬的人、妖、神三界所遵循的道德秩序邏輯。
二、小說《青蛇》的顛覆重構
《青蛇》是香港作家李碧華對白蛇傳故事的新編,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不論是從人物形象的塑造、敘事的角度,還是所要表達的文化內涵相較于之前的白蛇傳的傳說故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從角色方面來講,在《青蛇》中李碧華對白蛇的形象做了非常細致的描繪,與傳統視角中的白蛇形象有所不同,作者對白蛇的形象塑造突出其人性和世俗的一面,以現代人的視角帶入白蛇的形象,白蛇已然被塑造成一個擁有獨立意識、自主的現代女性形象。男主角許仙表現出更多的是懦弱、自私和精明。讓兩個女子為了他而爭斗,在與白素貞成親后他還想勾引小青甚至想攜款私奔,小說中也是多次寫道:“整個事件,他獲益良多,卻始終不動聲色”,“他簡直是財色兼收,坐享其成”。通過書名《青蛇》也可以得知,在這部小說中,青蛇成為了主角。她也和以往插科打諢的形象發生很大的變化,她好斗、嫉妒、爭強,卷入與許仙、白蛇、法海的多角戀中。但是作者也并不是只塑造小青的負面性格,她也有善良、無奈的一面,她不小心吃下呂洞賓的七情六欲丸,不得不面對情欲的掙扎,在她認清許仙的真實面目后,選擇將假仁假義的許仙殺害替姐姐報仇。這些傳統的人物被賦予了新的生命,上升到有血有肉的人的層面,在面對各樣的掙扎和困境時,真正的人性凸顯出來,這是對傳統民間故事的一大突破。
小說在敘事上也有獨到之處,在全新的人物形象基礎上,對白蛇故事的原有情節進行再創作,之前的作品都是以白蛇和許仙的愛情故事為核心,《青蛇》沿襲許、白的愛情發展這一線索不變,但是貫穿全文的主要線索變成了小青,變成小青與周邊一系列人物的情感變化。“于傳統的文本中尋找新的生發點,帶動故事情節發展”,這也是李碧華在改編小說時的一種方法,在舊有的人物關系上以青蛇為出發點生成新的人物關系,構成了故事的第二條線。將這些人物關系融合在一個故事中,構成了復雜的四角戀愛糾葛,同時也就揭示出“情”和“理”、“追求”與“背叛”的敘事主題。
小說《青蛇》之所以一直作為人物研究和探討的對象,在不同的層面上都對社會有很大程度的影響,比如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女性的覺醒意識和對女性的人文關懷,抑或是白蛇和青蛇尋求自我主體意識來隱喻當時香港在夾縫生存狀態下迫切尋求身份認同的現實狀況。李碧華在這部作品中有對現實展開不同深淺的嘲弄,從小說一開始充滿戲謔的語言就奠定了文章諷刺的感情基調。《青蛇》這部小說將以往歌頌真摯愛情的唯美傳說故事轉變為人倫愛情的悲劇,將故事本身放置在現代的思維邏輯下成就為另一個全新的故事。李碧華對傳統民間故事的改編給我們啟示,傳統的文化內涵要適當與現代書寫風格同向而行,傳統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生命力,采用后現代的創作手法,兩者相輔相成,成就了《青蛇》獨特的藝術特色和深刻的文化內涵。
三、從文字到影像的多重改編
在電影改編小說的過程中,要考慮故事的可塑性,與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主題相契合的同時也要超越原來的文本,體現電影與小說的不同之處。《青蛇》的改編是香港導演徐克和原著作家李碧華合力完成的,但是不意味著照搬原著的內容,企圖將小說一字不落運用在電影中,或者是選取小說中的片段帶入電影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做法。李碧華的許多小說都被成功改編為電影,如《胭脂扣》《霸王別姬》等電影都是享譽國內外的成功的改編作品,這也得益于李碧華非常熟悉劇本和小說的寫作方法。而相比于小說,電影在視聽語言的基礎上也形成與小說不同的藝術特征,在人物形象、敘事視角和主題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異,同時也是改編成功的因素。
從小說到電影的改編,在新的藝術形式下人物的設計是必然要考慮到觀眾的接受度與電影敘事的契合度,導演在電影創作中將每一個人物都設計成能與觀眾產生“共情”的人物形象,所以我們會發現電影中的人物被進行了某種“修正”。導演削弱了許仙的負面性格,而是使他處于一個游離和猶豫的狀態,他身上也存在人性的弱點,但是不觸及觀眾的道德底線。作為主人公的小青,她是一個以妖的身份來探索未知世界的女性,從小說到電影,青蛇的形象又開始回歸倫理。在電影中她是出于對最喜愛的姐姐的行為模仿而去引誘男人,她和許仙的那次出軌也只停留在精神層面。白蛇告訴她人間有情,她便毫不猶豫去尋找,在電影中青蛇多了一份真實和純真。這些人物形象是契合整個影片的敘事,也是導演在對原著深刻理解下加入自己的解讀得到的,是成功改編電影的基礎。
敘事視角也對電影的成功起著關鍵的作用,電影《青蛇》延承小說中的敘事視角,都采用青蛇作為故事的主角,首先是因為青蛇視角更具與沖突性,其次是青蛇是被動接觸人世的妖,在故事中可以給出這個角色完整的心路歷程,貫穿整個電影的全部,反映出影片關于個人身份定位的追尋。在電影中,徐克將原著中的人物關系和人物情感簡化,并且探討的主題也與小說不同。電影回歸倫理的討論,是對“情理”的一次平衡表達,雖強調情欲但是更加重視秩序和規范。20世紀90年代的香港處于回歸之時身份歸屬的困惑和對未來發展的迷茫之中,在電影結尾對于“我是誰”的追問也隱喻著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們的特殊心理狀態。從文學到電影的改編存在多種可能性,包括對于文學原著的原創尊重以及電影視聽語言的適應性。
四、從文本到舞臺的成功轉譯
田沁鑫作為當下中國極富創造力的戲劇導演,也熱衷于對人們所熟知的“舊故事”進行改編,田沁鑫將改編工作稱為“轉譯”,她曾經說過“我就是做了個讓經典落地的轉譯工作”。然而“轉譯”又包含了三個層面:首先是文本層面的,轉譯是文本的現代化,將傳統文本轉譯為戲劇劇本;其次是形式層面,將在文本上的文字語言轉化為舞臺語言,符合舞臺表演形式;最后是文化層面,轉譯并不是對原著的機械翻譯,而是要注入個體的精神思想,具有現代化的價值觀。田沁鑫導演將小說《青蛇》改編搬演到戲劇舞臺上,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導演對原著中的人物再一次顛覆重構,并且將小說改編成適用于舞臺的劇本,關注原作中人物所處的環境和人物的精神特質,再對原作進行充實和新的挖掘。
話劇《青蛇》在人物塑造上與小說的最大區別是對法海形象的塑造,提升了法海的角色地位,使法海也承擔著串聯整個故事的作用。在現代語境下,導演讓法海跳脫出本身的角色,在舞臺上作為現代人的代言人而存在,完成了對傳統法海形象的顛覆,在話劇中導演在重塑人物形象時也從“斬妖除魔”變為“授業解惑”,使得法海成為大慈大悲的和尚。除此之外,導演還在劇本中加入一個重要的人物,處在法海的對立面的濟著和尚,話劇中青蛇和白蛇初到人世的時候在宋朝的夜場遇見了濟著和尚,是他指引著青、白蛇獲得人的情欲,同時導演將他作為與法海相對立的角色,也從側面使法海的人物形象豐滿起來。在許仙的角色塑造上我們可以感覺到相對于小說電影中的這一個角色,在話劇中更加的負面,導演通過對許仙角色的闡述來探究人性的弱點。對于白蛇和青蛇的性格塑造,導演讓她們兩個的性格對立分明,就仿佛現代社會中的兩類不同女性,白蛇是擔負著家庭責任的中國傳統的女性形象,而小青對人間的一切充滿好奇心和探索欲,觀眾可以從她們的性格中觀照自我。
戲劇《青蛇》之所以能在人們所熟知的故事中脫穎而出,獨特的舞臺敘事策略是關鍵,田沁鑫在《青蛇》中采用“元小說”這一敘事手段。元小說是美國作家威廉·H加斯在其《小說與生活形象》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它主要是指敘述者在小說中超出情節或故事安排,評論小說、人物或敘述手法,元小說手法是一種現代主義的敘述手段。田沁鑫導演將“元小說”敘述手法運用到話劇《青蛇》的舞臺演繹中,通過法海和濟著帶領的一眾僧人不斷地在敘述中插入,法海在話劇一開始便告訴觀眾“故事,純屬虛構,源自中國流傳了六百年之久的民間傳說”,并且在演出中會常跳出所扮演的角色對法海這一角色進行評價,有時候也會作為演員來說話,這些設置導演都在告訴觀眾舞臺表演和故事的虛擬性,使觀眾在保持理性思考的同時感受人物在不同環境狀態下的心理變化。田沁鑫導演在她的導演闡述中說:“……其中的思想意識和人物要用當代意識去觀照、去解釋,我始終這樣做的,即使是排經典戲也要和當代人的思想靈魂去溝通。所謂挖掘,就是對人物、對生活的把握,用當代意識去觀照,不論是劇作內涵、人物性格、生活性格、生活觀念,還是對過去、今天及將來的勾連,對生活狀態的感悟,都是用現代人的方式。”這一直是田沁鑫在創作和改編戲劇時的創作態度和創作策略,屬于她自己獨特的舞臺敘事風格。
五、結語
任何方式的改編都不是通向成功的捷徑,相反在有被大眾熟悉的傳統故事后又有很成功的小說原著,在觀眾的期待視野下可能更難獲得認可。但是從最初的“白蛇傳”這一傳統民間故事之后的一系列嬗變,再到李碧華的小說《青蛇》和同名的電影、話劇等都表明經典作品不會被時代所束縛,經典傳說故事、經典作品之所以能被人傳誦,其永恒性是它可以借助任何藝術形式來與觀眾產生共鳴。這就要求創作者在創作的基礎上,找到與當代社會相連接的現實意義,拉近以往故事和當代觀眾的距離,緊緊把握現實和人生,圍繞一個故事做敘事上的改變和藝術形式上的改變,并且不同的藝術形式在詮釋改編作品時要找到文本與新藝術形式的切入點,更好地展現改編作品的故事主題。這是在改編作品中我們每一個人要進行思考和學習的,在跨文化的改編上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1]王立,劉瑩瑩.試論白蛇傳故事的嬗變[J].遼東學院學報,2005(5).
[2]李碧華.青蛇[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3]盧蕓.李碧華小說研究綜述(2000-2009)[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7(10).
[4]李金平,陳紅玲.議李碧華《青蛇》對傳統題材的改寫[J]. 語文學刊,2011(3).
[5]朱婷婷.從文字到影像:重溫《青蛇》的電影改編特色[J]. 電影文學,2018(14).
[6]閆琨瞥.從文學到電影的多重改編——以《青蛇》為例[J]. 視聽解讀,2019 (10).
[7]田沁鑫.我是經典的轉譯器[N].北京日報,2014-3-14.
[8]朱莜莜.試論田沁鑫劇作中現代藝術觀念和東方美學[D]. 貴州師范大學,2015.
[9]田沁鑫.東方禪意訴說中國文化——《青蛇》導演闡述[J]. 戲劇文學,2013(7).
[10]谷海慧.田沁鑫劇作論——基于文本與舞臺的雙重解讀[J].戲劇藝術,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