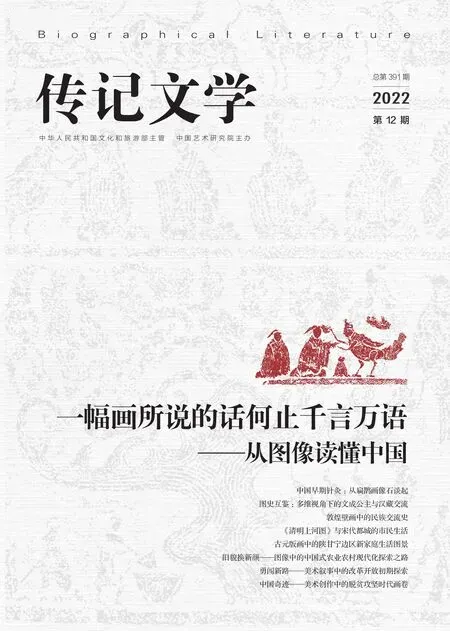一幅畫所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
——從圖像讀懂中國
本刊編輯部
“史料者何?過去人類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跡,有證據傳留至今日者也。”(梁啟超)現代史學將史料分為文本、口述、圖像三大類,其中文本史料占據著核心位置,重量級的史學著作都以占有大量而重要的文本史料作為其優勢和獨特性,相比之下對圖像史料的重要性,學界認識尚不一致,甚至還曾出現過圍繞圖像史料價值發生“可見中的不可見性”的爭論。
其實,作為具有以可見的形式記載人類往昔事件、歷史人物、自然萬物、風俗習慣等事物功能的史料,圖像在古今中外歷史敘述和研究中一直發揮著獨特的作用,圖像史料的物質性的可見視角能夠彌補文字史料所忽視或闕如的缺憾,尤其為歷史細節的生動再現提供了珍貴的證據。中國上古傳說中“河出圖”的記載,代表了人們對于圖像起源和功能的認知,借助圖像,人們得以認識自然宇宙的形象。唐代的張彥遠認為,圖像的功能是“無以見其形,故有畫”,甚至能夠“傳既往之蹤”,圖像兼具文字記錄的功能。宋代的歐陽修認為,圖像可以“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后學”,證經補史,補訂疑誤。鄭樵在考證“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的基礎上,認為“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于世者”,給予圖像以重要的史學價值。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作史者能多求根據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可見的圖像是作史者“目睹之事物”,是史料中“最上乘者”。由此可見,在中國歷代文人知識分子觀念中,圖像具有記錄歷史的功能,甚至能夠彌補或正訂文字所無法完成或謬錄的一些歷史細節。
公元前5 世紀,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在其著作《歷史》中講述了關于著名的里拉琴演奏者阿里翁逃脫船上水手的蓄意謀殺,投入大海,被一條喜歡音樂的海豚從海中救起的歷史故事。最初這個故事是希羅多德從科林斯人和雷斯波島人那里聽來的,后來希羅多德在特納魯神廟看到出土于雅典衛城的一個騎著海豚的青銅男像,這個歷史故事得到了實證。西方有學者根據貝葉掛毯《國王哈羅德在哈斯廷斯戰役中陣亡》(約1100 年)上敘事的故事細節,認為英國國王哈羅德因眼睛中箭而陣亡。18 世紀中葉,有批評家說,如果有更多的畫家創作像約瑟夫·韋爾內的法國海港畫一樣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將造福于后代,因為“從他們的繪畫中有可能讀到行為舉止的歷史,還可以讀到藝術史和民族史”。瑞士藝術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認為圖像和歷史遺跡是“人類精神過去各個發展階段的見證”,通過對圖像等史料的解讀,才有可能解讀特定時代思想的結構及其表象。
圖像是可見的歷史,但圖像的價值和意義并不局限于此,圖像還具有藝術性,具有審美功能和敘述性。今天的圖像學或圖像研究這兩個術語,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在藝術史學界運用。德國藝術史家歐文·潘諾夫斯基將圖像的解釋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前圖像學的描述,主要關注于繪畫的“自然意義”,并由可識別出來的物品和事件構成;第二個層次是嚴格意義上的圖像學分析,主要關注于“常規意義”;第三個層次是圖像研究的解釋,關注“本質意義”,揭示圖像中“決定一個民族、時代、階級、宗教或哲學傾向基本態度的那些根本原則”。圖像研究的第三個層次可稱為圖像文化闡釋學,解讀圖像所隱含的文化思想內涵。圖像的可見的形式是有限的,但圖像所敘述的故事往往會超越有限的形式,蘊含豐富的、生動的、多元的思想,藝術地呈現漫長歷史時間里發生的多重復雜的歷史故事,所以,圖像又被稱作“可視的敘事史”。可視的圖像是無言的見證者,更是能說會道的“講故事的人”,一幅畫所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
我刊2022 年第12 期推出封面專題“一幅畫所說的話何止千言萬語——從圖像讀懂中國”,邀請重慶大學藝術學院郝斌等八位學者,選取漢代畫像石《扁鵲行醫圖》、《步輦圖》、關于文成公主的西藏壁畫、敦煌壁畫、《清明上河圖》、20 世紀40 年代古元系列版畫、關于改革開放和新時代脫貧攻堅的國家主題性美術作品若干幅,這些圖像作品涵括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各個方面,記述了中華文化發展史、中華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百姓日常生活史、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發展史、改革開放史、新時代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史,通過對這些圖像作品的創作時間、時代背景、敘述的故事及其思想文化內涵以及影響等諸方面進行細致的梳理和研究,力圖以可見的圖像的形式敘述從春秋到當下的跨越2000 多年的中國社會發展簡史。
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的故事是真實的,屬于史學范疇;但講述故事的技巧是藝術的,屬于藝術史范疇。以可見的中國歷代歷史、社會、文化圖像,藝術地講述中國故事,既能直觀歷史的細節,讀懂圖像深層的思想內涵,又能欣賞藝術的魅力,這必定是講故事的“最上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