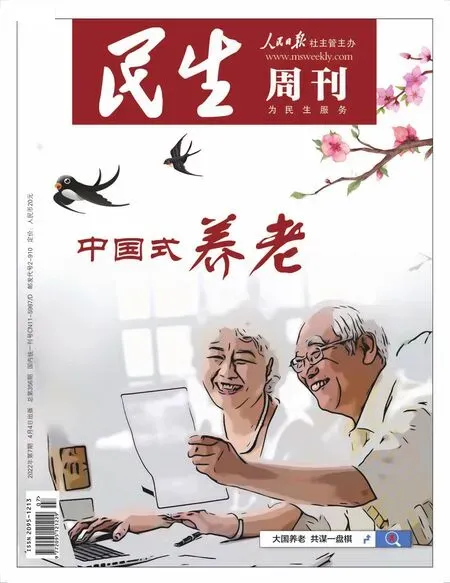全民健身公共服務升級正當時
□ 《民生周刊》記者 王迪
仲春傍晚,夕陽斜照,在一片鳥語花香中,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健身步道上,人來人往。良好的生態環境,使這里成為京城跑友們活動的集散地,跑步和散步是人們的主要健身方式。步道一側,每隔一段距離,都設有提示“運動距離”和“步數提醒”的智能電子屏。
家住附近小區的健身達人王漫,從服務站換好健身服后,正做著熱身運動,她準備待身體適應后,再按照預設的行程出發。
“全園皆有步道,而且基本都是塑膠顆粒鋪就;全線設備齊全,休息站、路程標志規劃合理。”王漫告訴《民生周刊》記者,她幾乎每天都會來這里“打卡”。“環境美、空氣好,步道也專業,走在上面就像踩在海綿墊上,十分有彈性,跑起來更有種身輕如燕的感覺!”言語中,王漫透露出對戶外步道的偏愛。
作為國家全民健身示范基地,北京奧林匹克公園是我國構建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一個縮影。如今,伴隨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圓滿落幕,群眾對健身的熱情又一次被點燃,全民健身再次被推上熱潮。
家門口健身
全民健身公共服務,即面向全體人民,以公益性和基礎性為導向,滿足群眾體育健身和運動休閑需求的場地設施、賽事活動、健身指導等產品和服務。
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構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體系,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2.6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比例達到38.5%。
如何實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場地設施是基礎,也是關鍵。
數據顯示,到2020年底,我國人均體育場地面積為2.2平方米,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比例達37.2%。目前來看,與實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務目標,還有一定差距。
對此,《意見》指出,“構建多層級健身設施網絡和城市社區15分鐘健身圈”,規定“新建居住區和社區要按室內人均建筑面積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的標準配建健身設施,納入施工圖紙審查,驗收未達標不得交付使用”。
隨著參與全民健身的群眾逐年增多,修建群眾身邊的健身設施,成為各地體育部門的重要工作之一。
以北京市為例,今年2月印發《北京市全民健身場地設施建設補短板五年行動計劃(2021年—2025年)》,提出到2025年,全市人均體育場地面積達到2.82平方米以上,新建社會足球場地380塊,新建或改擴建體育公園32個,新建或改擴建全民健身中心(小型體育綜合體)20個,新增公共體育用地面積287.27公頃。
家住北京西城區的李大爺,以前很少鍛煉。自從去年底,西城區圍繞南護城河修建的8 公里濱水健走步道亮相后,日行10000步,成了李大爺每天的“必修課”。
除了打造群眾身邊的體育生態圈,《意見》還提出,積極拓展全民健身新空間。《意見》強調,我國將推進體育公園建設,推動體育公園向公眾免費開放。在現有郊野公園、城市公園中因地制宜配建一定比例的健身設施。
接下來,我國將制定國家步道體系建設總體方案和建設指南。未來,國家步道將穿越山地森林、河流峽谷、草地荒漠等自然地貌或歷史文化遺址,讓人們在健身的同時還能感受人文之美。
支持學校體育場向公眾開放
“家附近學校的足球場,節假日能進嗎?”“一些事業單位和國企都有自己的健身房,可以對外開放嗎?”
基于以上問題,《意見》給出明確回復,要推動現有的健身場地全面開放共享。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要帶頭開放可用于健身的空間,做到能開盡開。已建成且有條件的學校要進行“一場兩門、早晚兩開”體育設施安全隔離改造。
然而,記者了解到,盡管國家體育總局就推廣體育場館向公眾開放的相關政策已經推行10 多年,但目前很多學校的體育場館向公眾開放的進程仍推進緩慢。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中小學體育場館在數量上比較多,體育條件和體育設施方面也相對完善,而學校對體育場館的利用都是有時間性的,“在特定的時間,對體育場館的使用可能還不夠充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向公眾開放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儲朝暉同時指出,學校體育場館向學生開放與向社會開放,管理成本是完全不一樣的,向社會開放時,會涉及一系列的管理問題,包括設施維護、秩序維持、治安管理等。

隨著2022年冬奧會的成功舉辦,北京迎來全民健身熱潮。圖/王迪
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的公益性,能實現嗎?溫州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教授易劍東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全民健身經費有公益屬性,要滿足基本的全民健身服務需求,而具體到個人,或者說更高端的運動,恐怕要有一定的付費,但是文件中也提到要可支付。
國務院2009年頒布的《全民健身條例》,就已經提到了全民健身的經費,尤其是公共體育設施建設經費要納入本級財政,每年都要進行專項檢查,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有所增長。
“另外體育彩票的公益金,每年5%會給到體育部門,中央和地方各一半,各地體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也有嚴格規定,60%以上都必須用于全民健身。這些年,體育總局甚至將90%的體育彩票公益金投入到全民健身,這應該也是全民健身經費的一個重要保障。”
易劍東提到,近兩年,國家相關部門對場館開放也進行了補貼,比如像浙江大學、溫州大學等學校,平時向市民開放體育場地設施,政府也會給予補貼。
此外,有專家認為,在國家層面上,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已有政策依據,但并非法律上的義務,亟須將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納入法律規范,才能依法推進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開放。這樣既能促進學校體育設施資源充分利用,又能給學校帶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