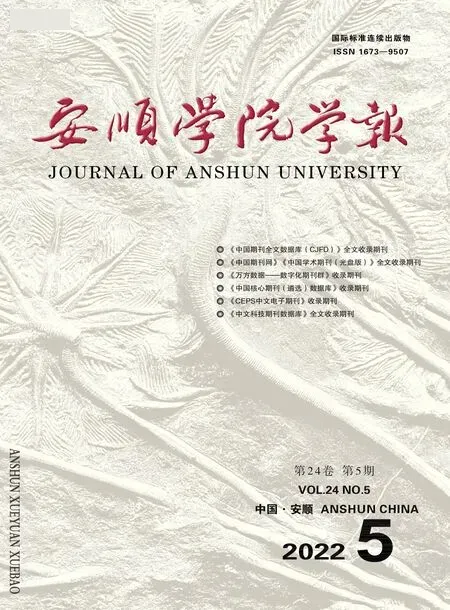形式作為網絡
——卡洛琳·列維尼的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
劉霖杰 李作霖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文學批評中的“形式”,通常是指文學作品的類型、小說的語言風格、詩歌的韻律等決定一部作品賴以生成與構建起來的原則。新批評將其視為文學作品所內在的“文學性”,新歷史主義對社會歷史材料的關注又使得文學形式淡出其研究范圍,而20世紀80年代末期,新形式主義作為對新歷史主義的反撥而出現,這一新興的形式主義研究方法反對空泛強調歷史,將失落已久的形式主義傳統重新帶回到文學批評理論的視野當中。
美國文學批評理論家卡洛琳·列維尼(Caroline Levine)通過將新批評的細讀方法與新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糅合在一起,提出自己的新形式主義理論方法,將形式視為一種跨時空運作的網絡,她將這一套理論方法稱之為“戰略形式主義”[1](Strategic Formalism)。在這一形式網絡中,當不同形式產生接觸時,將會激活其所蘊含的“功能可供性”(Affordances),表明形式這一存在能夠為主體提供各種行為可能性[2],從而產生不可預見的效果與影響。并且,在卡洛琳·列維尼的這一新形式主義網絡中,形式呈現出分散或分布式的非主權運作模式,使得在形式網絡的運作中,沒有一種形式可以主導其他形式。同時,這一形式網絡是動態而非靜態的,動態的形式網絡不僅強調網絡中的形式節點是互通互聯的,而且強調這些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
代表卡洛琳·列維尼這一觀點的著作《諸形式:整體、韻、等級制、網絡》(Forms:Whole, Rhythm, Hierarchy, Network)在2015年出版,而新形式主義這一名詞是在1989年12月的現代語言協會特別會議的標題中得來,即“邁向新形式主義:文藝復興時期新歷史主義和女權主義形式主義方法”,這一名稱由學者希瑟·杜布羅(Heather Dubrow)提出[3]。新形式主義對于形式閱讀的強調以及社會歷史的關注,使得形式主義方法再次重回文學批評學界的關注視野中。
一、從新批評到新形式主義
新批評作為舊形式主義中的一個主要流派,在“二戰”之后幾乎主宰著美國的文學批評學界,它不僅將文本與它們的文化母體隔離開來,而且還將共時存在的文本彼此隔離開來,將文本解讀為獨立的、統一的實體。雖然新批評中,也有像威廉·燕卜遜這樣關注文化和政治分析的學者,但是在大部分時間里,對于文本本身的關注仍然大于對于社會文化的關注。1971年,解構主義者保羅·德曼對新批評做出強烈批評,他認為過度關注文本會給文本帶來一種虛假的整體性,而忽略文本之間存在的斷裂。而福柯的譜系學研究對于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進作用,使得文學研究朝著政治歷史方面轉向[4]。在這些受到福柯譜系學影響的文學批評流派中,新歷史主義尤為明顯,其研究轉為從文本外部角度來研究文學。隨著新歷史主義在文學批評界地位的不斷提升,文學批評由對文本本身的研究轉向其背后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研究。
到了“后理論”時期,理論的失敗[5]似乎宣告著傳統經典理論已無遵循的必要,但是“后理論”并不意味著不再發展理論,而是需要在理論與文學批評實操之間建立起良好的銜接,而非將二者逐漸分離。伊格爾頓將“后理論”這一階段解釋為理論發展“黃金時期”的消逝[6],理論在這一階段中,仍然作為指導學者的重要工具而存在,并且理論的發展與轉向仍在進行,在后理論的轉向中,對于文學性的重新關注是最為突出的方向。
伊格爾頓認為文學批評實際上和政治批評離不開關系[7],在2007年出版的《如何讀詩》中,伊格爾頓提出“形式不是對歷史的干擾,而是進入歷史的一種方式[8]”,開始表現出其將形式分析融入其政治批評當中的趨勢,對于文本形式的關注重新回到伊格爾頓的視野當中。無獨有偶,1998年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一場研究文學領域邊界的論戰中承認,“恢復我自己的文學訓練中的嚴密的形式主義”對于他來說是十分必要的[9]。學界呼喚著形式主義研究的回歸,于是新形式主義帶著對于文學形式與社會歷史的雙重關注,來到文學批評的視野中。
撰寫《網絡美學》(Network Aesthetics)的帕特里克·賈戈達(Patrick Jagoda)在該書中不僅談到新形式主義與網絡美學之間的共同之處,同時還贊同新形式主義所作出的改變,同時賈戈達也進一步提出,對形式的關注不僅可以在文學批評領域內存在,同時也可以在美學、社會、文化等多維領域存在,以網絡美學,即非中心性的、發散性的方式來對待多維度領域的形式研究,頗具啟發意義[10]17-18。因此,網絡美學與新形式主義的協同運作,意味著這種網絡分析以多義的、網絡化的方式來看待各領域中所存在的形式,這可以減少分析上的封閉、對待歷史的草率以及對社會政治的排斥,使得形式研究變得開放且可擴展。
在《諸形式》的序言中,卡洛琳·列維尼提到,自己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福柯譜系學的影響,福柯把文學置入到一個時代的知識體系中,并從微觀話語體系的角度詳加考察,而列維尼利用“網絡”將新形式主義研究帶入到了一個新領域,在這一大量形式構建的網絡中,文學作為網絡其中一個節點,與大量同時運行的形式節點發生接觸,并因此產生各類影響。但不同的是,福柯在這一考察過程中忽略了文學的審美特性,即忽略了文學的形式,在新形式主義的研究中,對于文學本身的形式已經得到重拾。同時,列維尼的新形式主義網絡對于文學作品的分析,不僅僅包括形式本身,還包括不少非文學的形式,這使得她的新形式主義研究,或者說,戰略形式主義研究邁入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中。
二、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
(一)作為格式塔的網絡
卡洛琳·列維尼在作品中談到新形式主義需要對文學研究進行格式塔轉變,它要求對政治和政治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新的解釋[11]16。不以等級制的方式來看待政治與社會抑或是與文學的關系,而是轉變這一思考模式,以網絡的方式來加以看待。
新形式主義的網絡分析作為趨向于格式塔轉變的文學研究,需要對文學形式與非文學形式的“接受”與“拒絕”形成一套新的范疇。借助這一格式塔的新形式主義網絡,形式主義研究可以同時把握社會歷史和文學性這兩種形式。卡洛琳·列維尼發展出一種新式的細讀方法,她將其稱為“社會細讀”,這一閱讀策略能夠發現不同形式在文本以及社會之間的網絡式的相互流動。由于功能可供性的存在,文學研究的格式塔轉變才有了可能性,社會歷史的形式可以走入文學,反之,文學的形式也可以對社會歷史造成影響。《諸形式》中提供過葛莉·薇思瓦納珊(Gauri Viswanathan)關于英國批評家通過批評印度史詩來達成文化殖民目的的案例[11]58。
當時的英國政府需要一種特殊的方法,來使得印度民眾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利用基督教傳播可能會引發民眾的激烈反抗。于是,通過對《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等印度史詩著作的系統性批評,英國批評家促使印度青年人將梵語文學看作是“落后”與“墮落”的象征。例如,《摩訶婆羅多》中朵帕娣與五個男人結婚的記錄,這通常會引起讀者的道德反感,而這一史詩將其視為拉克希米女神與她的妃子毗濕奴的象征性結合,試圖賦予多妻制以神圣性,諷刺的是,當朵帕娣的這一事跡在《摩訶婆羅多》中被寓言化時,這些社會習俗獲得了一種神圣性,使讀者無法區分道德行為和不道德行為。于是,英國評論家從中找到突破口,將《摩訶婆羅多》描述為婆羅門階層的腐朽文化之體現,來撬動印度的社會文化政治[12]124-125。
在這一過程中,印度史詩這一形式被視為一種被編碼的信息,而印度文化可以這一信息來為個體提供信仰和行為模式的傳承,批評家對于印度史詩的批判,相當于切斷了“史詩-文化-教化”這一循環過程,從而通過對印度史詩這一“小形式”的批判來完成對印度傳統文化認同乃至社會政治等一系列“大形式”的翻轉,印度政治與印度史詩成為一個系統中所聯結的形式節點,對史詩形式的批判轉入到對印度社會文化形式的批判上,完成格式塔的轉變,印度青年對本土文化的認可被削弱,從而為英國的殖民統治鋪平道路。
同時,英國殖民政府將英國人撰寫的大量歷史著作作為印度學校和學院文學課程的一部分來教授,歷史學說被改造成了在非文學的基礎上對神話的重塑,通過這一重塑,印度社會的不和諧現象被逼到了明處。英國批評家們發現,只要印度青年沒有歷史意識,他們就能一直被束縛在殖民政府的統治下。這一措施的影響對于印度來說極其深遠,例如,直到1919年,加爾各答大學委員會仍將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列為規定學習課程的一部分[12]128。
通過對文學作品形式的功能可供性的充分利用,英國殖民政府將印度文學作品拉入到“落后”的政治范疇內,而這些制度化的文學課程在印度一直得到存續,將代表“先進”文化的英語作品不斷輸入到印度民眾的精神世界中,來完成用文學來撬動社會歷史文化這一目的。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文學作品與印度意識形態處于相互交織的并行狀態,梵語文學將傳統印度文化置于“落后”的體系中,而把持著英語文學話語權的殖民政府,使得印度民眾將英語文學視為先進文化的代表,從而系統地瓦解印度傳統意識形態。在列維尼看來,當文學或是社會歷史政治這一詞被提及的時候,它們并不是被孤立提及的,而是處于一個形式網絡中,其中一個節點被觸及的時候,其波動會傳導到與之相聯系的形式節點上。
因此,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逐漸重拾起被福柯以及新歷史主義忽略的文學審美特性,使得文學形式與非文學形式不再呈模糊狀態,而是相互平等、有機聯系的關系。
(二)形式網絡中的競爭與碰撞
形式網絡作為一種非主權結構,由復雜多樣且相互連接的形式“節點”組成,形式之間相互施加影響自身影響,并產生競爭,沒有一種形式節點可以在形式網絡中取得主導地位。在對形式進行網絡分析時,卡洛琳·列維尼借鑒了帕特里克·賈戈達的網絡美學以及不同網絡理論研究者的成果,并對此進行延伸,最能體現形式網絡的碰撞與競爭的是《諸形式》中分析電視劇《火線》的例子。
《火線》將一百多個角色以多種復雜的順序交織在一起,相互重疊和重塑,沒有一個單一的互聯原則將彼此聯系起來,它將看似疏遠或互不相關的人物通過形式網絡聯結。因此,列維尼認為《火線》可以使得我們改變對閱讀形式的慣性思維,從看似占據主導地位的形式上脫離,轉而關注大量的社會形式相遇所產生的奇異無序[11]132-133,社會是形式網絡關聯的結果,而非其原因。
在該電視劇的第三季中,區長官霍華德·考文在巴爾的摩私自劃分出一塊新區域,名為“漢姆斯特丹”,在這塊區域內,毒品交易以及其他犯罪行為被“合法化”,不受警察干擾,同時也允許公共衛生組織在此展開衛生服務,大量形式在此相遇。市長嘗試關閉這些非法區域,但由于在這方面工作上的不及時而導致他在選舉中失敗,使得卡瑟提成為了巴爾的摩市乃至整個馬里蘭州的領導人。從通常的角度出發可能會認為,大的形式定義了小的形式,即區長官作為政治形式的領導者,定義了“漢姆斯特丹”這一小的區域形式。實際上,“漢姆斯特丹”的存在極大改變了巴爾的摩乃至馬里蘭州的權力網絡,在這一形式網絡中,次要形式對主要形式產生競爭并影響后者。這三個區域形式在網絡中看似是相一致的,但并非為同一目的而相互協調。
另外,《火線》中內蒙德·布瑞斯是劇中少數得到圓滿結局的角色之一,這位少年的父親為了組織的利益自愿接受終身監禁,讓內蒙德受到保護。當毒販組織失去自己的地盤后,內蒙德被趕回街頭重操舊業,但是一位退休的警官注意到了他,并為他提供庇護地。內蒙德之所以能取得較好的結局,就在于他處在兩個空間形式的碰撞之處——學校與領養他的家庭。學校與家庭兩個形式的碰撞與競爭為內蒙德爭取到了自由空間,在這一空間中他能夠得到保護,不必受到其他形式的主導,免于淪為與同齡人一道[11]137-138。
從這一層面上考慮,《火線》并沒有產生一個預設社會類型的穩定網絡,而是展示了一個不對稱的無組織系統[10]111。在這個系統中,普通人的生活不是由統一的開頭和明確的結尾組成的,而是由大量碰撞競爭的形式捆綁在中間部分。《火線》通過跟蹤演員和他們隨著時間推移形成的動態網絡聯系,將鏡頭焦點集中于這種復雜網絡上,傳遞一種網絡審美。這一網絡式審美的關鍵在于,在形式網絡中,無處不在的碰撞與競爭使得看似穩固的等級制崩離,在其中,沒有一種形式能夠長期占據同一個位置,也沒有地方會空置,即便是貫徹《火線》全劇的官僚形式,都沒有作為單一且明確的獨立形式出現。
而卡洛琳·列維尼引述《火線》的用意在于,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對于理解形式碰撞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通過引入新形式,使得新舊形式對立碰撞,從而為一種新的社會實踐創造存在的可能性。意識到形式的重疊與沖突,形式網絡可以向我們展示,“系統”并不是一個有組織或強行整合的單一結構,而是不同有限整體、等級制度和網絡的堆砌組合。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所展現的文本與社會,是一個不斷被形式碰撞帶來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影響所擾亂的社會世界,在這一世界中,迎來的并非是福山式的“歷史的終結”,通過對形式碰撞的追蹤,可以為“對不公平的轉變”創造機會,創造新的可能的社會實踐。
(三)形式網絡的動態運行
形式網絡是動態運行著的,這就意味著這一網絡除了在空間內延伸運作外,還在跨時間的維度上運行。無論其形式節點組成如何,形式網絡從來都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10]8。在該網絡中,不同時空的形式相遇時會激活其內部的功能可供性,因其自身的物質性而發揮出超出本體的作用,并且從歷史上看,形式的互動是動態的,當它們相遇時,往往會產生一種激進的改變和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差異。
《英國童話》作為約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在1890年編撰的英國民間童話故事集,在其出版后就受到英國大量讀者和批評家的歡迎。雅各布斯向英國讀者介紹說,他認為《英國童話》是英國人民應有的文化遺產,并且聲稱格林兄弟編撰的德國童話中所蘊含的德國文化傳統形式對英國的影響過大,有可能會抹殺英國本土的文化傳統。于是,雅各布斯開始收集英國民間童話故事并對其進行編輯,以便英國兒童能夠吸收他們的民族遺產。實際上,這是對民族認同缺席所作出的補償,是在英國民族已經吸收了德國《格林童話》的文化財富形式之后才出現的。
《格林童話》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在與英國的民族認同遭遇時,它調動了多個形式之間的微妙關系,該童話作為不同地域的形式,在得到英國民眾的接受后,在這一英國民族文化這一網絡中占據著短暫的位置,當其與倡導英國傳統文化的意識相遇,網絡將《格林童話》與其德國文化出身聯系起來,激發出英國文化形式的抵抗性。在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這一視閾下,《格林童話》試圖實現對英國傳統民間文學的“代位”(surrogation),而英國民間文學這種形式在時間維度上來看一直是穩定存在著的,只不過尚未得到集結出版,而這一穩定意味著該民間文學形式需要反復重現的規則和實踐來構成[11]58,在維持民間文學這一形式穩定的過程中,許多民間作者積極地再現了英國民間文學的規則和實踐,以此來重復這一文學形式的本身。
在《格林童話》嘗試代位時,它并非是對這一規則和實踐的重現,無法再現英國民間文學這一形式本身,而英國民間文學并沒有消失,在網絡中因不同地域的《格林童話》的進入而與之產生聯系,對《格林童話》所施加的秩序進行抵抗。英國民間文學作為一種古老的文學形式,在與德國《格林童話》的聯系中實現了其形式的重復,這一重復并不是民間文學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簡單復制并重現這些民間故事,而是通過這一重復獲得了新的位置,使其與雅各布斯“利用英國傳統民間故事實現民族團結”形成呼應,并重申其特定的重復模式,與《格林童話》區分開來。雅各布斯的《英國童話》保留了各種形式,這些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重復,英國民間故事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穩定性。沒有這些重復,《英國童話》將不再是可識別的民間故事,而沒有《英國童話》這一集合的形式,英國民間故事將無法通過網絡對英國民眾身體、話語施加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雅各布斯本人實際上并不是在英國出生或長大的,他是一個在澳大利亞出生的猶太人,后來定居在美國,在那里他獲得了公民身份,并成為猶太歷史專家,這些事實雅各布斯并沒有試圖加以隱瞞。在《英國童話》的前言中,他愜意地談到他如何收錄了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的故事[13]。雅各布斯還聲明,他對每個故事都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和編輯。那么,根據文學研究的通常規范,可以將這本英國童話集稱為“英國童話”“澳大利亞童話”甚至是“美國童話”。而事實上,《英國童話》承載著大量不同時空的形式,成為形式網絡中形式所集結的“終端”,這一終端并非停留在一定時間空間范圍內,而是在時空維度上延伸,感知著不同時空的形式并在當下生產新的形式,突破了線性的時空,轉向形式網絡。
而新形式主義的這一網絡分析,不是作為一種重新激發我們對文學力量的興趣的方式,而是作為一種閱讀世界的方法[14]。通過擴大對于形式的定義,這一分析方法的使用范圍更為廣泛,來表明非文學的形式本身也是對世界施加秩序的嘗試,在形式的網絡中,社會、文化、政治和文學形式相互摩擦,同時運作但不一致。
三、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的運用
列維尼在《諸形式》中對文學以及新媒介的研究局限于維多利亞時代文學與單一的電視劇《火線》上,因此使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的實際作用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束縛。不過,可以通過這一方法來對網絡百科全書的發展進行有效且深入的考察,在此以微軟百科全書“Encarta”為例來進行分析。
微軟百科全書“Encarta”誕生于1993年,該百科全書在開發初始階段時設想為文字版的百科全書添加更多的插圖、音視頻資料等多媒體形式,為用戶提供紙質百科全書從未擁有過的信息量。進入微軟百科全書主程序時可以發現,每一個選項都有對應的圖標,并且其初始界面是一個介紹性的引導界面,為用戶介紹該如何使用百科全書。計算機以及網絡等新媒介的出現似乎為百科全書帶來了新的可能,微軟百科全書以紙質媒介難以企及的方式整合大量音視頻數據以及過往歷史資料,似乎通過堆積新媒介形式的數量,電子百科全書就可以創造出整合人類整體知識的媒介,從而擺脫紙質媒介的局限性。
在這一百科全書中,新媒介形式占據了程序窗口中的大部分內容,而文本信息被挪到了窗口的右側,這使得在同一個窗口中能看到多種不兼容的媒介形式。文本形式與音視頻等新媒介形式,后者作為麥克盧漢所提到的熱媒介的代表,從視覺上來看待文本形式與視頻形式,視頻形式會是一種充滿數據的狀態[15],將自身視為文本形式的替代物而試圖為用戶提供豐富的信息。在微軟百科全書這一大量新舊媒介形式組織成的網絡中,形式之間發生著強烈的競爭,圖像與視頻的存在允許用戶按照媒介形式的類型來進行搜索,在這種情況下,新媒介形式被視為百科全書中的一般知識,而文字形式似乎成為一種定位略顯奇異的特殊知識。
百科全書簡單地使大量媒介形式混合在一個窗口中并沒有使其有機結合起來。音視頻形式對文字形式的否定,對于百科全書來說是破壞性的,微軟百科全書的界面被不同的媒介形式分割為多個部分,而這些形式都是在討論同一個內容。總的來說,微軟百科全書在初期無法使得文字形式成為信息組織的一部分,削弱了百科全書信息記載的整體性,弱化了信息搜索的便捷性。
而從后續百科全書的發展來看,可以通過新形式主義網絡分析來發現“理清多種競爭形式之間關系”的重要性,以及捕捉古老的文本形式是如何重歸百科全書的中心位置的。維基百科作為電子百科全書的一種,它轉而將文字形式放置在網頁窗口的突出位置,多種媒體形式來到了窗口的邊緣位置。從微軟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表面上后者放棄了混合多種競爭的媒體形式的嘗試,但實際上,維基百科以社區和不同用戶為基礎的條目寫作和編輯,超越了舊式百科全書整合人類知識的夢想,而百科全書不再是基于超越特定媒體限制的理想化的知識模型,而是轉向了對媒介和知識使用的強調[16]。并且,維基百科社區的媒介并不依賴于新媒體形式的倍增,而是依賴于文本形式本身的性質,視頻、音頻、超鏈接等多種媒介形式不是簡單地放入到網頁中,而是通過接受寫作媒介的性質和限制而使之成為可能的用途,進入到維基百科的某一詞條中,視頻圖像資料等形式被精心編排,并從屬于位于中心位置的文字形式,在這一轉變下,多媒體形式的引用是受到文字形式的引導,從而在復雜的形式網絡中盡可能減少大量競爭形式之間的沖突與碰撞。
多種形式的有機組合,使得維基百科這一網絡電子百科全書走出“多媒體百科全書”的限制,這種知識組織呈現出網絡化的形態,并且允許用戶不斷對其作出修改,以便更新其中的各種文字及新媒介形式,文字與非文字形式在其中實現格式塔的有機整合,形式之間的競爭通過對文字形式的強調而形成一定的平衡,在維基百科中,沒有一種形式占據著主導地位,而非微軟百科全書那樣人為賦予多媒體形式主導地位而導致形式網絡平衡的撕裂。而且,在微軟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這一網絡化的轉變過程中,電子百科全書從其他媒介向以文本搜索為中心的功能的演變,是對這些電子文檔的文本性、書面性等傳統印刷媒介形式的重新接納。這些傳統形式在維基百科的發展歷程中得到重復,從過去的時間維度中抽出,在新的形式網絡中發揮著作用。
結 語
卡洛琳·列維尼在新形式主義所能運用的領域上顯得保守之外,她對形式主義發展所作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首先,她擴展了對于形式的定義,使得文本特征、理論概念、社會政治和文化形象可以并列在一個網絡上,認識到多種社會形式和文本形式的相互作用。其次,在吸收新形式主義前輩的理論以及福柯譜系法的基礎上,列維尼引入當下較為熱門的網絡理論來對新形式主義的研究范疇進行拓展,用網絡來組織文學以及非文學形式的研究,雖然她目前并沒有充分消化網絡理論,但是這一拓展為新形式主義注入了時代的新活力,帶來了不同學科的交叉分析。最后,卡洛琳·列維尼對形式的擴展定義,為分析文學文本以及社會結構開發一種更細微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