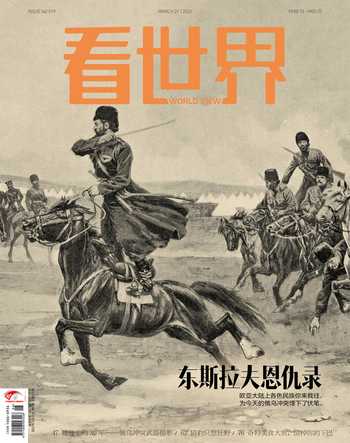冰雪運動:在美華裔“爬藤”捷徑?
徐芳

2022年2月6日,美國選手陳楷雯在北京冬奧會的花樣滑冰比賽中
這屆北京冬奧會上,華裔運動員大放異彩。尤其是花樣滑冰項目,在連續兩屆冬奧會代表美國參加單人比賽的6名選手中,5名是華裔:陳楷雯、陳巍、劉美賢、周知方和卓特蘭。
這讓外媒發文感慨,不到人口比例7%的亞裔美國人,“撐起了美國花樣滑冰半邊天”。
眼光投到更廣的冰雪運動,名單就更長了,譬如谷愛凌、朱易等。
很多家長,尤其是想走精英教育路線的家長們心動了,要不要讓孩子走冰雪運動的路線?
近段時間在美國,為孩子選擇冰雪運動(尤其是花樣滑冰)的華人家庭越來越多。這既是因為花樣滑冰等冰雪項目小眾,適合“爬藤”,也是因為這些項目更適合東方人的身體條件,受傷概率小。
所有這些華二代,幾乎都能跟美國的名校掛上鉤:谷愛凌去了斯坦福,陳巍是耶魯,陳楷雯是康奈爾,周知方是布朗大學……
基于美國大學獨特的篩選機制,“爬藤”是很多華人家庭走向精英教育的必經之路。標準化考試和競爭太激烈了,而小眾體育門檻高,能把很大一部分天賦好的競爭對手,擋在門外。
小眾是成本高昂的代名詞。但相比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亞裔家庭愿意為孩子教育和成功,付出更大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批涌現的華二代孩子的父母,多數是1980年代到北美的華人。他們大多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的留學生,屬于尖子中的尖子,起點比普通美國人要高得多。只有他們,既有財力,也有眼光和資源,帶著孩子走上這條代價高昂的小路。
另外,從身體條件和項目特點來看,像花樣滑冰這樣的個人項目,也是小眾體育中的優選。原因在于,個人而非團隊項目是“雞娃”的捷徑,家長和孩子可以無限量投入時間和精力,自行決定請私教、變換項目和賽道,風險可控。
團隊運動就很不一樣。譬如打冰球,需要一個好俱樂部、好的球隊、好隊友和好教練,才能把你送上競技的巔峰,不可控因素太多了,尤其基于北美的種族和文化差異。所以,早期的華人移民家庭,很多都選擇像滑冰、滑雪這樣的小眾個人項目。
身體條件上,一些需要極好的爆發力和耐力的項目,像田徑、游泳等,華人沒有任何優勢,只能放棄掉。團體球類運動,像籃球、足球和美式橄欖球等,東方人身材偏弱勢,也只能放棄。
因此,冰雪運動尤其是花樣滑冰,就成為華人的不二選擇,尤其是在科技人才扎堆的加州。
但“冰娃”和“冰媽”之路能否復制?
個人而非團隊項目是“雞娃”的捷徑,家長和孩子可以無限量投入時間和精力。

我們也是多年前因兒子在美國開始打冰球,才了解盛行于美歐的冰雪運動的一些內情。
總體來說,精英體育路徑,是一條代價高昂的成才路徑,需要極高的時間和金錢投入。首先,冰雪項目對硬件要求很高。我們之前住在布法羅,當地經濟雖然不咋地,但冰場資源很豐富。一個十來萬人的小鎮,就有一個很大的冰雪館,里面有十來個冰場。
冰雪館的價格便宜,分居民價格和非居民價格,本鎮居民價格減半。像溜冰場,一次溜3小時,只需要5美元。
后來我們搬到加拿大,發現冰雪運動條件也是相當不錯。譬如每年冬季,市政部門都會在我家后院邊上的公園,建一個滑冰場。周圍百來戶人家,每天都可以像在自己家的私有滑冰場里一樣去玩。
在旁邊的森林里,有人自建了簡單的滑雪道,坡道共長幾百米,還用土堆、木板等搭起了跳臺,像模像樣。大家從山上沖到山下,在樹林里飛速穿梭。不少青少年就是在這些地方,開始了自己的冰雪歷程。
所以,走冰雪運動路線,既需要家長砸錢砸時間,也需要整個社會投入。滑冰館算是簡單的投入,更難和更復雜的是滑雪場,還有其他各種高難度的冰上運動場,更是燒錢的項目。
這也是為何歐美國家和日韓更熱衷于玩這類運動。除了地理條件,普及程度和國家的富裕程度也息息相關。
在美國培養一個“冰童”,每年開銷不下于6萬~8萬美元。

2022年3月5日,加拿大渥太華,市民在里多運河滑冰場滑冰
并且,家庭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有媒體測算過,在美國培養一個“冰童”,每年開銷不下于6萬~8萬美元。美國中產的收入區間是4萬~12萬美元(2018年)。也就是說,一個中產家庭不吃不喝,一年也就剛好培養一個“冰童”。
就像這次冬奧會的明星們里,谷愛凌的家庭背景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像傳聞中“窮到交不起訓練費”的陳巍,其父親也是高科技人才,且有自己的創業企業,條件比一般美國家庭要好很多。

冰球一身入門級的裝備,至少要人民幣上萬元
只有這樣的家庭,才能持續上十年,支付巨額的裝備、訓練等費用。
具體來說,錢都花在哪呢?
還是以我們了解的冰球為例,一身入門級的裝備,包括衣服、護甲、冰鞋、球棍、手套、頭盔等,最少就要人民幣上萬元。
我們剛到美國時,了解到冰雪運動裝備的二手交易很活躍,于是找到了一條便宜的路徑。冰球俱樂部在每年開賽前,會搞幾場二手裝備的交易會。家長們把用過的裝備放在俱樂部去轉賣,非常便宜,價格基本是新品的1/10~1/2不等,我們用這個方式省了一大筆錢。
但有些省不了。譬如,當時沒有合適的球棍和頭盔,一個最便宜的球棍將近80美元,頭盔最便宜也要六七十美元。一年的訓練費加各種裝備的成本,需要1000多美元。
看上去最省錢的花樣滑冰,其實一點都不省錢。剛入門時還好,參加訓練和比賽的級別越高,費用也跟著水漲船高,比賽服裝和教練費用都是天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父母需要投入巨大的時間精力。不夸張地說,雙職工家庭,是不大可能培養出一個小眾體育運動員的,尤其是冰雪運動項目運動員。
記得剛開始練習冰球時,我家大兒子才6歲多。我們去鎮上的一個冰球俱樂部進隊訓練,才發現這項運動的忙碌之處。
拿到日程表后,我們傻眼了:他的訓練時間是早上7時!要知道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一般都睡到八九時才醒。7時開始訓練,意味著6時半以前要到冰場—因為要換衣服裝備和冰鞋,至少要15~20分鐘,尤其是對初次接觸冰雪運動的孩子和家長而言。
家里到冰場算很近的了,開車半小時左右。但6時半要到冰場,就意味著最晚6時就要出門,5時45分到50分期間,必須把孩子從床上薅起來。這對家長和孩子,都是折磨。
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為啥要把六七歲孩子的訓練,安排得這么早?
直到我們第一次進場館時,看到迎面走來一對剛下場的隊員,我們驚到了!
這群孩子比我家的還小,也就是5歲左右。也就是說,他們的訓練,清晨6時就開始了。那意味著,他們在凌晨4時多到5時期間,就起床了。
我們覺得這種節奏太瘋狂了,后來慢慢才了解到,因為冰場的日程特別緊張,尤其在繁忙的賽季,這已經形成慣例了:好一點的時間段,上午、下午和晚上,必須優先給正式比賽,或者重要的集訓;小孩子的訓練,尤其是這種入門級別的,只能見縫插針,有時間段排上去就不錯了。
雖然一個冰雪館有十來個冰場,但都非常繁忙,每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春季,經常是滿負荷運轉。兩個隊的訓練時間段,除了造冰機平整冰面的十來分鐘,完全是無縫銜接。經常是車子剛出場,隊員們就跟開閘的魚一樣,沖上去了。
陪伴孩子訓練,還有大塊的通勤時間,消耗在路上。雖然美國的冰雪基礎設施發達,我們一般半小時內都能到達冰場,但有些住得遠的家庭,有需要驅車一小時的;如果是Travel Team,經常要去別的鎮或城市打巡回賽,甚至經常要在車上呆一兩小時。
加上冰場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家長和孩子都是起早摸黑。
谷愛凌和陳巍的母親,都有這樣的經歷。陳巍就說:“我的媽媽和我一起在冰上度過了大半生。”為了帶孩子訓練和比賽,家長帶著孩子,常年在車上奔波。
家庭中,需要一個人做出犧牲,這個人一般都是母親—辭職成為全職太太,接送孩子,陪練陪讀。

2022年1月15日,孩子們在沈陽北陵公園冰面上學習滑冰
他們在凌晨4時多到5時期間,就起床了。
我們在鎮上冰場遇到過一個家庭,其三個女兒都在練冰雪運動。因此,夫妻倆一到周末就呆在冰場,或者在往返不同冰場的路上,從早上五六時,一直到晚上八九時。
所以,看到冰雪運動員的成功,更要看到背后數以十年計的,整個家庭和孩子的無窮付出。這種投入和韌性,不是一般家庭能堅持下去的。
北京冬奧會過后,像谷愛凌、陳巍這樣的明星運動員,激勵了不少家長,讓他們燃起了讓孩子去練冰雪項目的念頭,但我要先潑一盆冷水。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這一批成功者的獨特時代背景,以及這些家庭的代際傳遞效應。
谷愛凌、陳巍、朱易和其他這些華人二代的父母,都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的留學生。
那個年代極少自費留學生。出去留學的人數少,尤其是留學美國,幾乎全是公費,他們基本都是中國的學術精英。
當這些華二代開始練習冰雪項目時,趨勢剛剛開始。但2000年后,留學和移民的趨勢一直在快速增長,一直持續到疫情前,人數是之前的幾十倍。
隨后的20年,像冰雪項目這樣的小眾運動,在北美華人圈早已經大眾化了,現在早就是一片紅海,不是啥捷徑了。記得我們在布法羅的時候,一個小鎮上的體育館里,都能看到十來個華人孩子在練習花樣滑冰。
這么大數量移民的孩子,將來會把華人的冰雪項目,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相信在接下去的一二十年,“批量制造”的陳巍、谷愛凌等,會源源不斷地出爐。
所以,現在想趕潮流入場的家庭,要三思而后行。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