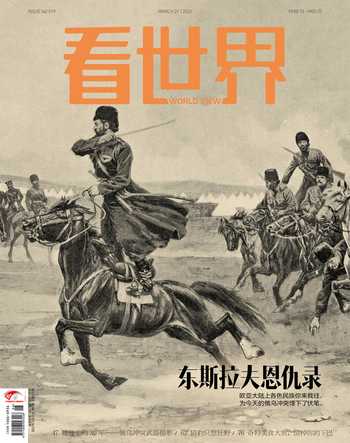諾亞方舟靠泊之地
樓學

阿拉加茨山
亞美尼亞是一個被高山和湖泊定義的國家。
在本地的神話傳統中,塞凡湖、凡湖、烏魯米耶湖是他們的“三大湖”,而阿拉加茨、大阿勒山則是三湖之間的親密姐妹。亞美尼亞的文化腹地,就是兩山三湖之間的這片土地。
但隨著歷史和政治的變遷,如今只有塞凡湖和阿拉加茨山保留在國境線內,這使亞美尼亞成為一個具有悲情色彩的國家。
時值6月,下午6時仍然天色大亮,參觀完代貝德河谷的薩那欣修道院后,我們決定前往首都埃里溫。
行程開始的一段仍是代貝德河谷,不久之后地貌景觀發生劇變—狹長的河谷、蓊郁的叢林轉為開闊的草原,遠處猛然出現一座高大的雪山,濃烈的色調如同油畫一般。這意料之外的美景,幾乎讓我們在車廂內叫出聲來。

深坑修道院
這座雪山就是亞美尼亞的最高峰阿拉加茨雪山,海拔4095米,但在冰雪覆蓋之下,卻是一座火山。密集的寄生火山錐,顯示著這里并不是太平之地。
在亞美尼亞人的神話中,阿拉加茨還有一位親密的姐妹—大阿勒山,兩姐妹在一場爭吵之后分開,從此成為了兩座山,也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兩座山。
在《圣經·創世紀》中,這座海拔5137米的大阿勒山是諾亞方舟的靠泊之地,對于亞美尼亞這樣的基督教國家而言,這是一座當之無愧的圣山。然而,國運多舛的亞美尼亞已經失去了它。
1922年,埃里溫批準了與土耳其之間的《卡爾斯條約》。在這一條約中,大阿勒山被劃入土耳其境內,這段歷史成為亞美尼亞人心中永恒的傷痛,也為本就復雜的土亞兩國恩怨又添了一把新火。但無論如何,這處國家文化的精神象征,從此只能出現在本國的國徽、貨幣上,而不再是地圖上。
大阿勒山距離首都埃里溫僅有幾十公里,在天氣晴好時,我們可以在市區內的高處望見這座完美的錐形火山。不難想象,在如此靠近兩河、小亞細亞、埃及這些早期文明的起源之地,有這樣一座雄偉神圣的雪山,會給宗教帶來怎樣的傳奇靈感和精神震撼—無怪乎《創世紀》中最重要的時刻被賦予這座雪山。
我們專門花了一個下午前往大阿勒山下的深坑修道院。這處修道院就坐落在亞土兩國的邊境線附近,是亞美尼亞最靠近大阿勒山的地方。我們的包車司機帶我們駛出了擁擠的埃里溫,太陽已經落到了土耳其一側,大阿勒山近乎一覽無余地顯現在晴空下的逆光之中。
司機一邊行車,一邊默默祈禱。這座失去的神山,是他心中缺失的拼圖。
在亞美尼亞旅行,埃里溫一定是最理想的大本營。幾處重要的修道院都已被列為世界遺產,它們無一例外都分布在埃里溫附近。
不過,沒有世界遺產桂冠的深坑修道院,似乎更受到旅行者青睞—地處早已被關閉的土亞邊境,它自帶歷史的傳奇色彩;地處大阿勒山之下,更賦予其無雙的自然背景。
何況,深坑在亞國的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亞美尼亞歷史上的第一位使徒格列高利,曾被國王梯里達底三世囚禁在這里長達14年之久,但在他的傳道之下,國王最終宣布皈依基督教。
公元301年,亞美尼亞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以基督教作為國教的國家,格列高利被尊稱為“啟蒙者”。甚至直到今天,亞美尼亞教會仍被稱為格列高利教會。深坑修道院就是后人為了紀念這段歷史而修建的。
亞美尼亞的文化腹地,就是兩山三湖之間的這片土地。

埃奇米阿津大教堂
這一信仰的轉變,從根本上塑造了亞美尼亞的歷史與人文風貌。盡管在此后,信仰拜火教的波斯人、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都曾在亞美尼亞攻城略地,卻從來沒有成功地改變過本地的信仰。
而與這一歷史密切相關的另一處古跡,是首都西面的埃奇米阿津。303年,當這個國家轉向基督教后不久,格列高利就在這里修建了第一座國家修道院,也是世界范圍內最古老的主教座堂。
有趣的是,由于亞美尼亞受到中國的許多援助,從埃里溫去往埃奇米阿津的公交車,特意在擋風玻璃上貼著中文的“埃奇米阿津”,令人有意外的親切感。
“埃奇米阿津”意為“獨生子降凡”。相傳格列高利在幻覺中看見上帝之子從天而降,指示他在此修建修道院。從此,埃奇米阿津成為亞美尼亞人的教廷所在,在他們尚未擁有屬于自己的獨立國家的漫長歷史中,這座教堂成為維系民族文化與身份認同的關鍵紐帶。
如今的亞美尼亞人,擁有如此強烈的民族意識,在強國林立中傲然存在,產出了與其渺小人口不成比例的大量杰出人物,也正與這樣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
埃奇米阿津的名聲遠播整個基督教世界,有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珍貴文物被收藏在教堂附屬的博物館中。其中包括諾亞方舟的碎片、曾刺進耶穌身體的圣矛,以及耶穌受難時的十字架碎片。
這些文物顯然被賦予了強烈的宗教色彩。我非常好奇這些文物會被如何斷代,又意外在新聞中發現了十多年前,曾有中國香港和土耳其的探險隊聲稱他們在大阿勒山上找到了諾亞方舟的木結構殘跡,碳十四測年被定位到距今4800年前—古老的神話似乎越來越真實。
距今4800年,確實是亞美尼亞歷史上的第一段繁榮時期。他們鍛造青銅、發明輪子、種植葡萄,將青銅文明的勢力傳播至高加索的其他地區。
無論真相如何,或許沒有比埃奇米阿津更適合保存它們的地方了。那天下午,大阿勒山不時隱現在教堂、墓地背后的濃云之下,一場驟雨倏忽而至,不免令人幻想將要陷入大洪水來臨的前夜。
不過洪水沒有到來,世界仍在雨后有條不紊地運行著。有當地的老者路過教堂廢墟,會做一段短暫、虔誠的禱告。我們還意外闖入了一場葬禮,全場的“黑衣人”們鴉雀無聲,目送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在巡游一番后匆匆離開。
公元301年,亞美尼亞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以基督教作為國教的國家。
在博物館中見到的圣矛,其實原本不是埃奇米阿津的收藏—這件文物來自埃里溫東面“上阿扎特山谷”中的圣矛修道院。
圣矛修道院是一座非常典型的亞美尼亞中世紀建筑,中央是尖尖的圓頂“帽子”,四個方向上分布著坡屋頂,組成一個平面上的十字形,被稱為“圓頂四瓣形”教堂。但這里的文化史可以上溯至基督教來臨之前,山谷中的巖穴、泉水很早就已成為崇拜的對象。


圣矛修道院
這處修道院的始創者仍然是格列高利,4世紀以后屢毀屢建,盡管后代增修了許多防御工事,但阿拉伯人、蒙古軍隊、帖木兒,都曾經洗劫過這里—兩旁的山崖上有著許多巖穴,有一些是王室的墓地,也有一些在戰亂時期成為修士們的避難所。
現存的圣矛修道院是13世紀重修的建筑,由于得到當時王室成員的贊助,這里收獲了一批重要的抄本及文物,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傳說中羅馬士兵刺入耶穌身體的長矛。如今它被精心收藏在寶石鑲嵌的圣物箱中,修道院也因此得名。
如圣矛修道院的興廢史所展示的那樣,上阿扎特山谷一直是不同文明勢力的角逐之地,自然在文化面貌上非常多元。
我們在返回埃里溫的途中,還順路游覽了加尼神廟。這是亞美尼亞境內一處重要的前基督教時期的古跡,有著典型的希臘–羅馬風格,由24根高大的愛奧尼亞式立柱圍合成一座壯觀的神殿。
我原以為其中供奉的可能是宙斯或阿波羅,卻在介紹文字里找到了密拉特的名字。這是來自瑣羅亞斯德教的光明正義之神,有著鮮明的波斯“血統”。
這是亞美尼亞無比寶貴的“異教”古跡。在以基督教為重要核心的信仰和藝術傳統中,我們還是能在這里仰望希臘式的經典柱頭,撫摸充滿人性光輝的雕刻,看見清新四溢的蔓草紋飾。
4世紀之后,這座神廟成為異教徒的象征而被夷為平地。但來自希臘與羅馬的藝術風格,來自波斯的神祇信仰,甚至還有來自中亞草原的征服欲望,都悄悄地融入了亞美尼亞的文化之中。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