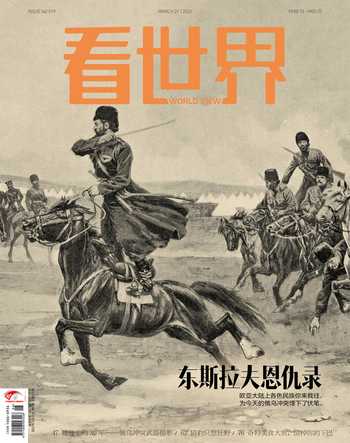罕見病為何頻現天價藥?
非田

2021年9月15日,患兒Marley在英國謝菲爾德兒童醫院接受Zolgensma治療
2008年2月29日,一個名為EURODIS的公益組織發起組織了一場大規模活動,而之所以選擇這個四年一度的罕見日子,是因為活動的主題是為如“閏年2月29日”般罕見的罕見病患者呼吁發聲。
這項活動在此后受到了各國公益人士的支持,每年2月的最后一天,也被定為國際罕見病日。
2014年,一場名為“冰桶挑戰”的公益活動火爆全球,以漸凍癥為代表的罕見病患者開始受到各界關注。
罕見病的單病種發病率低、發病機制復雜。世界衛生組織將患病率在萬分之6.5至千分之1的單個疾病定義為罕見病;而國際藥物經濟學與結果研究協會罕見病特別利益小組的報告顯示,罕見病全球平均發病率約為萬分之4至萬分之5。
盡管標準尚無定論,但大多數人談及罕見病時,第一印象無疑是罕見病藥的“天價”。2021年初,美國藥品價格跟蹤網站GoodRx公布了全球10大最貴藥物榜單,其中有7款是罕見病藥。

Zolgensma藥劑
定價最高的“Zolgensma”,是美國FDA批準的首個用于治療2歲以下兒童SMA(脊髓性肌肉萎縮癥)的基因療法,一針價格高達212.5萬美元。去年年底,同樣是治療SMA的諾西那生鈉注射液被納入國內醫保,該藥的價格,一度被傳為高達70萬元一針。
客觀來說,罕見病藥極高的技術門檻、漫長的開發和上市周期,以及相對較少的受眾,都注定其單價難以下降。但不可忽視的是,面對罕見病這一人類社會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藥企,也都為提高罕見病藥物可及性,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嘗試。
罕見病藥的高價要從40多年前說起。上世紀80年代初,風靡美國的電視劇《法醫昆西》,用了整整兩集的篇幅,講述了罕見病患者及其家庭的困境。美國民眾對劇中的故事感同身受,支持罕見病相關立法的來信,如雪片般飛向國會議員的案頭;華盛頓街頭乃至國會大廈門口,也出現了支持罕見病患者的大規模游行。
1983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孤兒藥法》。此后的數年間,國會還對法案進行了多次補充和修改,罕見病藥的研發,自此迎來第一個高峰。
制藥商甚至很難找到足夠的藥品臨床試驗對象。
事實上,60年代開始,美國醫學界發現,有越來越多罹患血友病、肌肉萎縮癥等的病人,因無對癥藥可用而去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與多位醫療專家曾聯名呼吁解決這一困境,但并未引發足夠重視。而《孤兒藥法》通過后,罕見病藥緊缺的問題有所改觀。
相關統計顯示,1967—1983年,經FDA審批的罕見病藥只有34種。而法案通過后的那幾年,共有370種藥物被認定為罕見病藥,49款罕見病藥的上市申請獲批。
全球頂尖的咨詢公司波士頓咨詢的研究顯示,自2015年以來的5年,罕見病藥市場年均增速為18%—截至2020年末,全球罕見病藥的市場規模已超620億美元,這一數字預計在2030年時將達到1940億美元。

新藥開發曾經有個著名的“雙十定律”,即研究時間10年,研究耗費10億美元。
年實際治療費用超出30萬元的藥,現階段很難進入醫保。
與極高市值不相稱的,是巨頭對罕見病藥研發熱情并不算高。一款新藥上市前,需要經歷基礎研究、I/II/III期臨床試驗、申請上市、待審批等階段。
業內人士指出,新藥開發曾經有個著名的“雙十定律”,即研究時間10年,研究耗費10億美元。“醫藥行業有個很著名的笑話,如果有人問,為什么一粒成本5美元的藥能賣到200美元?藥品研發人員會回答說,因為那是第二粒,第一粒(指研發)的成本是足足10億美元。”
這一當年看起來如天文數字般的數據,如今卻早已是明日黃花。研究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獲批上市的新藥平均研發費用已超過25億美元。
相對稀少的罕見病患者人數,則讓罕見病新藥研發難度更增。就醫學層面而言,絕大多數罕見病在發病機制和診療方法上都不明確。罕見病患者人數較少且地域較為分散,也讓患者醫療數據的采集和分析十分不易,制藥商甚至很難找到足夠的藥品臨床試驗對象。

2022年1月21日,土耳其安卡拉,9歲男孩患有罕見病早衰癥,目前已知只有4人在土耳其患有此病
如此高的研發難度自然會讓藥企望而卻步。全球頂尖的藥物研究合同委托機構“精鼎醫藥”指出,一款罕見病藥的基礎研究平均需要6年,臨床實驗平均需要8年,再加上平均2年的等待審核期,總共要16年。
即便藥企下了研發罕見病藥的決心,過小的市場空間也讓罕見病藥的高成本,面臨難以收回的巨大風險。一方面,較少的受眾意味著藥物研發成本平攤在每個病患身上更高;另一方面,過高的單價又讓罕見病藥難以被納入醫保,間接減少了藥物可覆蓋的罕見病人群,陷入惡性循環。
在成本收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最小化分析等傳統的藥物經濟學評價方法中,罕見病藥品并不具備優勢,因此常常被醫療保險拒于門外。
北京病痛挑戰公益基金會是國內最早一批關注罕見病的公益組織。據該機構政策信息研究總監郭晉川介紹,藥物經濟學將“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效果所增加的成本”,稱為“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劃定,當ICER值在1~3倍人均GDP范圍內,是具有成本效果的—根據中國的人均GDP計算,這個數值不應該超過31.9萬元。
這就意味著,年實際治療費用超出30萬元的藥,現階段很難進入醫保。郭晉川表示,盡管部分罕見病藥的價格偏高,但藥物使用者通常較少,這樣對醫療服務的總體成本影響有限。因此,在罕見病藥進醫保這命題上,如何盡可能平衡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對各國醫保決策者都是一個考驗。
除了極高的研發難度外,罕見病藥的天價也與專利保護期不無關系。

《溫暖漸凍心》劇照
目前,針對罕見病藥的專利保護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專利保護,即保護已申請專利的罕見病藥的產品工藝、配方及生產方法;另一種則指罕見病藥市場獨占制度。二者是平行關系。
傳統專利法中,對藥品專利保護的期限通常只有20年。為鼓勵新藥的研發,補償專利持有者在藥品研發和等候審批過程中失去的時間,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開始嘗試建立藥品專利期延長制度。
考慮到部分罕見病藥可能存在治療有效但尚未獲得專利的情況,美國還為這類藥物開了綠燈,設立了市場獨占制。以美國為例,無論一項藥物是否獲得專利或是否已過專利保護期,只要其獲得“孤兒藥”地位,就能獲得7年的市場獨占期。
另外,《孤兒藥法》還規定了相關配套措施以促進藥物研發,其中包括最高達50%的罕見病藥研發經費抵稅、州政府及私人保險經費支持、藥品快速審批流程,以及規模相對較小的臨床試驗等。
多層次的專利保護措施,本意是為研發難度較大、受眾人數較少的罕見病藥建立起更完善的制度護航體系。但這一系列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卻難免出現偏差。繁雜的專利保護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市場壟斷,進而導致藥價虛高。
知識生態國際組織KEI負責人James Love認為,罕見病藥受眾群體數量太少,一款罕見病藥上市后,基本就是市場獨占了,專門為其設定市場獨占,反而容易讓藥品研發企業利用政策漏洞賺錢。
約80%罕見病是基因遺傳疾病,只有不到20%與腫瘤相關。但業內人士稱,腫瘤相關藥一般是不少藥企開發罕見病藥的首選:一方面是腫瘤患者相對較多,另一方面也在于,一款腫瘤相關藥物若能被認定為罕見病藥,不僅能讓藥企獲得極高的利潤,還能阻礙其競爭對手對該領域的進一步投資,而這已經違背了設立專利保護及市場獨占機制的初衷。
此外,歐美等國的罕見病藥法案也被認為預設不當。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Steven Simoens認為,決定罕見病藥的價格的因素,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完全取決于罕見病患者人數多少,而并未考慮到服用藥品次數、療程期長短等其他影響“孤兒藥”利潤的因素。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副教授Panos Kanavos呼吁,對罕見病藥的盈利問題進行定期科學評估,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市場獨占期長短。為此,歐盟在2008年通過了《孤兒藥壟斷期評價指南》,決定對罕見病藥的市場獨占權實施評估機制,在市場獨占的第六年,對罕見病藥進行銷售額評估,若認定已能盈利,將縮短該藥物的市場獨占期。

2020年2月29日,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407人一起參加“冰桶挑戰”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罕見病藥的降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仿制藥。前些年,電影《我不是藥神》的熱播讓不少觀眾注意到了價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藥。郭晉川表示,對于血友病等部分罕見病而言,仿制藥可大大降低藥價,這對患者而言是有實際意義的,但這對于龐大的罕見病藥數量而言,無異于杯水車薪。
因此,各國市場間的協同顯得尤為重要。郭晉川認為,長久以來,因罕見病藥未被納入醫保、國內人均GDP低于1萬美元等原因,罕見病創新藥在歐美上市若干年后,才考慮中國市場。
約80%罕見病是基因遺傳疾病,只有不 為談資。到20%與腫瘤相關。
近年來,國內針對罕見病藥制定的多項利好政策,向國際藥品市場傳遞了積極信號。不少國際藥企會在向美國FDA或歐盟EMA提交申請不久后,在中國也提交上市申請,客觀上提高了藥企研發罕見病藥的意愿,也顯示國際藥企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除了政策外,商業手段也是助力罕見病藥走出天價怪圈的重要方式。郭晉川表示,現今不少普惠型商業補充健康保險有關于罕見病保障的條款,除了常規支付外,還創新了供給方和支付方協商“按療效付費”的方式,相當于在醫保和藥品供給方之間進行對賭協議,當療效得到確認后,醫保及患者才開始付費。
當然,罕見病藥的高價只是罕見病患者所面臨的眾多難題中的一個。想要切實解決罕見病患者的困難,還需要更多方面更持續的關注,而非僅僅將高藥價及“冰桶挑戰”等視為談資。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