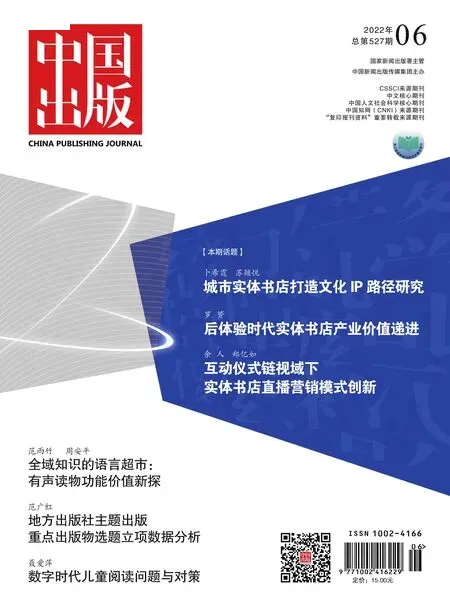城市實體書店打造文化IP路徑研究
□文│卜希霆 蘇穎悅
實體書店作為城市空間中重要的文化場所,承載著人們的文化實踐活動,是一座城市精神生活多元化的外在表現,[1]不僅為人們提供了文化交流與公共交往的平臺,也為營造書香社會、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中央以及地方有關部門提出多種扶持措施鼓勵實體書店的改革發展,但經營成本、線上市場競爭等問題依舊影響著實體書店的良性發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更使實體書店面臨不小的打擊。在此情形之下,實體書店單一的圖書銷售模式難以成為維系書店生存的有效模式。
《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提出,鼓勵各地加大實體書店支持力度,推動實體書店加快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探索多業態融合發展,全面提升管理、運營、服務水平,推出一批具有文化地標意義的特色書店。[2]越來越多的實體書店更新經營理念,將書店重新定義為集多元業務于一體的文化休閑場所,從空間、內容、服務等多方面進行品牌的系統化打造,以IP化思維積極探索公共空間與文化的融合突破,實現從單純的“消費場所”向“體驗空間”的轉型。[3]這種文化IP的發展模式為書店的創新轉型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維度,也逐漸成為書店未來發展的有效路徑。
一、城市實體書店轉型困境根源
實體書店具有鮮明的精神文化屬性,不僅是衡量城市文化發展的“文化舒適物”(cultural amenity),[4]也是寄托城市個體情懷的“文化窗口”。近幾年來,實體書店在政策扶持下探索轉型升級路徑,從單一的圖書銷售模式跳脫出來,嘗試復合多元的業態模式。但在轉型的過程中,書店也面臨著諸多困境,這些困境的根源可以總結為虛實空間博弈、閱讀場景變革以及價值認同式微三個方面。
(一)虛實空間博弈
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的劃分是伴隨著媒介的興起而產生的,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作為人的外化與延伸,能夠以一種積極能動的方式構建起一個中介化的環境。[5]媒介技術不僅開拓了空間的邊界,更在其構筑的賽博空間中重塑了個體的連接關系及其感知方式與行為模式。實際上,實體書店正是被互聯網帶來的網絡書店所定義,這種“逆命名”(retronym)的現象隨著網絡社會的不斷發展,逐漸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現象。[6]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網絡空間對于實體書店空間的壓迫。網絡書店自2000年以來迅速發展,憑借優惠的價格、便捷的物流吸引著書籍消費群體,目前線上銷售渠道在整個圖書零售市場占比近80%,實體書店的圖書銷售空間被嚴重擠壓。
(二)閱讀場景變革
互聯網的介入不僅為空間開拓提供了可能,對讀者的閱讀行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第十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雖然我國國民綜合閱讀率逐年上升,但其中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已達79.4%,電子書閱讀量的增幅較紙質圖書更大,[7]數字化閱讀因其內容的豐富性、獲取的便利性以及移動性等特征,能夠滿足人們快節奏生活中的碎片化閱讀需求,逐漸成為人們更青睞的閱讀形式。在數字化趨勢下,數字出版不僅優化了可視的文字內容,還將閱讀內容延伸至可聽的有聲書等,并推動數字閱讀終端以及微信讀書等線上閱讀平臺發展,促進了閱讀場景的全方位滲透。傳統紙質書難以適應人們不斷變化的閱讀場景需求,以紙質書籍售賣為主的實體書店也必然會受到相應的影響。
(三)價值認同式微
在全球化進程中,原本依賴于地域以及文化差異而建立起來的地理空間邊界變得日益模糊,信息依托媒介技術能夠穿越時空,在真實與虛擬的世界中自在漫游。[8]人們能夠足不出戶,在虛擬空間中找到替代的“網絡書店”,而這種書店是脫離了文化、歷史、地理意義的非地方性空間,[9]在地域性消解的同時,也使得包括實體書店在內的城市實體空間所擁有的原真性逐漸消逝。同時,隨著城市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不斷消減,文化空間便成為人們投射理想生活方式、尋求精神寄托的理想場所。根據調研結果,許多實體書店都在嘗試結合咖啡、餐廳、文創產品等,打造一個集閱讀、交流、休閑等功能為一體的復合式文化空間。但目前不少實體書店由于對文化的理解不透徹,在發展的過程中效仿部分成功的書店模式,盲目追求高顏值、多功能,極易產生同質化的問題,缺乏本地區的文化連接性,從而導致書店自身的文化屬性被削弱,讀者也難以從實體書店得到精神慰藉與價值認同。
二、轉型新路徑:以文化IP賦能書店發展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下,從“知識產權”的定義中跳脫出來,在“承載形象、表達故事和彰顯情感的文化生產過程中,成為一種情感載體、一種有故事內容的人格權”。[10]文化IP則在IP的基礎上進一步凸顯文化效益,指向文化產品之間的連接融合。它以內容和流量作為核心,能夠讓用戶追捧并轉化為消費行為、最終實現商業變現轉換。[11]
實體書店是城市文明不斷演進的空間所在,它一方面聚集了城市各個階段的精神與文化發展成果,一方面又是在當下特定的物質與精神基礎上建立的,[12]是一種獨特的“文化符號”。從實體書店的角度出發,其文化IP的內涵與外延可以簡單呈現為一個由內而外的洋蔥模型(如圖1所示),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能夠與消費者產生精神聯結的價值觀念,這是實體書店能夠實現有效區分并吸引消費者的根本要素。第二層是具有高辨識度的形象識別,包括從實體書店特定符號呈現,到視覺識別系統的打造,再到融入理念的場景沉浸,這是令消費者感知并形成印象記憶的外在基礎。第三層是品牌矩陣,品牌及其矩陣建設是在實體書店形象的基礎上對其主題和價值的整體性統合,建立并完善實體書店品牌群是增強粉絲黏性、形成文化IP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最后一層則是商業轉換。與IP一致,文化IP在商業意義上同樣具有可流轉的財產屬性。[13]優質的文化IP不僅能夠輸出良好的價值觀,更具有從文化資本轉向經濟資本的潛力。因此在這一層面,文化IP也包括開展跨界合作、實現產業鏈流通,從而獲取持續的商業利益。然而,實體書店文化IP的內涵和外延并非一成不變,隨著時代的高速發展,文化IP在實體書店發展進程中亦在動態演進、不斷生長。實體書店文化IP打造已成為實體書店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圖1 文化IP的內涵與外延
總體而言,“文化IP”是一個從價值體現延伸至整合開發、從文化屬性指向商業屬性的行業術語,以文化IP賦能實體書店的轉型,關鍵就在于借助文化IP的整合能力實現實體書店的空間與內容重塑,在多元場景和服務的連接下,為人們傳遞一種普世意義上的價值認同感和文化共鳴,[14]進而實現其商業價值。而文化IP之所以能夠幫助實體書店實現轉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IP重塑獨特的“場所精神”
諾伯格·舒爾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認為城市中的每個空間場景都有其深刻的含義,并與城市本身的歷史文化主題息息相關。[15]他以“場所”來表示這種由自然環境與人造環境結合的有意義的整體,[16]體現出場所背后物理與精神的雙重意義。書店之所以會成為現代人的記憶空間,很大程度上在于書店實體空間的場所精神所賦予的文化氣質與氛圍,從而帶給人們對于這一空間的情感依存。將文化IP用于實體書店的更新,能夠為實體書店空間的場所精神賦予延續的動力。如南京先鋒書店以“先鋒”態度作為自身的文化要義,將先鋒的精神和理念融入書店的建設與經營,打造出飽含先鋒人文精神的文化IP,讓先鋒成為折射南京這座城市文化氣質與精神靈魂的窗口。可以看到,文化IP作為實體書店的價值凝練,與書店的場所精神一脈相承,以先鋒書店為典型的實體書店以自身的獨立精神包裹著自身的文化特質,使實體書店不僅作為一個文化載體,更成了一種文化態度和文化標簽。
(二)文化IP重構讀者的價值認同
人們對空間的需求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從物質需求到精神需求的發展過程,而實體書店的功能也隨之從單一的圖書消費轉向更具審美體驗的復合功能,以更好地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17]但光具“顏值”而無自身文化特質的書店,也難以為信息裹挾與生活重壓之下的都市人提供一個良好的身心棲息之地。面對現代人的焦慮感,吉登斯指出,若給出一種清楚明晰的信念,尤其是堅持一種易于理解的生活方式的信念,便可消除焦慮。[18]實體書店通過自身文化理念的輸出,圍繞文化IP進行空間中的傳播實踐,能夠幫助讀者抵抗精神上的焦慮與迷茫。蔦屋書店以“提案生活方式”為IP內核,通過獨特的空間建構和體驗互動,將理想的生活方式傳遞給更多到訪書店的讀者,從而構筑了蔦屋在讀者心中的定位和認同感。此外,在特定的文化定位之中,實體書店以自身歷史、文化及其空間實踐的交織關系可以形成獨一無二的“靈韻”,如同莎士比亞書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之于舊金山,文化IP的打造使得實體書店不再是一個單純冰冷的容器,而是蘊含著書店深刻的文化情結,并使個人在空間參與的過程中建構起充滿個人經驗和情感的“地方”,進而重構讀者對實體書店的價值認同。
(三)文化IP重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實體書店的文化IP,除了能夠重塑書店自身的文化價值、重構讀者的價值認同外,還可以串聯起實體書店的空間打造、活動舉辦以及衍生品開發等,從而完成書店商業模式的更新,提升書店文化價值轉化力。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個體消費行為包括物質上的理性消費以及意義上的感性消費,而在當前時代背景下,商品的符號意義逐漸成為個體消費的重要目的,這種消費背后實際上展現了一種身份、品位以及價值觀的體現。互聯網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讀者的購書需求,而實體書店提供的則是獨一無二的空間體驗,圍繞文化IP打造“書店+”的復合模式正是以多元場景的文化實踐為消費者帶來獨特的情感消費,如“書店+服飾+展覽+生活美學”的方所、“書店+創意市集+畫廊+餐廳”的言幾又等,擺脫了傳統以圖書零售為主的單一商業模式,讀者進入實體書店,實際上是被具有美感的空間設計、創新的場景打造以及以文化IP為內核的衍生品所吸引,消費者基于對文化IP的認可,會更加愿意為這種價值觀買單,進而在活動體驗、文創產品購買的過程中推動了書店商業模式的持續運作。
三、實體書店文化IP的發展路徑建議
城市文化空間既是人類文化生活實踐的載體,也是文化意義表達的過程。[19]實體書店空間功能的內核實際上是一種書店文化,[20]書店轉型升級的核心也應當從“顏值”展示轉向文化內容輸出。建構文化IP,實際上就是通過一系列傳播手段將精神化的閱讀世界具象化,形成媒介再造的空間,最終再抽象為文化意義,在傳播之中建立讀者對書店的文化認同,使實體書店成為讀者與文化的連接橋梁和精神口岸。在智能融媒體時代,信息的生產與消費是多維多象限的,因此,對文化IP的傳播也不能限定在地方意象或空間軌跡上,需要改變以往在媒介傳播單象限內進行信息傳遞的固有認知,在媒介與傳播地理多維度之中探索建構文化IP的可能性,以“文化”作為空間實踐的呼應,并落腳于“IP”這一意象表征。
傳播既發生在空間與地方之中,又創造著空間與地方。[21]以實體書店的空間性與地方性為基礎,對于文化IP而言,空間與地方既可以是決定傳播的載體,也可以是傳播所生產的內容,因此,地理干預和地理表征、空間和地方這兩對關系形成了文化IP建構的四個象限(如圖2所示)。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一是文化IP的空間傳播,二是文化IP的空間呈現,空間中的傳播是多場景、多感官的,傳播中的空間則是多維度、多樣態的;從地方的角度來看,一是書店IP的地方實踐,二是具有地方感的文化表征,前者通過人們的具身實踐與多元體驗來塑造文化認同,后者則注重書店地方感的符號表征。這四個維度并非相互分裂,而是以不同的側重共同完成了對于實體書店的構型,助力實體書店更好地成為一個集閱讀空間、文化活動、文創設計為一體的公共文化空間。

圖2 建構實體書店文化IP的四個象限
(一)傳播與呈現:文化IP的空間營造
列斐伏爾(Lefebvre)將空間看作是“社會關系的重組與社會秩序實踐性建構的過程”。[22]作為城市文化空間的特色區域,實體書店通過書籍的文化屬性以及自身特定的文化空間意義進行文化編碼,[23]由此被賦予了特定的文化空間內涵。從書店作為空間的角度而言,文化IP的構建與傳播情境主要包括兩方面,一個是文化IP在書店空間中的移動,具體表現為空間中的設計與布局;另一個是文化IP的傳播對空間拓撲關系的改變,文化能夠沿著網絡中的連接關系輻射至更廣泛的區域,從而形成影響力。從文化IP的空間傳播到空間呈現,在完整意義上形成了從實體空間向多維時空的整合,從而擴大了文化IP的傳播范圍。
1.空間傳播:多元場景打造
書店空間作用于人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傳播的過程。人們在空間中的流連會自然引發各種社會性活動,[24]因此,良好的空間設計及功能布局能夠營造書店空間的良好氛圍,促成個體思想的產生與行為的發生。實體書店應致力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借助空間形式和人文環境來體現自身的理念與價值觀,為讀者提供良好的閱讀體驗。
一方面,實體書店應當以獨特的空間設計給人以視覺、聽覺、觸覺乃至嗅覺的舒適感展示書店調性。日本平面設計大師原研哉認為,人既是感覺的集合體,也是一個記憶再生裝置,能夠在感覺刺激與記憶的交織下形成對外界的印象,即對“信息的構筑”。[25]因此,書店IP的空間營造應當從“五感”的角度出發,通過調動讀者的視覺、聽覺、觸覺乃至嗅覺、味覺,來喚起讀者對于空間元素的綜合感知,從而更好地傳達書店獨特的價值觀。如中信書店以“多元文化、多維體驗”為經營理念,試圖通過調動多重感官來打造主題場景:自然書店圍繞自然主題,以白色的主色調以及植被作為店內裝修的基本要素;啟皓店則擺放著有聲書架,為讀者提供專業的書籍解讀。此外,書店還使用與所售書籍相呼應的香水,并按照特定的天氣和時段,播放符合書店調性的音樂。這些空間要素以多感官的方式展現出中信書店獨特的生活美學,讓書架、裝置、燈光等不再是擺放于空間中的呆板之物,而成為一種能夠與人進行對話的“信息”。
另一方面,實體書店應當圍繞IP進行空間功能區域的合理布局。作為城市中重要的“第三空間”,實體書店既是一個能夠進行思想交流與碰撞的文化空間,也是一個供讀者閱讀放松的休閑空間。因此,實體書店需要通過靈活多樣、動靜結合的功能空間布局,豐富整體空間形態,從而有助于讀者在書店更好地與物進行交流,并展示品牌性格。如成都三聯書店以讀者為中心,通過準確的空間劃分打造出“三聯生活”“三聯閱讀”以及“三聯活動”三個主要的功能區域,以獨特的場景展示為讀者、作者以及作品搭建起一個溝通的橋梁,讓書店空間真正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空間中的功能布局既要突出各區域的特點,也要把握區域之間的和諧與平衡,在結合書店自身文化調性的基礎上,使整個空間形成多元而不凌亂、分隔而又統一的文化有機整體。
2.空間呈現:多維時空交織
空間是由傳播來創造和定義的,若將不同的行業、媒體平臺以及眾多用戶看作是一個個節點,那么節點和連接的結構關系便使得書店空間成為了一個“由連接而非數量來決定大小”的拓撲網絡。[26]在此過程中,實體書店自身的空間局限被打破,文化與意義附著于網絡之上,沿著連接關系進行傳播,從而構成了兩種以文化IP為核心的復雜交織的空間,并進一步增強文化IP的對外輻射力。
首先是通過跨界合作搭建多業態空間。IP驅動的實體書店應當尋求自身文化IP的“一源多用”,[27]在多領域的合作中搭建起多樣態的拓撲網絡,并借由這些節點和連接關系推動IP價值的最大化。目前不少實體書店都圍繞自身的經營理念,嘗試與不同行業進行跨界整合,如誠品書店將圖書、餐飲、畫廊、出版、展演、文創產品等融為一體,在專業的選品與藝術的關懷之中體現誠品文化的精髓。而日本蔦屋書店不僅組合了多種業態,更將“家電”與書店進行結合,如在美容書籍旁放置美容儀,或在唱片區開辟出B&O店中店等,甚至還跨界房地產行業,力求為讀者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以“生活方式提案”的定位重構書店空間。實體書店還可以嘗試以IP授權的方式聚合不同領域的IP元素,如上海的“但是還有書籍”書店引入人物、游戲、動漫等各類文化IP,不僅形成了強大的引流效應,還在IP的碰撞交織中構筑起書店多元的文化生態,形成書店自身獨特的文化標簽。
其次是書店圍繞文化IP形成媒體矩陣。IP價值得以發揮的前提是能夠吸引粉絲聚集,并刺激粉絲進行消費,[28]而互聯網則為實體書店文化IP搭建了一個有效的傳播平臺,書店應當借助社交媒體以及多種媒介形態來進行IP營銷,不斷挖掘粉絲的消費潛力。如單向空間秉承“分享”的經營理念,對外搭建了豆瓣、公眾號、APP及微博等新媒體矩陣,對內則成立了“單談”“單選”“單讀”“單廚”等一系列品牌,并制作了網絡綜藝《十三邀》,兼顧內容傳播與書店品牌建設,有效促進了讀者與書店之間的良性互動。通過媒體矩陣的建立,空間得以從傳統的地理維度抽離出來,從而形成卡斯特所說的多維時空交織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實體書店需要在這種可延伸的、無邊界的媒介空間內通過多方位的媒介布局來完成對自身文化IP的塑造與傳播,進而對消費者的認知與記憶產生積極影響,為書店積攢更多的忠實讀者和積累更好的口碑。
(二)實踐與表征:文化IP的地方詮釋
實體書店文化IP的建構不僅停留在“空間”層面,還應體現為對“地方”的詮釋。地方是意義和注意力的中心,是由跨越時空的社會交往及其所積淀下來的社會意義構筑而成的。[29]作為城市中重要的文化空間,實體書店的文化內涵同樣也蘊含著作為區位(local)、場所(locale)以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綜合性的結構化意義。[30]如同“先鋒書店”在讀者的直接經驗與媒介化經驗的雙重建構下,已成為南京城市文化的代名詞,書店若要打造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文化IP,既需要以書店空間作為承載地方經驗的載體,又需要通過表征不斷延伸自身的地方意義,在此基礎上,書店與讀者才能夠形成一種更為緊密的聯結狀態,進而建立起讀者的情感認同,形成具有影響力的文化IP。
1.地方實踐:塑造認同的具身體驗
媒介地理學認為,人既是意識主體,也是身體主體,既通過思維認知,也通過身體進行認知。[31]實際上,地方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身體,通過具身實踐,客觀的表象空間得以被內化為“身體—空間”的耦合關系,[32]并對地方認知形成了更為深刻的影響。實體書店這一空間除了視覺吸引之外,還應通過獨特的沉浸體驗和互動分享,以感覺和經驗的綜合協同調動來打造書店的地方特質,從而形成讀者對書店IP的認知、理解以及認同。
首先,充分挖掘書店的“在地”潛力,通過打造沉浸式體驗,讓讀者直接置身于書籍、產品以及服務之中,從而將文化IP注入讀者內心。由于讀者對書店的綜合感覺以及主觀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具體的行為方式與知覺體驗產生的,[33]因此實體書店需要通過設計良好的體驗環節來營造一種“沉浸感”,即個體達到最優體驗的心理狀態,從而激發讀者與文化內容保持關系的意愿。[34]這種沉浸感的打造可以合理利用書店的“在地性”,讓知識分子、學者、作家、讀者之間相互聯結,[35]在打通“人—書—人”的基礎上,凸顯實體書店對人與文化的連接作用,重建書店對于人們精神生活的“啟蒙”功能。如日本的森岡書店秉持著“一冊一室”的運營理念,會圍繞當日所賣書籍重新設計書店空間,并舉辦相關展覽講座。如店內售賣《多肉植物圖鑒》時,書店便會變成一家“多肉植物店”,涉及服裝、食物等主題,書店還會變成“服裝店”“蛋糕店”等,書中世界在小小空間內得到了無限放大,讀者也不再以旁觀者的身份抽離于書籍,而是全方位感知文學的魅力,在體驗中得到對書店文化的強烈認同。
其次,實現實體書店與讀者的多元互動,促進地方意義的生發與表達。讀書會、講座分享、主題活動等不僅是實體書店增加經濟收益的手段,更是書店得以形成差異化風格的有效路徑,書店應當把握“實體”的優勢,圍繞IP開展豐富的在地活動體驗,從而實現書店的文化內容輸出與生活方式的倡導,提升實體書店的價值。上海海派書房作為國內首家以“海派文化”為主題的書店,舉辦了海派文化講堂、海派文創秀場、海派圖書展場等一系列活動體驗,形成了獨特的在地文化IP。可以看到,書店的文化IP建構需要依托地方資源,打造獨具特色的文化活動,如讀書交流會、講座、特色展覽、沙龍等,使實體書店與地域氣質進行融合交匯,從而讓書店這一獨特的文化空間成為人與人、人與文化、人與地方的連接中樞。
2.地方表征:獨具特色的文化符號
建筑藝術與文化始終存在著同構關系,杰出的建筑空間能夠通過自身的藝術風格、空間陳列喚起審美者從物質空間到情感共鳴的審美體驗。[36]因此,書店也需要重視文化符號的選擇組合,并將其作為一種地方意義的表征,形成差異化的文化IP。
這種地方表征首先體現在書店對地方文化主題的呈現。“主題”本意是文學、藝術作品思想內容的核心,實體書店作為城市的文化地標,其理念與城市文化始終是相互交融和相互型塑的,營造地方文化主題能夠在為城市注入更多活力的同時,也為書店賦予特定的文化意義,為書店的文化IP注入更多活力。在打造主題的過程中,書店需要注意關注個體的在地經驗與情感,一般而言,讀者在進入書店之前,腦海中會預先存在與此地相關的圖像、文字或音視頻等文本記憶。因此,書店選取以代表地方意義的符號元素作為表征時,這些意象便能以互文的方式喚起人們腦海中的記憶,從而使讀者產生微妙的認同感。
其次,書店文創產品的符號呈現也是實體書店建構文化IP的重要一環。目前實體書店與文創產品的結合已成為標配,圍繞書店理念提煉有價值的文化符號,并融入到文創產品的設計中,成為書店突顯自身文化特色、延伸文化IP理念的重點。文創產品是文化、功能、場景、美感等諸多元素的融合呈現,以文創產品推動文化IP的打造與傳播,首先需要選擇合適的文化內容,如杭州曉風書屋選擇以豐子愷藝術為原型,開發了鎮尺、書簽、筆筒、日歷等一系列文創產品,將“子愷藝術”打造為書店獨特的文創IP,體現出曉風書屋所代表的杭州氣質;其次,文創產品需要不斷創新文化IP的載體,即選擇合理的產品形態來承載IP內核,如西安萬邦書店深入挖掘關中文化,打造了限量的粗布系列文創;單向空間則圍繞書店品牌,開發了自有文創《單向歷》。目前實體書店開發的文創產品具有多樣化的類型特征,但書店應極力避免盲目開發帶來的同質化問題,既要注重文創產品的在地性以及與書店文化的一致性,也需要注意審美性與實用性的統一,滿足讀者理性與感性的雙重消費需求。
四、結語
書籍,承載著人類文明,是賦予人類生命永恒價值的重要途徑之一,而實體書店則是人類靈魂與情感的棲息地,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象征與精神地標,是人類綜合的精神文化消費場。面對閱讀方式的數字化以及書店的網絡化、同質化等現象,諸如先鋒書店、誠品書店、西西弗書店等部分實體書店已經開始以打造獨特的文化IP來探索實體書店的創新發展。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實體書店的IP化轉型,既有利于提升書店的文化輻射力,也有助于加強實體書店的文化價值轉化,即促進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37]因此,本文試圖從空間與地方、媒介的干預與表征兩組張力關系入手,為實體書店的文化IP建構提供了四條路徑,以空間的傳播與呈現以及地方的實踐與表征共同作用于文化IP傳播力與影響力的有效提升。
借助文化IP優化內容供給、賦能業態升級,從而實現實體書店的轉型,既是對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效統一”的踐行落實,也是對當前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訴求的積極響應。在未來,實體書店構建良好的文化IP,切需緊緊圍繞實體書店的閱讀文化建設,以用戶需求與技術發展為驅動,促進線上線下的深度融合,打造高質量、個性化的書店文化體驗,從而推動實體書店的轉型升級,實現良性、可持續發展。
注釋:
[1]趙慧.下一代書店[M].上海:東方出版社,2018:184
[2]國家新聞出版署.出版業“十四五”時期發展規劃[J].中國出版,2022(3)
[3]劉益,謝巍,等.實體書店扶持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5:71-72
[4]吳軍.文化動力——一種城市發展新思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
[5]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麥克盧漢精粹[M].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6,428
[6][20]夏德元,寧傳林.城市空間實體書店的功能再造與價值回歸[J].編輯學刊,2020(1)
[7]國家新聞出版署.第十八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成果發布[EB/OL].(2021-04-26)[2021-06-22].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80/75981.shtml
[8]李沁.沉浸傳播的形態特征研究[J].現代傳播,2013,35(2)
[9]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M].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465
[10]騰訊互動娛樂.騰訊程武:泛娛樂探索不變的三原則[EB/OL].(2016-03-25)[2021-06-22].http://up.qq.com/webplat/info/news_version3/7694/22238/22239/m14327/201603/444892.shtml
[11]騰訊網.2018中國文化IP產業發展報告[EB/OL].(2018-09-25)[2021-06-22].https://cul.qq.com/a/20180930/011408.htm.
[12]劉士林.都市與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J].江海學刊,2007(1)
[13][27]向勇,白曉晴.新常態下文化產業IP開發的受眾定位和價值演進[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4(1)
[14]陳瓊.文化IP:在無形資產中創造文化價值[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7:3
[15]陳育霞.諾伯格·舒爾茨的“場所和場所精神”理論及其批判[J].長安大學學報(建筑與環境科學版),2003(4)
[16]劉珊.環境、類型、精神——建筑外部空間設計的核心問題[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09(1)
[17]張萱.以培養閱讀習慣為核心的知識傳播空間——智能時代下實體書店作為公共閱讀空間的發展路徑[J].出版廣角,2019(8)
[18]李強.現代性中的社會與個人——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述評[J].社會,2000(6)
[19]董慧.秩序與活力:城市文化空間的意義構建[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32(4)
[21][31]袁艷.當地理學家談論媒介與傳播時,他們談論什么?——兼評保羅·亞當斯的《媒介與傳播地理學》[J].國際新聞界,2019,41(7)
[22]張一兵主編.社會批判理論紀事[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180
[23]張梅蘭,杜怡卓.轉向知識的想象:當下實體書店的空間生產[J].人民論壇,2021(3)
[24]劉鳳云.市廛、寺觀與勾欄在城市空間的交錯定位——兼論明清城市文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5)
[25]原研哉.設計中的設計[M].朱鍔,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75
[26][29]保羅·亞當斯.媒介與傳播地理學[M].袁艷,譯.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0:64
[28]張錚,陳雪薇.“云端”之上:實體書店的現實困境、存在價值與發展方向[J].出版發行研究,2020(8)
[30]R.J.約翰斯頓.人文地理學詞典[M].柴彥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13
[32]張震.“回到運動本身”的具身化研究[J].體育與科學,2015,36(5)
[33]Middleton J.Sense and the city: Exploring the embodied geographies of urban walking[J].Social &Cultural Geography,2010, 11(11)
[34]Theotokis A, Doukidis G.When Adoption Brings Addiction: A Use-Diffusion Model for Social lnformation Systems [A].America: lC1S 2009 Proceedings,2009:254-276
[35]雅倩.書見:30位獨立書店者說[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118-119
[36]黎明.“互聯網+”時代實體書店的多維空間生產[J].現代出版,2017(5)
[37]侯德賢.城市文化功能空間構成及其治理探析——基于城市文化生態系統的視角[J].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5,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