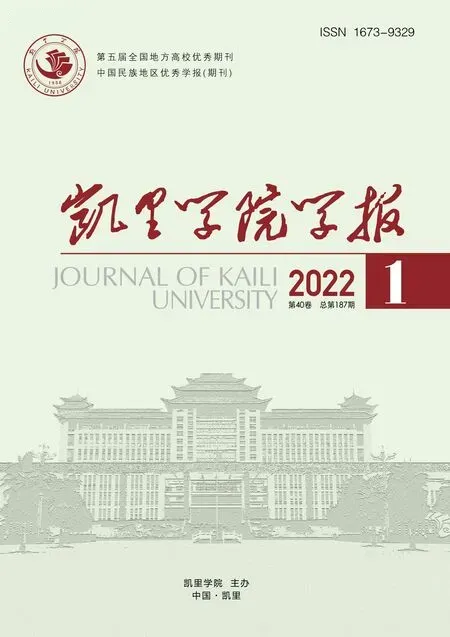論苗族花山節的文化特征
羅 軍
(貴州財經大學,貴州貴陽 550025)
一、前言
花山節是苗語西部方言區苗族最隆重、活動地域最廣、參加人數最多的大眾傳統節日之一,凡是操這一方言的苗族地區,都有這一節日流行。苗族花山節多在每年春節之后舉行,也有在農歷七月份舉行的。對于花山節的名稱,各地的漢語稱謂不盡相同,他們根據這一節日的形式,賦予“踩花山”“跳花山”“跳花”“踩山節”“跳廠”等不同的稱謂,但都不能直接表現花山節的文化內涵。“花山節”,苗語稱為“nghouk daox”,根據相關學者研究,應為“祭山節”之意。①羅興貴:《論苗族花山節的起源及社會文化功能》,載于內部刊物《苗侗文壇》,1999年第2期。
苗族花山節由來已久,據《永寧廳縣合志》寅卷載:“每年正月初旬,椎牛釃酒,約會于高埠,名曰跳山,夜聚曰跳月。”清愛必達的《黔南識略》卷一載:“每逢孟春,合男女于野,謂之跳月,擇另壤月場,以冬青樹一木植于地上,綴以野花,名曰花樹,男子皆艷服,吹蘆笙,踏歌,跳舞,繞樹三匝,名曰‘跳花’。”《貴州通志·土民志》載:“苗人,每年于正月十一、十二、十三日,男女裝束一新,覓高埠敞地,植冬青其上,曰‘花樹’。女兒持布一端,互相牽引。兩少年吹笙其前,作鳳鸞和鳴之聲,左右舞跳為節。女則隨其而緩步作半圓繞之,曰‘跳花’。十三日完,鳴爆竹,倒花樹。”此后有關花山節的漢文文獻逐漸增多,但很多都和上述記載大同小異。
至于苗族的口傳文獻,則多為對花山節來源的敘述,且因地域差異、方言土語差異而不同。譬如流傳于貴州省六盤水市一帶的苗族傳說敘述,明朝中葉,統治階級在洞庭湖一帶圍剿苗族,苗族人民被迫遷到湘、桂、黔邊的雷公山居住。到了清朝又被朝廷派兵圍剿,苗族人民奮起反抗,相持了二十余年。后來由于清軍要攻打太平天國,被圍苗民才趁機從雷公山突圍出來,往黔西北遷徙,突圍的這天正好是農歷二月十五,為了紀念這一天的艱辛和勝利,當時的三位族老議定,在每年的這一天讓大家都來聚一聚,歌舞歡慶。①馬貴林:《苗族跳花坡的起源》,載于內部資料《水城文史資料》,1989年。
流傳于黔西北一帶的苗族傳說敘述,過去苗族居住的地方比較富饒,后來異族部落羨慕苗族居住的這塊土地,派兵來搶占,于是爆發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戰爭從雞年②雞年即十二地支中的酉年,每十二年作為一個輪回。在此,苗族古籍中不是一個確定的年份,下文中生肖年份、月份均同此。開始,打了77年,至雞月③雞月為五月,參見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西部苗族古歌》,《花山節的來歷》,197-199 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初五日,苗族部落戰敗,他們撤離家園,向外地遷徙。第二年,為了紀念陣亡將士,決定在五月初五這一天舉行祭祀活動,他們登上高山,眺望自己美好的家園。此后,每年農歷五月初五都要舉行一次祭祀活動[1]。流傳于苗族滇東北方言地區的《“阿儀鏖”歌》這樣唱道:“十二支系苗族開拓了直米利大平原,建立了勞錮、勞鎢兩座城。蕩利莫大平原呵,一派景致像日出,生活美好似日升,天下太平人安康,人心安穩如同簸箕箍。天狠也有軟弱時,時到猴月挨雞月,蹈家與苗家起戰爭……蹈家來爭苗家地,蹈家苗家爭地盤,整整打了一輪甲子年,從雞年打到雞年,整整打了十三年。苗家子孫受害慘,苗家人馬傷亡多……苗家族長對眾說,打仗不避熱,當兵擋不住寒風,戰爭將會害兒孫。咱遷往篤秋地才不妨礙他人手,咱遷往篤秋地才無人跟隨來……為了擺脫格炎敖孜勞的暴戾,大伙‘阿作’來歡跳……‘阿作’回過頭眺望,留念失去的直米利、蕩利莫好地方。回頭眺望直米利,冰涼淚水如泉涌,看著蕩利莫大家放聲哭,只好‘阿作’轉圓圈,十二支苗家‘阿作’根由從此起。”[2]
流傳于云南省金平縣一帶的苗族傳說敘述,相傳在遷徙途中有一對夫婦失散了兩個孩子,多年得不到消息,夫妻倆為了要找到孩子,就商議在高山上豎起了高達10余米的花桿,并在花桿上掛上了青色、藍色和白色的麻布條,在花桿下放2瓶酒,號召民眾每年的正月初二到花桿下游玩。消息傳開之后,人們從幾十里甚至上百里的地方趕來參加,夫妻倆終于在人群中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全家得以團圓,后來逐漸演變成節日。從不同地區不同方言的苗族對花山節的口傳記述來看,苗族花山節的口傳資料非常豐富,反映了不同的地域特點和文化特色。
我們知道,苗族花山節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與它的文化生態結構密不可分。從各地有關的花山節起源傳說來看,其文化生態構成大約可以分為歷史文化生態、祖先崇拜文化生態、生育文化生態、農耕文化生態、婚姻文化生態、服飾文化生態等多個方面,它們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就像生物界一樣,完全依賴于各種文化為它提供服務,而一旦其中一種文化生態受到破壞,必會對其帶來嚴重的影響。
二、歷史文化生態
苗族是我國歷史比較悠久的少數民族之一,據《苗族簡史》載:“在我國長江中下游和黃河流域一帶,很古的時候就生活著很多原始人類,他們經過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過艱辛的勞動,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漸形成了部落聯盟。這個部落聯盟叫‘九黎’,以蚩尤為其首領。”[3]從苗族的歷史來看,苗族先民曾經過大大小小很多次遷徙,可以說,遷徙是苗族歷史的主要活動和重要組成部分。從傳說中的蚩尤和黃帝開始,苗族就經受了無數次的戰爭與失敗,迫使苗族先民離開了原來的地方,開始進行幾千年不斷地遷徙。在這不斷地遷徙過程中,為了讓子孫后代不要忘記自己的歷史,他們便把自己的歷史以節日的形式構筑在人們的生活之中。如侯健和王萬榮收集整理的《花山起源之歌》就是這一節日歷史生態的反映,歌中這樣敘述:“話說遙遠的上古/苗家住在黃河壩上/苗王名叫蒙孜尤/是他領導真有方/人人生活不用愁/不知哪樣叫花上……不為別的什么事/只因黃帝心太黑/強占苗家好地盤/村村寨寨都遭殃/孜尤率領我苗兵/攻克黃帝八座城……苗人會戰不會防/苗田苗地被強占/黃帝張弓又射箭/孜尤中箭身陣亡/苗兵心散無首領/方從黃河遷長江/苗人會攻不會守/苗田苗地被霸完/黃帝揮刀又舞劍/孜尤被刺砍了頭/苗人傷心無處去/方從河南逃江西/族長心里多憂愁/眼淚悄悄心里流/背著大刀上山去/砍下楓樹插壩上/將事告訴眾苗人/這是苗族踩花山……”[4]又如,流傳于六盤水苗族地區的關于花山節的來源這么傳說,在明朝年間,統治者對苗族進行殘酷的鎮壓,苗族被迫遷徙到湘、桂、黔邊的雷公山居住。到了清朝的時候,統治者又對他們進行圍剿。后來由于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調兵攻打太平天國,苗族才突出重圍。人們為了紀念這一天的勝利,商定每年的農歷二月十五這一天,大家來相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苗族的花山節[2]240-243。除此之外,許多地方的花山節起源傳說,都或多或少地與苗族的遷徙歷史有關聯。
關于苗族的戰爭與遷徙,古代的漢文文獻也多有記載。如《史記·五帝本紀》載:“軒轅之時……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之后便是“竄三苗于三危”。可以說,苗族遷徙的歷史文化生態,是苗族花山節文化生態的主體成分,是它的基礎。
三、祖先崇拜文化生態
眾所周知,苗族普遍認為萬物皆有靈,在生活中崇拜祖先和自然。在人們的觀念中,鬼和神是不分的,鬼是祖先的一個靈魂。一般認為,老人死后,有一個靈魂回到祖先的發祥地和自己的祖先在一起,一個靈魂回到墓地看守他的家園,保佑子孫和家業,如若得不到祖先的保佑,將使后人致病甚至家破人亡。因此,祭祀祖先是苗族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這項活動在苗族地區已被演繹成一種文化生態植入到花山節文化之中,以警示后人。例如六盤水苗族在舉行花山節時,先將雞、酒祭奠花樹,再由兩名蘆笙手載歌載舞,一名歌師唱著酒令,另一人捧一段紅布,眾人把花樹請到花場,繞場三圈,然后栽到花場中央。寨老和主辦人家坐在花樹下,數百對蘆笙手圍繞花樹,奏起肅穆的樂曲,踩著端莊的舞步,長轉不止。①王建湘等:《三口塘苗族跳花節》,載于內部資料《水城文史資料》,1989年。而長順縣廣順的苗族在舉行這一活動時,先砍一棵最好的竹子,然后在竹子的頂端掛一小塊紅布,齊胸處掛一把馬刀,下面擺一張小桌,放上四碗酒。寨老喝完酒后,用苗語念咒。然后宣布任命當年花場場長,新任場長要半跪著從寨老手中接過寶刀。寨老指定兩位老人先在竹竿前吹奏一曲蘆笙,這時人們才從四面八方涌向花場,圍著竹竿正反各跳三圈后,再分堆來跳。①貴州省志民族志編委會:《民族志資料匯編》(第二集),1986年,內部資料。花溪區苗族在跳場開始前,由組織者挑選童男童女各六名,男孩子手拿小蘆笙,女孩子拿糯米飯、自家釀的酒、雞和豬頭,在組織者的帶領下,圍繞竹竿按順時針走三圈。然后把這些食品放到竹竿下敬供。之后,跳場才正式開始。[5]從上述的儀式程序來看,活動前的祭祀是必不可少的,體現了苗族對自己祖先的虔誠。而這個祖先——花樹(竹或冬青樹等),不是單一個體家族或家支的祖先,它是整個民族或氏族的共同始祖、氏族長,花樹在此是全民族祖先靈魂的象征符號。它在這里是一個民族或氏族加強團結的一種精神力量。
四、生育崇拜文化生態
在原始社會,由于自然的(如疾病、各種災害等)或人為的(如戰爭等)因素導致人口減少,這時,人們考慮得最多的除了生存以求得生命的延續外,就是關于種、氏族和部落的繁衍問題。因此,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序言中指出:“歷史中的決定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花山節中的生殖文化生態,是花山節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許多儀式和起源傳說,與人們的生育有比較多的聯系。例如在普定縣,花山節活動結束以后,組織者要找一個父母雙全,有兒有女的男子做代表,再請幾個年輕人把“花樹”扛上送到無子女人家。一路上要放鞭炮,吹嗩吶。這家人看見以后馬上把門關上,送花樹的人到了門口,叫開門,屋里的人問:“你們是什么人,來這里有什么事?”送花樹的代表說:“滾進不滾出,滾進主人大堂屋,堂屋裝不下,拿去買田又買壩;買塊大壩好跑馬,買塊大田好喂蝦;買的好馬跑千里,喂得魚蝦重千斤。”這時眾人一起說:“祝你家發財又發富,明年生個胖娃娃。”[5]安順舊州一帶的苗族在跳花結束的那天,等到倒花樹的時候,大家爭先恐后去搶花樹的枝、葉,有希望人丁興旺、五谷豐登之意。③貴州省志民族志編委會:《民族志資料匯編》(第二集),1986年,內部資料。有的地方還把花桿(竹做的)剖開,做成床墊鋪于床上,說這樣已婚未生育的年輕人就能生育。流傳于納雍一帶的苗族認為,過去人間沒有花樹,花樹是天上長的,后來飛鳥去游玩,碰到花樹種子,落下生長在半空中,成為第一棵花樹。之后,鳥雀把花樹種啄落到地上,在地上長大開花,成了第二棵花樹。有一對苗族青年在花樹腳對歌,談情說愛,結為夫妻。可幾年后沒有生男育女,于是他們商量把花樹移到大草壩中間。花樹栽好后,兩人圍著花樹吹笙跳舞,求花樹給他們送兒女。不久,這對夫妻真的生下了兒女。從那時起,人們相互仿效,逐漸成俗。④政協納雍縣委員會:《納雍苗族》,2005年,內部資料。歷史上,苗族是一個飽受戰爭苦難的民族,在長期的征戰與遷徙過程中,人口的銳減(苗族《戰爭與遷徙》唱述,血腥戰爭打了九年,兩軍將士廝殺十載;鮮血染紅黃水河邊,血光映紅渾水河畔;兵馬尸橫九十九個平原,將士骨拋八十八道山灣)是他們面對的首要問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不僅可以延續自己的生存,而且還可以擴大自己的力量,增強同外族抗爭的能力。于是,在苗語西部方言區苗族人民共同歡度的節日里,增添生育生態文化這一要素,成了歷史的必然。人們通過祭祀花桿,以期得到祖先的保佑,從而人丁興旺。正如流傳于云南省威信縣苗族地區所傳頌的《花山歌》一樣:“花桿要送到哪里?送到婆婆神龕上,世間人拿去繁種;花桿要送哪里去?送到公公的神龕,世上人拿去繁衍。”
五、農耕文化生態
人類要生存,衣食住行是重要的生活資料保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農業開始從其他產業中分離出來,成為古代社會的主要部門之一。漢文文獻記載,早在五千多年前,苗族的先民就在長江及黃河流域一帶繁衍生息,辛勤勞作,“蒙博婁拓地開荒,在滔滔黃河岸邊,開拓了丘丘良田;蒙尤婁辟地開疆,在滾滾渾水河畔,開墾了壟壟沃土”,反映了苗族先民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民族,農耕生態文化成為花山節文化的主要文化構件。范勇、張建世說:“農耕民族,常常在農業生產的開始和結束(收獲)時進行活動,舉行這種活動的目的和背景比較復雜,既有對農業豐收的渴望和企求,也有對生活的喜悅,對自然環境與生態及人自身的生產方式的調適和平衡,等等。”[6]苗族的花山節,大都是在春播之前的正月間或秋收之前進行,其主要目的是企求來年五谷豐登。安順、普定一帶的苗族民間還流傳有“苗族不跳花,谷子不揚花,苗族不跳場,谷子花不揚”的諺語,可以看出,苗族舉行花山節活動,有祈求五谷豐登的內容。流傳于織金縣的《青山花場的傳說》敘述,有一年天干,已經抽穗的秧苗快枯死了。苗家凡是能動的都上山找水源,一天、兩天、三天,全都失望而歸,有一個叫楊谷花的姑娘,獨自繼續在青山上找水,她找了一天、兩天、三天,餓得再也走不動了,最后倒在一塊巖石上睡著了。睡到半夜,她聽到石頭下面有一陣淙淙的流水聲,高興得連夜摸下山來,帶領大家打鑿巖石,連打了七天七夜,終于把巖石打穿,一股清清的泉水奔流出來,秧苗全都得到了澆灌,正常地揚花了,苗族熱熱鬧鬧地慶祝了一番。①織金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織金縣卷》,1988年。其實,很多地方的苗族花山節,都是預祝當年風調雨順,獲得好的收成。由此可見,苗族花山節活動,是農耕民族農事活動的一種反映,帶有比較濃厚的慶祝色彩。
六、婚姻文化生態
苗族花山節也和其他節日一樣,不是單一的一種文化生態類型,它往往是很多種文化生態類型雜糅在一起,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節日文化生態,即由多種文化生態構件組合在一起的文化生態集合。除了上述文化生態元素,婚姻文化生態也是其主要構件。我們知道,苗族過去通婚都要在本支系(本文化圈)中進行,嚴禁與其他支系通婚,以致形成了一個一個的小婚姻圈,人們只能在這個婚姻圈內進行婚配。但由于歷史原因,他們居住較為分散,相距較遠,年輕人要相互認識了解,只有靠農閑時的節日活動,于是,這類節日就成了他們相互認識、相互了解的良好平臺。“晚上,老的小的圍著一堆堆篝火談天,青年人大都和相好的,一群群、一隊隊地敘唱著衷腸,或是搶花背、討信物、嬉笑打鬧。男青年以搶得的花背越多越榮耀,女青年則將所有花背穿上,一件件脫給那些她認為可以信得過的小伙子,直到最里層的一件花衣為止,到了東方發白這些花衣將安然無恙地還到每個姑娘手中。”②王建湘等:《三口塘苗族跳花節》,載于內部資料《水城文史資料》,1989年363頁。清鎮、平壩等地的苗族青年在跳花結束以后,女青年要請小伙子去家中吃飯,全寨姑娘作陪。三天之后姑娘送小伙子回家,男青年家也要招待一番。約一個星期后,姑娘把自己親手打的草鞋送給小伙子。過了兩周,小伙子要送姑娘一些錢。關系一般的從此成為路人。感情好的,兩三年后就定下終身。①貴州省志民族志編委會:《民族志資料匯編》(第二集),1986年,內部資料。因苗族支系繁多,方言土語復雜,文化樣式多樣,其婚姻文化也隨著支系的不同而五彩紛繁,形成了一幅燦爛的婚姻文化畫卷。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除了婚喪嫁娶以外,苗族姑娘的許多手工藝品一般難有展示的機會,花山節正好給她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場所。因此,節日這天,凡有姑娘的人家,都要傾其所有,給自己的女兒打扮一番。有些地區的花山節,姑娘要穿上所有自己親手繡制的衣裙,表示富有和自己心靈手巧,以博得男青年的歡心。姑娘們借此“偷師學藝”,看誰的衣裙漂亮,便暗記在心,回家后再制作比其更加漂亮的衣裙。所以,花山節可以說是苗族服飾文化的展覽盛會,是苗族姑娘進行手工藝比賽的場所,苗族服飾在這里得到不斷地升華和提高。
上述的歷史文化生態、祖先崇拜文化生態、生育文化生態、農耕文化生態、婚姻文化生態,是苗族花山節文化生態構成的五大要件,既相互交融,又相互獨立。如圖1 所示,它們以歷史文化生態為中心,為歷史文化生態服務。

圖1 苗族花山節生態文化結構圖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文化話語權的逐漸喪失,花山節中的這些文化生態已逐漸從它的附體中淡出,很少受到關注。筆者最近與一位苗族中年(從普定到貴陽打工,后在云巖區五里沖新建苗嶺小學,為該學校老師)交談時,發現很多這些文化生態他都無從知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張祺女士告訴筆者,說她到苗族村寨調查時,年輕人多已不了解這些文化,對花山節文化的失傳感到擔憂。有部分了解并熱愛花山節文化的年輕人在外打工回到家以后,組織苗族服裝表演隊在花山場進行表演,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沒有得到當地人的認同。
七、對花山節保護與傳承的幾點思考
花山節是苗族的重要傳統佳節,2007年已被確定為貴州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4年云南屏邊苗族花山節被確定為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充分證明了保護好這一節日文化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要保護好苗族這一傳統節日,使之能傳承下去,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注意對其每一個文化生態的保護。
第一,提高人們對花山節的認識,加強人們對花山節文化的了解。花山節是操苗語西部方言各支系苗族最隆重的傳統節日,每年都要按時舉行。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參加這一節日活動,僅是形式而已,年輕人借此進行交流活動,老年人借此走親訪友。花山節上的許多儀式和程序,已不被人們重視,更少有人關注原有的文化生態,加上當今的年輕人由于受到主流文化的影響,忽略或者忘記了自己的傳統文化。因此,要做好對花山節的傳承與保護,首先要提高人們對這一節日的認識,讓他們了解這個傳統節日的來源及意義,提高他們對花山節的了解。
第二,加強對花山節文化生態的挖掘工作。花山節的文化生態內涵非常豐富,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來看非常有限,大多只是一些關于這一節日來源的傳說,而且還比較零散和稀少,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挖掘整理。因此,各地相關部門,應該根據所屬區域的實際,把挖掘花山節文化生態納入工作范疇,切實做好挖掘工作。可以采用現代化的手段,如錄音、錄像、攝影等,對花山節文化生態作一個全方位的調查和記錄,讓下一代的人能了解花山節的文化,并能代代傳承下來。
第三,加強對花山節傳承人的調查與保護。花山節文化的傳承人是這一節日文化生態的組成部分,如果這一生態消失了,那它也就會很快地消失。這些人隨著年歲的增長逐漸離開我們,這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損失,也是苗族文化的一大損失。如對于花山節的來源,有散文體的傳說,也有韻文體的歌謠,而這些都掌握在一些年歲已高的老年人手中,一旦他們離開,這將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為此,有關部門特別是文化部門、民族事務部門,要加大對這些傳承人的調查和保護,制定保護措施,建檔立案。
第四,加強對花山節文化繼承人的培養,重構這一文化生態。隨著人們對節日文化保護意識的增強,有一部分年輕人開始認識到保護自己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并積極參與進來,這是一種好現象。但是,由于他們很多都不懂花山節文化,以致無從入手,加之這是一種活態文化,必須有傳承人來繼續傳承。因此,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對這些有積極性的年輕人進行培養,使他們掌握花山節的整個文化,成為新一代的文化繼承人。
第五,努力重建花山節文化環境,保護花山節文化的各種文化生態,鑄就民族文化自信。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文化自信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強調“堅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生態的保護和傳承,不僅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更應提高民族自信。
八、總結
習近平總書記2019 年9 月27 日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借鑒。”[7]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歷史上中華民族戰勝種種艱難險阻而薪火相傳的偉大精神瑰寶,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精神支撐。苗族花山節,是苗族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歷史文化生態、祖先崇拜文化生態、生育文化生態、農耕文化生態、婚姻文化生態、服飾文化生態等都包含在這一傳統節日文化之中,這一節日的衰亡,不僅是苗族文化一大的損失,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損失。因此,我們必須結合苗族地區各支系、各地域的文化實際,開拓創新,加強保護,讓這一傳統佳節代代傳承下去,繼續為苗族地區的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