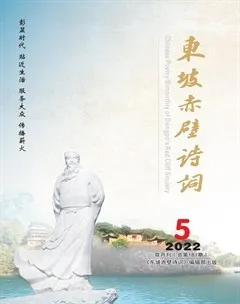論覓句
周嘯天
作文是從造句開始的。作文好的學(xué)生,無一例外是造句好的學(xué)生。造句,也是詩人的功課。唐代詩人于此非常用功——“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劉昭禹)、“吟安一個字,捻斷數(shù)莖須”(盧延讓)、“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方干)等,就是夫子自道。
當(dāng)興會到來的時候,假如你覺得沒有一首詩足以表達(dá)此時此刻的心情,這說明你已經(jīng)有了新意。一二詩句隨著詩思同時到來,古人稱之得句。最初的得句,往往就是詩中妙語、主題句。詩人往往據(jù)以定韻。其他詩句,則是在得句的基礎(chǔ)上,循韻覓得的,古人稱之覓句,今人或稱造句。
有人說:“造句乃詩之末務(wù),煉字更小,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此言大謬。“胡馬依北風(fēng),越鳥巢南枝”“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非漢人之詩乎?“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有風(fēng)自南,翼彼新苗”,非陶公之詩乎?豈不造句、煉字耶?只是得來不琢耳。
以琢不琢為分水嶺,詩句大抵分為兩種,一曰清詞,一曰麗句。清詞就是單純質(zhì)樸口語化的不琢之句,麗句則是密致華麗書面化的追琢之句。
一般說來,民歌偏于清詞,文人詩偏于麗句;漢魏陶詩偏于清詞,六朝詩人偏于麗句;李白偏于清詞,李賀、李商隱偏于麗句;韋莊偏于清詞,溫庭筠偏于麗句;李后主偏于清詞,花間派偏于麗句;李清照偏于清詞,周邦彥偏于麗句,等等。但也沒有截然的鴻溝,大體而言,古代詩人大多是清詞與麗句相濟(jì)為用,其效果往往相得益彰。
清詞是一種天籟,沒有太多的加工,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風(fēng)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李白)、“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岑參)、“多少恨,昨夜夢魂中”(李煜)、“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李清照),天然好句,得力于愛好口語和學(xué)習(xí)民歌。麗句則是錘煉、追琢、推敲、意匠經(jīng)營的結(jié)果,古人工琢句者,往往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如“風(fēng)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周樸)、“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同前),等等。杜甫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我們應(yīng)取這種態(tài)度。
“覓句”這個說法,好像詩句是現(xiàn)成地?cái)[在那里,只待詩人去找到就是。就像羅丹論雕塑,說雕像本來就在石頭里,只需將多余的部分剔除就是。像是大言欺人,其中也有妙理。古人形容覓句就像捉貓似的:“終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覓不得,無可奈何。然而,當(dāng)它不請自來時,總不能讓它逃走。晚唐詩人唐求平時出游,得到詩句、聯(lián)語,即捻稿為丸,投大葫蘆瓢中,數(shù)日后足成之。李賀騎馬出門,從平頭小奴子,背古錦囊,得到詩句,即書置囊中。凡詩先不命題。及暮歸,始研墨疊紙足成之。我自己在旅途中,會隨時掏出手機(jī),用短信的方式,記錄突如其來的、讓我感到驚喜的詞語、句子或點(diǎn)子。對我來說,手機(jī)就是錦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