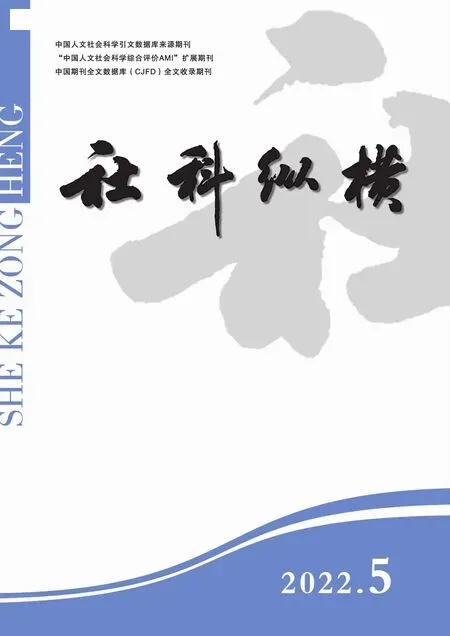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若干重要問題研究》
劉翠芬 賈素波
(包頭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內蒙古 包頭 014031)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若干重要問題研究》于2021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11章近50萬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維度、思想維度、邏輯維度、認同維度、心理維度和實踐維度,展開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全書將歷史和現實、事實和價值、圖示和本質以縱橫交織的方式,融為一個整體,從概念術語的解釋開始,在話語敘述上層層遞進,在邏輯脈絡中環環相扣,在主題凝練上突出特色,將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貫穿全書中,彰顯了學術研究的高度理論自覺、政治自覺和實踐自覺,全書兼具理論性、學術性和時代性高度。
一、在社會事實的研究中突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若干重要問題研究》一書充分揭示了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和現實的重要意義。該書從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高度,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宏觀視野下揭示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該書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經驗告訴我們,建構面向社會現實的引領中華民族進步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突出理論的先導和凝聚作用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勝利的法寶。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史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百年奮斗史。中國共產黨通過把握時代精神建立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高度的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引作用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國共產黨歷史同行的關鍵;中華民族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信仰也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
在這一理論視域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工作的“軸心概念便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現成的且最直接表述馬克思新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存在概念,就是馬克思提出的社會存在概念”[2]。
社會存在論涵蓋了該書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視野,構成了該書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為基礎的內核,說明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是有歷史和現實依據的社會事實”[2]。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各族群眾中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牢固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對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關重要。”[2]基于這樣的認識,該書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社會事實作為認識歷史上各個時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不同表現的依據,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和基礎作用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中介環節進行闡述。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社會事實包括社會層面上的“一切行為方式”,社會事實具有普遍性、外在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其內涵“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法律道德、社會習俗和文化傳統之外,還包含家庭和社會組織以及國家的根本制度,同時也包括各國的城市及居民分布情況、人口特點等其他方面”[3]。因此,社會事實不僅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象性的社會實踐活動相關聯,而且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的生產方式及交往方式有關。該書分層次、分階段和過程表述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識,涵蓋了從最初階段的抽象表象符號、發展階段的內在邏輯、鑄牢階段的真理性認識這樣一個完整過程,中華民族的實踐在此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該書在對諸多社會實踐中的社會事實進行分析時建構的認識論在全書中始終與唯物史觀的表述過程同步進行,實現了作者預定的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實踐相結合的雙重自覺的目標。在這樣的研究范式中,全書凸顯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的主體性向度和社會事實價值目標的意義,賦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中華民族爭取自由解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豐富深遠的內涵。該書構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反映論和“合力”生成論凝聚了社會共同意識和集體共同意識,引導和規約著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彰顯了社會事實是來源于、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的本體之維,強調了社會事實背后的整體性規范性道德性的形塑作用。
二、在歷史的話語中突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4]該書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為依據,認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有賴于中華民族對自己歷史的創造和貢獻,這種創造和貢獻與中華民族對自然、對社會的認識和改造是分不開的。這種改變自然和社會的活動,表現為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表現為對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這些活動概括起來說就是勞動和交往兩大類活動。因此,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的組成,不僅將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作為社會歷史延續的基礎,而且將精神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作為社會歷史延續的基礎,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是本源的、第一位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的一個最基本的思想。
該書不局限于把中華民族創造歷史的活動僅僅歸結為一般意義上的勞動,即體力和腦力的活動,而且將其歸結為馬克思提出的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即中華民族開展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活動。因為作為表現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和現實的活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不僅具有客觀性的歷史和現實的存在,也具有主觀性的自覺自主的創造。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人的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正是因為遵循社會發展的規律才能夠表現為推進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發展和成熟建立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之上,又有賴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實踐,因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體根據就在于中華民族本身,是由中華民族的需要和利益驅動的價值取向引領的。該書抓住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展、進步和成熟的主線,彰顯了貫通其中的價值取向的重要作用,表現了中華民族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長河中的自覺自愿。該書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價值取向是指在歷史和現實層面上由中華民族這一主體從整體需要、整體利益出發選擇和形成的價值立場和價值態度,具有影響中華民族歷史進程和現實發展勢態的導向作用。
該書認為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和現實活動的利益滲透性和價值滲透性,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觀和社會觀的層次和水平。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和現實活動中,各民族不僅要關注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合規律性,也要關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運行的合目的性,表現作為合理性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因而,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應當確立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和現實認識的解釋框架,也應當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評價以及確定其方向和目標提供根本的價值尺度。該書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在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指導下沒有離開對歷史事實的客觀、真實的敘述,也沒有離開對這個活動主體動機中價值取向動態的考察。通過肯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歷史觀和社會觀價值維度對認識維度的導向作用,進一步彰顯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的主體性和主體自覺性,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的視角更加多樣、全面。
三、在主題的敘述中突出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5]該書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在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題敘述中突出強調作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引領者、推動者和踐行者的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發展和成熟過程的經驗總結和規律性概括,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符合中華民族的成長規律,符合中國共產黨成長奮斗的歷史規律。1922年7月黨的二大宣言把“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作為民主革命綱領的重要內容。中共二大通過的《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把“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等7項列為“極力要求做的事情”[6]。此后,黨的文獻中頻繁出現“中華民族”一詞。在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百年奮斗中,中國共產黨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該書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呈現出的差異性和特殊性,認為中國共產黨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一貫邏輯和鮮明主題,就是對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的辯證把握。與此同時,由于一直牢牢把握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基礎作用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對統一性的引導,不僅依靠系統的體制機制支撐,而且牢牢抓住解決民族問題核心就是促進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物質基礎建設和民生改善,不斷夯實增進各民族共同性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引領,以“五個認同”推進各民族文化心理建設,有效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新格局、新局面的開創。該書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概念和實踐概念的豐富內涵通過中國共產黨不斷展現的主體性、能動性,不斷形成的現實性和對象性活動充分揭示出來,熔鑄在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進行的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之中。該書一再強調應該認識和理解中國共產黨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形成的新格局的重要意義,強調要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中,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在黨的理想信念、宗旨目標中認識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該書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全面的政治制度、厚實的經濟基礎、先進的思想文化的支撐,形成了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戰略布局和資源配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經成為復興民族主體性建設的強大動力和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