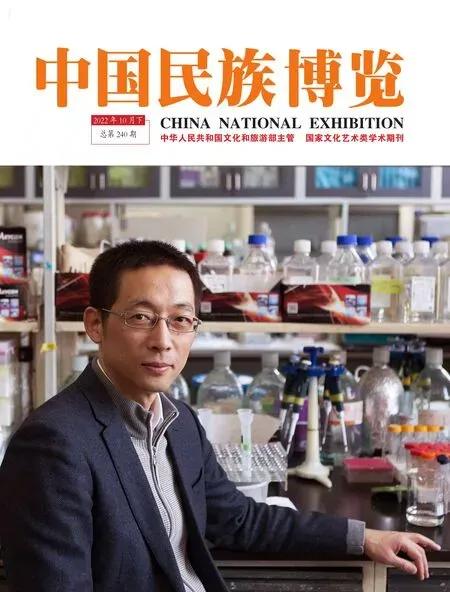敦煌俗文學故事《伍子胥變文》的敘事學分析
王 睿 竇佳琪
(1.吉林大學,吉林 長春 130012;2.內蒙古科技大學,內蒙古 包頭 014030)
一、敘事學與敦煌俗文學
(一)敦煌俗文學
敦煌俗文學的界定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 年,日本漢學家狩野直喜在其作品《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中提出了“俗文學”的概念[1];此后,胡適將敦煌卷子中的文學作品定名為“俗文學”,并且在作品《白話文學史·自序》中說明了俗文學資料的重要性;自20 世紀20 年代以來,鄭振鐸不斷深入研究敦煌俗文學的相關內容,并發表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中之中國小說與戲曲》《敦煌的俗文學》等文章,展示了敦煌俗文學的價值,并且指出敦煌俗文學并非敦煌文學的全部,“敦煌俗文學”一詞才逐漸為世人所用。
按照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給出的定義,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為學士大夫所重視,而流行于民間,成為大眾所嗜好,所喜悅的東西。敦煌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它包括了敦煌歌詞、詩歌、變文、話本小說以及敦煌賦五大類藝術形式,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1]”。
(二)敘事學
敘事學是在結構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敘事文本進行研究的理論[2]。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有關敘事學的理論就開始在法國文學研究領域岀現,例如, “敘述符號學”“敘事語法”等。而敘事學一詞首次出現是在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托多洛夫1969 年出版的《〈十日談〉語法》中,書中說道:“……這門著作屬于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于敘事作品的科學。”[2]
進入80 年代,敘事學的相關理論開始被逐步介紹到中國。1986—1992 年間,中國不斷對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敘事理論作品進行翻譯,并且在敘事學理論本土化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例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羅鋼的《敘事學導論》、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等[2]。此外,學者們也嘗試運用西方的敘事分析體系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進行敘事分析,進一步推動了敘事學理論的本土化。
(三)敘事學分析于敦煌俗文學故事的適用性
1.敘事學的研究對象
敘事學是研究敘事文的科學,在《敘事學》中,胡亞敏采用分類比較的方法為我們界定了敘事文的定義,她將文學劃分為敘事文、戲劇文學和抒情詩三類并進行比較:與戲劇文學相比,二者雖然都擁有故事情節,但敘事文存在敘述者以及以敘述者為中心的一套敘述方式;與抒情詩相比,它們都擁有敘述者,但敘事文擁有較為完整的故事情節。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得到敘事文的特征,即敘述者按一定敘述方式來傳達給讀者的一系列擁有完整情節的事件。
2.敦煌俗文學故事可用敘事學分析
敦煌俗文學故事需要滿足的條件是:1. 必須是敦煌俗文學 2. 必須是故事;前文中已經對敦煌俗文學的定義進行了說明,即敦煌歌詞、詩歌、變文、話本小說以及敦煌賦五類藝術形式,接下來將對這里的“故事”進行界定。
金榮華曾明確指出:“每一個故事必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情節單元。”情節單元包含人物、情節、環境三個基本因素,如果缺少了任意一個因素,那就不能稱為一個完整的情節單元。因此,人物、情節與環境亦是故事的三個基本要素,如若不能同時具有以上三個要素,那么就不能構成一個故事,只能被稱為事件。
敦煌俗文學故事雖多半簡潔短小,情節偏于簡單,但其具有“故事”的基本條件,即人物、情節、環境,除此之外,敦煌俗文學故事還包括主角內心矛盾與沖突、作者創作作品的目的以及給讀者的啟發等。這即意味著,敦煌俗文學故事滿足前文中敘事文的特征,可以作為敘事學分析的材料。
二、《伍子胥變文》的敘事學分析
(一)情節
1.《伍子胥變文》的情節構成分析
情節是故事結構中的主干,是人物、環境的支撐點,情節又可分為三個層次,最底層為功能,中間層次是序列,最高層為情節[3]。接下來將從功能和序列兩個方面剖析文本。
(1)功能
功能是敘事文結構分析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故事中最小的敘事單位[2]。俄國的民俗學家普洛普最早將這一概念從人類學引入文學文本研究。
他舉例說:
1.沙皇贈給好漢一只鷹,鷹將好漢送到了另一個王國;
2.老人送給蘇欽科一匹馬,馬將蘇欽科馱到了另一王國。3.巫師贈給伊萬一艘小船,小船將伊萬載到了另一王國。4.公主贈給伊恩一個指環,從指環中出了的好漢們將伊萬送到了另一個王國。
在上述例子中,角色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基本的動作并沒有變化,這些動作就是我們所說的“功能”。
顯而易見,在敦煌俗文學故事中“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伍子胥變文》中,如:
“……觀君艱辛日久,渴乏多時,不可空腸渡江,欲設子之一餐,吾家去此往返十里有余,來去稍遲,子莫疑怪。……”
其文字敘述很長,但其實功能就是魚人歸家為伍子胥取食。又如:
“……梁王聞吳軍欲至,遂殺牛千頭,烹羊萬口,飲食堆如山岳,列在路邊,帳設鋪施。……”
其功能則是梁王烹牛宰羊討好伍子胥。
普洛普還提出,“功能由其在情節發展過程中的意義來確定”,也就是說,功能的意義是依賴語境的,梁王烹牛宰羊討好伍子胥的目的可以是祈求生路,也可以是歡迎盟軍,只有通過上文語境“即發天兵,討伐梁帝”,我們才能夠確定其目的為前者。
除此之外,羅蘭·巴爾特還將功能做了更加細致完備的分類,他將功能分為兩大類,即為分布類(功能)與結合類(標志),如下圖所示:

這里我們主要討論分布類。核心功能也就是情節的既定部分,它在故事中十分重要,能夠決定情節的走向。如《伍子胥變文》中:
“……楚王使獄中喚出仵奢、子尚,處法徒刑。……遺語已訖,便即殺之。父子二人,同時誅戮。楚王出敕,遂捉子胥處,若為? ……”
便為核心功能,如若楚王沒有誅殺伍子胥父兄并且下令捉拿伍子胥,那么就不會有后續伍子胥逃亡、復仇的一系列行為。也就是說,若抽掉了核心功能,劇情就無法繼續發展。
催化功能則起著填充、修飾、完善核心功能的作用。它在敘述上起著加快或減慢話語速度的作用,有時甚至能夠阻礙事件的發展。如《伍子胥變文》中伍子胥逃亡路中叩門乞食遇其阿姊以及遭外甥追擊下咒阻攔都屬于催化功能。
《伍子胥變文》中存在著大量催化功能,為的是體現逃亡路途艱險以及伍子胥復仇之決心,使情節更加跌宕起伏,敘事更加曲折、生動、形象。
(2)序列
序列是由功能組成的完整的敘事句子,通常具有時間和邏輯關系。序列又可分為基本序列和復雜序列[2]。
所謂基本序列,便是只由三個功能組合而成的序列,這三個功能通常為起因、過程、結果。如《伍子胥變文》中,父兄被殺、禍及自身為起因;逃亡吳國、四處征伐為過程;成功復仇為結果。這便是最基本的序列,基本序列又可通過不同的方式結合,形成復雜序列。按照結合方式的不同,復雜序列可以分為鏈狀、嵌入和并列。顧名思義,鏈狀序列即一個序列的結尾便為下一個序列的開頭;嵌入序列意為將一個序列嵌入另一個序列之中;并列序列就是將同一層次的序列借助某種相似點作平行連接。
就《伍子胥變文》來看,其主要結構多以鏈狀序列串聯,如:
楚平王本為子擇婦,卻自納為妃(起因)—伍奢直言進諫,楚平王震怒(過程)—伍子胥父兄被殺,心懷仇恨,被迫逃亡(結果)
而這個序列的最后一個功能便是下一個序列的第一個功能:
伍子胥心懷仇恨,被迫逃亡(起因)—吳王收留,伍子胥心懷感恩,輔佐吳王治理吳國(過程)—伍子胥復仇成功,繼續效忠吳國(結果)
但其在內容補充上也使用了嵌入序列,如在前文所說“吳王收留,伍子胥心懷感恩,輔佐吳王治理吳國”與“伍子胥復仇成功,繼續效忠吳國”之間,故事插入了復仇過程的序列:
伍子胥發兵討楚(起因)—伍子胥指揮有方,十戰九勝(過程)—伍子胥大戰得勝,取楚平王骸骨施刑,祭奠父兄(結果)
如此鏈狀序列與嵌入序列相結合,既使故事具有條理性和連貫性,又做到了故事內容豐富、情節飽滿;既完整通暢地敘述了伍子胥逃亡復仇的故事,又充分地表現出了逃亡之路的曲折艱險,使得故事敘述更加形象、生動。
2.《伍子胥變文》的情節組織原則
情節的組織原則是指序列組合為情節的規律[2]。主要有兩大原則,一是承續原則,其主要包括時間連接、因果連接和空間連接;二是理念原則,包括否定連接、實現連接和中心句連接。
在《伍子胥變文》中,既有承續原則又有理念原則的應用,二者中最典型的分別為時間連接與否定連接。
首先,故事由楚王納為子婦為妃,伍子胥的父親伍奢諍言直諫,卻被處以嚴刑,伍子胥也因此被追殺。到逃亡路上遇到的許多人(打紗女、阿姊、娘子等)并且衍生出一系列劇情,這些配角以及劇情都在凸顯伍子胥這個“主角”報父仇的決心。然后寫伍子胥逃到吳國,借由吳國的兵力打敗楚國;最后寫到吳王的兒子夫差即位,卻不聽老臣言,伍子胥因之被殺,越國見吳國主要支柱已無,便出兵攻打吳國。整個故事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排列,沒有回想、倒敘的手法,使用了承續原則中的順時時間連接。
從理念原則的角度來看,故事又運用了否定連接。否定連接即序列逐步向對立面過渡,可以是由順境下到逆境,也可以是由逆境轉入順境。在《伍子胥變文》中,
“……南有楚國平王,安仁(人)治化者也。王乃朝庭萬國,神威遠振,統領諸邦。……楚之上相,姓仵(伍)名奢,……伍奢乃有二子,見事于君。小者子胥,大名子尚。一事梁國,一事鄭邦,并悉忠貞,為人洞達。……”為順境;
“……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大夫魏陵啟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遂遣魏陵,召募秦公之女。……其王見女,姿容麗質,忽生狼虎之心。魏陵曲取王情:“愿陛下自納為后。……”伍奢聞之,忿怒,……楚王使獄中喚出伍奢、子尚,處法徒刑,……, 楚王出敕,遂捉子胥處,……”為逆境;
“……子胥捉得魏陵,臠割捥取心肝,萬斬一身,并誅九族。子胥喚昭王曰:“我父被殺,棄擲深江。”遂乃偃息停流,取得平王骸骨。并魏陵昭帝,并悉總取心肝,行至江邊,以祭父兄靈。……”又為順境;
“……王賜子胥燭玉之劍,今遣自死。子胥得王之劍,報諸百官等:“我死之后,割取我頭,懸安城東門上,我當看越軍來伐吳國者哉!” ……”又為逆境。
這種由順境與逆境交錯的情節表現,讓整部作品高潮迭起,情節充滿戲劇性,最后伍子胥被賜死的橋段,更是讓人充滿憤慨之情。
(二)環境
1.《伍子胥》變文的環境呈現方式
通常我們認為環境是完全客觀的,它包含了三大要素:自然環境、社會背景、物質產品。它們在敘事文中的呈現方式不盡相同,胡亞敏的《敘事學》中根據環境在故事中的地位和形態列舉了三組對應的表現形式,即支配與從屬、靜態與動態、清晰與模糊,在這里我們主要從前兩個方面對《伍子胥變文》進行分析。
從支配與從屬的角度來看,通常情況下,情節在敘事文中占有主導地位,但以人物為中心或以環境為主體寫成的故事也十分常見。若故事中的環境所占比例超過人物和情節,那么便屬于支配式的環境;反之,若環境所占比例小于人物和情節,那么便屬于從屬式環境。很顯然,在《伍子胥變文》中,雖然有為數不少的環境描寫,但其所占比例遠低于情節與人物,因此,《伍子胥變文》中環境的呈現方式屬于從屬式環境。
從靜態與動態的角度出發,首先,這里所說的靜態與動態是就環境在故事中的空間位置而言的。靜態環境指的是故事在唯一的地點發展,動態環境則是指故事中人物所處的環境不停地變動。在《伍子胥變文》中,故事以伍子胥的經歷為線索進行環境轉換,由楚國到山澗再到潁水、川中、吳江、吳國,到了吳國之后又借用吳國的兵力攻打楚國。這種便是典型的動態環境——隨著人物的行蹤,背景地點不斷發生改變。
2.《伍子胥變文》的環境類型
根據環境在故事里的功能,以及它和情節與人物的關系,我們將其分成三種類型:象征型環境、中立型環境以及反諷型環境。象征型環境與人物、行動關系密切,具有較明顯的內涵;中立型環境與情節完全無關,只用作標志地點;反諷型環境與人物的行為不和諧或相對立。
《伍子胥變文》中存在大量的環境描寫,在逃亡過程中,伍子胥看到的不斷變化的地貌、風景,無一不體現了他面臨的惡劣環境,屬于典型的象征型環境。如:
“唯見江鳥出岸,白露鳥而爭飛;魚鱉縱橫,鸕鴻芬泊。又見長洲浩汗,漠浦波濤,霧起冥昏,云陰叆叇。樹摧老岸,月照孤山,龍振鱉驚,江沌作浪。……”
“至漭蕩山間,石壁侵天萬丈,入地騰竹縱橫。遙望松羅,山崖斗暗,蟲狼離合,百鳥關關,……”
這些環境描寫都具有表現人物心理、體現人物處境的作用。
除此之外,《伍子胥變文》中還存在著許多象征型環境,這些環境通過伍子胥所看到的,它們將伍子胥所經歷的惡劣環境與艱苦條件得到更加透徹的體現,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立體,讓人物內心的情感充分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更加真切地感受情節的發展與人物內心的想法。
(三)人物
敘事學理論中包含多種人物理論,形成了不同的分類方式。根據胡亞敏的《敘述學》,我們將關于人物的分類分為特性論和行動論兩種。
1.從行動論角度分析《伍子胥變文》中的人物塑造
從行動論角度出發,普洛普根據人物執行動作的情況將人物分為七種角色:對頭(加害者)、贈予者(提供者)、相助者、公主要找的人物及父王、派遣者、主人公、假冒主人的行動者。但是,在這種分類模式下,某一角色可能由多個人物擔任,同一人物也可能擔任不同角色。因此,格雷馬斯在普洛普分類的基礎上根據不同角色的功能將敘事作品里的角色分成三對,它們分別是主角與對象、助手與對頭、支使者與承受者。
在《伍子胥變文》中,主角為伍子胥,其追求的對象為獲得重用以及為父兄報仇;打紗女、阿姐、妻、漁人是助手,楚平王、吳王夫差是對頭;支使者即動力是為父兄報仇以及獲得重用,承受者是伍子胥本人。
2.從特性論角度分析《伍子胥變文》中的人物塑造
美國敘事學家查特曼《故事與話語》中堅持人物是由特性構成的觀點,他將特性界定為相對穩定持久的個人屬性。就如《伍子胥變文》中,伍子胥就是一個“忠臣”,這便是他的人物特性。但是,相同特性的人物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因此查特曼提出的概念具有局限性。因此,福斯特和埃溫分別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分類,在這里我們將根據埃溫的軸線法對《伍子胥變文》中的人物塑造進行分析。
為了避免過于簡單,埃溫在《敘事文中的人物》一書中提出了一種依照“一個連續體上的各個點”來表示的人物分類法,將人物分成三種軸線:復雜性、發展以及對內心生活的深入。我們這里主要針對復雜性軸線對伍子胥這個人物形象進行分析。
復雜性軸線講的從人物單一的性格特征逐漸變得復雜化,或者說是圍繞著一個主導的特性逐漸發展其他特性來塑造這個人物。
在《伍子胥變文》中,伍子胥的主導特性是“忠臣”,之后隨著劇情的發展,他不斷發展出新的人物特性,使人物形象不斷復雜化:父兄被楚王所殺時,產生了仇恨的特性;逃走過程中,產生了不安、吳國收留他,產生感激之情、夫差繼位后聽讒言,產生無奈。
這些特性隨著劇情不斷被發掘出來的同時,伍子胥這個人物形象也隨著劇情逐漸變得豐滿、栩栩如生起來。《伍子胥變文》根據復雜性軸線來塑造人物形象,讓讀者隨著閱讀的深入逐漸了解伍子胥復雜的人物形象,貼近讀者的接受心理,更加真實、生動地向讀者展現了一個恩怨分明、有情有義的伍子胥形象。
三、結語
敦煌俗文學故事雖然情節多半趨于簡單,但具備了敘事文的條件,其中的《伍子胥變文》更是變文敘事藝術的典范之作。本文從敘述學的角度切入,參照胡亞敏《敘事學》中的理論框架將敦煌俗文學故事《伍子胥變文》按照情節、環境、人物的順序系統地進行分析,挖掘出其獨特的敘事藝術,有利于敦煌俗文學的研究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