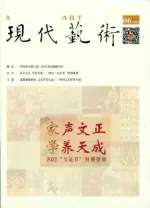語言是存在的家

《巴中民間語言》由上、下兩編組成,上編對巴中民間語言進行了論述,言及了語言的神奇與魅力,論及了川東北方言與川西方言的異同,以及《巴中民間語言表現形式》,最有意思的是,里面還附有《巴山情歌里的方言詞》,其中內含50首情歌。后面的《最巴中100句民間方言詞》《最巴中100句民間俗語》《最巴中100句巴中歇后語》讓人既忍俊不禁,又倍感親切。下編為《巴中民間語言集成》,通過巴中民間的方言詞、民間俗語、民諺、歇后語、謎語、順口溜,完全可以體驗到巴中民間語言的風貌和特色。
一
今年上半年剛收到陽云先生所著的《巴中風尚志》 《巴中山水志》兩部新書,兩部“大書”各30萬言,我還在消化之中,他又發來了他與其夫人陳俊合著的《巴中民間語言》的定稿,并囑我作序。
這三部厚重新著,是陽云、陳俊伉儷給故鄉的獻禮,體現了他們的文化情懷,我雖淺陋,倒也樂于從命。
多年來,夫妻二人筆耕不輟。他們對巴中的書寫,可謂不遺余力。兩人的文字都不是簡單地輯納,而是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華,有自己的視角和看法。兩人都是巴中文化的書寫者,也是研究者和宣傳者;既有對山川大地、民俗風情的歌唱,也有對人文和歷史的梳理和解讀。由此可見,夫妻兩人對巴中這片土地都“愛得深沉”。他們所寫的,絕大多數都是巴中的人和事,都是巴中的歷史文化、山川河流、草木動物。他們對家鄉的熱愛,從字里行間,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就在想,一個人對故鄉要有多么深沉的愛,才會傾注一生來做這件事?
我十七歲當兵入伍,在北方生活了二十二年,說句實在話,鄉音還是有所改,自己聽不出來,老家的人一聽便知。我曾經想寫故鄉,但就是因為少年離家,對故鄉了解不多,感受不深,所以提筆生怯。
陽云和陳俊傳遞給我的,無疑是“故鄉消息”,無疑是一個紙上故鄉。他們所書寫的山水、歷史、文化,是我所熟悉的,但又了解不深,大多流于傳說。他們的文字,無論是對歷史的書寫,對山川河流的描摹,還是對筆下人物故事的敘述,都變得可信,使我對故鄉的認識,有了“信任”的依憑。他們所寫的山水風物,每時每刻都在變化,都在呈現殊異之美,但會永存;而有些已存之數千年的東西——比如方言、風尚,卻正在消失。這些都是值得書寫和記錄的,也有人在做,但很少有人像他們那么認真、徹底和扎實。
二
作家一生都在與語言戰斗,想著怎么用語言盡可能準確地描繪這個世界,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我是一個以文字為生的人,對語言自然充滿無限的敬意。
1880年11月,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3個月,他在給普希金同時代的俄羅斯作家阿克薩科夫的信中寫道:“我承認,作為朋友我向您承認,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報》后,經常跪著久久祈禱上帝,愿上帝賜我一顆純潔的心靈,賜給我純正完美的語言,無邪無欲的語言,不惹眾怒的語言。”
他已寫完《卡拉馬佐夫兄弟》,五十九歲了還在祈禱,“我經常痛苦地發現,我連二十分之一想表達,甚至也許能夠表達的東西,都沒有表達出來。拯救我的,是鍥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總有一天賜予我力量和靈感,讓我更完整的表達,總之,讓我全部表述我的心跡和想象。”
所以說,即使再偉大的作家,也不會認為自己找到并駕馭了語言。因此語言是神秘的。它是一個獨立的生命體,有自己的色彩、個性和樣貌,同樣的詞句,不同的人說出來,會有不同的意味和韻致,相同的詞句,不同的人寫出的文章各有文采。除非錄音重放,人間沒有一段相同的話,除非抄襲,天下沒有一篇相同的文章。給一堆同樣的詞語,有人能用它寫出人間華章,有人卻只能寫出酸腐之文,即使一個人,因人生的階段不同,用相同詞句寫出的文章也會不一樣。
語言如人的基因,代表了他的出身、生活地域、家鄉的地理位置,乃至人生境況、境界、學識,一個人的品質也多在其言談中表現。
少小離家,鄉音無改。每個人對自己的家鄉話都是倍感親切的,沒有一個人能真正忘記自己的家鄉話,就像一個人不能忘記自己的父母兄弟、故鄉親情一樣。它是人之本,會像血液一樣供養我們的生命,伴隨我們一生。
文學其實是一種方言的呈現。方言按字面的意思來理解,就是一方之言。就世界范圍來說,每一個語種——英語、俄語、法語、德語、烏爾都語等都是一種方言,當然,漢語對于他們來說也是。而每一種語言又可細分為東西南北腔,山南海北調。
在文學創作中,方言自古就有運用。《詩經》中的《風》相對于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王畿”而言,就帶有民歌色彩,是周的十五個諸侯國的土風民謠,傳唱者也是多用各地方言歌唱的民間歌手,被視為《詩經》中最具文學精華的部分,故排在《雅》《頌》之前,后人將其與屈原的《離騷》相提并論,并稱“風騷”。在沒有“普通話”之前,作家的作品也是用廣義的“方言”創作的,《金瓶梅》用了大量山東方言,《西游記》中則有淮安土語,《儒林外史》用了安徽全椒話,《紅樓夢》則使用了南京和北京兩地的方言;而李劼人先生《死水微瀾》對成都方言的嫻熟運用,使其成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成熟的標志”。《尤利西斯》被著名翻譯家肖乾先生嘆為“天書”。喬伊斯就運用了拉丁語、古英語、中世紀英語、方言俚語和洋涇浜語,他將語碼轉換作為敘事策略,以用來顯示人物身份,表現語言優越感,以改善人際關系和談話氣氛。到后來,文學正是在“普通話”的影響下,造成了“同質化”,失去了文學的鮮活度和多彩性,以致韓少功先生用方言寫出《馬橋詞典》時,它帶給人的,竟然是“先鋒小說”的印象了。
陽云對此也有認識,他在該書中說:“早在宋代,釋惠洪在《冷齋詩話》的文學評論中,就談到了方言俗語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說:‘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韻。”
他進而論及:“方言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其原因首先是方言自身的獨特魅力,方言作為中國多元文化的承載者,是中國民間思想最樸素的表現形式,也是含義最豐富、最深刻的語態。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環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載和記錄著這方土地上的歷史和原住居民的情感,充分體現了民間語言的凝練、生動和富于表現力。”
三
方言是一個族群的標志性特征,所以才有“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之說。
民間語言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更閃爍著內涵豐富的文化光芒,民俗學、社會學、歷史學、文藝學等多種學問都包含其中。認知、考察、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當從這個地方的語言說起。而民間語言以方言土語為承載,包含多種表達形式,如俗語、諺語、歇后語、諺語、順口溜等。
陽云、陳俊伉儷對巴中民間語言的研究已有時日,陳俊多年前就曾贈送給我一部她著的《巴中方言土語》。陽云也有多篇論及巴中方言的文章——如《散談巴山歇后語》《鄉罵》《說話帶把子》《川北人的方言普通話》等。兩人都對民間語言形式進行過分析,探究過其特點,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巴中民間語言》由上、下兩編組成,上編對巴中民間語言進行了論述,言及了語言的神奇與魅力,論及了川東北方言與川西方言的異同,以及《巴中民間語言表現形式》,最有意思的是,里面還附有《巴山情歌里的方言詞》,其中內含50首情歌。后面的《最巴中100句民間方言詞》《最巴中100句民間俗語》《最巴中100句巴中歇后語》讓人既忍俊不禁,又倍感親切。下編為《巴中民間語言集成》,通過巴中民間的方言詞、民間俗語、民諺、歇后語、謎語、順口溜,完全可以體驗到巴中民間語言的風貌和特色。
可以說,《巴中民間語言》既是一部川東北民間語言辭典,也是一部全面、系統、深入探究川東北民間語言的集大成之作。
英國著名思想家培根說過:“從一個國家的格言和諺語里,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才智和精神面貌。”那么,也可以這么說,從巴中的民間語言里,也可以看出巴中甚至川東北地區的才智和精神面貌。
民間語言最能體現一個地區對文化的認同,從而體現出一個地區的凝聚力和歸屬感。但據媒體報道,2020年,全國的普通話普及率已達80.72%。就消除語言交際障礙,提升社會交際效能,負載知識和機遇而言,這無疑是好事;但隨著普通話的普及,方言自然面臨消失的危機。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說過:“語言是存在的家。”如何保住民間語言這個“家”,已經作為一個迫在眉睫的課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而陽云、陳俊伉儷合著的《巴中民間語言》,就是為了保留民間語言這個“家”做出的努力。因此,這部書在這個時候完成,無疑更能彰顯其價值和意義。
盧一萍
巴中南江籍作家,曾任成都軍區文藝創作室副主任。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白山》,小說集《銀繩般的雪》《天堂灣》,長篇非虛構《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貧志》,隨筆集《世界屋脊之書》等。曾獲解放軍文藝大獎、上海文學獎、天山文藝獎、四川文學獎、中國報告文學大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白山》被評為“亞洲周刊十大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