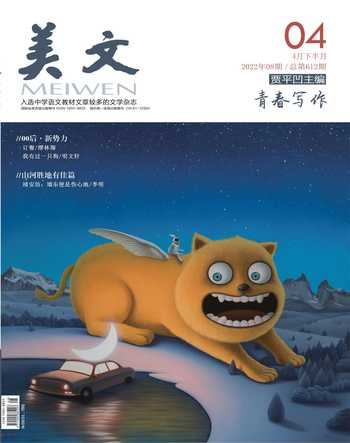百草集,陶缽響,芳香生,情誼起
張峻維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于奮進中奮起,中國共產黨迎來了百年華誕,舉國歡慶,闔家振奮。回顧黨的百年征程,立足閩西闊土,讓此間人民最難以忘懷的便是那場孤注一擲的戰略大轉移!
辛丑秋日,在國慶的歡愉氣氛中,穿過那條記憶中的羊腸小道,一行人回到鄉間探望許久未見的家人,不似鳳姐那般不見其人先聞其聲,卻也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味,數里之隔也隔不斷茶香連綿,抵達后縱使是萬般推辭也推不下茶香熱切,依舊是熟悉到有些厭倦的味道,奶奶看著我將茶飲下,在她欣慰的笑之下是我苦澀的臉龐。
“為什么每逢大事,每遇佳節總是少不了這道擂茶呢?”看著面前的茶,我終究是隱晦地表示了自己的些許厭倦。奶奶停下手上的動作,沉甸甸地看著我,注視著那雙有些渾濁的眼睛,一個塵封已久的故事浮現在我眼前……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這個小村莊已頗具規模,漫山遍野似乎都染上了一層紅色,遠方是鑼鼓喧天的樂曲練習,山間是頭戴斗笠的村人,《詩經》中所云“采、掇、捋……”的動作伴著喜慶的樂曲充滿了韻律,安詳而美好。若是熟悉客家風俗的人看到這般景象,定會意識到這里即將舉行一場盛大的婚宴。
是的,在黨中央決定進行戰略轉移之時,這個遠方的山城即將有一對新人喜結良緣。一切都在緊張有序地布置著,直到一天夜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經過十余天的準備,在那個醉人的黃昏,樂手胸有成竹地擦拭著諸如嗩吶、鑼鼓等樂器;遮陽避雨的斗笠已在墻角斜立,擂缽中盛滿了各式野菜嫩葉,在擂棍的敲擊下似鄉人的心跳般有力,預示著萬眾矚目時刻的到來。入夜,擂茶出鍋,茶香喚醒了全村的百姓,也振奮了接親的行列,一切本該順理成章地收工,但兩名紅軍戰士的出現卻帶來了變數。
他們徑直走向正熬著擂茶的灶頭,頗難為情地問道:“老鄉,咱們這擂茶足夠鄉親們喝嗎?我們是紅軍,這次是要到陜北會師,但我們的食物供不上隊伍吃飯了,想來問問你們,方便分給我們一些嗎?戰士們真的受不了了……”原來,在中央紅軍下令會師陜北之時,廣大寧化子弟兵就踴躍參加紅軍的行列,石壁鎮已經是他們的第四站了,若是再無法得到糧食供給,可能走出福建都有困難,于是便有了先前那幅場景。
“可這是結婚喜宴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啊!這婚姻咱老百姓一生可就這么一次,那可不風風光光的嘛!”數個村民似乎是難以抉擇地回復道。也許是新郎官聽見了遠方的討論,停下轎子,示意樂曲停一停,來到了紅軍戰士身邊。在了解原因之后,那個身披紅花的男子沉默了,他默默走到一旁,回頭望了望戰士們臉上不飾偽裝的著急,踱步良久,一會兒他緊皺的眉頭緩緩舒展,和女方的長輩一番交談后,他回到灶頭,答應了紅軍戰士的請求。第二天,這一場婚禮沒有了眾人習以為常的擂茶,卻多了百余位臉龐稚嫩卻目光堅毅的年輕戰士,他們無不心懷愧疚地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捧著村人十余天的成果,細細品嘗著他們無比熟悉的味道。一碗濃濃的擂茶淌進了戰士們的腹中,臨行之時,戰士們一個個細心地在村邊小河旁認真清洗碗筷,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原來的位置,齊刷刷地以軍禮致謝。
村民們哪見過這種場面,只是大聲喊著:“不用謝,為我們老百姓邁出了離鄉腳步的你們不僅是戰士,還是我們的孩子!”說著,村民們紛紛從家中抱出了每家一個的保溫壺,壺子里裝下的是鮮美的擂茶,可載不動的是思鄉情愫,裝不下的是軍民魚水情!明白鄉親們的用意,也沒推辭,紅軍戰士們抱起沉甸甸的壺子,再次鞠躬后,沿著來時的那條羊腸小道,堅定地走了,他們也必將帶著百姓的祝愿勇往直前地到達陜北!
興許是乏了,奶奶眨了眨眼,我眼前的畫面逐漸模糊,惟見手中仍冒著熱氣的“紅軍飲料”,心中依然激蕩:“百草集,陶缽響,芳香生,情誼起。”手中仿佛已不是令人厭倦的擂茶,而是至今悠長的情誼!我將手中的茶一飲而盡,抑住眼眶中的淚水,喊道:“再來一碗……”
(指導老師:張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