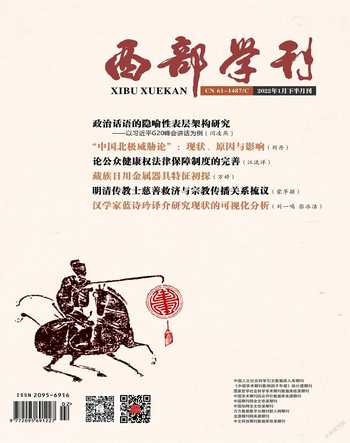漢學家藍詩玲譯介研究現狀的可視化分析
劉一鳴 張冰潔






摘要:運用文獻計量學方法,借助CiteSpace可視化工具,對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收錄的百余篇與藍詩玲譯介相關的論文題錄信息進行可視化分析,繪制研究時空分布可視化圖譜,發現國內對漢學家藍詩玲的譯介研究大致可分為基礎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史研究兩大類。基礎翻譯理論研究是傳統翻譯研究的延續,不僅涉及文本語言特征,還包括翻譯規范、譯者主體性等方面的內容。隨著上個世紀末西方“文化學派”翻譯理論的引入,描述性翻譯研究常用的方法有語料庫法、語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個案研究法、訪談法等。目前,在藍詩玲英譯作品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待提高。
關鍵詞:藍詩玲;CiteSpace;譯介;可視化分析
中圖分類號:H3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02-0165-05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中國文學“走出去”和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西方漢學界涌現出了一批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譯介的翻譯家。由于這些漢學家本身所具有的跨文化屬性,及其在外語創作、文化認知、市場認可度等方面的優勢,他們在中國文學譯介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英籍漢學家藍詩玲(JULIA LOVELL)是活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舞臺上的著名翻譯家之一,現任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現代中國歷史和文學教授。她筆耕不綴地為西方社會貢獻了大批優秀的中國文學譯介作品。其首部譯作是韓少功的《馬橋詞典》,之后又翻譯了欣然的《天葬》與《中國證人》(與NICKY HARMAN等合譯)、朱文的《我愛美元》、閻連科的《為人民服務》、張愛玲的《色·戒》以及最具代表性的《阿Q正傳及其它中國故事——魯迅小說全集》等。其中,《色·戒》和《魯迅小說全集》被收錄進了堪稱“書界奧斯卡”的“企鵝經典”叢書。
國內譯學界對藍詩玲的研究起步較晚,直到2009年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發行了藍譯《魯迅小說全集》之后,藍詩玲才逐漸進入國內譯學界的視線。因此,本文將借助信息可視化軟件CiteSpace,對知網近十年收錄的有關藍詩玲的學術研究成果的題錄信息進行聚類分析和共引分析,通過可視化知識圖譜,多維度地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計量分析和解讀,以期較為客觀地揭示近年來國內關于藍詩玲譯介研究的基本態勢,為翻譯研究科學化和中國文學“走出去”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研究方法
數據可視化始于20世紀50年代,是指運用計算機圖形學和圖像處理技術,以圖形的方式呈現數據,將學科知識的發展進程和結構關系更全面、直觀、形象地展示出來[1]。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分析工具CiteSpace是一款“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視化分析軟件”[2],由美國費城德雷克塞爾大學的陳超美教授開發,隨著其功能的不斷升級和日臻完善,目前已在數據分析領域有著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和愈加強大的影響力。
本文將選取與藍詩玲譯介研究相關的文獻數據作為研究內容,通過CiteSpace建立時空分布圖譜、文獻共被引圖譜、關鍵詞聚類圖譜和突現詞檢測圖譜,實現可視化知識圖譜的分析和解讀,從而在該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研究現狀、熱點和前沿等方面得出結論。
2.數據來源
本文所分析的文獻數據全部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KNS7.0平臺。為了獲得更為全面、客觀的基礎數據,我們在“高級檢索”中將檢索范圍設為“文獻”,將檢索主題設為“藍詩玲”,勾選“中英文擴展”,檢索時間不設限,檢索后共得到116條數據結果。我們在檢索結果中剔除書評、傳記以及訪談類文章,最終得到有效數據108條,采用Refworks格式導出后,供CiteSpace軟件進行數據預處理。
三、結果與分析
(一)時空知識圖譜及分析
研究時間和空間分布可視化圖譜可用于對藍詩玲譯介研究現狀時空維度的分析和探究。
1.研究時間分布圖譜及分析
根據圖1可知,藍詩玲的譯介研究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肇始期(2010—2013年)和發展期(2014年至今)。隨著“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的啟動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設立,國內第一篇與藍詩玲譯介相關的研究論文發表于2010年。文章從翻譯環境、翻譯本質、語言差異、文體考量、文化差異與讀者接受等角度宏觀地評析了藍詩玲的翻譯觀。在肇始期隨后的三年中,年度發文量從3篇增長到5篇,大部分以藍譯《魯迅小說全集》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國文學“走出去”的譯者風格、文本選擇和翻譯策略[3]。從2014年開始,藍詩玲翻譯研究成果也隨之增多,年度發文量保持在10篇以上,最多達到20篇,研究對象和研究視角也更加多元化。但博士論文僅有1篇,核心期刊發文量為7篇,說明國內學界在給予藍詩玲越來越多的關注的同時,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均有待進一步拓展。
2.研究力量空間分布圖譜及分析
研究力量空間分布圖譜同樣可借助CiteSpace來生成。我們將時間分區(Time Slicing)設為2010—2020,在節點類型(Node Types)中僅勾選“作者”(Author),其他參數均為默認設置。隨后,在結果中將節點標簽(Node Labeling)的閾值設置為1,得到如下圖譜:
如圖2所示,該研究領域的高產作者很少,發文量為2篇以上的作者僅有5人,說明在該領域穩定、高產的研究優勢群體尚未形成。在相對高產的作者中,繼研究生階段后仍從事該研究的作者僅有2人,由此可見,該領域大部分作者都是初探者,對問題的探討也多為淺嘗輒止,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同時,研究力量分散,研究人員合作程度低,研究團隊更是少之又少。
(二)內容知識圖譜及分析
通過繪制內容知識可視化圖譜,并結合詞頻分析和共現分析方法,我們可以直觀地掌握近十年來該研究領域的前沿熱點、動態演變及其相互關聯性。
1.研究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論文主旨的濃縮和提煉,出現的頻次越高,說明該關鍵詞所表征的研究主題的熱度指數越高。因此,關鍵詞共現圖譜可以有效反映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和發展動向。
我們沿用之前設置的時間分區,在節點類型(Node Types)中僅勾選“關鍵詞”(keyword),其他參數均為默認設置。隨后,在結果中將詞標簽(Term Labeling)的閾值設置為1,調整字體、節點大小和顯示比例,得到如下圖譜:
在該圖譜中,一個圓形節點對應一個關鍵詞,節點大小表示該關鍵詞共現頻次(Frequency)的高低,節點越大說明共現頻次越高。節點間的連線體現了關鍵詞共現系數,連線越多說明關鍵詞之間的關聯越密切。共現頻次最高的9個關鍵詞(頻次≥3)分布見表1。
在CiteSpace中,節點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也是衡量關鍵詞在該研究領域內重要程度的指標之一。一個關鍵詞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說明它為其他非中心節點提供的戰略性中介作用越多,也就意味著它控制的關鍵詞之間的信息流越多[4]。表2匯總了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5個關鍵詞,反映出該研究領域的熱點和發展態勢。
結合圖3、表1和表2,就研究內容而言,傳統譯論及譯學研究的語言學方法仍被用來指導文學翻譯研究。從統計數據來看,所有文獻中有21篇是以魯迅小說的藍譯本和其他譯本為研究對象,其中《阿Q正傳》和《吶喊》英譯本是迄今為止國內譯學界研究最多的兩部作品。研究者大多將宏觀思考與個案研究相結合,旨在對譯介策略、譯介方法、譯介效果進行探索,進而探討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反思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范式,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中國文學在語言層面上的英譯研究。
隨著翻譯研究的范式變革,越來越多的學者在社會文化背景下展開描述性譯介研究,并認識到文化差異以及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所帶來的“文化誤讀”,是中國文學文化譯介中最大的挑戰。批評家李建軍曾指出“由于文化溝通和文學交流上的巨大障礙,使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無法讀懂原汁原味的‘實質性文本’,只能閱讀經過翻譯家改頭換面的‘象征性文本’。在轉換之后的‘象征性文本’里,中國作家的各個不同的文體特點和語言特色,都被抹平了”[5]。因此,“文學翻譯”“文化翻譯”“文化詞”仍是該研究領域出現頻次較高的關鍵詞。比如,藍詩玲譯作中有關鄉土語言、文化負載詞等的翻譯策略、文化翻譯觀、譯介與接受等話題都頗受國內學界關注和重視。
另外,“語料庫”“副文本”等文學翻譯研究的新視野在該領域已悄然出現。“當下翻譯研究不僅是實現語言學與文化學派的跨學科研究,更應該實現打通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學科的超學科研究。”[6]因此,語料庫翻譯學的出現和發展使得該研究領域愈加多元化。盡管在藍詩玲的譯介研究中,利用語料庫進行實證研究的學者并不多,發表于核心期刊的文獻僅有2篇(李德鳳等、呂奇和王樹槐),但翻譯學的跨學科屬性無疑會體現在藍詩玲的譯介研究中。而作為解讀、構建文本的重要形態之一的副文本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探討副文本與翻譯之間的關系,分析譯介過程中副文本的書寫策略,有助于提高異質文化間的整合能力,為真正實現文化間的交流、增益與融合提供新的路徑。在這一點上,藍詩玲在翻譯《馬橋詞典》和《魯迅小說全集》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2.高被引文獻分析
文獻共被引分析只能采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的數據,因此,我們仍然用“藍詩玲”為標引詞在CSSCI中進行檢索,結果顯示,收錄進數據庫的來源文獻僅有3篇:
由于來源文獻數據太少,無法用CiteSpace做共被引分析。但該研究的學術內涵及空間拓展從這3篇文章可見一斑。兼具譯者和魯迅研究者雙重身份的漢學家寇志明,從舊體詩探究魯迅思想軌跡,發掘魯迅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價值,也說明魯迅作品研究是該研究領域的重中之重。近年來,研究者運用不斷更新和發展的批評理論,使研究內容更加多元化。比如,王洪濤和王海珠將布迪厄的反思性社會學理論應用于藍詩玲的譯者慣習研究,賦予了譯介研究更多的文化內涵和理論品格,也預示著該領域研究縱深化、精細化的發展趨勢。此外,李德鳳等開展語料庫庫助研究,將藍詩玲英譯本與其他譯本進行對比,考察藍詩玲的翻譯風格。其研究以跨學科研究的視野,將譯介研究向多級度、多層面、多模態推進。
四、藍詩玲譯介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首先,藍詩玲譯介研究投入不足,與其翻譯的文學作品在國內的文學地位嚴重不符。近些年,盡管中國政府和相關部門想方設法助推中國文學“走出去”,但收效甚微,依然無法改變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之林的“小眾化”“邊緣性”的地位。正如閻連科所說:“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文學在世界上很‘弱勢’”[7]。而中國文學作品在海外的傳播渠道不暢,接受度不高,影響力不足等問題極大地制約了學界對中國文學譯介的整體研究。因此,如何加大對譯介研究的投入力度,提升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是目前學界亟待解決的問題。
其次,藍詩玲譯介研究內容缺乏深度。盡管中西方在對待譯介作品時接受語境和接受心態存在不對等性,但對中國文學譯介缺乏深度的研究,也是西方產生接受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對藍詩玲譯介的現有研究來看,宏觀把握性研究、描述性翻譯研究數量偏少,微觀研究占比較大,研究重心大多為譯本對比、翻譯策略探析、譯者風格考察等等,缺乏從多元系統論和詩學層面對中國文學異質性進行深刻剖析,從而導致結論空泛,缺乏深度。
此外,國內現有研究對海外漢學家的譯介模式關注不夠,文獻中鮮有對海外漢學家譯介歷程、學術貢獻、譯介理念等方面的系統論述。因此,如何將海外漢學家的譯介理念和譯介模式實踐于中國語境下的現當代文學的譯介研究,如何從方法論的意義上啟迪譯介學建設,將是中國現當代文學譯介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
結語
在當下全球化語境下,“他者視角”不僅有利于我們重新審視自身文學、文化,而且有助于學界更好地進行“走出去”語境下的外譯思考。國內對漢學家藍詩玲的譯介研究大致可分為基礎翻譯理論研究和翻譯史研究兩大類。基礎翻譯理論研究是傳統翻譯研究的延續,不僅涉及文本語言特征,還包括翻譯規范、譯者主體性等方面的內容。隨著上個世紀末西方“文化學派”翻譯理論的引入,描述性翻譯研究常用的方法有語料庫法、語篇分析法、文獻計量法、個案研究法、訪談法等。目前,在藍詩玲英譯作品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有待提高。因此,本文通過深入而系統地審視與梳理藍詩玲譯介研究的現狀,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條分縷析,并以辯證的眼光把握和分析該領域研究的發展趨勢和前景,以期通過歷史觀照現實,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英譯研究提供一定的啟示和借鑒。
參考文獻:
[1]李健,王麗萍,劉瑞.美國的大數據研發計劃及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科技資源導刊,2013(1).
[2]梁靜,任增元.我國研究生教育研究進展的文獻計量分析[J].現代教育管理,2015(12).
[3]覃江華.英國漢學家藍詩玲翻譯觀論[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
[4]SMALL.H.The Synthesis of Specialty Narratives from Co-citation Cluster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1986(3).
[5]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N].文學報,2013-01-10(18).
[6]王峰,陳文.國內外翻譯研究熱點與趨勢——基于譯學核心期刊的知識圖譜分析[J].外語教學,2017(4).
[7]高方,閻連科.精神共鳴與譯者的“自由”——閻連科談文學與翻譯[J].外國語,2014(3).作者簡介:劉一鳴(1984—),女,漢族,河北石家莊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英語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