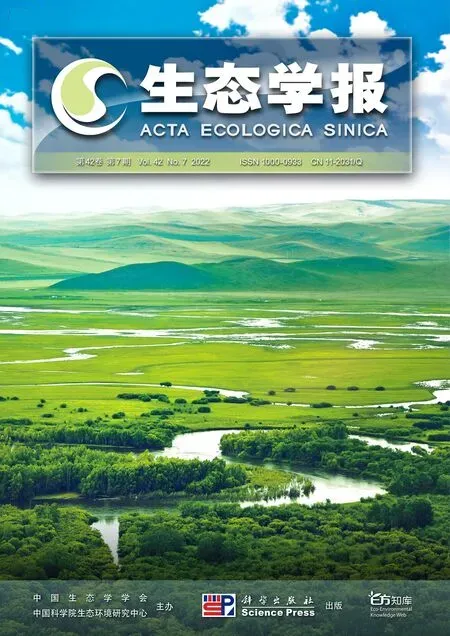河南濟源人工引水渠隧道蝙蝠冬眠生態學特征
劉 森, 戴文濤, 尹香菊, 冷海霞, 朱 越, 江廷磊,*
1 河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新鄉 453007
2 河南理工大學資源環境學院, 焦作 454000
3 吉林省動物資源保護與利用重點實驗室, 東北師范大學, 長春 130117
蝙蝠是翼手目(Chiroptera)動物,它們捕食昆蟲或傳播種子,對維護生態系統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受到全球變暖、生境破碎化、農藥富集、疾病等因素影響,蝙蝠種群數量銳減[1]。由于蝙蝠越冬后繁育后代,深入了解蝙蝠冬眠生態學特征,特別是蝙蝠冬眠種群數量變化趨勢及其冬眠場所環境情況,對準確評估蝙蝠物種瀕危等級、種群繁衍和發展趨勢至關重要,是量化種群變化響應生態擾動的基本前提。
國外研究者在蝙蝠冬眠種群監測、冬眠棲息地選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過長期監測發現,一些冬眠物種種群數量出現年度增長趨勢,比如,意大利西北部52個冬眠場所的6種蝙蝠種群數量在1992—2019年期間增長了3.5%—15%[2],而有些物種種群數量則由于疾病或者人類活動干擾等因素而銳減,如真菌誘導的白鼻綜合癥導致北美Myotislucifugus大量死亡[3];20世紀80年代美國西北部Shoshone Desert管理區洞穴旅游的興起,致使Corynorhinustownsendii種群數量減少[4]。對眾多冬眠棲息地蝙蝠數量和環境數據分析發現,蝙蝠傾向冬眠于微氣候相對穩定的場所[5]。同時,冬眠場所結構,包括空間大小、地形、出口數量、氣流等,也會影響到蝙蝠種群數量[6—7]。
在我國,有關蝙蝠冬眠的研究相對較少,包括絨山蝠體內貯脂在冬眠期消耗情況[8],中華山蝠的冬眠陣長度、覺醒后呼吸頻率變化、冬眠環境溫度等生理特性和生態習性[9],大菊頭蝠的冬眠棲點特征[10],以及西南鼠耳蝠和皮氏菊頭蝠的冬眠生態學特征(冬眠數量、冬眠姿勢、棲點位置,以及棲點溫度與冬眠體溫相關性)[11]等。然而,目前鮮有對蝙蝠冬眠種群數量進行長期監測的研究報道。
2005年2月,趙黎明[12]發現河南省濟源市布袋溝水庫引水渠隧道中有大量蝙蝠冬眠(超過1600只)。該引水渠包含多個長短不一的隧道,且隧道內部有流水,可為蝙蝠提供眾多適宜冬眠場所。然而,由于缺乏相關數據,尚不清楚在這種濕潤環境下,蝙蝠冬眠種群數量是如何變化的。2017—2020年期間,每年1月份對該引水渠隧道進行調查,初步分析蝙蝠冬眠生態學特征,包括:1)冬眠蝙蝠種類組成、種群數量現狀,以及變化趨勢;2)冬眠方式、棲點位置,以及棲點溫度與蝙蝠體溫的關系;3)環境因子對蝙蝠冬眠場所選擇的影響。研究工作旨在豐富我國蝙蝠冬眠種群生態學的基礎數據,并為我國蝙蝠保護策略及其冬眠棲息地管理決策制定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1 研究地區與方法
1.1 研究地區概況
布袋溝水庫引水渠位于華中北部地區、太行山南段東麓的太行山獼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行政區劃隸屬于河南省濟源市,該區域地貌屬流水作用的斷塊中山,區內峽谷、溝壑縱橫,氣候類型為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3.28 ℃,年平均降水量為 695 mm,平均無霜期為 190 d[13]。森林植物類型以針葉林、針闊混交林、落葉闊葉林、半常綠闊葉林為主,多為天然次生林。動物主要包括太行山獼猴、金錢豹、林麝等國家重點保護動物[14]。
布袋溝水庫引水渠隧道由長短不一的77個隧道構成,從上游至下游,依次編號C1—C77。總長約13 km,最短約10 m,最長約770 m。長度≤ 60 m的隧道有34個,占總數的44%,其中24個位于C1—C29之間。每個隧道首尾均有一個洞口,內部曲折,隧道高約2—5 m,寬約2—4 m (圖1)。C56與C57銜接之處,設置有閘門,將水截流用于發電,因而從C57開始,水位開始降低(圖1),隧道溫度逐步升高。
部分明渠采用人工砌石封頂(圖1),組成隧道的一部分,因而形成較多的長隧道,比如有16個長度超過300 m的隧道均存在多個人工砌石處。這種拱形頂厚約50—70 cm,該區域受外界環境影響較大,有極少數蝙蝠冬眠于此(圖1)。

圖1 引水渠隧道特征
1.2 研究方法
1.2.1蝙蝠種類、數量、冬眠方式、棲點位置調查
2017—2020年期間,每年的1月份調查了冬眠蝙蝠的種類、數量、冬眠方式和棲點位置。所有調查人員認真檢查每個石縫和凹窩,對不確定的個體需輕輕摘下認真鑒定,之后原地放回,以減少漏查和鑒定錯誤的幾率。對個體較多的聚集群體拍照,后續通過照片確定個數。參照龔小燕等[15]定義,將蝙蝠在某一隧道內的具體棲掛或棲臥位點稱為“棲點”,測量棲點到隧道口的距離。調查過程中,盡量降低人為噪音,并避免非必要的直接碰觸,以減少對蝙蝠的刺激。
1.2.2影響蝙蝠冬眠隧道選擇的環境因子測量
考慮到長度、高度和水深影響冬眠空間,風可以改變微氣候的穩定性,聲強差異可能干擾蝙蝠(對聲音敏感)冬眠,水溫和環境溫度(空氣溫度)可能會影響蝙蝠冬眠的適宜度,2020年1月,本次研究對歷年均有蝙蝠冬眠的隧道,測量了上述環境因子數據。除隧道長度外,所有參數每30 m測一組數據,取平均值。風速由數字式風速計(TM856D)測定,聲強由數字式聲級計(TD1357)測定。
1.2.3隧道不同位置環境溫度、相對濕度的測量
為評估隧道不同位置環境溫度和相對濕度的差異性和穩定性,選擇一個長約310 m、包含人工砌石區域且有較多蝙蝠分布的隧道(C41),對其不同位置進行為期3個月(2019年10月15日—2020年1月15日)的溫度和相對濕度監測(華圖USB溫濕度記錄儀HE173,溫度精度± 0.5 ℃,相對濕度精度± 3%),每6 h獲取一組數據,共獲得372組數據。依據前期調查的蝙蝠分布數量情況,共設置了6個位置,包括距離洞口0 m、30 m、70 m、130 m、160 m (隧道正中間)、人工砌石處等位點。0 m、30 m和人工砌石處蝙蝠數量< 3只,其余位點均有較多蝙蝠冬眠(超過10只)。
1.2.4蝙蝠體溫與棲點溫度測量
將Fluke紅外測溫儀(62MAX,精度± 1.5 ℃)置于離蝙蝠背部約5 cm處測量體溫,在距蝙蝠約2 cm處測定棲點巖壁溫度,均測3次取平均值,用于評估棲點溫度與蝙蝠體溫的相關性。冬眠位置過高或蘇醒的個體不進行測量。
1.3 內業數據處理
統計并計算距離洞口不同位置的環境溫度、相對濕度的變異系數,以判斷其波動程度。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評估環境因子與蝙蝠冬眠數量的相關性程度,并通過逐步回歸獲取顯著影響蝙蝠冬眠場所選擇的關鍵環境因子。回歸分析用于評估棲點溫度與蝙蝠體溫的相關性,獨立樣本t檢驗判別組間差異顯著性。所有統計分析通過SPSS 22和R 4.1.0完成。
2 結果
2.1 種類組成和種群數量的年度變化
通過外部形態鑒定,在該水渠冬眠的蝙蝠一共有2科5屬7種(圖2),包括菊頭蝠科的馬鐵菊頭蝠(Rhinolophusferrumequinum)和小菊頭蝠(R.pusillus),蝙蝠科的華南水鼠耳蝠(Myotislaniger)、白腹管鼻蝠(Murinaleucogaster)、金管鼻蝠(Mu.aurata)、奧氏長耳蝠(Plecotusognevi)和亞洲寬耳蝠(Barbastellaleucomelas)。
冬眠蝙蝠總數呈歷年增長趨勢,即從2017年774只到2020年1092只(圖3)。馬鐵菊頭蝠數量占絕對優勢(約52%—73%),2017年數量最低,有407只,逐年增至765只。小菊頭蝠數量次于馬鐵菊頭蝠(約占19%—37%),2017—2019年期間從288只降至183只,2020年又增至247只。華南水鼠耳蝠數量約為總數的5%—8%,其余物種數量總和不足總數的3%,其中2018年未發現奧氏長耳蝠,2020年未發現金管鼻蝠。除馬鐵菊頭蝠數量逐年增加外,其余物種數量在這4年期間處于增、減波動狀態。

圖3 2017—2020歷年每種蝙蝠冬眠個體數量的變化
2.2 影響蝙蝠冬眠場所選擇的主要環境因子分析
2017—2020年期間均有蝙蝠冬眠的隧道共有42個,各隧道冬眠蝙蝠數量是年際變化的。每年馬鐵菊頭蝠和華南水鼠耳蝠在這42個隧道中幾乎均有分布,而63.1%—78.7%的小菊頭蝠冬眠于C58隧道,其余個體主要分布在C58后的隧道。通過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發現(表1),隧道平均高度、水位、風速、聲強、水溫、環境溫度等因子與冬眠數量相關性均不顯著(P均> 0.05),隧道長度與冬眠數量呈顯著正相關(P=0.001),經逐步回歸分析獲得的最佳模型僅保留了隧道長度這一個環境因子(Fst=11.76, AdjustedR2=0.208,P=0.001),表明隧道長度是影響蝙蝠冬眠場所選擇的主要環境因子。

表1 環境因子對冬眠蝙蝠數量影響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此外,有些隧道的固定位置,每年有比較穩定的蝠群冬眠,比如C41隧道距洞口約20 m處有一個馬鐵菊頭蝠聚集群體,C58隧道距洞口100—110 m處有超過100只小菊頭蝠獨棲。
2.3 蝙蝠在隧道內分布特征及其冬眠方式
蝙蝠在各隧道分布存在空間差異性。在長度≤ 60 m的隧道中(占隧道總數的44%),冬眠個體數不及總數的5% (表2),超過95%的個體冬眠于長度> 60 m的隧道。至少有3/4的蝙蝠個體冬眠于長度超過200 m的隧道(占隧道總數的36%),特別是最長的C58隧道(長約770 m)擁有至少1/5的冬眠個體(歷年最低197只)。此外,選擇在人工砌石處以及距洞口≤ 30 m處進行冬眠的個體數量不及總數的20% (表2),包括約13.5%—22.9%的馬鐵菊頭蝠、1.6%—4.5%的小菊頭蝠、24.7%—36.8%的華南水鼠耳蝠個體;約4/5的個體選擇在隧道深處冬眠。

表2 歷年在短隧道(≤60 m)、人工砌石處以及距洞口≤ 30 m處冬眠蝙蝠的數量和比例
表3表明,隨著距洞口距離的增加,環境溫度逐步上升,相應的變異系數也逐步降低,相對濕度呈現相似變化。人工砌石處的溫度和濕度及其變異系數與距洞口30 m處相當,這些區域易受外界環境影響。上述數據表明,多數個體選擇相對溫暖且穩定的隧道深處而非環境波動較大的地方作為冬眠棲點。

表3 距離洞口不同位置的溫度和相對濕度及其變異系數
蝙蝠冬眠方式是多樣的。絕大多數個體(> 90%)以獨棲(solitary)方式進行冬眠,但也存在聚集現象(huddling),比如最大的一個馬鐵菊頭蝠聚集群體包括了43只個體。不同物種冬眠的姿勢并不相同,菊頭蝠科蝙蝠一般垂直倒掛,獨棲的馬鐵菊頭蝠采用翼膜包裹身體,聚集的馬鐵菊頭蝠則不包裹身體,而小菊頭蝠一般不展開翼膜包裹身體;蝙蝠科蝙蝠一般是腹部貼壁倒掛或呈匍匐狀臥棲姿勢,不用翼膜包裹身體。菊頭蝠一般選擇較空曠的區域冬眠,而蝙蝠科蝙蝠則會選擇石縫或凹窩處冬眠。
2.4 棲點溫度與冬眠蝙蝠體溫
棲點溫度與蝙蝠體溫之間呈顯著正相關(R2= 0.98,P< 0.001) (圖4),表明棲點溫度直接影響了蝙蝠體溫。二者的差異值主要分布在-0.5 ℃至0.2 ℃范圍內(88.7%),大約64.1%的蝙蝠體溫低于棲點溫度。

圖4 冬眠蝙蝠體溫與棲點溫度之間的關系
距洞口≤ 30 m以及人工砌石處冬眠棲點溫度((8.2±1.6) ℃,n=183),顯著低于隧道深處棲點溫度((9.6±1.3) ℃,n=671) (P< 0.001)。不同物種棲點溫度有所不同,馬鐵菊頭蝠((9.2±1.4) ℃,n=658)和華南水鼠耳蝠((8.8±1.1) ℃,n=60)之間無顯著差異(P> 0.05),約9 ℃,但均顯著低于小菊頭蝠棲點溫度((11.2±0.8) ℃,n=126) (P均< 0.001)。上述結果表明,蝙蝠冬眠所需的棲點溫度不僅具有種內差異性,也具有種間差異性。
3 討論
3.1 冬眠數量呈增長趨勢
2017—2020年期間,河南省濟源市邵原鎮人工引水渠的隧道共有2科5屬7種蝙蝠物種冬眠,其中馬鐵菊頭蝠數量占絕對優勢,且逐年增加,其他物種的數量則處于增、減波動狀態。雖然調查時間有限,但一些長期的野外調查研究也發現了冬眠優勢物種數量增加的現象[2, 16],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優勢物種更加適應當前的冬眠環境,且基數大,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其種群的恢復和增長。第二,隧道內部寒冷黑暗,積水較深,人為干擾程度低,是較為安全和適宜的冬眠地,這可能促進蝙蝠種群繁衍和增長,如瑞典南部的廢棄礦洞冬眠蝙蝠數量,在安裝防護門后出現了增長和穩定[17]。然而,由于本次調查區域有限,存在臨近區域的冬眠地(如廢棄礦洞)不再適合冬眠時,蝙蝠可能遷徙到隧道內進行冬眠,從而造成數量增加的情況,但這有待進一步調查。
雖然冬眠蝙蝠數量呈逐年增長趨勢,數量已超過了1000只,但仍明顯少于2005年2月的數量[12]。華中北部地區的一些極端寒冷事件帶來的地表熱變化(如2007年為冰凍日數高值年[18],2009年為極端降溫事件多發年[19]),可通過基巖的熱傳導引起冬眠場所低頻熱變化[20],進而增加蝙蝠越冬風險,這可能是引水渠隧道冬眠蝙蝠數量銳減的一個主要原因。但由于缺乏2006—2016年期間冬眠蝙蝠狀況、隧道環境溫度等相關數據,尚無法將數量銳減與極端氣候變化建立關聯。
3.2 隧道長度可能是蝙蝠選擇冬眠場所的主要影響因素
在外界氣候幾乎一致的背景下,引水渠為蝙蝠提供了長短不一的77個冬眠隧道,但僅有42個隧道每年均有蝙蝠冬眠,且各隧道冬眠蝙蝠數量在4年間是不同的,因而隧道的微生境環境差異可能直接影響蝙蝠冬眠場所的選擇。一般認為,微氣候是決定蝙蝠選擇冬眠場所的主要原因[5,21]。然而,當考慮到棲息地內部其他環境因子時,微氣候的影響力會降低。例如,荷蘭“New Dutch Waterline”防御地堡的內部空間大小和隱蔽空間的數量對冬眠蝙蝠數量的影響力比環境溫濕度更大[7]。
在影響蝙蝠冬眠隧道選擇的環境因子中,僅有隧道長度與冬眠蝙蝠數量顯著正相關。隧道越長,內部微氣候相對穩定的空間越大,能有效減少蝙蝠種內、種間的競爭,容納更多的蝙蝠冬眠;同時隧道越長,其溫度梯度越大(如C41,溫度范圍為3.4—10.0 ℃),能夠使蝙蝠依據自身生理狀態,在同一隧道內選擇適宜溫度的區域進行冬眠[22],進而降低因更換冬眠場所導致的能量過多消耗及被捕食風險。蝙蝠一般會選擇較高的地方作為棲點,可有效避免天敵,而引水渠隧道相對安全,因而決定垂直空間大小的隧道高度和水深,可能不是影響冬眠場所選擇的主要因素。風可以引起隧道內部溫濕度波動,然而蝙蝠可以選擇微氣候相對穩定的石縫和凹窩冬眠[23],以減少風帶來的不利影響。蝙蝠長期在流水環境中冬眠,各隧道的背景聲強差異對冬眠的影響作用可能甚微。由于每個隧道內部存在一定的溫度梯度,蝙蝠可根據自身生理狀態選擇更適宜的溫度區域冬眠,因而隧道的平均水溫和平均環境溫度可能不會顯著影響到隧道內冬眠蝙蝠數量。
3.3 不同的棲點位置和冬眠方式可能有利于冬眠成本優化
每個隧道內,蝙蝠冬眠棲點位置是不同的。大部分蝙蝠冬眠于相對溫暖且穩定的隧道深處(距洞口>30 m),而并非集中在最冷的區域。在相對溫暖環境下冬眠,可能會降低蝙蝠蟄伏持續時間,并增加能量消耗[24],似乎并不利于蝙蝠越冬。一些研究發現,脂肪儲備多的蝙蝠個體更傾向于溫暖環境冬眠,而脂肪儲備少的個體則傾向冬眠于較冷區域[22, 25],這種策略既可保證越冬存活率,又可降低長時間蟄伏的代價(如增加生理和被捕食風險,減少交配機會等)[26]。考慮到棲點環境的熱穩定性與冬眠哺乳動物的代謝支出成反比[27],在隧道深處溫暖且穩定的環境中冬眠,蝙蝠的能量使用效率可能會更高[28]。
蝙蝠具有多樣的冬眠方式。絕大多數蝙蝠是獨棲的,這種方式能夠降低被捕食和一些依賴于密度傳播的疾病感染幾率,比如白鼻綜合癥[29]。不同物種可能通過不同方法降低獨棲冬眠個體的體熱或體能損耗,比如馬鐵菊頭蝠采用翼膜包裹身體,蝙蝠科物種則選擇環境相對穩定的巖縫內冬眠。少量的蝙蝠采用聚集方式冬眠,該方式可減少暴露在外的體表面積,提高周邊環境溫度,降低體內熱量損失和水分的蒸失[30]。遇到環境異常時,聚集群體任何個體的覺醒都可能促使其他個體被動覺醒,節約覺醒所需能量[31]。由此可見,不同的冬眠棲點和多樣的冬眠方式,可能是蝙蝠對冬眠成本優化的策略。
3.4 棲點溫度顯著影響蝙蝠體溫
要保持節能的蟄伏狀態,蝙蝠需要將體溫降至周邊環境溫度,以接近蟄伏代謝率(torpid metabolic rate)。因而,棲點溫度往往顯著影響冬眠蝙蝠體溫。小菊頭蝠棲點溫度顯著高于馬鐵菊頭蝠和華南水鼠耳蝠,表明不同蝙蝠物種的棲點溫度有所差別。這種棲點溫度的種間差異性現象,可能普遍存在于冬眠蝙蝠中,比如湘西及武陵山地區冬眠的大菊頭蝠((11.3±2.4) ℃,n=14)、中華菊頭蝠((12.7±1.0) ℃,n=11)、西南鼠耳蝠((10.4±2.4) ℃,n=49)等具有不同的棲點溫度[10, 32]。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不同物種的體型差異較大,其蟄伏代謝率可能存在種間差異[33],從而造成物種的蟄伏適宜溫度范圍有所不同。第二,不同地區的冬季氣候差異,導致冬眠場所之間存在溫度差異,進而影響到蝙蝠棲點溫度,比如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北部較冷洞穴中冬眠的Perimyotissubflavus和Myotisvelifer的棲點溫度,要高于南部溫暖洞穴冬眠的同種個體棲點溫度[34]。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蝙蝠體溫是略低于棲點溫度,這與一些已有的報道不一致[11, 15]。一方面,可能與冬眠狀態有關系,比如當蝙蝠處于冬眠陣的深眠階段,接近冬眠過程中最低體溫,會略低于棲點溫度[35]。另一方面,調查時間的不同,以及物種差異都可能影響到這個結果。
4 問題及展望
第一,調查時間僅限于每年的1月(冬眠中期),事實上,在不同的冬季時期,蝙蝠數量和冬眠棲點位置可能是動態變化的[22],因而相關結果可能具有時限性。第二,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相關設備的缺乏、儀器供電困難等),用于分析的微生境環境參數數值不是動態的,可能與真實情況存在偏差。
未來工作可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關注冬眠不同時期的蝙蝠數量和冬眠位置動態變化趨勢,調查引水渠附近區域潛在的冬眠地及蝙蝠冬眠情況,還要排查當地蝙蝠種群受到威脅的因素,這是野生種群保護和冬眠棲息地管理的基本前提。
致謝:感謝袁樹信、陳傳毓、韓鵬舉、劉詢、李子昊、李奧強、李仲樂等在野外調查中給予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