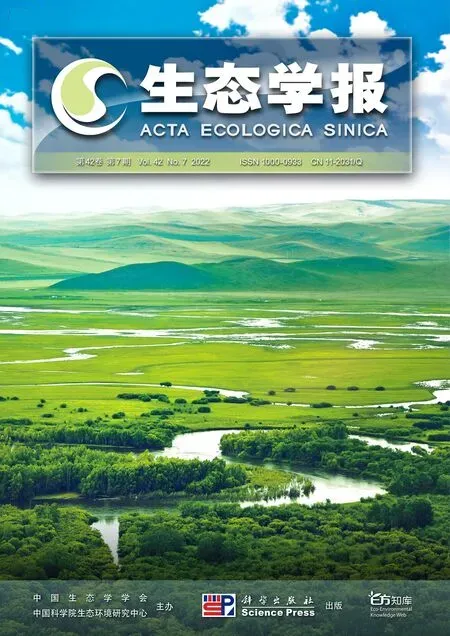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棲息地利用對海岸線等變遷的響應
王新星,陳 濤,*,李 敏,王躍中
1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南海水產研究所/農業農村部南海漁業資源開發利用重點實驗室, 廣州 510300
2 廣東珠江口生態系統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 廣州 510300
環境干擾會影響鯨豚類動物對棲息地的選擇利用,持續干擾及襲擾可能導致其分布范圍和核心棲息地發生轉移,長期系統收集分布數據是分析動物對環境變化響應的關鍵。中華白海豚(Sousachinensis)為沿岸河口定棲性小型齒鯨類,又名印度太平洋駝背豚(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屬海豚科(Delphinidae)白海豚屬(Sousa),廣泛分布于東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近岸水域,1988年被國務院列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被IUCN(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中列為“易危”狀態[1]。中華白海豚分布范圍東起中國沿海的中部(最北擱淺記錄出現在長江口),向南遍及整個東南亞,向西延伸到孟加拉國與緬甸邊界[1—2]。在我國中華白海豚主要分布于廈門沿岸、臺灣西部沿岸河口、汕頭南澳島水域、珠江口至海陵島沿岸、湛江雷州灣、廣西北部灣沿岸河口及海南三亞等海域,其中珠江口-漠陽江口種群規模最大,初步估計在2600頭以上,遠遠大于其它各地種群[3—12]。珠江口沿岸河口區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海上航運、沿岸填海、水體污染以及漁業過度捕撈等威脅因素較為突出,中華白海豚棲息地可能已出現退化,其面臨的生存壓力日益增大[5]。
對于珠江口-漠陽江口這一已知最大的中華白海豚種群,香港水域于1990年開始調查,廣東一側水域于1997年以后開始系統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該種群的分布范圍為:東起香港大嶼山東部水域、西至陽江海陵島東部水域,離岸分布不超出沿岸20m等深線[3—4, 7, 13]。在珠江口伶仃洋的分布,以淇澳島東南部水域、內伶仃島西部水域、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青洲-三角島水域目擊較多。在過去的40年里,由于不可逆轉的人為活動(如圍填海、沿岸工程和港口建設等),大量的沿岸水域被蠶食[14—17]。長期棲息地縮減對海豚的影響已有報道,最明顯的表現是其分布模式和核心棲息地發生變化。Keith等通過海豚目擊數據分析南非理查德灣海豚的棲息地使用,海豚覓食、休息和社交等不同行為對具體區域呈現明顯的選擇偏好性[18]。Karczmarski等分析臺灣西部沿岸中華白海豚棲息地被長期侵占下海豚的分布變化,結合歷史數據推斷白海豚棲息地不連續分布是由棲息地退化導致[19]。Wang等利用衛星數據和不同階段的中華白海豚目擊數據分析廈門海岸線改變對海豚棲息地的影響,白海豚目擊由近岸向離岸轉移并遠離人工海岸線,同時原來的沿岸核心棲息地轉移到中心航道水域[20]。Wu等利用近40年的衛星數據反演北部灣海岸線變化,結合中華白海豚歷史出現位置的問卷調查數據得出核心棲息地被占用的結論[21]。以上研究均是針對種群規模較小、人類活動多發生在小范圍內海豚棲息地變動情況分析。然而,對于珠江口這一長期棲息在人類活動強度超大的區域內且規模較大的種群,長時間尺度上種群分布對人類活動的響應還不是很了解。
珠江口-漠陽江口中華白海豚種群分布水域范圍內共設立了兩個保護區,分別是位于伶仃洋水域的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以及位于黃茅海水域的廣東江門中華白海豚省級自然保護區。有研究指出,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功能區與白海豚棲息地使用及核心棲息地的分布格局完全不相匹配[22],但根據我們的長期監測結果,認為對這一問題很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商榷。本文通過近20年使用船基截線抽樣法獲取的中華白海豚觀測數據,結合Landsat衛星數據,主要研究以下3個方面的內容:(1)根據多年的海豚調查數據,基于種群棲息地利用模型分析近20年來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分布和核心棲息地的變化;(2)根據多年中華白海豚觀測數據分析海豚的棲息地選擇偏好變化;(3)基于分析結果分析保護區的保護功能現狀。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
珠江水系是中國境內徑流量僅次于長江的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積為415000km2,其中珠江三角洲面積約為50000km2,僅次于長江三角洲,是中國第二大三角洲[23]。珠江水系主要有八大入海口,河水直接或間接的流入南海,其中東部的4大口門(虎門、焦門、橫門和洪奇門)徑流匯入伶仃洋形成珠江東部河口區。由于海域管轄的制約,本研究調查區域未涉及香港水域,即本文所述珠江口伶仃洋未含鄰近的香港水域。研究區域水深普遍較淺,水深大多小于20m,調查區內設置一系列與主要海岸線垂直的平行觀測截線,截線間距約為3km,截線覆蓋水深變化范圍基本上為3—20m。研究區域及觀測截線設置見圖1。

圖1 研究區域圖
1.2 海豚觀測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海豚觀測數據是通過船基截線抽樣法獲取,船基截線抽樣法是國際上比較成熟的小型鯨類調查方法,多年以來常用于香港水域和廣東珠江口水域的鯨豚調查[3—4, 7]。本文的調查數據主要包括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7—2000年,第二階段為2005—2006年和第三階段為2015—2016年。其中第一階段調查包括兩個周年,1997—1998年度調查范圍為伶仃洋中部水域,1999—2000年度調查范圍為伶仃洋北部、東南和西南水域,均為每月1個航次共12個航次;第二階段調查為一個周年,調查范圍包括伶仃洋北部、中部、東南和西南水域,每月1個航次共12個航次;第三個階段調查也是一個周年,調查范圍同第二階段,由于5—7月休漁期未能開展調查,分別于雨季和旱季各調查了5個航次,共10個航次。
1.3 遙感數據獲取和處理
遙感數據采用陸地衛星Landsat1、Landsat5和Landsat8可見光影像資料,根據研究區域的衛星圖片區域代碼(122/131列,44/45行),選取高質量的衛星圖片進行海岸線提取,即每張圖片整體云層遮蓋量低于20%或圖片陸地和海島周邊云層遮蓋量為0,并下載相對應的衛星數據(數據獲取網址:http://glovis.usgs.gov/)。使用圖像處理軟件將下載的所有衛星圖像處理為假彩色圖像,利用波段組合獲取清晰的對比度來區分水體和陸地區域[20—21]。研究區域的衛星圖像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將此年度的衛星圖像作為底圖,識別原有水體被陸地占用的區域。不同年度衛星圖片各海岸線占用流失的海域面積之和定義為指定時間內研究區域海域流失總面積。本文所使用的衛星圖像信息見表1。

表1 珠江口伶仃洋海岸線變化使用的Landsat衛星影像信息
1.4 數據分析
棲息地分布采用概率密度函數來計算,它描述了動物所使用的相對空間,通過動物位置坐標抽樣計算獲取[24]。為估算海豚的棲息地使用,根據本文研究區域的地理位置,將所有的群體目擊位置投影到UTM49N坐標系中。由于伶仃洋周邊海島和陸地區域無法被海豚利用,選取含障礙核插值(Kernel interpolation with barriers)方法估算海豚的分布和核心棲息地使用情況[25]。含障礙核插值工具區別于傳統的核密度估計工具,計算中涉及點之間的最短距離,其中點之間的連線與障礙(海島、陸地等)無交叉,允許密度等值線在障礙邊緣突然變化。
使用含障礙核插值方法的關鍵是輸出網格大小和帶寬值的設定。本文選取的輸出網格大小為200m×200m,這樣研究區域中海島及沿岸附近狹小區域均可包含數據。設定核函數為一階多項式,嶺參數選取默認值為50。帶寬值是一個平滑值,它決定了核的寬度,確定了范圍區間內的點對Kernel Density Estimates(KDE)的貢獻,當前對于帶寬的選擇還沒有直接的方法[26—27]。帶寬的選取根據研究目的、樣本大小及研究物種的空間使用格局來決定[27]。對于含障礙核插值方法的帶寬值可以通過目視檢查方式確定[28]。本研究帶寬值的選擇通過連續運行測試選取估計值,并結合對現有種群已有的研究確定選取帶寬值。
KDE值代表在網格內每平方公里可能出現的目擊次數。研究區域內棲息地使用范圍定義為動物群體有95%的概率被找到所形成的最小區域[26],是KDE通過計算閾值,即所有觀測總數的95%得出[25]。海豚分布(即棲息地使用)與核心棲息地分別用95%KDE和50%KDE來表示,它們與研究區域內海豚的目擊位置有關。
為比較同一調查階段海豚到海岸線距離的差異性,分別提取了各階段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和人工海岸線的最短距離,并分別進行配對T檢驗。同時,對各個調查階段的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及人工海岸線的距離分別做方差分析,檢驗其差異性。為比較不同時間序列研究區域內自然保護區的作用,比較50%KDE與保護區的重疊區域,將3個階段的50%KDE分別與保護區范圍比較以獲取重疊比例,分析自然保護區的保護作用。
2 結果
2.1 調查努力量與海豚目擊
3個階段調查總努力量為14408.5km,其中1997—2000年調查努力量為5373.9km,2005—2006年調查努力量為4961km,2015—2016年調查努力量為4073.6km。3個階段截線調查優良海況(海況3級或以下,能見度較好)分別為84.5%、71%和77%。3個階段目擊海豚群體數分別為162群次、184群次和176群次,為消除惡劣海況對觀測數據的影響,分析中所選的數據均為優良海況下海豚目擊的數據。
2.2 伶仃洋水域范圍變化和海豚目擊位置變化
圍填海及沿岸工程建設使原有的自然岸線發生改變,致使水域變為陸地。衛星影像(圖2)數據呈現了過去43年海岸線和陸地特征的變化(圖3)。自1973年至2015年,因圍填海、沿岸改造和港口建設等,伶仃洋水域流失的海域面積為344.08km2。海域流失面積較大的時期主要發生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海域流失年平均面積為20.96km2,至1997年后,海域流失面積增速趨緩(圖4)。

圖2 1973—2015年珠江伶仃洋Landsat圖像

圖3 珠江口伶仃洋水域被永久占用區域

圖4 1973—2015年海域占用面積
海豚目擊位置可以間接的反映其對棲息地的偏好,食物資源豐度、海洋工程及其它人為活動等會臨時或永久性影響其棲息地偏好。根據各個調查階段海豚的目擊位置,分別算出海豚到最近的自然海岸線及人工海岸線的距離(圖5)。對不同調查階段海豚到最近自然海岸線的距離進行方差分析:1997—2000年海豚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的距離均值為5.07km(SD=3.19km),2005—2006年均值為4.97km(SD=4.12km),方差分析顯示差異不顯著(F=0.09,P>0.05);2015—2016年均值為4.18km(SD=3.02km),1997—2000年與2015—2016年比較差異顯著(F=8.52,P<0.05),2005—2006與2015—2016年差異顯著(F=4.22,P<0.05)。對不同調查階段海豚到最近人工海岸線的距離進行方差分析:1997—2000年海豚目擊位置到人工海岸線的距離均值為7.79km(SD=3.23km),2005—2006年均值為6.4km(SD=3.33km),方差分析顯示差異極顯著(F=19.52,P<0.001);2015—2016年均值為5.53km(SD=2.97km),1997—2000年與2015—2016年比較差異極顯著(F=53.9,P<0.001),2005—2006與2015—2016年差異顯著(F=6.56,P<0.05)。另外,對同一調查階段海豚到最近自然海岸線和人工海岸線的距離進行配對T檢驗,3個調查階段的檢驗結果均為極顯著,結果分別為1997—2000年(t=1.97,P<0.001), 2005—2006年(t=1.97,P<0.001),2015—2016年(t=1.97,P<0.001),而且每個調查階段海豚到自然岸線的距離均小于到人工岸線的距離。

圖5 1997—2016年海豚目擊位置離自然岸線和人工岸線的距離
2.3 海豚分布范圍和核心棲息地的變化
95%KDE代表海豚分布(即棲息地使用)的范圍,50%KDE則代表海豚核心棲息地,不同調查階段海豚分布范圍和核心棲息地的面積見表2。不同調查階段95%KDE對比結果顯示,2005—2006年的95%KDE面積最大,2015—2016年95%KDE面積最小。此外,50%KDE代表的核心棲息地占對應調查階段95%KDE的面積比例變化范圍為29.43%—33.97%。

表2 各調查階段棲息地面積
海豚棲息地使用在南北方向的分布范圍變化不大,95%KDE最北端分布到深圳大鏟島附近,南端到東澳島,然而95%KDE在東西方向上,位于伶仃洋中南部寬度呈現先收窄再變寬(圖6)。50%KDE空間分布格局變化較大,1997—2000年有2塊核心棲息地,分別位于內伶仃島西北部和伶仃洋的中南部,重心在伶仃洋中南部水域。2005—2006年共有3塊核心棲息地,分別位于內伶仃島周圍水域、伶仃洋中南部到三角島水域和橫琴島東南水域,重心集中在伶仃洋中南部到三角島水域。2015—2016年共有3塊核心棲息地,分別為內伶仃島至伶仃洋中部保護區核心區水域、大嶼山西南水域和三角島周圍水域,整體呈狹長分布,伶仃洋中南部的部分核心棲息地消失。

圖6 不同調查階段海豚分布和核心棲息地范圍
2.4 保護區內的核心棲息地變化
50%KDE即核心棲息地是海豚棲息地中最重要的水域,位于保護區范圍內的核心棲息地占全部核心棲息地的比例可以反映出保護區對海豚的保護作用。各階段海豚核心棲息地位于保護區范圍內的比例分別為:1997—2000年占比79.94%;2005—2006年占比63.87%;2015—2016年占比49.39%,占比呈下降趨勢,不同調查階段位于保護區范圍內的核心棲息地面積及比例見表3。從核心棲息地的分布格局來看,1997—2000年保護區水域范圍的核心棲息地主要集中于保護區東部和南部水域,2005—2006年主要集中于東部和中部水域,2015—2016年主要在中北部和東南部水域,而且保護區內核心棲息地碎片化,分開為兩部分(圖6)。

表3 各調查階段保護區范圍內核心棲息地面積及比例
3 討論
鯨豚類動物的季節性分布變化通常與食物季節變化及環境特征相關[29—30],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的區域性分布亦呈現出明顯的季節變化[3—4, 31]。珠江口魚類群落格局及其季節差異與環境變化密切相關,春秋兩季魚類群落均隨鹽度梯度而變化明顯[32]。本研究選用了周年海豚調查數據可以減少海豚因季節性區域移動所產生的棲息地使用偏差。珠江口伶仃洋不同調查時期的分析結果顯示,相對于人工海岸線,中華白海豚的分布更偏向自然海岸線,而海豚分布離自然岸線和人工岸線的平均距離均在減小。1997—2016年,白海豚在伶仃洋的分布范圍在2005—2006年有所增加后2015—2016年明顯縮小,核心棲息地在不同時期出現明顯的范圍和空間格局變化,而且2015—2016年面積縮小明顯。主要核心棲息地萎縮成條帶狀,分布于伶仃洋主航道和無人海島附近水域,并在伶仃洋南部的三角島周圍水域形成一個分離的核心棲息地。同時,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范圍內的核心棲息地呈減少趨勢,核心棲息地在保護區內的占比已從1997—2000年的79.9%減少至2015—2016年的49.4%。
3.1 海岸線變遷對中華白海豚分布的影響
珠江口伶仃洋每個調查階段中華白海豚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的平均距離均小于到人工海岸線的平均距離,而不同調查階段比較,海豚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和人工海岸線的平均距離都在逐步減小。自然海岸線附近水域的自然生態較為完好,而且受到的人為活動直接干擾較小,因此海豚更偏好在自然岸線附近水域活動。Wang等[20]發現伴隨海岸線改變,不同年代廈門水域的中華白海豚分布呈現明顯的由近岸向離岸方向移動并遠離人工岸線,這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略有不同。從兩個種群所處的地形環境特征來看,廈門種群以廈門島為中心近似于東西向沿岸分布,外面為開闊海域,而伶仃洋為一個半封閉的河口灣,河口東西兩側陸地限制了海豚向東西方向擴展,而灣內分布有多個無人海島,海豚的目擊分布主要往海上工程施工等干擾較少的北部內伶仃島、東部大嶼山以及南部的青洲、三角島等一帶水域靠攏。
1997—2000年與2005—2006年的海豚目擊位置到自然海岸線的距離均值方差檢驗差異不顯著(F=0.09,P>0.05),但2015—2016年調查海豚目擊位置至自然岸線的距離均值跟前兩個調查階段比較均減小了且差異顯著(F=8.52,P<0.05;F=4.22,P<0.05)。說明在2006年以前伶仃洋白海豚受到的海上人為活動干擾變化不明顯,2015—2016年受到的海上干擾明顯變大,而這個時期正是港珠澳大橋工程施工期,可能是海上施工干擾迫使海豚逼近岸邊活動。而自1997年以來的3個不同調查階段,海豚目擊位置到人工岸線的平均距離均在減小,方差分析檢驗出顯著差異,表明過去20年里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選擇偏好發生了一些變化,被迫逐漸適應人類活動的干擾。
3.2 中華白海豚棲息地使用范圍和核心棲息地的變化
整個監測期間,伶仃洋白海豚棲息使用(95%KDE)和核心棲息地(50%KDE)在范圍和空間分布上呈現很大的變化,面積先增大后減小,其中2015—2016年95%KDE和50%KDE的面積均比1997—2000年和2005—2006年明顯萎縮。海豚在南北方向分布范圍變化不大,可能是海豚的餌料資源年度間南北方向分布范圍變化不大,海豚季節性的在這些區域分布的結果。而伶仃洋中南部海豚東西方向分布呈現先收窄再變寬,可能是仃洋東西部沿岸圍填海及人類活動影響所致,即先受影響遠離西部岸線,海上的活動空間受到擠壓后被迫適應該岸線附近的人類活動。從核心棲息地的分布格局來看,白海豚的分布重心偏向伶仃洋東部水域,其中原因:一方面伶仃洋西部為珠海、澳門等市區沿岸,多數岸線已開發人類活動頻密,而東部多為自然海岸線,人類活動相對少一些;另一方面由于地球自轉引起的海水流向影響,東部水域主要受外海水支配,水較深且比較清澈,而西部水域主要受河流沖淡水影響,水體渾濁且淤積相對較淺。3個調查階段白海豚的核心棲息地遷移變化明顯:1997—2000年核心棲息地主要位于內伶仃島西北和保護區范圍;2005—2006年則分為三部分,分別位于內伶仃島周圍、保護區至三角島附近水域以及橫琴島東南水域,其中三角島附近水域和橫琴島東南水域是新出現的核心棲息地;2015—2016年也分為3個部分,分別位于內伶仃島西北至保護區核心區、大嶼山西南至桂山島東北之間水域和三角島周圍水域。
珠江口伶仃洋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的空間分布呈現向主航道和無人海島附近水域收縮的格局,核心棲息地發生遷移可能是海豚食物——魚類資源的密度分布格局發生改變所致[33—34]。1997—2000年和2005—2006年兩個階段的核心棲息地面積變化不是很大,除了2005—2006年在三角島附近和橫琴島東南水域出現新的核心棲息地外,這兩個階段的核心棲息地大部分重疊。2015—2016年核心棲息地面積與前兩個階段比較,減小的比例分別為20.81%和26.03%,并形成了以主航道和無人海島附近水域為主要核心棲息地的分布格局。
關于湛江中華白海豚對覓食機會與覓食面臨的風險權衡研究顯示,白海豚為了較高的食物回報而選擇接受更大的死亡風險(在海上船舶繁忙且食物資源相對豐富的航道周圍目擊海豚較多);當棲息地間食物回報相似時,海豚會選擇低風險棲息地[35]。此外,長江江豚也被記錄到在碼頭附近頻繁覓食,碼頭地區食物資源較其它區域豐富但來往船只頻繁,江豚選擇在碼頭區覓食可能是迫不得已的選擇[36]。伶仃洋大部分水深在6—8m,而主航道因為開挖或自然形成水深在17m以上,相當于一條深水溝槽連通外海,可能是底層魚類由外海洄游進入河口內灣的主要通道,因此主航道附近水域的魚類資源可能較為豐富。另外,伶仃洋的漁業捕撈壓力一直存在,隨著漁船馬力和捕撈方式的升級,漁業資源逐年減少,而主航道附近來往船只頻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漁業捕撈作業,航道附近水域的漁業資源密度會相對高一些。以上原因可能導致白海豚核心棲息地收縮在主航道附近水域,即海豚已無太多選擇只得經常冒險在主航道附近水域覓食。而海島附近因海底地形以及水文等因素,底棲生物資源一般較為豐富,礁棲性魚類較多,自然成為白海豚的另一核心棲息地。

圖7 2011—2015年目擊記錄珠江口海域(統計數據不含中國香港水域)中華白海豚50%和95%核密度估計棲息地使用格局(Or C,2017)
此外需要指出,根據Or等2011—2015年的調查[22],KDE分析結果顯示整個伶仃洋(不含香港水域)主要有5塊核心棲息地(50%KDE),分別位于香港大嶼山西南部、內伶仃島西部、三角島周圍、淇澳島東部和澳門東南部等水域,核心棲息地大多分布在保護區范圍以外(圖7),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差異較大。本研究2015—2016年的分析結果顯示伶仃洋內有3塊核心棲息地(50%KDE),分別是內伶仃島西部及南部水域、三角島周圍水域和桂山島東北至大嶼山西南水域,除了澳門東南部水域以外,大部分區域核心棲息地均覆蓋Or等提出的區域,而保護區范圍內的核心棲息地面積約占了整個伶仃洋核心棲息地的近50%。再者,Or等的95%KDE分析結果顯示伶仃洋中西部水域無白海豚分布,與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差異也較大。兩個研究的50%KDE和95%KDE分布情況差異較大的原因可能是采用不同的調查采樣方法所致,Or等的調查是以尋找海豚拍照進行個體識別為主要目的,而未系統地設置調查路線[22],每次調查的路線不固定,根據經驗海豚發現概率較高的地方可能會給予較多的關注,這會導致整個研究區域的調查努力量空間分配不均勻,而后期的KDE密度計算方法無法消除這個影響。本研究采用的是船基截線抽樣法,調查前設計了系統的樣線,每次觀測沿著預設的樣線在整個調查區域平均搜尋海豚,因而整個研究區域的調查努力量基本上是均勻的。因此,本研究因調查努力量空間分配不均勻而引起的潛在偏差要比Or等的小,結果應更加接近海豚的實際棲息地使用分布情況,這與Huang等強調在棲息地保護研究中應采用系統方式調查以避免空間采樣偏差的主張是一致的[37]。
3.3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的變動
廣東省人民政府于1999年10月批準建立珠江口中華白海豚省級自然保護區,國務院于2003年6月正式批準珠江口中華白海豚省級自然保護區升格為國家級。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覆蓋的棲息地情況,尤其是核心棲息地覆蓋范圍間接反映了保護區的保護作用。3個不同調查階段的核心棲息地范圍與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重疊分析顯示,位于保護區的核心棲息地分布格局及面積均發生了變化。1997—2000年保護區內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面積占對應階段伶仃洋核心棲息地的比例為79.9%,保護區核心區和緩沖區基本上為核心棲息地。2005—2006年保護區內海豚核心棲息地占比下降為63.9%,保護區核心區和緩沖區內的核心棲息地面積也有所減少,但保護區內的核心棲息地是連貫的。到了2015—2016年,保護區內海豚核心棲息地的占比進一步下降至49.4%,保護區內的核心棲息地分布呈現碎片化。
保護區范圍內中華白海豚核心棲息地總體呈下降趨勢,可能是伶仃洋人為活動(海上工程施工和漁業捕撈等)干擾增大,海豚覓食和活動空間受到壓力的結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于2003年批準建立,當時規劃是依據1997—2000年的調查結果,劃定的保護區范圍比較合理(保護區內核心棲息地約占了80%),但是隨著伶仃洋人類活動增加,中華白海豚的分布格局發生了一些改變,核心棲息地也發生了變化,因此有必要對目前的保護區范圍和功能區作出一些優化調整,以適應當前的棲息地變化格局。但是,目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周圍的伶仃洋水域大多已開發,可以調整的空間非常有限。保護區南部的青洲、三角島一帶水域雖然是白海豚的核心棲息地,但已建成海上風電場,不再適合劃為保護區。北部的內伶仃島周圍水域在廣東省海域功能區劃中屬于生態保留區,也是海豚的核心棲息地,比較適合調整為白海豚保護區。此外,今后有必要統籌考慮整個珠江口及其周邊海域的生態保護規劃,建立國家公園,以更好地保護珠江口中華白海豚種群及河口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