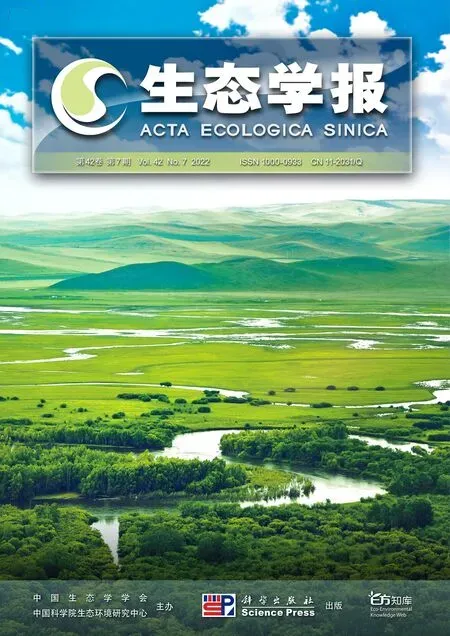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文獻綜述
陳曉宇,姚 蒙,李 晟,*
1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學生態研究中心,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 北京 100871
隨著人類土地利用等活動對環境的加速改造,全球自然棲息地破碎化日益嚴重,導致生物多樣性急劇喪失[1—2]。環境變化與棲息地破碎化直接威脅野生生物個體生存與種群延續,種群的持續縮減繼而導致種內遺傳多樣性下降,而遺傳多樣性的下降又進一步促使種群遺傳衰退和存活力下降,導致種群進一步縮減乃至物種瀕危[3]。因此,為了保護物種及其遺傳多樣性,一方面需要了解決定生物多樣性維持與喪失的微觀機制,另一方面需要關注棲息地景觀格局的形成與改變將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4—5]。為回答與探究這些問題,景觀遺傳學(Landscape Genetics)應運而生,它將影響生物多樣性格局和種群生存的宏觀(景觀尺度)與微觀(基因水平)機制有機地聯系起來,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與應對全球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效應。景觀遺傳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它結合了種群遺傳學與景觀生態學的原理與方法,旨在揭示景觀特征與微進化過程(如基因流、遺傳漂變和自然選擇)之間的相互作用[6—8]。Stéphanie Manel于2003年首次提出了景觀遺傳學的概念,標志著景觀遺傳學學科的正式誕生[6]。隨后,景觀遺傳學快速發展。美國景觀生態學會在2005年舉辦了首次以景觀遺傳學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7—8]。LandscapeEcology與MolecularEcology雜志分別在2006年與2010年發表了以景觀遺傳學為主題的專刊。第一本以景觀遺傳學命名的專著《LandscapeGenetics:Concepts,Methods,Applications》于2015由Niko Balkenhol等人撰寫出版[9]。
許多山地生態系統是全球或區域尺度的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如中國西南山地、東喜馬拉雅山地、中亞山地、東部赤道非洲山地、赤道安第斯山等[10]。山地因為其自身的海拔高差大,溫差明顯,形成了山地垂直自然帶,即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形成了不同的氣候、土壤環境,使得適應不同環境的生物能夠共同棲息于同一連續的生態系統中[11—12]。山地生態系統的獨特性及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為生態學研究的重點生態系統類型之一。同時,山地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非常敏感,氣候變化、土地利用的改變、旅游業的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棲息地破碎化都能對山地生態系統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13—15]。因此,我們需要了解物種在時空尺度上如何適應山地景觀特征,以及各種環境變化因素如何影響山地物種的遺傳多樣性分布模式。山地景觀遺傳學(Mountain Landscape Genetics)正是在景觀遺傳學的學科發展中,針對山地生態系統和物種遺傳格局的獨特性和重要性發展形成的新興分支。
山地景觀遺傳學通過綜合景觀生態學、空間統計學、地理學和種群遺傳學等數據和分析方法來了解山地景觀中物種遺傳多樣性的空間分布,了解山地景觀的形成過程對種群遺傳空間格局的影響,了解山地景觀特征對種群基因交流和遺傳分化的影響。為了全面了解目前山地景觀遺傳學的發展狀況與重點研究問題,為山地生態系統及其生物多樣性保護管理提供科學參考,本研究基于系統的文獻檢索與綜述,回顧了山地景觀遺傳學的發展歷程,探討了目前該領域主要的研究方向與關鍵問題,總結了常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并對該領域內目前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發展趨勢進行了討論與展望。
1 發展情況
1.1 論文發表數量統計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Core Collection),分別以landscape ecology和 population genetics、landscape genetics和mountain為主題詞,對1900—2020年間學術期刊發表的英文研究論文與綜述的標題、摘要、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到的結果逐一審核,去除與該領域無關的文獻,共獲得479篇景觀遺傳學文獻,其中192篇為山地景觀遺傳學相關文獻。山地景觀遺傳學文獻與其他景觀遺傳學文獻的發表數量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圖1)。第一篇山地景觀遺傳學方向的文章發表于1999年,研究了美國西南部“山地島嶼(mountain islands)”松科黃松類喬木的分類與遺傳結構[16]。其后,2008—2013年該領域論文發表數量增長最為迅速,2013—2016年發文數量經歷短暫的下降,2016年至今該領域研究又逐漸回升(圖1)。

圖1 山地景觀遺傳學英文文獻發表趨勢
此外,基于中國知網,以“山”和“種群遺傳”或“群體遺傳”為主題詞,對1900—2020年間學術期刊發表的中文研究論文與綜述的標題、摘要、關鍵詞進行檢索。對檢索到的結果逐一審核,去除與該領域無關的文獻,共獲得31篇山地景觀遺傳學相關的中文文獻。由于基于知網搜索的文獻均為在中國進行的研究,為避免造成統計偏差不加入后續的文獻統計分析,僅對中國所進行的相關研究的關鍵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詳見本文第2部分。
1.2 研究國家與地區
山地景觀遺傳學是世界各地研究者廣泛關注的研究方向,截至2020年底,來自46個國家的研究機構參與發表過山地景觀遺傳學相關英文論文。就國家而言,美國是發表山地景觀遺傳學文章數量最多的國家(占所有發表文獻數量的48.4%),其次是德國(12.5%)、加拿大(12.0%)和中國(10.9%),中國也是發表山地景觀遺傳學文章數量最多的亞洲國家(圖2)。從研究地點來看,研究最多的是歐洲(38.4%)與北美洲(31.5%)的山地生態系統。落基山脈(Rocky Mountains, 27篇)、阿爾卑斯山脈(Alps, 19篇)、內華達山脈(Sierra Nevada, 11篇)、喜馬拉雅-橫斷山脈(Himalaya-Hengduan Mountians, 6篇)、比利牛斯山脈(Pyrenees, 5篇)、阿巴拉契亞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 5篇)是研究熱點山地(圖3)。

圖2 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者單位從屬國家與大洲

圖3 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熱點山地
1.3 文獻網絡
利用HistCite軟件[17]對系統文獻檢索獲得的192篇山地景觀遺傳學英文研究論文進行分析。分別基于GCS(Global Citation Score, 即該文獻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的總被引次數)與LCS(Local Citation Score,即該文獻在所有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中的被引次數)進行了文獻網絡圖繪制(圖4和圖5)[17]。基于GCS與LCS做出的網絡圖,除節點大小具有差別外,網絡關系相似,說明該領域研究與其他領域交叉較少,原因可能在于山地景觀遺傳學本就是交叉研究的產物。該領域引用次數最高的是2005年的一篇關于哥倫比亞斑蛙(Ranaluteiventris)的研究,截至2020年底已被引用超過250次。該研究的結果顯示,哥倫比亞斑蛙的基因流動受山脊和海拔的限制,低海拔地區基因流動水平高,種群內的遺傳變異與海拔高度呈顯著負相關[18]。

圖4 基于LCS繪制的山地景觀遺傳學文獻網絡圖(N=192)

圖5 基于GCS繪制的山地景觀遺傳學文獻網絡圖(N=192)
1.4 研究類群
植物是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最早關注的生物類群[16]。在所有研究類群中,脊椎動物是研究發表最多的類群,占發表文獻總數的62.0%;脊椎動物中,又以對哺乳類(占脊椎動物發表文獻總數的52.9%)與兩棲類(23.5%)的研究最多(圖6)。較早的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集中于脊椎動物與植物,這可能主要與其相對容易觀察、樣品易于獲得等特點有關。近年來山地景觀遺傳學的研究類群更為廣泛,重要原因之一是DNA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使研究者能夠以較高的成本效益獲得大量的遺傳數據[19—21]。

圖6 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類群
2 山地景觀遺傳學的關鍵研究問題
景觀遺傳學重點關注的問題主要包括:識別基因流的路徑與障礙;量化景觀特征對種群遺傳結構時空變化的影響;識別種群源匯動態和遷移廊道;理解景觀屬性影響生態過程的時空尺度;以及檢驗關于特定物種的生態學假說等[22]。山地景觀遺傳學是在山地景觀尺度上進行的遺傳學研究,通過對Web of science檢索出的192篇山地景觀遺傳學論文的研究內容進行逐一分類統計發現,最受關注的是識別山地景觀中的基因流路徑或阻礙(占所有研究論文數量的82.8%),以及量化評估山地景觀特征如何影響種群遺傳結構的時空變化(67.2%)。
山地景觀中垂直高程差、地形復雜性等景觀特征都可能對種群擴散或基因流動造成影響[18,23—30]。海拔成為限制基因流動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種群在低海拔和高海拔之間的擴散受到限制,二是在低海拔種群和高海拔種群之間存在交配前隔離[18,23]。低海拔種群與高海拔種群如果在擴散能力上存在較大差異,則可能導致高、低海拔種群之間出現交配前隔離,進而限制了基因在低海拔和高海拔區域之間的交流[18,23]。海拔作為一個重要的生態限制因子,除去它對生物的直接影響外,也與它對環境條件中其他因素的影響密切相關,比如溫度、生長季節、森林覆蓋等[18,24—25]。由于海拔高差導致的氣候差異可能是限制基因在景觀中流動的關鍵因素[24]。山地景觀中山脊的存在是另一影響種群遺傳結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可能阻礙種群間的基因流動,另一方面山脊的存在也可能促進異域物種形成[26—28]。對于有潛力進行長距離遷徙的物種而言,由于山脊的存在使其擴散速率很低,阻礙了種群間基因流動,從而導致山地兩棲動物種群分化程度較高[18]。對于種群數量較大的物種而言,山脊的存在可能促進異域物種形成[27—28]。要了解基因流動究竟受到哪些山地景觀特征的限制,需要獲取實地山地景觀特征的量化信息,同時獲取不同山地景觀下的種群遺傳數據,才能驗證真正阻礙或限制種群擴散與基因流動的原因。此外,需要了解種群的主要基因庫是低海拔種群還是高海拔種群。如果低海拔種群為一物種主要的基因庫,則該物種可能存在更大的瀕危風險,因為低海拔種群往往最先受到棲息地喪失、破碎化以及外來物種入侵的影響[19,29—31]。
此外,對中國山地景觀遺傳學的31篇研究論文進行分析發現,其中“識別山地景觀中的基因流路徑或阻礙”(占所有研究論文數量的58.1%)與“量化評估山地景觀特征如何影響種群遺傳結構的時空變化”(45.2%)為中國山地景觀遺傳研究最為關注的問題。
近十年來,中國山地景觀遺傳學快速發展,截至2020年基于在中國進行的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已發表論文53篇(Web of science,22;知網,31)。研究類群主要關注植物(占發文總數的62.3%)和脊椎動物(35.8%)。對脊椎動物的研究中以兩棲動物為最多,占所有脊椎動物發文數量的52.6%。相較于世界范圍內其他區域的山地景觀遺傳研究而言,中國相關研究在無脊椎動物與真菌等類群的研究上較少或存在空缺。中國的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地點主要集中于喜馬拉雅-橫斷山脈與秦嶺,其中喜馬拉雅-橫斷山脈的研究主要關注植物。喜馬拉雅-橫斷山脈的相關研究中藏川楊(Populusszechuanicavar)的研究最多,研究發現對于青藏高原塞吉拉山的藏川楊而言,海拔對于該物種的基因流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限制因子,但并未造成高低海拔種群間的地理隔離,高低海拔種群均處于較高的遺傳多樣性水平,而且結合景觀基因組分析發現了4個與海拔變化相關的基因[32—33]。 此外,還對喜馬拉雅-橫斷山脈的山生柳(Salixoritrepha)、金露梅(Potentillafruticosa)與喜馬拉雅鐵杉(Tsugadumosa)等展開了研究[34—36]。在秦嶺則主要開展了針對大熊貓(Ailuropodamelanoleuca)與兩棲類的研究[37—38]。研究物種中有2種受威脅程度較高,分別是大熊貓與寧陜齒突蟾(Scutigerningshanensis)[37—38]。針對秦嶺地區大熊貓種群的研究發現,該種群的基因流強度主要與坡向和地形復雜度這兩個因素有關,東向坡向促進基因流動,地形復雜的景觀限制基因流動;基于研究結果,研究人員提出了能夠促進棲息地斑塊間大熊貓基因流的最佳廊道[37]。對寧陜齒突蟾的研究發現地形復雜度及秦嶺山脈的阻隔是誘使該種群遺傳結構形成的重要原因,并根據局域種群的遺傳結構將該物種劃分為3個管理單元,為該物種的保護與管理提供了科學信息[38]。
3 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方法
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融合了景觀生態學與種群遺傳學的研究方法,通過獲取山地生態系統中生物種群的遺傳信息,量化山地景觀中的特征變量,同時結合空間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山地遺傳格局形成的原因[6,39—40]。
3.1 遺傳標記
種群遺傳學常用的標記包括等位酶(Allozyme)、限制片段長度多態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 RFLP)、擴增片段長度多態性(Amplified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 AFLP)、隨機擴增多態性DNA標記(Random Amplified Polymorphic DNA, RAPD)、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微衛星位點(Simple Sequence Repeats, SSR)和線粒體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葉綠體DNA(Chloroplast DNA,cpDNA)等[41—44]。在山地景觀遺傳學的早期研究中,特別是在植物研究中,研究者常選擇形態學或生化標記如等位酶[16,41]。等位酶是最早用于種群遺傳研究的遺傳標記之一,其表達呈共顯性,易于進行簡便的親本分析,但不能反映非編碼蛋白的基因差異[45]。RFLP、AFLP等基于位點或片段差異計算不同樣本DNA之間的遺傳距離,但也存在工作量大、依賴放射性標記等缺點[46—47]。迄今在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遺傳標記是SSR,有63.5%的研究均使用了SSR。SSR分子標記具多態性高、數量豐富、突變率高、分辨率高、共顯性遺傳、操作簡單、開發成本較低、檢測技術高效等諸多優點[48—49];且隨著測序技術的普及和成本降低,SSR分子標記技術的使用日益經濟簡便[50—51]。近年來,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與生物信息學的發展,相關研究中SNP的使用頻率逐漸上升,占所有研究10.4%。SNP標記相較于其他標記具有性價比高、可大規模自動化檢測、在基因組中廣泛分布、穩定性好等特點[52—54]。
3.2 空間遺傳格局分析
在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中,常用遺傳多樣性指數來量化評估種群的遺傳多樣程度。常用的遺傳多樣性指數包括等位基因頻率(Allele Frequency)、等位基因數(Na)、有效等位基因數(Ne)、觀察雜合度(Observed Heterozygosity, Ho)、期望雜合度(Expected Heterozygosity, He)等[55—56]。種群間的遺傳差異程度常用遺傳分化系數如Fst或Rst衡量,并可通過個體網絡圖、主坐標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PCoA)等方法進行可視化[57—59]。對山地景觀中不同地理種群進行遺傳分化程度劃分,可使用分子變異方差分析(Analysis of Molecular Variance, AMOVA)、貝葉斯分配檢驗(Bayesian assignment test, 如STRUCTURE、Geneland分析)等[60—61]。探究遺傳格局與山地景觀空間屬性的相關性常用Mantel檢驗(Mantel′s test)、回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距離隔離檢驗(Isolation By Distance, IBD)等[62—63]。
4 討論與展望
4.1 研究挑戰
與其他類型的地理環境相比,山地景觀具有高度的異質性,隨之形成的種群遺傳結構及過程也十分復雜,對研究者提出了諸多挑戰。首先,許多經典的種群遺傳模型和空間格局分析方法不考慮景觀異質性,且存在一些嚴格的前提假設。如果將這些常規模型和統計分析方法直接應用于山地種群遺傳的分析,可能導致遺傳格局和空間的錯誤匹配,難以合理解釋實際的生態現象。其次,物種種群遺傳結構的形成是長期歷史氣候和環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山地景觀在短時間內發生較大的改變,其對種群遺傳結構的影響將存在時間滯后性,因此,在相關研究中需要同時考慮物種的世代周期與景觀變化時間尺度的關系[64]。此外,由于不同的遺傳標記進化速率不同,可能反映不同的時空尺度種群遺傳格局的變化,因此需要對遺傳標記的突變速率進行分析,慎重選擇遺傳標記。不同的景觀遺傳學研究中如果選用不同的遺傳標記,則不同研究的結果之間可能缺乏可比性。另外,不同生物類群具有不同的擴散方式和繁殖模式,需要選擇適用于目標類群行為特征的空間統計方法。
4.2 研究應用
山地生物種群的結構與遺傳變異模式是長期景觀格局與歷史氣候的結果,但是近年來,氣候變化和人為活動(如土地利用改變、大規模森林砍伐、過度放牧等)使自然棲息地迅速退化和破碎化,山地物種的棲息地面積縮小、破碎化或喪失,導致很多山地生物種群迅速縮減、遺傳多樣性下降[65—70]。對于長距離擴散能力弱、有特殊棲息地偏好的物種而言,棲息地的破碎與喪失往往對物種或種群往往會造成嚴重影響[68—69]。棲息地破碎化將直接導致景觀連通性變弱,物種擴散阻力增加,難以充分進行基因交流,使得小種群遺傳多樣性下降[71—72]。棲息地破碎化還直接影響到山地物種依賴的食物資源、小氣候條件等[71—72]。因此,山地瀕危物種保護策略不僅要考慮其棲息地形的復雜性,同時需要了解棲息地隔離狀況,確定瀕危物種受脅關鍵景觀原因,從而保護和恢復遷移通道以促進棲息地斑塊間的基因流動,保障小種群存活力[62,73]。
山地景觀遺傳學的研究對于山地生態系統具有重要應用價值。山地景觀遺傳學研究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山地景觀中基因流動與種群擴散模式的形成與阻礙,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發展導致山地景觀改變將如何影響遺傳多樣性、種群生存力、物種多樣性、群落結構甚至疾病傳播[74]。基因組學方法和分析手段的快速發展,使我們可以更精確地量化評估山地物種中基因頻率、基因流隨著時空變化而發生的改變。可以通過整合景觀遺傳數據與氣候數據進行建模,預測物種可適應各種景觀屬性的邊界,闡明物種可能以何種方式適應環境與景觀的變化,評估物種適應性、遷地保護或滅絕的概率與風險。
4.3 未來展望
景觀遺傳學是21世紀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新興交叉學科,山地景觀遺傳學是其中的重要分支,相關研究對于山地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目前我國的相關研究,在研究區域、研究類群和研究方向上均存在部分空白(圖6),在諸多亟需科學信息的山地物種的研究上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需要大力培養相關人才推動領域發展。山地景觀遺傳學作為交叉學科的衍生分支,對研究人員的知識背景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校相關專業的課程設置上,除傳統的生態學和種群遺傳學課程外,應增設景觀遺傳學等課程,并配套相關實驗或實踐課程,奠定未來科研人員的知識基礎。目前,山地景觀遺傳學與其他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深度交叉仍存在很大潛力(圖4和圖5),未來應考慮與生物信息學、人工智能等多種研究領域的交叉與融合。此外,現代各科學領域研究的發展都離不開大數據的支持,應積極推動建立全球景觀遺傳與山地景觀遺傳學的研究數據庫,以便相關研究人員跟進領域研究最新進展,開展地區間的比較研究,填補現有研究類群與研究區域的空缺。隨著景觀遺傳學方法與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山地景觀對種群遺傳過程的影響,從而制定更科學合理的保護策略,更有效地保護山地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