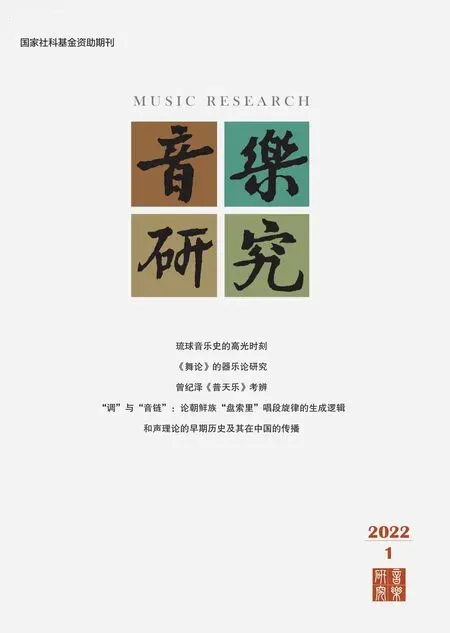對鄭覲文與大同樂會之關系的歷史敘事與闡釋
文◎李 昂
鄭覲文與其創辦的大同樂會,對于中國20 世紀民族器樂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學界對其多有專論。本文圍繞鄭覲文在上海建立大同樂會及其音樂活動展開歷史敘事,旨在探討:哪些因素促成了鄭覲文1919 年在上海建立大同樂會,其音樂活動受到哪些方面的影響,進而思考應該在何種語境下理解和看待鄭覲文及大同樂會的音樂行為。
一、鄭覲文為何在年逾不惑的1912 年才來到上海?
學界對于鄭覲文的研究,均從其1915年來到上海任教于倉圣明智大學開始。但1872 年出生的鄭覲文,在1908 年就曾來過上海,①陳正生《鄭覲文年譜》,《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2015 年第1 期,第65 頁。為何1912 年在他已年過40 的時候又來到上海定居?這一問題可以通過梳理鄭覲文來滬之前的活動來尋求答案。
1889 年,鄭覲文參加江南鄉試,取得“副貢”功名,其間購得明琴一張。返回江陰后,他跟隨著名琴家唐敬詢習古琴。
1902 年,31 歲的鄭覲文進入江陰文廟擔任教授廟堂音樂的助教,因發現新制樂器全不合律,便開始研究律學和樂器制作。1905 年,科舉廢除,興辦學校,在這樣的背景下,鄭覲文于家鄉老宅開辦學堂,并赴上海購置風琴,開設音樂課。1906 年,他又與堂弟鄭立三同赴湖南瀏陽,向已故古樂專家邱之稑的門人求教古樂。1912 年,他加入國民黨,參與地方自治,并來到上海。
鄭覲文從17—31 歲的14 年間,不只學習了古琴,并且對于古籍和民間音樂中與雅樂相關的內容做了大量研究。那么,在31 歲進入江陰文廟擔任古樂助教之前,鄭覲文是如何生存的呢?
清朝末年,以科舉“正途”考取功名的文人即為“紳士”。由于鄭覲文地方士紳的身份,31 歲時他得以進入江陰文廟擔任古樂助教。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大部分時間里,文廟延續著“廟學合一”的功能,既是官方主導下儒家文化的祭祀場所,亦是學校教育的主要機構。②張國鵬《政權與信仰變革下的民國文廟——以上海文廟為考察中心》,南開大學2016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9 頁。這說明彼時鄭覲文在家鄉的社會地位應該不低。
1905 年,清末新政廢除科舉,鄭覲文則將教學古樂調整為教唱歌曲,并曾去上海購買風琴輔助教學。1905 年到辛亥革命期間,科舉制度、文廟相繼廢除,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對于在封建社會“體制內”以制禮樂活動為生的鄭覲文來說,其生活條件必然每況愈下。同時,文化的劇變,又迫使他在江陰迅速調整自己的音樂活動以適應周遭社會環境的變化,但這對他來說并非易事。
當時鄭覲文的堂弟鄭立三已在上海立足,他早年留學日本,與孫中山私交甚篤,且是同盟會會員,曾任江蘇省議員。于是鄭覲文便來到上海投靠鄭立三。鄭立三則為其引薦上海的知名人士史量才、周慶云等。③陳正生《鄭惠國教授早年在上海的音樂活動》,《上海藝術家》2011 年第1 期。同時,鄭覲文憑借自身的專長,于1915 年被上海商界英籍猶太大亨哈同所創辦的倉圣明智大學聘為古樂教師;在這所以傳授中國古典傳統文化為宗旨的教育機構中,他試制仿古樂器、教授女子學生演奏古樂達8 年之久;哈同為其古樂的制作和研究提供了相當程度的支持。鄭覲文曾在《中國音樂史》的序中提到哈同對他有“知遇之恩”。④在鄭覲文離開倉圣明智大學若干年后的1931 年,哈同去世,鄭覲文率大同樂會樂隊“以倉圣大學校友資格”在其中式葬禮上奏樂致哀。參見墨逸《愛儷園速寫》,《申報》1931 年7 月22 日,第17 版。
由此便可明白,鄭覲文為何會在40 歲之后才來到上海定居。
二、為何大同樂會成立四年之后才開始展開活動?
有關大同樂會的成立年代,較多學者認為是1920 年。但值得注意的是,鄭覲文在1928 年7 月22 日的《申報》上有如下敘述:“本會發生在民國七年,初名琴瑟學社,民國八年五月,改名大同樂會,正式成立”⑤鄭覲文《鄭覲文在大同樂會演說制樂》,《申報》1928 年7 月22 日,第2 版。。所以,大同樂會確切的成立時間應是1919 年5 月。而作為國民黨員的鄭覲文,在1919 年5 月將琴瑟學社更名為大同樂會的原因,結合其后鄭覲文多次表述的“研究中西音樂歸于大同”的宗旨,學界普遍認可乃是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但是,于1919 年成立的大同樂會并未立刻開始活動,據早期會員柳堯章回憶,1923 年他最早加入大同樂會之時,會址門前還掛著“大同樂會籌備處”的牌子,直到這一年大同樂會才完成了籌備工作。⑥陳正生《談談大同樂會的成立年代》,《音樂周報》1992 年12 月11 日,第2 版。
一個社團的籌備,固然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1918 年即有結社意愿,1919 年即打出大同樂會招牌的鄭覲文,為何直到四年后的1923 年才正式完成大同樂會的籌備?鄭覲文與《申報》所有者史量才的親密關系至少在1920 年之前就已建立,那么為何直到1923 年大同樂會的活動宗旨才在《申報》的醒目位置昭示于眾?
《申報》上有關大同樂會的最早消息,刊載于1923 年11 月17 日。學界往往只注意到刊載在第17 版闡述大同樂會宗旨、文化理想、組織結構等內容的《大同樂會之新組織》,而未注意到大同樂會在《申報》上的第一則廣告也在同期第9 版以醒目標題刊發。此廣告寥寥數語,將《大同樂會之新組織》所言大同樂會三個部門(設有專門學校的研究部、編譯部、研究制造部)再次簡述一遍,然后提出“如有愿入本會研究或代售樂器、樂書者,請函上海愛多亞路一千零零四號,電話西三千三百六十三號索閱章程或駕臨接洽可也”。如此少的文字內容,為何不放在同樣刊有許多廣告的17 版的《大同樂會之新組織》中,而要在全部刊登廣告的第9 版單獨刊出?這讓人感受到一絲鄭覲文對于社團主旨言說的嚴肅態度,以及商業行為出現的“矛盾”心態。
鄭覲文1915 年起所供職的倉圣明智大學,于1923 年停辦告終。大同樂會會員程午加曾寫道:
大約在1921 年左右……倉圣學校停辦后,學校的教師也只好失業出走,鄭覲文老師也只好離開倉圣學校古樂室……⑦程午加《二十年代民族器樂活動情況的回憶》,《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與表演版)》1984 年第3 期,第93 頁。
所以,對于1923 年之前的鄭覲文來說,哈同為其研究古樂提供的條件已使他別無所求,從未想過將組織社團、研究和表演古樂這樣的事情投入到社會活動和商業化的語境中。然而,據筆者統計,僅1923 年末大同樂會開始媒體宣傳之時到1924 年8月的半年多,《申報》上刊載的大同樂會有關樂器和書籍的售賣、招收學員、演出售票等廣告,就達20 條之多,其中還不包括音樂會評述、新樂器試制成功等“隱藏”鮮明商業宣傳功能的內容。
顯而易見,1923 年倉圣明智大學的停辦,讓鄭覲文意識到自己的生計問題再一次擺在了面前。他不得不通過大同樂會,為自己的生活求得基本的保障并對其進行經營。所以,大同樂會成立四年之后才規模性地展開活動,并顯露出強烈的“商業化”色彩。
三、1923 年后大同樂會音樂活動特點及興盛原因
1933 年是大同樂會活動最為繁盛的一年,基本涵蓋了大同樂會自1923—1935 年鄭覲文去世的所有活動類型。筆者將1933年《申報》刊載的大同樂會音樂活動信息整理為表1,從表中看出如下三個特點。

表1 1933 年《申報》載大同樂會音樂活動
其一,大同樂會的活動場域,是其他上海的絲竹國樂團體難以企及的:多為商界活動、政府文化活動或招待名流等,有著典型的“精英化”“商業化”特點。
其二,其“精英化”活動的場域,是與贊助人的關系緊密相連的。如12 月16日法國領事館為法國議員餞行,由蔡元培主持;多場在世界社的活動,則因世界社的建立者為李石曾。
其三,其演出內容與其他絲竹國樂團體有著顯著區別:既有濃重“復古”傾向的《中和韶樂》等曲目,也有以“崇雅”為取向的大套琵琶和古琴曲;還有根據大套琵琶、古琴曲創編的《國民大樂》《春江花月夜》等“新絲竹”合奏曲,并不見《三六》《行街》《四合》等當時已頗為流行的江南絲竹曲目。
至于大同樂會興盛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個因素所致。
(一)贊助人提供的輿論宣傳與經費支持
1923 年,鄭覲文再次遭遇失業后,不得不將大同樂會推向社會作為謀生的手段。值得慶幸的是,此時史量才、李石曾、繆云臺、王曉籟、周慶云、蔡元培,甚至杜月笙等政商界名流給予他不小的支持。作為上海的傳媒巨頭,史量才的《申報》對大同樂會的宣傳是非常全面的。據筆者統計,從1923—1935 年,《申報》上有關大同樂會的消息就達到11 萬余字,除了大量的廣告之外,還有對于大同樂會音樂活動的評述和對音樂思想的宣傳等。
據大同樂會會員鄭體思所言,同盟會的元老李石曾,作為一位成功的商人和文化界名流,每月給予大同樂會的資助為100元;另王曉籟和杜月笙每月各撥補助30 元。以當時上海的物價水平,這160 元已經相當于五個中產家庭的生活開銷。⑧鄭體思《抗戰前后的兩個“大同樂會”(上)》,《樂器》2012 年第9 期,第73 頁。可以說,以上因素是大同樂會得以順利開展各類活動的重要輿論和物質基礎。
(二)上海獨特的城市地位與業余絲竹國樂活動繁盛的音樂環境
其一,上海作為西方音樂輸入中國的橋頭堡與近代國際化大都市,大量的演出場所,以及政治、商業、文化活動,為坐落其中的大同樂會提供了豐富的藝術活動空間。此外,得益于上海在近代工商業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地位,諸多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重要人物也充當了大同樂會的贊助人;諸多中產階層業余國樂愛好者亦繳納會費加入大同樂會。大同樂會教授昆曲、舞蹈,以及小提琴等西方音樂,以求“有價值之國樂,以與世界音樂相見”,除了高水平的絲竹樂師外,還吸引了戲劇家、舞蹈家歐陽予倩和小提琴家羅曼麗等擔任教員。
其二,上海繁盛的業余絲竹樂社及其活動。據統計,自20 世紀初至30 年代,上海市區、郊區有據可查的絲竹社團就多達200 個。⑨李民雄《絲竹樂述略》,《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上海卷》(上),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 年版,第240 頁。這樣的環境不止為大同樂會提供了大批水準頗高的絲竹教員,如琵琶泰斗汪昱亭、施頌伯、吳夢飛,洞簫及古箏好手王巽之等;還為大同樂會招收學員提供了較為良好的環境,如柳堯章、衛仲樂、秦鵬章、許光毅、許如輝、程午加和金祖禮等,都曾在大同樂會學習琵琶、古琴等樂器,而后成為大同樂會的中堅力量。
正如程午加先生回憶道:“大同樂會就是主要面向各單位的職工、銀行職員、中學教師、學生等,當然大多還是為有錢的資產階級服務。”⑩同注⑦。所以,上海獨特的城市地位與業余絲竹國樂活動繁盛的音樂社會,為大同樂會提供了龐大的受眾群體,也是其音樂活動“精英化”特征得以實現的重要前提。
可以看出,大同樂會在應對社會變革“適應性”轉變下,既進一步獲得了維持運轉的基礎保障,更重要的是,也使文人音樂傳統有機地融入了當時的上海社會生活。
四、對大同樂會與鄭覲文之關系的闡釋
通過前述對于鄭覲文與大同樂會之關系相關三個問題的敘事與分析,可以發現:鄭覲文個人經歷形成的社會地位及其“國樂觀”,上海獨特的城市地位與業余絲竹國樂活動繁盛的音樂社會,都對大同樂會的建立及其音樂活動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辛亥革命之后,相比北洋軍閥激烈爭奪的北京,上海由于租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為舊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成為政、商、文化界進步人士矚目的中心。
在此宏觀歷史語境下,迫于生計問題來到上海的鄭覲文得益于其堂弟的引薦,結識了日后贊助大同樂會的政商界名流;得益于哈同的“知遇之恩”,獲取一份賴以謀生的職業。但是,如果鄭覲文青年時期不曾獲取“副貢”功名,得以在江陰文廟教授古樂,積累了扎實的古樂與國學研究積淀,就很難想象他來到上海可以獲取倉圣明智大學古樂教師這一體面職業;更難想象他在1923 年再一次面臨失業后,能以體面的身份與諸多政商界社會名流交往,獲取資助,并將自身“國樂觀”進行“適應性”轉變,依托上海業余絲竹國樂活動繁盛的音樂社會招攬賢才、“改良絲竹”吸引受眾,使得大同樂會成為上海最有影響力、最為活躍的中國音樂社團。
1935 年鄭覲文去世后,繼任樂務主任的衛仲樂,雖有杰出的音樂素養,但當時仍舊年輕的他,無論教育背景還是社會關系,顯然都無法與鄭覲文相提并論。隨著李石曾等人停止贊助,大同樂會也日漸渙散。衛仲樂操持的中國管弦樂團,延續了大同樂會為絲竹愛好者培訓、售賣樂器的“商業性”色彩。但作為成長于“五四”之后的音樂家,衛仲樂不再堅持鄭覲文時期的“復古”傾向,在與著名音樂學者沈知白的合作下,其音樂活動保留了一定的“崇雅”特征,更帶有鮮明的以西方音樂“改進國樂”的特點。
所以,大同樂會呈現出“精英化”的活動特征,有賴于鄭覲文個人經歷形成的“國樂觀”及其社會地位。因此,離開了鄭覲文領導的大同樂會,就不再是原本的大同樂會了。
由鄭覲文之子鄭玉蓀在重慶另立的大同樂會,雖有王曉籟等政府要員支撐贊助,但就其音樂活動內容來看——主要為在“抗日救亡”背景下,生產“童子軍”所用軍樂器、編排新劇等,顯然,由于失去了上海本地業余絲竹國樂活動繁盛的音樂環境,而失去了受眾及社會基礎,大同樂會上海時期“復古”“崇雅”色彩的絲竹音樂活動不復存在。
結 語
20 世紀初的十幾年間,受過封建科舉教育、擁有功名的上層士紳中,放眼看西方的那一群體,成為主導社會變革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大多擁有較為扎實的傳統文化積淀,而接觸西學又使他們對中國舊有文化如何“求變”與“傳承”有著獨到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們具備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使他們得以高居文化思潮涌動的浪尖,作為社會文化變革的“意見領袖”,為世所矚目。
毫無疑問,鄭覲文也是其中一分子。他的個人經歷雖然造成了他的歷史局限性,但是同時也使他得以在上海成立大同樂會并在音樂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